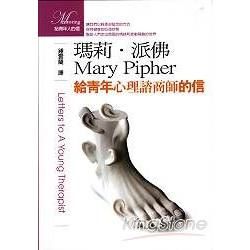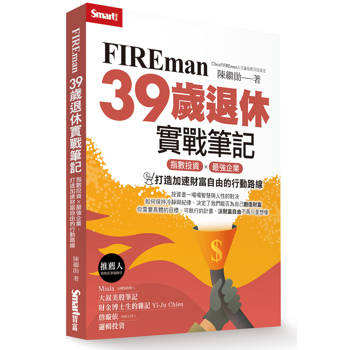我在一九七二年首次為一個來自暴力酗酒家庭、流浪街頭的年輕婦女進行心理治療。夏綠蒂怯生生地帶著抱歉的表情,信步走進大學的免費心理諮商中心,之後的一個星期療程中,我倆努力地為她孤寂、亂糟糟的人生理出一些頭緒。每當低聲傾訴自己被強暴和毆打的遭遇時,她總垂下頭任油膩膩的瀏海蓋住雙眸,她是那麼害怕別人溫柔的對待,連我對她一些微足不道的小事發出讚美,她都顯得有點退縮。經過半年的心理治療,夏綠蒂把前額瀏海撥到一旁露出眼睛正視我的臉,第一年近尾聲時,她已經會對我咧嘴笑,有時甚至試探性的笑出聲來。在三年的相處中,我相信我對她沒有什麼害處,我們相互喜歡且彼此尊敬,我從她身上學到的東西絕對多過她從我身上學到的。
從那時開始,我陸續看過形形式式的人──過動學童、受凌虐的婦女、天賦異秉的學生、同性戀父親、哀痛逾恆的寡婦、暴躁易怒的青少年、做出各種蠢事的成人、精神變態者、身負過多照顧他人重擔的人、迫切想要保有家庭完整或急於想分道揚鑣的家庭。卅年來,我看著無數的痛苦在橋下流過。
我現在可以說是研究人類痛苦的博士,我聽過太多有警世意味的遭遇,且見識到人類傷害自己和別人的各種手法,我也間接從別人的經驗中學到不要犯那些錯誤,我曾目睹隨著婚外情而來的毀天滅地,我不需親自下海賭博、瞌藥和欺瞞,便能體會那些行為最終帶來的破壞力,從我所做的不同選擇產生的後果中,得到了終身免費的教育機會。
在我臨床執業生涯中,我大部分都在離家六個街區的診所和我先生吉姆及好友珍一起共事。我們開了一家「小而美」的診所,診所的打掃清潔工作都是由我們的子女自己來做,等他們離家自立,我們便自己動手。我們也自己料理收費會計和安排看診時間等雜事,有一次,一個位高權重的精神科醫生對我說:「我會叫我的助理打電話給妳的助理。」我卻必須當場承認:「我沒有聘請任何助理。」
經過數十寒暑,心理治療工作已有很大的改變,不斷有新的理論躋身中央舞台,很快又退場,我們心理醫生在口沫橫飛中,走過令人暈眩的一九七○年代,而且在回復記憶療法當道的一九八○年代,幾乎毀掉我們自己。我們一路從冗長、鬆散的療程轉到鎖定目標的短程治療。「家族治療」曾是我們最優秀的技術,現在幾乎消聲匿跡了。而如同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最愛的「像酒般深沈的大海」,心理治療也是「總是不斷變化,又全都一個樣」。
我深愛心理治療工作。不時有人問我整天聆聽別人的問題,會不會讓人心情低落,我總回答說:「我不是聽取問題,而是為解決問題而聽。」個案通常是想要做些改變才找上門來,他們花錢是為了要得到一些建議,而且已做好洗耳恭聽的準備。我身為一個心理醫生的經驗是,悶悶不樂的個案來找我們之後,變得更加快樂;經常鬥嘴的小倆口變得更能體會對方的好處;家庭也終能言歸於好並攜手共度人生。在幾個療程後,雖不盡然如此,但常常我便開始聽到治療出現成效的故事了。
心理治療領域一如人生,總見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滿天飛。做為一個心理醫生,我會稍微從個案的問題中跳開,試著將注意力放在為他們量身訂製,但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的良好建議:我要求我的個案保持更冷靜、更溫和且更樂觀的感受,我也要他們在面對人生選擇時更有企圖心,而且在很多案例中,我要個案在面對自己本能的欲望時,少憑衝動行事。
羅伯?佛斯特(Robert Frost)曾寫道:「教育把苦惱推到更高的境地。」心理治療亦復如此,它是探索痛苦迷惘、從而呈現意義和希望的途徑。這本書集合了我從那些徐徐踱進我辦公室、撲通跌進我的舊沙發,找我談問題的個案身上學到的經驗教訓,它是我花數百個小時聆聽個案回答「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這個問題的濃縮精華。與人交談和做愛、睡覺、分享食物一樣,是所有人類最基本的行為之一,儘管這個論調其實也有待商榷。兩個或更多的人彼此交換心事,努力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重拾歡笑和內心的平靜。佛洛依德以新的方法建構這些交談行為,然後學者針對它們進行研究,最後,人藉著交談解決問題構成了心理治療的內涵。
心理治療是一項複雜的工作。大文豪馬克吐溫形容自己是「硬塞進一套衣服內的所有人性本能」。每一個走進我辦公室的人,都有我們其他人的影子,而且我們都基於本性行事,我們都會推諉搪塞且自抬身價,也害怕承認自己感到多麼脆弱,並試圖掩飾自己的缺點,我們必須一遍又一遍的學習如何只做一個普通人。
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曾是個在同事眼中的「笨手笨腳的高智人」,我母親常開玩笑說我沒學會走路之前已先會寫文章。我一隻眼睛失明、情緒起伏不定、缺乏時尚感和方向感、患有幽閉恐怖症而且很容易倦怠,但是,不曉得什麼緣故,我發現有一些人還挺愛我,而我全都知道他們的缺點,也很愛他們,事實上,他們是我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我至親至愛的人。
做為一個心理醫生,我自認是個通才,相當於我母親在醫學界通科醫生的地位。我不是一個遊戲治療心理師,在對幼童進行心理治療時,我幫他們的父母想出如何與他們相處的方法,我避免碰觸法律方面的事務和精密深奧的診斷。專精於某一個領域會帶來財富和職業上的報酬,但是對我來說,心理專科聽起來總是很單調乏味,用卅年的時間來解決一個問題,委實太長了。
就我而言,幹這行最好的訣竅,就是不要耍任何手段。每當我想要裝出一副聰明老練的樣子,常把我自己和個案弄得一臉胡塗。有一次,我指派給個案一個自認很漂亮、詭秘的家庭作業,他卻反問我是不是正在嗑藥。另外有一次,我試圖想要製造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對個案的未來做了一番預測,那個酒精中毒已深的個案直勾勾地看著我,突然爆聲說:「如果妳能預測未來,那妳應該到拉斯維加斯去試試手氣。」
大部分時候,我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都是很普通的辦法,不外是多休息、好好工作、一天同時做好幾樣事、以及找一些人來愛等。當然,簡單的建議並不必然容易,且不是都有效果,當不見成效時,我通常會仰賴對心理治療過程本身的信念。愛因斯坦曾說:「一個問題無法被製造它的心智本身解決。」心理治療提供個案一個安全的人際關係,使他們能探索自己的內在世界,並考慮在外在世界中採取一些冒險的行動,它為他們混沌特殊的宇宙提出另一個觀點。
我在學生時代研究卡爾?榮格(Carl Jung)、哈利?沙利文(Harry Sullivan)、奧圖?藍克(Otto Rank)、費里茲?普爾斯(Fritz Perls)和喬治?凱利(George Kelly)等心理大師的理論,我也閱讀佛洛依德的著作,但是,我對他的所有良好的行為都是情感的昇華的概念,從來就不太欣賞,我也拒抗他所謂人生大部分是競爭、攻擊和性的觀點──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理論。成長和著重以人原有的良知良能去發展(strength-based)的原型理論常常吸引我,我敬重信仰人本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家,例如亞伯翰?馬斯洛(Abe Maslow)、羅洛?梅(Rollo May)、維克多?法蘭克爾(Victor Frankl)和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我認為卡爾?葛理根(Carl Gilligan)與史東?仙特(Stone Center)有關自我和他人關係的觀念很有意思,甚至在正向心理學派存在之前,我便深信把焦點放在好的面向是很重要的。
我從一九七二年開始接受心理醫生訓練,那時的心理學家主要是試驗者,我們學習如何主持智力測驗、人格量表和心理投射測驗,後者即是拿模糊難辨的刺激物如墨跡圖形給個案看,要他們說出眼中所見到的東西。起初我覺得那些測驗十分神奇,但是經驗一多後,我變得比較喜歡以交談來作為心理診斷的方法。
後來,我在德州大學醫學中心實習,那時該中心正在進行好幾項家族治療的先驅實驗,我很喜歡家族治療的生動活潑,隨後我在內布拉斯加州大學教授女性心理學的課程,當時我是頭幾個開這種課的人之一。從某些方面來說,我是在心理學主流中泅泳,但我也是在獨力行舟,我對家庭bashing、隔離治療和歸咎於無法在場為自己辯解的第三者的方法,存有很強烈的偏見,我總是力勸我的個案回家度假並與家人團聚,我從不使用「不健全家庭」這個術語,或鼓勵別人去控告自己的父母親。
我甚至在小時候,便已覺得應該保護自己有點古怪的家人,我深深體驗自己的雙親是一對擁有他們自身複雜的問題、沒時間陪小孩的不稱職父母,但我也能感受到他們很愛我們,而且盡最大努力給我們幸福,我內在世界的風景大部分是從與他們的交談中形成,我不用嚴苛的標準去評斷他們,而且也不想以嚴苛的標準去評斷別人。
也許是我在人類學方面的訓練,我總認為心理健康的毛病和更廣大的外在環境息息相關。憂鬱症、焦慮、家庭暴力、濫用毒品和酒精等問題,都源自於我們極為不健全的社會文化,更遑論過動兒和暴食症患者。在一個兒童可以觀賞內容涉及嫖客妓女和連續殺人犯電影的社會,有誰心理會健康呢?如果大多數人都不認識他們的鄰居,不和家人親戚往來,或沒有時間在星期天六下午小睡一番,我們如何能期待他們快樂?
我們深陷否定我們自己對他人、大地和下一代具有影響力的文化當中,我們忽視兒童、難民、老年人和窮人的問題,我們的媒體鼓勵我們生活在膚淺的表象世界,叫我們想想如何美化門窗,而不去思考世界和平或我們自己精神需求的問題,我們被教導把一切事物區隔化,我們的文化導致我們身心方面的病態。
好的心理治療以輕柔卻堅定的方式,讓人們走出否定的情緒和區隔化的世界,它幫助個案發展更豐富的內在生活以及更寬廣的自我認知,它也幫助個案與他人和諧相處,同時增進他們自我存在的認知,並讓人責無旁貸的對這個世界發揮最大影響力。
對我而言,幸福,就是對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就實際層面來說,這意味要降低我們對事情是否公平或能否如願發生的期望,也代表我們要在平凡事物中找尋樂趣。我不是電視迷或購物狂,而且,我盡最大的努力勸導人們不要有幸福與否和擁有更多、更多的物質息息相關的想法。
做為一個成人,意味要接受不斷做選擇的神聖責任,我相信我們長到某一個年歲後,除了罹患慢性心理疾病以及心理遭到嚴重創傷的人之外,都要為我們自己的人生負責;若不這麼想,就是心存傲慢和蔑視。我鼓勵人們了解並接受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過去的事實,勸他們拋開過往繼續前進,並為自己和他人創造一些美好的事物。我們都有自己的傷心事,但是,不能因此就免掉我們該盡的義務。
我在一九七九年開了自己的診所,我大部分的心理治療都是在那個心理醫生擁有很多時間來幫助個案的黃金年代進行的。我的個案大多有心理治療方面的保險,甚至工廠的工人也可以要求加長療程,且悠悠閒閒地探討他們的問題,而個案也不期待心理醫生能創造迅速具體的改變。「管理式照護」之風猛然吹進我們這州時,我抱著置之不理的態度,因為我樂用自己的方式來從事心理治療,且已行之有年,我無法容忍局外人對我的個案發號施令。
最近我碰到一位忙得不可開交的心理醫生,他吹噓自己做的是「如假包換」的心理治療,並宣稱他可以在四個療程內治好大部分個案的心理問題,我簡直無法掩藏我的懷疑。好的心理治療就像烹飪一樣,都很費時費工,當然,有些個案和心理醫生濫用舊有的制度,但是我們多數都能精明的善用時間。過去,我們可以和個案發展紮實的關係,現在為了節省時間和金錢,心理醫生必須動作快,且每周都要展示進步的成果,很多東西便因而流失了。
我在內布拉斯加州大學心理研究所擔任臨床心理治療指導老師好些年,有時我開車到學校在教室授課、或坐在只能從外往裡看的鏡牆外,觀察學生做臨床心理治療,而我的研究所學生常常把他們的臨床實習錄影帶拿到我家,用我的錄音機放映出來,我邊看邊給他們指點和讚美。
我用寫信給蘿拉的形式來撰寫這本書,她是我最鐘愛的研究生。蘿拉廿來歲、單身未婚,她思想開放不預設立場、待人熱情誠懇且愛極了心理學。她和我一樣是個喜歡在外面跑的人,但她不像我那麼保守,是個勇於冒險的年輕人,她喜好泛獨木舟、溜直排輪和攀岩運動。一如大多數的年輕心理醫生,蘿拉有時會害怕、有時又過度自信,她想要實地蒐集各式各樣的病例,但又很容易被弄得驚慌失措。
我希望心理醫生和一般讀者都能好好品味這些信函的內容,我舉了很多自己工作中碰到的臨床實例,我省掉大量的引用語,但又忍不住在文章中加進了一些我最喜愛的語錄,我儘量避免使用心理學上普遍的行話和社會科學術語,但是我仍想溫柔地提醒讀者,心理治療可以是你在面對人生艱難坎坷時刻的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都是在清晨寫這些信,從我的書桌可以俯看一株老楓樹、我的花園和為鳥兒跟松鼠所設的餵食站。以信函的方式寫書是為期一年的計畫,而季節的變化影響我的心情和寫作(讀者或許樂得分析我的心情受季節影響產生混亂!)。
我從2001年12月2日開始動筆寫這些信,這正是內布拉斯加州苦寒的季節,我們正要把過去一年發生的點點滴滴埋入心底,其中包括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我們無不期望新的一年能帶給我們更好的訊息,但當時是全世界陷入黑暗的時刻。寫這些信對我來說恰似在度假,它給我一個機會把重心放在人的問題上,遠離全球大事。
親愛的讀者,我希望你們會發現這些信函兼具教育意義和趣味。身為心理醫生,我的觀察是,生活樂趣絕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是我們擁有的最美好的事物之一。所以,為自己在陽光下或火爐邊找一個舒服的位子,泡上一杯水蜜桃茶,並找一隻貓擱在你大腿上,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尋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