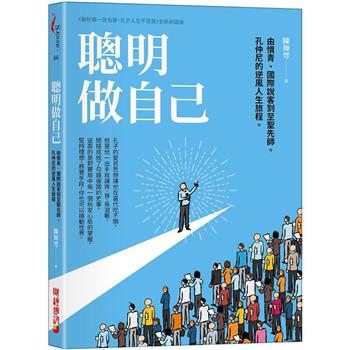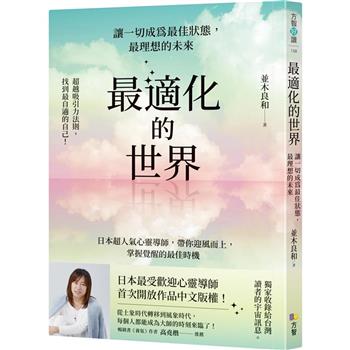CHE★切•格瓦拉語錄
卷一
青春
藥•一九五○年•拉丁美洲
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甚至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回答一千零一遍,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在描述行走的要義時,這位偉大的詩人與散文作家,給了這樣一個答案。從一開始,他們對於旅行的定義,其實就是青春的衝動以及那種類似浪漫的阿根廷氣質中的荷爾蒙故事的刺激。這句話用於他的第一部日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這次旅行花去了切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之間的二百多天。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我們仍然不厭其煩的把這條摩托車路線圖抄錄如下,因為他對於我們重新沿著這位偉大的行者的足跡來感受拉丁美洲,有著真實的指南作用,不論是出於對於革命的尊重還是對於那條旅行路線的親近。這都是值得的。
這個早熟的青年有一個寬闊的胸懷,他樂意去擁抱整個世界。旅行改變了切的生命軌道,使他從夢想「當個著名的研究者」,轉而希望「為人類服務」,並最終成為人類追夢的代表者。如果沒有旅行,他或許不會去革命,他也許就只會成為一名普通的醫生。
◆
「我們為了旅行而旅行。」
◆
旅行就這樣決定了下來,它沒有脫離我們當時做任何事的原則:隨興而為。
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切幫自己找到的要去旅行的理由。說真的,這句話有點道盡了革命者的真實理想──隨興而為。不論是情感還是偉大的旅行。而他們要旅行的原因,不過源於某次聊天。在這本日記裡,他記錄了自己的心情:
那是10月的一個早上,趁著17號的假日,我去了科多巴。我和阿爾貝托坐在他家的葡萄架下,喝著甜絲絲的馬黛茶,胡亂說著最近的時事……。我前一段時間也辭職了,不過跟阿爾貝托不一樣,我可是高高興興離開這份工作的。我覺得很不自在,因為我是個天生的夢想家,讓我為醫學院、醫院和考試所困,我真是感覺疲憊不堪。
◆
我們還在做著白日夢,在天馬行空的幻想中,我們已經到達了遙遠的國度,在熱帶海洋上乘風破浪,走遍了整個亞洲。突然,一個問題就那麼自然而然地從阿爾貝托口中跳了出來,「為什麼我們不去北美走走?(編者注:拉美人口中的北美,指的並非北美洲,而是拉美北部。)」
「北美?可是怎麼去啊?」
「騎著這輛拉波特拉撒啊,老弟。」
切的摩托車之旅地圖。他用雙腳丈量了整個拉美。
這輛諾頓牌摩托車是格瓦拉的象徵。就在那個漫長顛沛的旅程中,這輛破舊的機車承載著兩個年輕人的野心與欲望,在南美洲的大地上呼嘯奔馳。它伴隨著這兩位戰士闖蕩了二千多公里,在到達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時,它終因不能再進行修理而被棄置。剩下的路其實是兩個流浪者用腳開始的故事。不過,切仍在其後把自己的這部日記命名為《摩托車日記》(The.Motorcycle.Diaries,台灣發行的版本名為《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當切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他就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0年1、2月暑假時,他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四千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路線是這樣決定的:沿著安地斯山脈(the.andes)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中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痲瘋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切才真正瞭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成型,他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背後,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後,切在1952年9月搭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句話。切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成為他所撰寫的那本影響幾代人的青春指南讀物《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他這樣描述對於這次歷程的感受。「這並不是一個講述英雄行徑的故事,也不是一個憤世嫉俗者的敘述,至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這是兩個生命對世界的匆匆一瞥,他們擁有著同樣的希望與夢想。在一個男人9個月的生命中,他會想到很多事情,從對哲學最深沉的思考,到對一碗熱湯最絕望的渴望──考慮什麼東西,是決定在這個人現在是飽是飢。」.切在1953年6月1日回到阿根廷,他正式成為醫學博士。切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也改變了美洲的某一部分世界。
在切去世將近四十年後的2004年,好萊塢投資將這部美國的敵人所寫的遊記拍攝成為電影《革命前的摩托車之旅》。
◆
希望你隨時準備著接待兩名來去無蹤、隨風揚帆、無根無源、四處漂泊的流浪漢。
切離開痲瘋病院後寫信給該院社會助理佐萊達,她曾經和切有過一段情。佐萊達是第四位與切交往過,並有文獻證據的女子。而這不過是這位革命浪子的青春期的一段愛情花絮。
◆
現在我明白了。這一切幾乎都是命裡註定的。我的命運就是外出遠行。在這件事情上,阿爾貝托和我完全一致。也許有朝一日我會對環遊世界感到厭倦,那時我將會回到阿根廷安居。
◆
我要給每個優秀探險者的第一個忠告便是:每一次探險都有兩個端點,一個是起點,另一個則是終點,假如你真的想要完成這段旅程,那麼,就千萬不要反覆考慮這其中的過程。
◆
我越來越覺得走出家鄉是個正確的決定。我的醫學知識並沒有增長多少,反而是吸收了大量更能引起我興趣的其他知識。
──1954年4月。旅行中。給母親的信。
◆
無論如何,我想說,我仍然在繼續著自我放逐,下一步將要到達墨西哥,從那裡,我將來到歐洲,然後,可能是中國。
──切寫給異性知己蒂塔•因凡特的信。瓜地馬拉城。1954年8月。
◆
我們並不是特別缺錢,可是對於擁有了像我們這樣經歷和地位的探險家來說,打死也不能去住那種為中產階級準備的青年旅館。
◆
很多人稱我為冒險者──我的確是,但確是另類的一種:為了證明自己的陳詞濫調而用生命去冒險的。
◆
沉默是另一種爭辯。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Che語錄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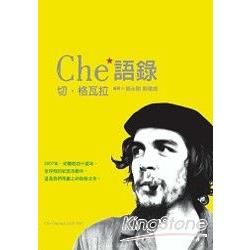 |
Che語錄 作者:師永剛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10-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76 |
社會人文 |
$ 277 |
歐美當代人物 |
$ 277 |
西方哲學 |
$ 277 |
人文歷史 |
$ 308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Che語錄
世界需要一部聖經,那些無法被《聖經》所容的人,那些永遠孤獨的看著切的畫像而淚流滿面的人,需要一部《切語錄》……
我們需要找到一部可以讓更多讀者更便於查閱,並且能夠快速領略到他精神的語錄。找到切在四十年後的精神形象,屬於每個閱讀中文的青年都可以接受,在切的話語中,找尋他的靈魂或啟示。這本書的企圖是:描述切所製造出來的影響力、全球化、網際網路交流、以英語、西班牙語、中文,或者更多的不同語言的閱讀者,在這樣的精神共識下,領受一代浪漫革命家的精神最精髓。
本書的編選原則是以切的精神線索與他所創造出
作者簡介:
師永剛,《世紀華人畫傳叢書》的策劃與發起者、曾策劃編著的《鄧麗君畫傳》、《切‧格瓦拉畫傳》、《三毛私家相冊》、《鄧麗君私家相冊》、《紅軍1934-1936》等叢書在中國大陸掀起畫傳熱潮,發行總量達上百萬套。他研究鳳凰衛視的專著《解密鳳凰》,出版後成為媒體焦點。研究《讀者》雜誌的專著,先後以《讀者時代》、《讀者傳奇》圖文版、《讀者故事》雜誌版三個版本發行,創下媒體研究專著發行超過30多萬套的全新紀錄。其之前出版數部長篇小說《天蒼茫》與《西北望》。長篇小說《迷失的兵城》即將改為電影。現為香港鳳凰週刊雜誌社執行
章節試閱
CHE★切•格瓦拉語錄卷一青春藥•一九五○年•拉丁美洲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甚至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我們將回答一千零一遍,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在描述行走的要義時,這位偉大的詩人與散文作家,給了這樣一個答案。從一開始,他們對於旅行的定義,其實就是青春的衝動以及那種類似浪漫的阿根廷氣質中的荷爾蒙故事的刺激。這句話用於他的第一部日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這次旅行花去了切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之間的二百多天。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我們仍然不厭其煩的把這條摩托車...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師永剛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10-08 ISBN/ISSN:9789570831719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