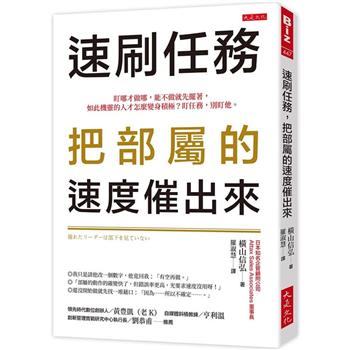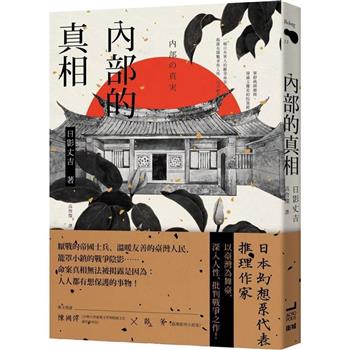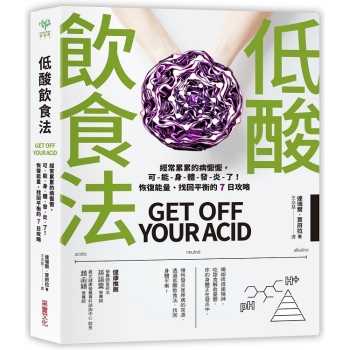詼諧之美
在崑曲裡面,詼諧占了不小的比例。
崑曲裡的詼諧時常能傳遞給我們一種生活的態度和人生的智慧。人們都說「不如意事常八九」,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未見得一時半會兒就能解決得圓圓滿滿,生活裡面的大智慧,就在於能夠把一個大事情拆解為一個個小細節,再讓它化有為無,可以一笑而過。
這種手法在崑曲裡並不少見。
崑曲對於詼諧的展現不單是集中在某一行當的表演中,也不是非要丑角出場的時候才有詼諧,而是在各個行當裡,在不同的情節裡,都能夠抖一個小包袱、賣一個小機關,讓大家會心一笑。詼諧之美,有的時候是貫穿於整個演出過程的。
《孽海記•下山》就是一齣很詼諧的戲。我們曾經提到的《思凡》中的小尼姑色空,剛逃下山便遇到了小和尚本無,《下山》就是從小和尚本無演起的。小和尚本無,與色空的身世有些許相像,在襁褓之中就病病歪歪。父母請了算命先生推算,說他「命犯孤鸞」,活不長久。無可奈何之下,父母將他「舍入空門,奉佛修齋」。隨著年齡的增長,小和尚也心事漸多,他想到人生易老,光陰易過,想要回家養起頭髮,討個渾家,過一段神仙般的生活。
由於角色行當不同,小和尚與小尼姑在表演上的差異很大。《思凡》中小尼姑色空雖然也正值青春年少,憧憬未來的人生,但她是一個俊扮的旦角(色空雖是尼姑,為了扮相上的美麗,被處理成一個帶髮修行的道姑形象),她的唱念基本上還是要依循常理來表演,而不是詼諧的路數。但是小和尚不同,他是個丑角小花臉,動作都是誇張的,說的話都是口語的、直白的、幽默的,可以毫不遮掩地說出自己的人生理想。
小和尚一出場的心理告白,自一開始就營造出了渾然一片的喜劇氣氛。他希望自己能逃下山去,「一年二年,養起了頭髮;三年四年,做起了人家;五年六年,討一個渾家;七年八年,養一個娃娃」,到了九年十年,小娃娃可以叫自己一聲和尚爹爹,想到這裡,他高興得簡直是手舞足蹈!他雖也曾有過小小的猶疑不決,但遠沒有小尼姑那麼多的愁思婉轉,很快就下了決心,頭也不回地逃下山去了。
《下山》又被稱為《雙下山》,因為在本無逃下山的途中與小尼姑色空有一段有趣的相逢。《下山》的曲詞比較通俗,有不少民歌的痕跡。一個略帶羞澀的旦角和一個天性率真的小丑,兩個少年人的相遇,帶著一種天生的歡樂,而他們相遇之後的對話就好像是一段民歌的對答。
兩個人彼此看一看都是年少之人,又都是出家人,覺得很有意思,就用話來互相試探。小和尚先問小尼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小尼姑說,自仙桃庵來,回家探母。小和尚說,出家人本來是不顧家的,你怎麼說探母呢?小尼姑說,沒有辦法,母親臥病在床,必須要回去看看。反過來,小尼姑問小和尚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小和尚說,自碧桃庵來,要下山去抄化。小尼姑說,出家人在山上自食其力,何須抄化?小和尚說,沒有辦法,師父病了,自己要盡孝心,所以下山抄化。兩個人各自撒了一個很圓滑的謊,為自己下山的行徑找一個合理的藉口,同時又都在試探對方。
一番招呼打過,兩個人又都裝作若無其事,準備各奔前程,所謂「正是相逢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前程」。最有意思的是,兩個人最後還要假裝一本正經地口稱「南無佛,阿彌陀佛」才各自分開了。小和尚一邊走一邊縮頭探腦地看小尼姑,恰被小尼姑看了個正著。小尼姑責問他,既然各走各的,你為什麼轉回頭來瞧我?小和尚說,你那邊有一個小和尚走過來,我想指點他一下而已。兩個人心下雖戀戀不捨,卻第二次裝作若無其事地各自分開。這時候小尼姑又忍不住回過身去看小和尚,小和尚看到了也不依不饒,問她,你看我幹什麼?小尼姑說,你那邊來了一個小尼姑,我也怕她不認識路,所以回頭看她。兩個人第三次裝作若無其事地各奔前程。
這三小段的來來回回,在敍事上沒有情節的推動,但是在情緒上輕鬆幽默,一波三折。這不同於一般的書面文字敍事。倘若書面文字只是一味的重複,而在情節上沒有推進,它可能就會失去對讀者的吸引力,但是在舞台上,情趣往往就產生於這樣的一種重疊之中。
這是一種屬於崑曲的奢侈。所謂奢侈,是說它在表演中不一定充滿戲劇衝突。一方面,因為崑曲載歌載舞,有太多對手角色之間的配合,會令觀者感覺滿場生輝;另一方面,崑曲的表演將人物心理活動外化成語言、動作,使所有人都能看到台上人物內心的種種變化與發展,所以有時候它對情緒的展示要勝於情節。
戲演到這裡,本無與色空二人的試探已經有了結果。小尼姑一邊走一邊尋思,那個小和尚聰明俊秀,他似乎也有意於自己,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土地祠,不如進去假裝燒香等等他,看他來不來找我。與此同時,小和尚心裡也在想著這件事,年少美貌的小尼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彷彿是心有靈犀一般,小和尚果然進到土地祠去找她。小和尚看到小尼姑打盹睡著了,想趁著她迷迷糊糊似醒非醒的時候喊一聲老尼姑來了,看她害不害怕,她若害怕就說明是逃下山來的。哪想到小尼姑是在假寐,趁小和尚不注意,在他背後喊道:「前面有一個老和尚來了!」這下子倒嚇壞了小和尚。這就是一個幽默的包袱,是舞台上的詼諧。一丑一旦在分別講述自己的心理活動給台下的人聽,當他們聚到一起,他們的心理活動就會衝突為外在的一個小情節,產生一個小噱頭。這種小衝突,輕盈、幽默而不沉重。
這一嚇的結果,是小和尚的一番心事全部暴露無遺了。一個仙桃庵的尼姑,一個碧桃庵的和尚,兩個人坦然相對,突然間明白了一件事:「仙桃也是桃,碧桃也是桃。和尚與尼姑,多是桃之夭夭。」小和尚很風雅地用《詩經》的話答了一句:「你既知『桃之夭夭』,須知『其葉蓁蓁』。我和你做個『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吧。」雖然小尼姑有些羞惱,但已經表白了心跡的小和尚很高興,執意要與小尼姑一同下山去做夫妻。小尼姑忸怩著不肯過去,小和尚說,倘有人看見就說我們是夫妻。小尼姑說,哪有光頭的夫妻呢?小和尚說,咱們就說從小就是禿子。兩個渾然天真的少年男女,嬉笑言談,看起來是一僧一尼,談的卻又是人間情事,讓人更加忍俊不禁。
中國傳統戲曲中有三小戲之說──小生、小旦、小丑。小戲裡並非沒有大美。小就有它的輕盈,小就有它的婉轉,這種婉轉不一定是一往情深,也許就是生活裡面一個普通的細節,有時候卻如同花朵盛開,突然間綻放出一種情趣。
本無與色空兩個人相約要去做夫妻。小尼姑說,一個人從廟前過水,一個人從廟後過山,約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到那邊再見。小和尚一開始不幹,生怕小尼姑誆他,小尼姑再三保證,兩個人才達成協議,一個過水,一個過山。接下來,兩個人又要在舞台上進行很多虛擬情景的表演,令人看起來更眼花撩亂。小和尚因為要背著小尼姑,所以叼著靴子過河,他戴的那串念珠還要繞著脖子飛轉起來,這一造型構成了一幅幽默的、詼諧的、充滿了生機的、妙趣盎然的圖畫,而兩個人身段的配合、聲腔的配合、心思的配合,包括這兩個已經逃出山門的出家人還在不斷地念「南無佛阿彌陀佛」,又變成了一個非常幽默詼諧的點。再加上,在這一系列動作的同時,他們還在反覆地唱著幾句民歌小調般的句子:「男有心來女有心,那怕山高水又深。約定在夕陽西下會,有心人對有心人。」整整一齣《下山》,詼諧無處不在,它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見到的情形,用一種幽默詼諧的形式傳遞出來,卻又在每一個細節上演得栩栩如生。
講《下山》,必然要談一談丑行。丑行中也有精細的劃分。小丑,又叫小花臉,也叫三面,扮演的基本上都是生活裡面的小人物,地位較低卻心地善良。由於他們的地位卑賤,所以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比那些達官顯貴要多,而這些難題又大都是為生計所迫的小事。小丑無法像戲曲中的官生、巾生、閨門旦之類那樣,總要拿出端莊肅穆的態度來,直面問題以求最終的迎刃而解,他們不能一步登天,用經世致用之學去改變生活的大格局,所以這些小人物在面對難題時往往要運用一些小智慧,有時候則想方設法將難題暫時繞開。其實這也是一種人生態度的傳遞。小丑也有臉譜,他們的鼻樑上有一個白色的小方豆腐塊,這一點染代表的是小人物卑微生活裡的無邊的智慧和聰明。利用這樣的一種智慧,他們依然可以獲得一種有品質的生活。也許正因為他們具有這種解構難題的能力,才更討人喜歡。
在我們今天的生活裡,包括我們看的小說、電視劇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人物,比如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那個張大民。如果在崑曲舞台上,貧嘴的張大民應該就是一個丑角。他是一個在生活中處處遭遇尷尬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拮据,家中弟妹成群,老母有病在身,無錢無房,不得不圍著一棵樹搭了一間房;他的工作並不順利,一個下崗的工人,前途未卜。倘若將這些元素一一羅列出來,實在看不出張大民具備了幸福的資本,但是小說卻一直圍繞著一個核心──他的幸福──去講述他的生活。
事實上,貧嘴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張大民的貧嘴化解了不少生活中的困難,遇到事情他能夠有另外一種想法,能夠有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結婚沒有房子,他可以圍著樹搭出房子;床中間有一棵樹,他覺得倒很有紀念意義,所以給兒子起名叫小樹。這些誇張的細節,讓人覺得既出乎想像,但又合乎情理。
同理,小丑的幽默、詼諧讓人感到可愛,來自於他對生活有一份認真,他願意投入這個生活。這個生活可能是瑣細的,例如《下山》裡的小和尚,無非就是想有一個孩子叫他一聲和尚爹爹。就僅僅為了這個,他會認真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應該說,中國的傳統戲曲正有這樣一種一脈相承的能量,也許戲曲的形式不會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但是會傳遞一種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于丹.遊園驚夢-崑曲之美的圖書 |
 |
于丹.遊園驚夢-崑曲之美 作者:于丹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9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音樂 |
$ 272 |
傳統戲劇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華文文學研究 |
$ 765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于丹.遊園驚夢-崑曲之美
崑曲裡的詼諧時常能傳遞給我們一種生活的態度和人生的智慧。人們都說「不如意事常八九」,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未見得一時半會兒就能解決得圓圓滿滿,生活裡面的大智慧,就在於能夠把一個大事情拆解為一個個小細節,再讓它化有為無,可以一笑而過。
崑曲之美在於它可以放開,放開到無邊無際,我們用心去體會,永遠體味不完;它也可以收結凝取,記住一個意象,你就會銘心刻骨。其實真正美好的藝術形式大體都是如此。當它擺在你的眼前,透過遠古的塵埃,你真正能夠看懂其中多少的美妙意蘊,取決於人心的感悟能力。
作者簡介:
作者于丹,影視傳媒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副院長。
更多于丹精采好書:〈于丹系列書目〉
曾獲得1996年北京市優秀教學獎,2000年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大賽一等獎第一名、北京市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北京師範大學優秀教學獎,2001年中國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北京師範大學勵耘獎、北京師範大學十佳優秀教師獎,2004年被評為北京市十佳電視藝術工作者、中國百佳電視藝術工作者,2005年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2006年獲得「中國十大教育英才」稱號,被評為2006年品牌中國年度人物之一,2007年第三屆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所講課程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精品課程。
2006年10月以來,先後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解讀《論語》和《莊子》,回響熱烈。2007年國慶長假期間,在央視「文化訪談錄」節目連續七天播出「于丹˙遊園驚夢」再次引起關注。著有《于丹〈論語〉心得》、《于丹〈莊子〉心得》等書。
章節試閱
詼諧之美在崑曲裡面,詼諧占了不小的比例。崑曲裡的詼諧時常能傳遞給我們一種生活的態度和人生的智慧。人們都說「不如意事常八九」,當我們遇到困難時,未見得一時半會兒就能解決得圓圓滿滿,生活裡面的大智慧,就在於能夠把一個大事情拆解為一個個小細節,再讓它化有為無,可以一笑而過。這種手法在崑曲裡並不少見。崑曲對於詼諧的展現不單是集中在某一行當的表演中,也不是非要丑角出場的時候才有詼諧,而是在各個行當裡,在不同的情節裡,都能夠抖一個小包袱、賣一個小機關,讓大家會心一笑。詼諧之美,有的時候是貫穿於整個演出過程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于丹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570832433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