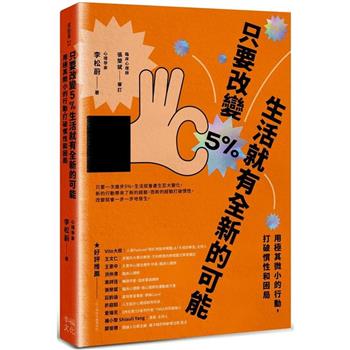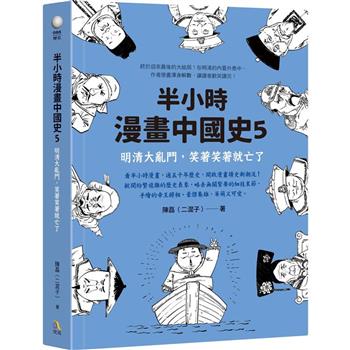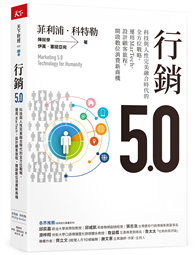這是一部完整的西藏歷史,由藏人的起源談到現今。
在長達三年的時光裡,賴爾德面對面訪談達賴喇嘛,聽達賴坦誠敘述自己的信仰,內容涵蓋歷史、科學、轉世化身的制度,以及他畢生對佛教的研究。賴爾德以多彩多姿內容豐富的敘述,說明了數千年文明、神話和精神信仰的精華。
賴爾德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一起勾勒了數千年的西藏歷史及神話,由遠古第一個西藏人源起的西藏神話,一直到第八世紀吐蕃帝國的發展,探究了西藏與蒙古的關係、第五世達賴喇嘛西藏的黃金時代,西藏在滿清皇帝時期的歲月、二十世紀上半期獨立的四個時期、達賴喇嘛在1959年流亡前與毛澤東的會面等歷史時刻。完整呈現了達賴喇嘛對西藏過去歷史的個人觀點,也凸顯了他畢生作為藏人政教合一領袖的成果。
本書特色
●本書是通俗的西藏歷史──針對現代西方人和華人,更精確、簡要,而且易讀的歷史。
●本書是基於數十年來的研究,以及由1997年11月至2000年7月間與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的18次訪談而成。總共50個小時的會談都是以英語進行,並以錄音或錄影器材或兩者一起記錄。
●除了正式訪談之外,作者在過去三十年也與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同住,過去二十年曾至西藏旅遊,因此了解西藏及其人民的想法。
作者簡介
湯瑪斯.賴爾德
在尼泊爾加德滿都住了三十年 ,如今往返於加德滿都和紐奧良之間。他曾任《時代》(Time)雜誌、《亞洲週刊》(Asiaweek)和《新聞週刊》(Newsweek)記者,攝影作品曾出現於兩本著作及逾五十本雜誌。他第一本非小說作品是《深入西藏:中情局頭一個原子彈間諜和他的拉薩秘密行動》(Into Tibet :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的圖書 |
 |
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 作者:Thomas Laird /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旅遊 |
$ 332 |
人文歷史 |
$ 332 |
史地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插圖說明
前言
緒論
1.開天闢地
2.第一位西藏皇帝(西元600- 650)
3.西藏帝國與佛教在西藏的普及(西元650- 820)
4.郎達瑪滅佛,分崩離析、動盪時期(西元797- 977)
5.佛法重興,百家爭鳴(西元978- 1204)
6.蒙古帝國和問題的根源(西元1207- 1368)
7.大計畫:第一至第四世達賴喇嘛(西元1357-1617)
8.第五世達賴喇嘛和滿族的興起(西元1617-1720)
9.第六至第十二世達賴喇嘛(西元1705-1900)
10.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西元1876-1933)
11.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早年生活(西元1935-1950)
12.中共占領下的生活(西元1951-1959)
13. 1959年之後
14.結語
參考書目
註釋
序
前言
本書是基於數十年來的研究,以及由1997年11月至2000年7月間與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的18次訪談而成。總共50個小時的會談都是以英語進行,並以錄音或錄影器材或兩者一起記錄。我在此特別感謝我們的秘書維克多(Michael Victor)花了數個月的時間來整理這些錄音帶,這是了不起的大工程。學者丁利(Tenzin Tinley)熱心的核對草稿與錄音帶。超過320頁單行距的定稿則是本書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來源,也是一系列與達賴會談關於西藏故事的精髓。
我在文中已經把達賴的談話和我的意見陳述區分得很清楚。我及許多其他參與此計劃的人士對西藏歷史的見解,和達賴喇嘛的見解有非常清楚的區隔,即使本書中有些不同的見解,也並不意味著達賴為這些意見背書。達賴鼓勵我在必要時校訂他的英文,但我只有在必須澄清意義時才會校訂,或為他增添字詞(以斜體字括於斜體的括號內)。他也准許我在主題相同但訪談時間不一時,可以合併字句。 例如,他在稍後回想起和先前某個主題相關的事物。達賴挑選了三位學者仔細檢查他於本書的所有語錄,以確保正確:我對這些學者表達感謝之意。
在我第一次與達賴會談之前,曾花了數月的時間,埋首準備研究,提出一系列要討論的問題,這些提問形成我們討論的骨幹。這些研究不單在訪談中、而且在撰寫本書的六年時間中,都持續進行。在印度達蘭莎拉(Dharamsala)的西藏作品與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是珍貴無價的資源,我並感謝圖書館員貝瑪怡喜(Pema Yeshi)的協助。同樣地,位於馬里蘭州的國務院國家檔案室幫助我瞭解1942年至1960年這段期間的世界情勢。讀者如對於書中事實感到興趣,可進一步研究。
西藏文並沒有公認的音譯標準,若用最精確的翻譯方式,對不諳此道的讀者往往會有詰屈贅牙的困擾。雖然專家知道松贊干布(Srong-brtsan-sgam-po)是西藏第一位偉大君王的確實譯名,但一般讀者會比較喜歡(Songzen Gampo) 。本書的譯音以易讀和通用為主。對於可能持反對意見,認為因此會缺乏一致性的專家們,我在此表達歉意。
若無達賴喇嘛的慷慨與耐心,本書將無法問世。我並感謝天津秋結 (Tenzin Choegyal)、丹增格西哲通 (Tenzin Geyche Tethong)及塔克拉 (Tenzin Taklha) 在訪談對話中的多方幫助,以及拉克多(Lhakdor)於訪談中予達賴喇嘛的協助。我也感謝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及桑頓普(Anne Thondup)引導我最初對西藏的興趣。西方的西藏學者的熱心地參與數小時的會談以提供我關於西藏的文化與歷史的關鍵教育。我特此對史密斯(Warren Smith)、戈德斯坦(Melvyn Goldstein)、瑟頓(Robert Thurman)、葛倫菲 (Tom Grunfeld),及史皮爾林(Eliot Sperling)表示謝忱,雖然我知道他們每人都會對本書的某些部分不表贊同。這份名單無法一一列出在過去三十年嘉惠我對西藏的瞭解的許多學者及朋友。謝謝費納(Jann Fenner)毫不慳吝不計代價地一路支持我。主編史凱霍斯(Brando Skyhorse)及發行人安特金(Morgan Entrekin)對本書的良多貢獻,使我欠他們一份情。我也對穆瑞(Kay Murray)、康斯坦丁(Jan Constantine)及作家協會致上我誠摯的謝意,大衛(Donald David)、凱斯勒(Scott Kessler)及歐康納律師事務所(Cozen O'Connor)的布魯姆(Brian Bloom)適時給我慷慨的支持。我個人承擔任何因事實或翻譯上的謬誤所引起的責任。
許多藏人慷慨地應允列入記錄的訪談,包括達賴的兄長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以及巴三拉莫(Pasang Lhamo)和卻央康山(Chuying Kunsang)兩位尼姑。除此之外,我在西藏所訪談一些藏人及華人都姑隱其名以保護他們。有些在印度及尼泊爾的藏人也不願公開姓名。
除了正式訪談之外,我在過去三十年也與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同住,過去二十年曾至西藏旅遊,因此了解西藏及其人民的想法。數百名藏人及尼泊爾人,不論是犛牛牧人、作家、僧侶、農夫、學者、接線生、地毯編織者、鞋匠、瑜伽修士、企業經營者、油漆工、計程車司機、神職人員,以及其他人,全都 親切地提供他們的友誼、智慧、歌曲、神話,殷勤招待我,教我永生難忘。我衷心的謝謝你們。
湯瑪斯.賴爾德
紐奧良
StoryofTibet@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