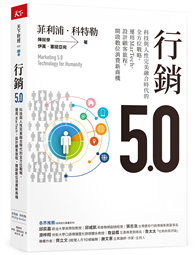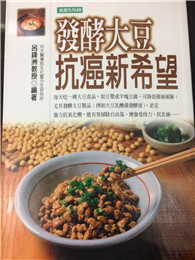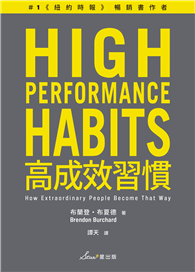必要的民主:他─我對抗還是你─我平等?
錢永祥
一、
上個世紀的美國神學家尼布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因為人類能行正義,民主才有可能,不過人類又好行不義,所以民主方有必要。」
這次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的論壇,針對台灣二十年民主實踐的經驗,想要進一步探索民主社會如何「可能」。這是一個嚴肅真實的課題:確實,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依賴於很多複雜的人性、社會、歷史、以及文化方面的條件,不是藉教科書上臚列的制度(例如定期選舉、例如多黨政治)本身就可以竟其全功。換言之,民主政治必須寄身、存活於某種民主的社會生活中。
可是在追問「民主社會如何可能」的時候,我們似乎假定了「民主」本身的含意已經很清楚明確,問題僅在於創造、補充所需要的現實條件,來幫助它的實現,從而關於「民主」含意的深入討論便顯得次要。這是一種過於樂觀的想法。其實,民主之所以不能簡單的界定,原因正在於民主並不僅是一套定型的制度或者狀態,更是一種人類群體之間互動的方式。民主制度為這種互動提供了大致的路徑,可是互動的意義、方式、結果、以及目標,並不會由制度的路徑所完全決定。下面所述台灣既有民主經驗的特色,會進一步彰顯這一點。
筆者因此臆想,如果在「如何可能」之外,我們也追問民主「何以必要」(雖然這裡已經完全離開了尼布爾的論述脈絡),那麼由於「必要」乃是相對於特定的政治課題而言的,民主本身的含意便可以「問題化」。既然課題乃是具體而特定的,那麼在認定民主對於解決此一課題乃是必要的途徑時,就不免需要說明,民主何以具有這種能力,從而我們便不得不對「民主」在這個課題脈絡裡的含意有所反省。在今天的台灣,當民主一詞的意義已經浮泛臃腫而無所不包之時,這種提問更有其現實意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追問「民主何以必要?」,首先便需要說明,相對於甚麼課題,民主是必要的?我們希望實現民主,是因為這個社會中有些嚴重迫切的問題,除了民主,其他途徑均無力處理解決,所以民主是必要的。那麼,解嚴二十年之後,當政黨政治至為發達、政權已經二次輪替、大致公平的選舉無年無之、五權分立與司法獨立、媒體自由等等也都接近實現,台灣社會還有甚麼問題,是非民主不足以解決的?
對這個問題,每個人的回答不會一樣。有人會說建國未成,有人會說主權流失,也有人會說金權猖狂、人權倒退、文化霸權宰制依舊等等,不一而足。但無論所指認的問題是甚麼,繼續主張民主的人,都有義務說明,一方面,為甚麼民主原本便旨在處理他所關切(或者憂慮)的問題,以及另一方面,為甚麼他所謂的民主有助於建國、伸張主權、維護人權、追求進步價值等等。坦白說,在這兩個問題上,似乎還難以見到足以服人的說詞。
筆者想要改弦易轍,捨教科書而回到台灣現實,指出台灣的民主受到其歷史課題的影響節制,業已發展出了一種特殊的內容。在過去,這種民主觀曾經激起過龐大的道德能量與動員效果。可是隨著課題的物換星移,這種以對抗為主調的民主,卻無力處理台灣當前最大的政治課題。這時候,我們面對的選擇是:民主還必要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就必須修正、拋棄台灣民主在內容上的歷史包袱。
二、
要凸顯上述的論點,筆者不忌粗疏,先提出一套歷史的分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展開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從最早期的1. 反抗威權體制與解嚴開放(社會對抗黨國),歷經了2. 本土化(對抗「外來──其實是黨國餘緒──政權」與建立主體意識),3. 締造新國家(藉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將中華民國體制台灣化),到4. 新世紀沿著政黨、族群、省籍、地域等歷史斷層的全面分裂,台灣社會從伊始充滿理想主義的「民主運動」,逐步演化到了一個破壞性的「民主內戰」的局面。在每一個階段,「民主」都被賦予獨特與鮮明的內容,成為特定主體的禁臠:相對於第一階段,民主是「民間」做為主體追求自由主義式的憲政民主;到第二階段,民主指新民族、新國家的消極主體意識(因為以排外為主軸);在第三階段,逐漸成熟的憲政民主程序,為主體意識提供了體制上操作的架構,從而浮現了跨政黨的積極而能量可觀的建國主體;到了第四個階段,激盪逼出另一種對應的主體意識,藍綠兩色的分裂主體隨著政黨的分界,蛻變為兩極,民主卻不再具有在其間整合的功能,反而成為衝突的戰場。在這四個階段,由於課題不同,民主何以「可能」與何以「必要」的理由也不會一樣。課題如何不同?上文所強調的主體之變即是關鍵:民主的任務,從整合的全民對抗一個外在的威權,逐步演變到這個主體的分化以及內在相互對抗。詳情不論,這四個階段一路發展下來的一個結果,就是令台灣社會從一個尋求解放的、(表面上)整合的社會,逐步分裂成兩個充滿敵意的國度。
但在這個並不算長的歷史過程中,所謂民主化,顯然仍有其不變的一個面向:民主在台灣,始終意指「我們」與「他們」的對抗。由於所面對的課題使然,台灣的民主一直是一個召喚與鞏固「我們」的過程,而「我們」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始終有一個「他們」作為對立面:沒有「他們」,「我們」也將喪失了整全性與主體性。在台灣,歷史條件使然,民主,其實就是對抗他者而鞏固我群的一個鬥爭過程。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與他們之對抗,在這四個階段之間,已經從人民與統治者、本土與外來、國民與外敵、逐漸演變成為人民內部之對抗。不意識到這種根本課題上的轉變,以及所帶來的主體之轉變,我們談論民主會流於空疏。
有人會說,台灣的歷史使然,「人民」的這種分裂在所難免,甚至於內戰才是台灣政治的真實面貌,有待一場決戰或者時間的清洗(即是某一世代死亡殆盡),才能出現一個新的、整合的台灣。我個人不接受這種歷史定命論。我的理由不是歷史條件不足畏懼,而是這種結局下的社會,不會是一個健康的、自在的、正義的社會。而不去挑戰這樣的命定,有愧於任何以進步與理想主義為念的知識人。
但是面對這樣的內戰局面,我們還是得問,民主是它的解決方案嗎?對於克服當前這種局面,民主是必要的嗎?
三、
我相信民主是必要的,因為我不認為任何非民主的方案,更能處理這個局面,尤其當這個局面乃是人民內部的敵意。那麼,此前幾種關於民主的理解(自由憲政主義的民間主體、消極排外的本土主體、積極的建國主體、直到兩種分裂主體敵我鬥爭的內戰狀態),當然必須有所調整。在今天,「必要」的民主所面對的課題,已經不復僅是人民對抗統治者或者外來者,而是還要緩和與調節人民內部的敵意與對抗。如果我們想要循民主鬆緩這種人民內部的對抗,甚麼樣的民主,才是堪當此任的「必要」計畫?我還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是下述粗略的想法,似乎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出發點。
首先,民主之所以成為內戰,當然是因為原先人民與其外某個統治勢力的矛盾,延伸擴散成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所致。因此,民主思考必須要擴大焦點,從處理人民與統治者的關係,轉成人民內部的「公民如何相互對待」的議題。這種焦點的擴充與轉移,要求關心民主的人發展相當不同的價值預設與制度想像。
其次,民主之所以演成內戰,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殆為,民主被理解為敵我之間的「競爭/輸贏」。而這種理解,乃是「多數決」民主觀的邏輯結果。換言之,在制度方面,民主思考必須不再習慣性地完全循「多數決」觀念來理解民主,即認定民主僅僅等於選舉或者投票的多數決程序。在多數決的思考模式之下,民主乃是伸張、實現一部份人既定的主張、利益的程序。而經多數決洗禮的一部份人,自然取得了政治甚至道德上的正當性。多數決在公民之間造成的輸與贏、得與失的對比,也進而轉成道德意義上的輸贏。因此在多數決之外,民主需要發展出其他鬆緩爭議、調節利益的管道,讓公民之間的分歧不至於惡化成為輸贏的決戰。換言之,在制度上,不能再讓選民、政黨、投票、選舉等等「多數決」原則的異化產物,壟斷民主的現實運作。
「多數決」原則之所以取得壟斷的地位,有一些重要的成因,包括其形式上的公平以及程序的簡單明快。但是現代人對於價值問題的一種理解(或者說誤解)也在作祟,值得特別正視。今天,大家普遍相信,價值問題「見仁見智」,無所謂客觀的是非高下,從而不可能找到任何價值上的原點、某種最根本的公共價值或者道德原則,可以為全社會所共享,進而作為「公民們相互對待」的準則。既然「價值多元」而其間又無法調和,那就無須刻舟求劍,尋找甚麼基本原則,能作的不過就是根據選票,從數量上計算、加總「偏好」了。
可是,多數決之外,民主社會真地再沒有甚麼最根本而必須為全社會所服膺的價值原則嗎?當然有,並且哲學家已經在發展筋骨結實的陳述可以參考,雖然這個問題在這篇短文中無法細說。 我們得承認,每個人的價值判斷與政治認同即使再「見仁見智」,但在最低度的標準上,一個民主社會不能不承認所有成員的平等參與權利,從而民主社會必備的價值觀勢必仍有排斥性(一套價值觀若是無所排斥,定然空洞而並無內容可言)。它至少要排斥三種態度:1. 認為某一族群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擁有、歸屬於這個政治共同體,因為這抵觸了成員身份須普及的原則;2. 認為我群的利害比他群的利害值得優先考量,因為這抵觸了平等關懷原則;3. 認為我群的願望比他群更有正當性與優先性,因為這抵觸了平等尊重原則。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奉某種這樣的價值觀為公共生活的圭臬、為成員相互對待的原則,則它無論實行了甚麼樣的選舉制度,仍然不算一個民主的社會。就近取譬,一個藉民主過程,讓我群與他群的敵對幾乎制度化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正好不是民主的,一如根據階級成分、種族膚色、宗教信仰、經濟能力等等而容許我群凌駕、歧視他群的社會,絕對違逆了民主的道德要求。
在台灣,二十年幾年的民主運動,卻並沒有將這樣一種價值觀普及落實,在民主化的旗幟之下,成為整個社會的公共道德。相反,台灣的民主觀一路耽溺在「我們」與「他們」的對抗之中,即使我們與他們都已經蛻變移位,仍然樂此不疲。為甚麼?
這是一個很複雜也極其棘手的問題,牽涉到台灣歷史曲折陰暗、因此人格與心靈很難開放,牽涉到台灣隔絕於現代世界的左右派國際運動、因此反抗意識缺乏普世、進步意識的滋潤,也牽涉到台灣既有的思考資源貧乏、道德視野狹窄、因此無力擺脫族群、「我們」意識的羈絆。結果,雖然整個社會嚮往民主,卻始終無力發展出普同的參與身份與平等的尊重關懷,只能用「對抗」做為民主的集結號聲,用「我們」與「他們」之分窮盡社會的相處關係。我們不必抽象地評論這中間的是非;但不妨自問一句:這條路走得下去嗎?以內戰為形式的民主,是有價值的嗎?再走下去,民主在台灣還有可能嗎?
四、
綜合以上所言,當前台灣社會的內戰狀態,說明了民主乃是必要的;但是這裡所謂必要的民主,不能因襲既往,繼續以對抗為僅有的內容,而是必須擴展一套有關平等的參與、有關普及公民身份、有關公平制度的理念,方足以處理眼前的迫切問題。類似的想法,以前筆者曾經用「合作型」、「對手型」、「敵我型」的三分法來表達,其目的在於尋找一種適合於「公民社會」的民主觀。可是這種「公民社會」的想像,卻正好沒有放在台灣的民主發展史的流變中來取得內容。結果,「公民社會」似乎只是一種在教科書意義上「比較好」的民主政治的形式,卻無法說清楚,因為台灣今天的政治形勢乃是民主內戰,因此更需要我們在選舉民主、多數決、民主對抗的格局之外尋覓出路。我猜想,今天備受推崇的審議民主、社會運動等等補充性的選項與公民社會一樣,也需要放在二十年來的歷史脈絡中重新陳述定位,它們的複雜價值預設才會顯現其及時性和說服力。
其實,台灣的民主運動史,除了在政治領域的對抗之外,本來還有更廣闊的關懷的。(所謂「黨外運動」,原本即涵蓋一片外於政黨政治的議題與嚮往。)階級、資源分配、生態、種族、性別、直到跨國界的剝削、團結等領域,各自都有如何落實公民的平等參與的議題,也都有各自的對抗陣線。在這些陣線上,民主的價值涵蘊,也就是普遍的參與和平等的關懷尊重,不僅十分相干,並且還可以取得更真實、明確的內容,成為指導性的原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說,民主的意義不只在於政治、不只在於政權移轉,更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民主之內容的窄化、我群化、敵對化,會侵蝕、淘空這些社會領域的平等價值意識,結果社會運動化為利益團體,社會生活中愈難見到正義與人道關懷,社會的民主生活也就愈發不可期。
所以,針對台灣,尼布爾的名句是不是可以改寫如下?「因為我們勇於對抗,選舉民主已經可能;但因為我們耽溺於對抗,超越選舉、超越對抗的民主更有必要。」──即使這種不止於選舉與多數決的民主將是甚麼樣貌,還有待摸索和充實。
錢永祥,供職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並擔任本刊編委兼總編輯。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思想(11):民主社會如何可能?的圖書 |
 |
思想(11):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政治概論 |
$ 284 |
社會 |
$ 306 |
社會人文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華文文學研究 |
$ 324 |
台灣歷史 |
$ 324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360 |
社會科學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思想(11):民主社會如何可能?
本期的專輯是:「民主社會如何可能?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希望對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有進一步的理解,也希望社會學的研究,對民主政治有所幫助,並對台灣的民主實踐進行反省與展望。本期還有「藍綠之外」專欄,對紅衫軍和野草莓學運作了紀錄和檢省。另外,台哲會的徵文活動,也以「政治與道德」專欄呈現兩篇入選作品。本期的訪談人物是擺盪在文學與科學之間的蝴蝶人吳明益先生。本期還有對四川大地震的人文關懷、探討西藏問題、金融大海嘯的啟發等,均為去年國際上的大事。
作者簡介:
編輯委員名單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沈松僑、汪宏倫、林載爵、陳宜中、單德興
章節試閱
必要的民主:他─我對抗還是你─我平等?錢永祥一、 上個世紀的美國神學家尼布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因為人類能行正義,民主才有可能,不過人類又好行不義,所以民主方有必要。」 這次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的論壇,針對台灣二十年民主實踐的經驗,想要進一步探索民主社會如何「可能」。這是一個嚴肅真實的課題:確實,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能,依賴於很多複雜的人性、社會、歷史、以及文化方面的條件,不是藉教科書上臚列的制度(例如定期選舉、例如多黨政治)本身就可以竟其全功。換言之,民主政治必須寄身、存活於某種民主的社會生活中...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思想編輯委員會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570833881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