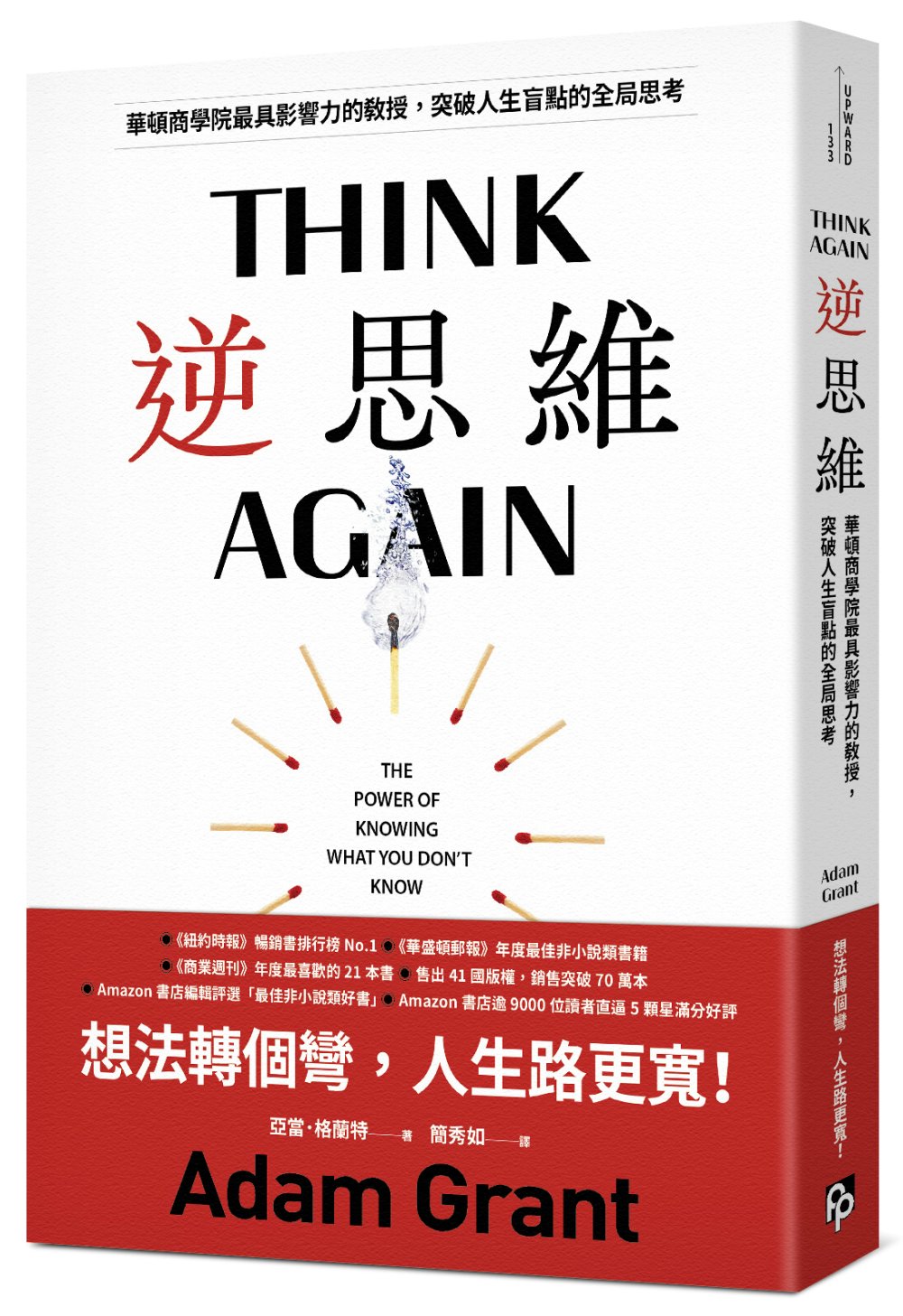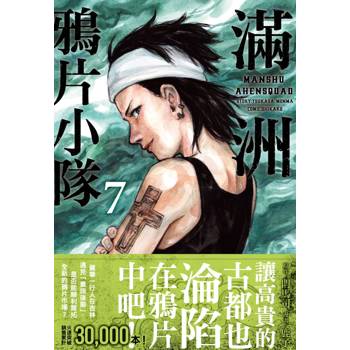一、天葬台
四周都是綠色的山巒,從東邊望過去,可以看到那個叫做古格的聖山,插在山上的鮮豔的經幡在遠處迎風飄揚。
我腳下踩著的是塊不大平展的石頭,它上面有暗紅的血垢,這使青白色的石顯得很骯髒。在它旁邊那些被人摧殘的花草無精打采地享受這個一望無際草場上充裕的陽光。而身邊縱橫交錯的經幡因為沒有風而無奈地垂掛著。似乎要配合這氛圍。
沒有被禿鷲消化完的已經辨不出部位的骨頭睡在石頭和它的周圍,它們借著刺眼的光線發出沒有質感的光芒。不曉得這是誰的骸骨?那樣要與天地一同腐爛,一同憂慮的人的屍骨。
我的朋友達倉活佛現在給我望風。他說天葬台不允許漢人接近,特別是女人。
他一再勸我放棄這個計畫。他用不很流利的漢語說得簡明扼要,意思卻表達得很準確。不要去,那很危險,有麻煩。
我不跟他解釋,不說去也不說不去。
我們從林多來到這個叫梅尕的村子已經四天了。我當時不知道天葬台的位置,試圖在這些不懂漢語的藏人中尋找與扎西倉活佛相像的面孔。達倉說,扎西倉所有的家人都在這裡。但我看不見紮西,只看見了一個瘋了的女人。她很漂亮,已經不年輕了,她的眼睛是那麼黑,那麼亮。她拉著我的手,說呀唱呀的,是藏語,我聽不懂。後來才知道她就是扎西倉的母親。他那有名的媽媽。然而這個女人所有的希望在一年前就破碎了。不管眼睛曾經如何美麗,現在那裡只有空洞的漠然了。
我心裡是一陣陣揪扭的疼痛。
這個村子有十來戶人家,他們不明白一個漢族女子到這個人煙稀少的草場幹什麼。這裡很少有觀光客,或者幾乎沒有。我剛到這個村時,想四處看看,突然,一個藏獒肆無忌憚地撲向我。是一個藏族老阿媽奮力牽住那只全身毛髮烏黑鋥亮泛著高貴色澤的藏獒,才使我安全走進她家低矮的土屋。不能給他們說我是來看扎西倉的,藏族人對自殺身亡的人充滿鄙視。特別是他以前還是轉世活佛。而且我又是一個女人,還是漢族。
在離這個村幾十裡地的寺院,扎西倉的下一世——十二世扎西倉,一個只有九歲的孩子,我想他現在正在那個華麗的經堂裡誦經。
其實,我不是對什麼天葬台感興趣,我只是想看看肢解並葬我的朋友扎西倉活佛的地方。我真的很想念他,對他滿懷敬意。
他是為了愛情去死。
在這個年代,人們根本不相信愛情,還有誰為此捨棄自己寶貴的性命呢?
因為我尊敬愛情,這或許就是我不畏危險要敍述這個故事的最本質的理由吧。
達倉活佛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千里迢迢從南京的奢華來到這個偏僻的藏族草場,他更想不通我為什麼對他們的天葬台有無限的嚮往。扎西倉已經死了,我為什麼還非得這樣?達倉覺得不可思議。他知道我在寫書,他說,你寫那些東西幹什麼?看起來真是沒有意義。我說,你不會明白,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我們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我們存在那麼大的差異。什麼是差異?他甚至連這個都不懂。但他全心全意地對我好。我覺得自己很卑鄙,借著他對我無私的愛,挖掘並接近這個故事。
我知道他愛我,他不會拒絕我的要求。
在到達梅尕的第四天,我攀緣到位於山谷深處的這個天葬台。
這裡天葬了無數的藏人。“天葬”,說得多好,那是神的旨意,是釋迦牟尼在西天的召喚。
扎西倉死了整整一年了,我是從電話知道的。達倉在他死後一周後的一個夜裡打來了電話。
那天南京下著很大的雨,天非常非常的黑,我關閉了所有的門窗,我怕冷。就在我瑟縮在柔軟的白被單腦子出現奇怪幽靈的幻覺時,達倉的電話攪醒了這淒涼又鬼魅的雨夜。他說,紮西死了。我的腦子一下子像睡過去一樣一派茫然,感到徹腹的冷。
“不,不可能。他那麼年輕。”
“死了。真的。為了女人。”
“為什麼?他是怎麼死的?”
“自殺。”
“那麼卓瑪呢?”
他沒有回答我。我們誰也沒有再說什麼。
只有沈默。
可是我腦子裡在長長的空白過後竟是那樣的痛。扎西倉和一旦卓瑪都如此漂亮美麗,而且他們真摯的愛情,連神都要退避三舍。我多少次這樣想。
然而扎西倉就這樣沒了。
達倉的漢語講得不好,所以總是用最少的單詞與我交流,沒有形容詞,沒有講究的語法,更沒有時尚的修飾語。但他的語言像高原美麗的雪蓮花一樣張揚著魅力和芬芳。我喜歡在及將入睡的子夜聽到他那天籟般的聲音。我的手指輕輕握著話筒,聽著他的呼吸,那些來自西域紛紛落在我床榻的模糊又細小的問候就這樣舒緩地進入我的睡夢。
我總是很平靜,因為我是城裡人,因為我受過良好的教育,因為我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心房四周建起堅固的圍欄。我不為所動。在電話裡我很少言語。他總在無邊無際的失望中掛掉電話。
可是,在扎西倉死的那些日子(不,準確地說,在我得知他死訊的日日夜夜),我的心臟老是不規律地跳動,它那急於穿越時空的念頭使我沒有睡意。因為這個,在達倉來電話的時候,我的話很多,總在詢問,我想知道所有的細節。
我覺得自己很可恥。我在利用達倉對我的愛。他知道我要寫扎西倉和一旦卓瑪的愛情。他苦笑,你會寫我嗎?
不,我只寫死亡的愛情。那樣的愛情才能永恆。
達倉非常失望,你是想讓我死嗎?
不,不。好好活著,你這麼年輕。你只有24歲。
其實扎西倉也是。
天葬台處在很美麗的地方,它的四周遍佈青翠的綠色,是綿延的草原,星星點點的格桑花點綴其中,有白色、黃色、紫色,當然還有那最惹人眼目的紅。
我坐在冰涼的屍骨和香氣幽幽的花草之間,天葬臺上幹成褐色的血污同樣悲傷地注視著我。我的腦子紛亂異常,它像這裡的陽光一樣活躍,反復地探索這個映在我眼瞼神奇的風景。這樣美麗空靈的地方,竟是葬人的所在。與神靈最接近的藏人,他們似黑夜般憂傷、似藍天般明亮的眼睛,最終就要在這樣的地方反復地衰老、衰竭並暗淡。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向上蒼禱告,他們單獨地睡去,他們習慣孤獨地行走在廣袤的草原,然後單獨地死去。
現在是上午十點鐘,我不再感到冷了,把那件牛仔外套扔在花草叢中,它軟綿綿地倒下,就像饑餓的孩子鍾情麵包一樣喜歡大地。
忘我地匍匐在天葬台的一側,我知道自己的目光柔和、癡迷,沉湎在對扎西倉憂傷的追憶中。風流倜儻的他也在這裡被肢解,敲碎,拌上炒熟的香噴噴的青稞面,天葬師幾聲通靈般的吆喝,成群接隊的的禿鷲就從對面的山坡而來,俯衝向下,匍匐在草地上,向屍體接近,然後準確地叼起一塊,慢慢咀嚼。然後飛上藍天。扎西倉那杏仁色芬芳的肉體也是這樣被帶到天堂的。
扎西倉屬於這塊神秘的土地,這註定他從一出世就與釋迦牟尼緊密相關。他的父親,一個最後的貴胄,曾經是個喇嘛。在他一出生時就抱到寺院,讓活佛給他取了名字,旦江才讓,這個名字後來就像佛一樣跟隨著他,直到他出家,直到他轉世。在他呀呀學語時,他的父親一字一句教他誦經。他手裡拿著厚厚的經書,他不識字,但他會讀,除了放牛羊,他所有的時間都給了印刷得整整齊齊的經書。他不曉得裡面說的是什麼,知道他的生命將與此密切相關。他搖頭晃腦,嘴巴一張一合,忘我的神情讓他的父親很欣慰。男孩嘛,本來就是為佛祖而生的,去寺院當喇嘛是天經地義,這才叫有出息。
扎西倉總在鮮豔的經幡和華美的經堂裡編織自己的夢想,他綣伏在寺廟的門檻下,對佛祖執著的神態使他一步步地走進寺院,他從沒有想到要離開經堂,也沒有想過離開這塊草場。他的笑容是那樣燦爛天真,他所有的心思都在經書和萬能的佛祖上。除了吃飯睡覺,他生活的一切就佛。
萬物如此美麗,草原的水如此清甜,那都是佛祖的光耀。
現在我的眼睛閃爍著淚花。天很藍,很近。頭頂的太陽驅走了大地上的寒氣,連花都這樣舒展。我的心為這四周無邊的寂靜所震撼。
扎西倉一米七五魁偉健壯帥氣的身體就在這塊石頭上歸到了天堂。他的腦袋上有一個洞,他還沒被背到這裡之前就有了。他對卓瑪的愛就在那聲劃破天際的槍聲下終結,他讓那個終他一生的愛情在身體上鑄下一個黑洞。那個黑洞是對絕望愛情的報復。他沒有什麼可以喝彩的,他的愛情將他推向死地。他心甘情願。
他無法想像那個與他肌膚百般契合的卓瑪會背叛愛情。她說,我不愛你了,我們得分開。他發瘋地質問她,揪住她的衣領。他顯出了兇殘相,冷和絕望迅速掠過全身。當看到卓瑪冷漠而平靜的目光時,他知道自己完了。
愛情在反復變老。他不理解。這一刻輪到他了。他的愛也在怒放了一季後倉促落幕。他想不通。
他不知道。
當他背叛宗教的時候,愛情也隨之要背叛他。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活佛之死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活佛之死【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唐卡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5-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344頁/15*21cm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3 |
現代小說 |
$ 230 |
小說/文學 |
$ 237 |
中文書 |
$ 238 |
小說 |
$ 2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活佛之死
兩位喇嘛與藏族女孩、一個漢人女作家,小說著墨這四個人濃郁的愛、友誼與掙扎,也將西藏的風土文化背景自然描摹其中。
這兩位喇嘛角色與一般喇嘛不同,他們是活佛,也是年輕、熱情的生命,不知是否命運弄人,當年輕活佛堅貞的宗教信仰與同等忠貞的愛情信念相互違背,生命巨大的矛盾充斥著,難道正如小說裡所言:極端的愛情終究躲不過死神的魔爪?小說將搭配幾幅西藏精采的風景圖片,無論愛情的主題或是對西藏人文與自然背景的鋪陳,都可緊抓住讀者的目光,更讓人暗地思索信仰與愛情之間,選擇與承擔之間……無盡的人生課題。
作者簡介:
唐卡,詩人、作家。中國某地簽約作家。曾學經濟,後又修心理學。有詩集《沼澤地的吟唱》、長篇小說《你是我的宿命》、《荒誕也這般幸福》、《頂樓的女人》、《魔匣,別打開》、《你在找誰》、《天堂鎮》出版。另有劇本《為了愛》拍成數位電影。旅居生活。
章節試閱
一、天葬台四周都是綠色的山巒,從東邊望過去,可以看到那個叫做古格的聖山,插在山上的鮮豔的經幡在遠處迎風飄揚。我腳下踩著的是塊不大平展的石頭,它上面有暗紅的血垢,這使青白色的石顯得很骯髒。在它旁邊那些被人摧殘的花草無精打采地享受這個一望無際草場上充裕的陽光。而身邊縱橫交錯的經幡因為沒有風而無奈地垂掛著。似乎要配合這氛圍。沒有被禿鷲消化完的已經辨不出部位的骨頭睡在石頭和它的周圍,它們借著刺眼的光線發出沒有質感的光芒。不曉得這是誰的骸骨?那樣要與天地一同腐爛,一同憂慮的人的屍骨。我的朋友達倉活佛現在給...
»看全部
目錄
目次
一、 天葬台
二、 初到林多
三、 小喇嘛
四、 與活佛散步
五、 香浪節
六、 一旦卓瑪
七、 六世達賴倉央嘉措
八、 到活佛家
九、 扎西倉的身世
十、 初夜
十一、 轉經
十二、 逛聖山
十三、 關於更敦群培
十四、 深夜電話
十五、 背叛宗教
十六、 同居生活
十七、 歸西
十八、 尾聲
一、 天葬台
二、 初到林多
三、 小喇嘛
四、 與活佛散步
五、 香浪節
六、 一旦卓瑪
七、 六世達賴倉央嘉措
八、 到活佛家
九、 扎西倉的身世
十、 初夜
十一、 轉經
十二、 逛聖山
十三、 關於更敦群培
十四、 深夜電話
十五、 背叛宗教
十六、 同居生活
十七、 歸西
十八、 尾聲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唐卡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ISSN:9789570834192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4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