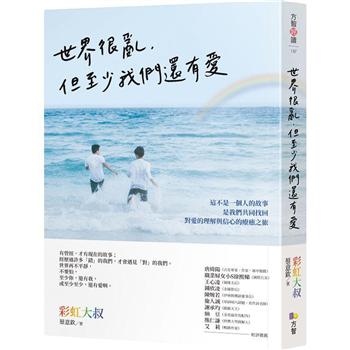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靈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靈山(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十周年紀念新版) 作者:高行健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10-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靈山
《靈山》是一部獨樹一格的長篇小說巨著,根據作者中國西南偏遠地區的漫遊印象,由不同的人稱代詞「你」、「我」、「他」呈現不同的內心觀點,更呈現主人公旅程的反思與朝聖心路,瑞典皇家學院的頌辭提到:「在高行健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文學從個人在群眾歷史中的掙扎,得到新生。」
邊陲地帶流傳巫術、民謠、江湖好漢,奇風異景,一趟探索心靈的桃花源,敘述者到處遊蕩,只為尋找心中的樂土。作者從各個角度切入,體現一個向靈山朝聖的心路歷程,並藉此撥開中國文化的多樣神秘面紗。
在作者的運鏡之間,心境的蒼涼與迷濛中,世界萬千之景,富麗磅礴的山水、曲折典雅的小城窄巷,在藝術家/小說家的虛實筆觸之下,吐納出無盡的魅力……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14/09/02
2014/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