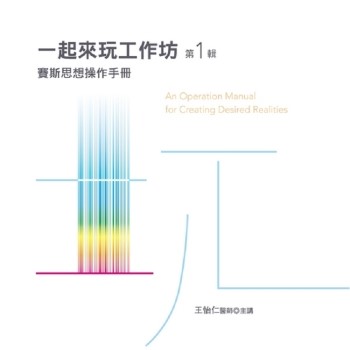引言:「中國」作為問題與作為問題的「中國」
也許,「中國」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冠以「中國」之名的著作,僅僅以歷史論著來說,就有種種中國通史、中國政治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等,在我們的課堂裡,也有著各式各樣以中國為單位的課程,像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文化等等。通常,這個「中國」從來都不是問題,大家習以為常地在各種論述裡面,使用著「中國」這一名詞,並把它作為文明的基礎單位和歷史的論述前提。
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質疑說,真的有這樣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中國」嗎?這個「中國」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還是一個具有同一性的歷史單位?它能夠有效涵蓋這個曾經包含了各個民族、各朝歷史的空間嗎?各個區域的差異性能夠被簡單地劃在同一的「中國」裡嗎?美籍印度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響,而且獲得大獎的中國學著作,名稱就叫《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個美國評論者指出,這部著作的誕生背景,是因為「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國族主義情緒高漲和族群關係日趨加劇的地區」,因此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及其歷史脈絡,而這一問題直接挑戰的,恰恰就是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這些過去不曾遭遇的質疑,可能使原來天經地義的「中國」,突然處在「天塌地陷」的境地,彷彿「中國」真的變成了宋人張炎批評吳文英詞裡說的,「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本來沒有問題的歷史論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嗎?
至少在歐洲,對於民族國家作為論述基本單位的質疑,我相信,是出於一種正當的理由,因為民族國家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建構起來的,它與族群、信仰、語言以及歷史並不一定互相重疊,正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地圖上國界內的「領土」只是政治權力的領屬空間,而作為政治領土的「空間」也不過就是地圖上的國界所標誌的地方,與其用後設的這個政治空間來論述歷史,不如淡化這個論述的基本單位。所以,就有了類似「想像的共同體」這樣流行的理論。至於「中國」這一歷史敘述的基本空間,過去,外國的中國學界一直有爭論,即古代中國究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民族─文明─共同體」,一個浩瀚無邊的「帝國」,還是從來就是一個邊界清楚、認同明確、傳統一貫的「民族─國家」?但是,對於我們中國學者特別是大陸學者來說,很長時期內,這似乎並不是問題,因此也不屑於討論。
應當承認,超越簡單的、現代的民族國家,對超越國家區域的歷史與文化進行研究,是一種相當有意義的研究方式,它使得歷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動的歷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歐美、日本的學者,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出於自然的感情和簡單的認同,把「中國」當作天經地義的歷史論述同一性空間,更不能要求他們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有意識地去建設一個具有政治、文化和傳統同一性的中國歷史。所以,有人在進行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描述時,就曾經試圖以「民族」(如匈奴和漢帝國、蒙古族和漢族、遼夏金和宋帝國)、「東亞」(朝鮮、日本與中國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閩廣、川陝甚至各個州府縣)、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觀察立場,來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這些研究視角和敘述立場,確實有力地衝擊著用現代領土當歷史疆域,以政治邊界當文化空間來研究中國的傳統做法,也改變了過去只有「一個歷史」,而且是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論述。
但是,需要追問的是,這種似乎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方法和立場本身,是否又過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歷史的差異性,或者過度看小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歷史延續性和文化同一性?因為它們也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只是來自某種西方時尚理論的後設觀察,成為流行的後殖民理論的中國版,那麼,它背後的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如何理解?特別是作為中國學者,如何盡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這些理論和立場之後,重建一個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這是本書要討論的中心話題。
一、從施堅雅到郝若貝:「區域研究」引出中國同一性質疑
1982年,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亞洲研究》上發表了題為〈750-1550年中國人口、政區與社會的轉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論文,他提出,中國在這八百年來的變化,應當重點考慮的是(一)各區域內部的發展,(二)各區域之間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組織,(四)精英分子的社會與政治行為的轉變。他把唐宋到明代中葉的中國歷史研究重心,從原來整體而籠統的中國,轉移到各個不同的區域,把原來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分解為國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職業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紳(localelite or gentry),他特別強調地方精英這一新階層在宋代的意義。這一重視區域差異的研究思路,適應了流行於現在的區域研究,並刺激和影響了宋代中國研究,比如韓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eter Bol)對撫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區域的研究。
當然,對於中國的區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並不是從郝若貝這裡才開始的,而是早在施堅雅(William Skinner)那裡已經開端。施堅雅在他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非常強調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不過,在中國史領域裡,這種具有明確方法意識和觀念意識的研究風氣,卻是從八、九十年代以後才開始「蔚為大觀」的。公平地說,本來,這應當是歷史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研究確實在很長時間裡忽略地方差異性而強調了整體同一性,這種研究的好處,一是明確了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差異,二是凸顯了不同區域、不同位置的士紳或精英在立場與觀念上的微妙區別,三是充分考慮了家族、宗教、風俗的輻射力與影響力。比如,近來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區劃,重視宗教信仰、市場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種「關係」構成的空間網絡,使這種超區域的區域研究更吻合當時的實際社會情況。
這一區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學術界同樣很興盛,不只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樣得到廣泛使用,領域也在擴大,除了衆所周知的斯波義信在施堅雅書中關於寧波的研究,以及此後關於江南經濟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會史研究中,也同樣有相當的呼應,這一類研究成果相當多,正如日本學者岡元司所說的那樣,尤其是1990年以後的日本中國學界,對於「地域」的研究興趣在明顯增長,這種區域的觀察意識在很大程度上,細化了過去籠統的研究。舉一個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領域,小島毅的《地域からの思想史》就非常敏銳地批評了過去溝口雄三等學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點根本的問題,第一是以歐洲史的展開過程來構想中國思想史,第二是以陽明學為中心討論整體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揚子江下游出身的人為主,把它當成是整體中華帝國的思潮。這最後一點,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運用了「區域」的觀察視角,它使得原來朦朧籠統的、以為是「中國」的思想與文化現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個區域,使我們了解到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動,其實只是一個區域而不是瀰漫整個帝國的潮流或現象。如果在這種區域研究基礎上,對宋代到明代中國的進一步論述,這應當是相當理想的,至今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
但是,有時候一種理論的提出者,其初衷與其後果卻並不相同,理論與方法的使用,並不一定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區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卻意外地引出了對「同一性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
二、從亞洲出發思考:在亞洲中消融的「中國」
如果說,作為區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蘊涵了以地區差異淡化「中國」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化解「大」,那麼,近年來區域研究中對於「亞洲」或者「東亞」這一空間單位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大」涵蓋「小」,也同樣在淡化中國的歷史特殊性。
對於「亞洲」的特殊熱情,在日本,本來與明治時期的亞洲論述有關,那是一段複雜的歷史,我在第五節還將詳細討論,這裡暫且從略。其實,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敘述空間的芥蒂,也不始於今日,而是在明治時代就已經開始,追隨西方民族與國家觀念和西方中國學,逐漸形成日本中國學研究者對於中國「四裔」如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的格外關注,他們不再把中國各王朝看成是籠罩邊疆和異族的同一體。這一原本只是學術研究的取向,逐漸變成一種理解中國的觀念,並在二戰前後的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舉一個例子,二戰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史》,開頭就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滿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敘述。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在廣島大學的系列報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敘述理論,此年以《大東亞史の構想》為題出版,這一構想和當時日本官方對於通過歷史促進大東亞共榮圈認同的意圖完全一致。當然這都是陳年舊事,但是,近年來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日本、韓國與中國學術界出於對「西方」即歐美話語的警惕,接受後殖民主義理論如東方主義的影響,以及懷著擺脫以歐美為「普遍性歷史」的希望,這種「亞洲」論述卻越來越昌盛,他們提出的「東亞史」、「從亞洲思考」、「亞洲知識共同體」等等話題,使得「亞洲」或者「東亞」成了一個同樣不言而喻的歷史「單位」,從宮崎市定以來日本習慣的「アジア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楊柳枝」。
應當承認,近二十年來,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是,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什麼時候可以成為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他者」(歐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這還是一個問題。且不說亞洲的西部和中部現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也不說文化和歷史上與東亞相當有差異的南亞諸國,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空間」,承認過一個「歷史」?「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這還是一個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別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不必說「亞洲」或者「東亞」本身就是來自近代歐洲人世界觀念中的新詞,就說歷史罷,如果說這個「東亞」真的存在過認同,也恐怕只是世紀中葉以前的事情。在第四章裡我會指出,在明中葉以前,朝鮮、日本、越南和琉球對於中華,確實還有認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漢晉唐宋文化,畢竟還真的是「廣被四表」,曾經讓朝鮮、日本、琉球、安南感到心悅誠服,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也就在這種「衆星拱月」中,靠著「以夏變夷」的想像而洋洋得意。可是,這種以漢唐中華為歷史記憶的文化認同,從17世紀以後開始瓦解。先是日本,自從豐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發布驅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為「神國」,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鮮,不再顧及明帝國的勢力,其實,日本已經不以中國為尊了。不僅豐臣秀吉試圖建立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大帝國,就是在學了很多中國知識的德川時代的學者那裡,對於「華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麼按照地理學上的空間來劃分了,從中世紀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來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他們開始強化自我認識。1614年德川秀忠發布「驅逐伴天連之文」中,自稱是神國與佛國,「尊神敬佛」,在文化上與中國漸行漸遠,特別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後,他們更接過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接著是朝鮮,毫無疑問,在明帝國的時代,朝鮮儘管對「天朝」也有疑竇與戒心,但是大體上還是認同中華的,然而,由於本身是「蠻夷」的女真人入主中國,改變了朝鮮人對這個勉強維持的文化共同體的認同與忠誠。所以,他們一方面始終堅持明代的衣冠、明代的正朔、明代的禮儀,一方面對他們眼中已經「蠻夷化」的清帝國痛心疾首,反覆申斥道:「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
近來,為了破除那種把現在的民族國家政治空間當作歷史上的「中國」的研究方式,也為了破除試圖證明歷史上就是一國的民族主義歷史觀念,「亞洲」被當作歷史研究的一個空間單位,這很有意義。但問題是,當「亞洲」成為一個「歷史」的時候,它會不會在強化和凸顯東亞這一空間的連帶性和同一性的時候,有意無意間淡化了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差異性呢?從中國歷史研究者立場看,如果過於強調「從亞洲出發思考」,會不會在「亞洲」中淡化了「中國」呢?
三、某些台灣學者的立場:同心圓理論
關於台灣歷史學的討論,最麻煩的是政治化問題。我的評論不可能完全擺脫兩岸立場的差異,但是,我試圖盡量從學術角度討論而不作政治價值的判斷。對於「中國」這個議題,台灣方面某些學者當然一直有相當警惕,他們對於大陸用現在的中國政治領土來界定歷史中國,有種種批評,有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如一位叫作呂春盛的學者,對大陸流行的四種關於「中國」的論述,都作了尖銳有力的批評,他說,要界定一個完整意義的「歷史上的中國」,恐怕也幾近是不可能的事。
避免界定一個包括台灣的「中國」,避免一個包含了台灣史的「中國史論述」,試圖超越現代中國政治領土,重新確認台灣的位置,這一思路當然摻入了現時台灣一部分歷史學家太多的政治意圖。不過,在歷史學領域,確實也有人從台灣本土化的願望出發,藉著超越民族國家的區域研究之風氣,重新檢討中國史的範圍。其中,一些台灣學者提出了「同心圓」的理論,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杜正勝先生。在一篇相當具有概括性的論文中,他說,「到1990年代,此(指台灣代表中國)一歷史幻像徹底破滅覺醒了,新的歷史認識逐漸從中國中心轉為台灣主體,長期被邊緣化的台灣史研究,已經引起年輕學生的更大的興趣。我提倡的同心圓史觀扭轉『中國主體,台灣附屬』的認識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他覺得,這是反抗文化霸權,因而試圖瓦解傳統的「中國」論述,代之以一個以台灣為中心,逐級放大的同心圓作為歷史論述的空間單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鄉土史,第二圈是台灣史,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
在杜氏的理論背景中,除了依賴區域史與世界史論述,分別從「小」與「大」兩面消解「中國論述」之外,把「中國」這個國家的政治整合與文化認同分開,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支柱。由於杜氏的論述是建立在把「台灣」從「中國」認同中「拯救」出來的基礎上,因此他強調,所謂「中國」是在戰國晚期逐漸形成的,「此『中國』與以前具有華夏意味的『中國』不同,它進一步塑造漢族始出一源的神話,漢文化遂變成一元性的文化,這是呼應統一帝國的新觀念,完全扭曲古代社會多元性的本質」,這種依賴於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強行整編到中國的文化,又隨著政治力量進入「中國」的周邊地區,改造土著,因此,「漢化」這個過程,並不像過去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文明化(華夏化)的過程,而是一個政治統合的歷史,在強勢力量的壓力下,土著只有漢化,因為「漢化是取得社會地位的惟一途徑,堅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價值所鄙視」,因此,按照他的說法,台灣是被迫整編進中國論述中的,要增強台灣的族群認同,當然就要破除中國文化同一性神話,這種所謂同一性,不過是在政治權力的霸權下實現的。
他們覺得,這是祛除台灣文化認同與歷史敘述的「混亂」的良方。但是,且不說這種論述的歷史依據如何,從歷史論述上看,台灣的清晰,帶來的是中國的殘缺,原來似乎沒有問題的中國論述,在這種「離心」的趨向中,也發生了同樣的「混亂」。2003年底,在慶祝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週年的會上,作為原所長的杜正勝,又發表了一篇相當重要的講話,其中提到當年在大陸時,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歷史學,即「不該有國情之別,只有精確不精確,可信不可信」的學術,但是一方面又由於內心關懷和外在環境,有很濃烈的「學術民族主義」,這種「學術民族主義精神使史語所扮演另一個愛國者角色」,可是,如今卻不同,他在第六節〈期待新典範〉中提出,「史語所在台灣,客觀情境讓它跳出『中國』這個範圍的拘限,讓它走出與人爭勝的『國』恥悲情」,這個時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國的中國史」,是「從台灣看天下的歷史視野」。
從台灣看天下,因此台灣是中心,歷史論述中,時間如果被王朝所捆綁,那麼歷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為經,以皇帝更替為緯的王朝史,空間如果被帝國所限制,那麼歷史描述常常就會有中心與邊緣的層級差異,但是,當這種時間與空間被新的視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換,那麼確實會形成新的論域。1998年,鄭欽仁在《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反思》中引述了日本人尾形勇、岸本美緒《中國史》、矢吹晉《巨大國家中國のゆくへ―― 國家•社會•經濟》、《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 中華形成の東方と世界》以及李濟的《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再論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等等,重新討論古代中國的範圍,他覺得,還是日本支那史的「中國」範圍比較適合,他說,古代中國的精神線,大約應當在長城以內,並批評所有中國學者都用現在的中國政治疆域來處理古代中國問題,什麼都說成是中國的,這是民族主義。而廖瑞銘的《遠離中國史》,不僅有一個驚世駭俗的題目,而且提出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宣告」,覺得過去台灣的中國史有太多的迷思,總是沉湎於四點,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是在中國歷史中尋求智慧,三是中國歷史提供太多詞彙來定義現代事物,四是世界二分並立。他說,這裡面有太多的政治考慮,「歷史是一種詮釋的學問,具有理性與感性的雙重性,它可以是一種學術、真理,也可以是族群情感的黏合劑」,但是,當他斬釘截鐵地要遠離中國史的時候,他是否也是落入了以台灣為中心的「太多的迷思」,或者完全變成台灣「族群情感的黏合劑」了呢?
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杜正勝引起極大爭議的一個話題,就是重新繪製地圖。他設想以台灣為中心,改變過去橫向東西縱向南北的地圖畫法,使它轉個九十度,他認為這樣一來,台灣就不是「中國」的東南「邊陲」,而中國沿海就是以「台灣」為圓心的上方的一個邊緣,而琉球以及日本則是台灣右邊的邊緣,菲律賓等就是台灣左邊的邊緣。那麼,在這樣的歷史與空間敘述中,「中國」是否就被消解了呢?
四、大汗之國:蒙元與大清帝國對「中國」歷史的挑戰
在過去習慣的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中,最不容易被規整地納入「中國」的,就是元朝和清朝兩個帝國的歷史。在宋代「中國意識」逐漸清晰也逐漸確立以後,歷史彷彿有意製造了一個曲折,讓蒙古人建立了一個遠遠超過漢族中國的世界性大帝國,而在明代漢族人重新建立了一個漢族中華帝國,彷彿再次確認族群與國家重疊的這一空間後,歷史再一次讓來自長城以北的清人取得勝利,建立了又一個遠遠超過了漢族中心區域的大帝國。
這兩個帝國對於「中國」史學帶來的「麻煩」,就是它必須超越漢族中國這個中心,採集更豐富的、來自不同立場、不同語言、不同敘述的文獻資料,論述更廣大的地域空間、更多的民族和更複雜的國際關係,這使得傳統的「中國史」似乎不能勝任。這一歷史學的困局在晚清學術界已經被敏感地注意到了,晚清西北地理研究和蒙古史的興盛,無論是否有主動回應這一歷史現象的自覺意識,實際上都是這一歷史的刺激。而對於明代所修《元史》的反覆重寫,包括從晚清以來的魏源《元史新編》、屠寄《蒙兀兒史記》、洪鈞《元史譯文訂補》到柯紹忞《新元史》等等,之所以反覆出現,也就是因為以「元朝中國」為歷史空間、以漢文史料為主要文獻來源所敘述的歷史,並不能充分反映那個「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的王朝。特別是,這個王朝既是漢地政權,又是大蒙古帝國(Yeke Mongghol Ulus)中的一部分,正如蕭啓慶所說,「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與中原帝王的雙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孫不能僅以中國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須自蒙古『大汗』的觀點著眼,否則會引起嚴重的政治問題」,漢族在這個大帝國中始終只是被統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這個王朝絕不同於漢唐宋這樣的漢族王朝。因此,近年來,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和杉山正明就提出世界史中的「蒙古時代」,他們認為,用這一概念工具重寫歷史,是一個讓世界史也是讓中國史改變面貌的歷史現象,他建議學術界要研究「蒙古時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這個歷史不是「中國史」的,而是「世界史」的。杉山氏本人最近不僅出版了《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ゥルス》一書,而且也運用超越中國的地圖資料和域外文獻,撰寫了〈東西方地圖顯示的蒙古時代的世界像〉、〈伊朗、伊斯蘭文獻所描繪的蒙古時代的世界像〉等等論文。
蒙古時代史並不是中國元朝史,它不同於當年重編《新元史》,只是擴充史料,而是要跳出以元朝史為中心的中國史,站在更大的世界空間來看歷史,這個歷史雖然包括了中國這個空間在內,但中國卻並不是一個天經地義的空間,更不是唯一的歷史敘述空間。同樣的是清帝國,年,美籍日裔學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著作《最後的皇朝:清代皇家機構的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再度表達一種超越「中國史」的觀點。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論述的是,清朝能夠成功維持三百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並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說的「漢化」或者「中國化」,而是滿族作為一個入主中原的群體,不僅依賴保持本身的特點,實施異於漢族的統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漢族民族的支持,從這一點上來說,清朝統治者是以中亞諸族的大汗身分,而不是中國傳統皇帝身分出現的,滿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東西,所以,清帝國和中國並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
羅友枝是在回應兩年前的一次論戰。1996年,當羅友枝針對何炳棣年〈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關於清朝「漢化」的論點,在全美亞洲年會上以前任會長身分發表會長演講〈再觀清朝: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作為一個中國出身的歷史學家,何炳棣曾經尖銳地反駁,寫了〈我對漢化的再思考:對羅友枝「再觀清朝」一文的答覆〉。何認為,對於滿清來說,儒家化就是漢化,儒家化和中國化是一回事,因而隱含的一個結論就是滿清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而羅友枝的這一論述無疑是對何炳棣的回應,也是對超越「中國」的清代歷史的再度論述。
在這一爭論表面,毫無疑問有出身美國(羅友枝是日裔美國人)和出身中國(何炳棣是基本教育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的兩種學者之間,在認知上和感情上的差異,不過,在這些論爭的背後,卻還有關於「世界」和「中國」的不同觀念。從魏特夫(K.A.Wittfogel)的《中國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以來到現在,在西方學術界仍然很有影響的「征服王朝」理論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於否認所有外來民族都被漢族「同化」,而強調各個民族成分的延續和傳統的影響。換句話說,強調征服王朝的「超中國」意義,一是保持雙重民族性的歷史描述,二是強調歷史過程中異族對漢族的反影響,三是否認以現在的漢族中國,來追認一切以往的歷史。因為在他們看來,從現在漢族中國的特性來追溯歷史,就會把所有歷史都按照一個後設的目的,百川歸海似地歸入「中國」。
五、後現代歷史學:從民族國家拯救什麼歷史?
最後,挑戰還來自歐美的後現代歷史學。
後現代歷史學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對近代以來現代民族國家天然正當性的質疑。自從傅柯關於「權力」與「話語」的理論被普遍用於歷史,對於任何「天經地義」的論述的質疑,就有了相當鋒利的武器。而在關於民族國家方面,特別是自從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論問世以後,對於從現代民族國家反觀歷史的質疑,曾經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研究中的對於「國家」的誤解,這就是我們習慣於用現代國家來想像、理解和敘述古代國家。可是,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彷彿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歷史有時編整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系,因此,為了維護現代國家的「天經地義」,這種看起來很正當的歷史書寫,常常給我們帶來一些尷尬。
前面我們提到過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也許,正因為上述困惑,杜贊奇提出的「複線歷史」理論的確有其意義。不過,我以為,杜贊奇解構了以當然的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後設歷史,指出民族國家並不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而是本來有「爭議的偶然的民族建構」,所謂民族國家的歷史,其實是「虛假的同一性」,所以要從這種民族國家虛構的同一性中把歷史拯救出來,這當然很敏銳也很重要。但是,我們反過來提問,歷史學家是否要考慮與歐洲歷史不同的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中國尤其是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是「偶然的」和「爭議的」嗎?中國是一個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漸建立的民族國家嗎?
我們知道,後現代歷史學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與論據,一方面來自被瓦解和被分割的殖民地經驗,如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如非洲的大湖區的部族與國家,在這種已經被撕裂的族群和國家的重建中,確實有按照新的民族國家重新建構歷史的現象,但是,始終延續的中國卻並不是在近代才重構的新的民族國家;後現代歷史學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和依據,另一方面來自歐洲的近代歷史,我們知道,歐洲近代有民族和國家重構的普遍現象,因此霍布斯邦說「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相當晚近的新現象,而且還是源於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然而這裡所說的「人類歷史」其實只是歐洲歷史,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分裂,但因為一是有覆蓋更廣的「漢文化」,二是經歷了秦漢一統,習慣認同早期的「華夏」,三是中心和邊緣、「漢族」和「異族」有大小之差異,所以,政治、文化與傳統卻一直延續,所以既無所謂傳統「文藝的復興」,也無所謂「民族國家」的重建。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我有一個可能是很固執的觀念,即從歷史上看,具有邊界即有著明確領土、具有他者即構成了國際關係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後,由於逐漸強大的異族國家的擠壓,已經漸漸形成,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生活倫理的同一性又相當深入與普遍,政治管轄空間又十分明確,因此,中國民族國家的空間性和主體性,並不一定與西方所謂的「近代性」有關。在這樣的一個延續性大於斷裂性(與歐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籠罩下,中國的空間雖然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和穩定,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定、層層積累的傳統。而在宋代之後逐漸凸顯出來的以漢族區域為中心的國家領土與國家意識,則使得「民族國家」相對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認同的基礎。不僅如此,從唐宋以來一直由國家、中央精英和士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因此,這個幾乎不言而喻的「國家」反過來會成為漢族中國人對歷史回憶、論述空間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使他們一提起來就說歷史是「三代秦漢唐宋明清」,使他們一想起來就覺得應當遵循「三綱五常」的秩序,使他們習慣地把這些來自漢族文明的風俗當作區分自我和異族的標準。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很「特殊」,或者說,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途徑很「特殊」,在中國,至少從宋代起(這就是為什麼宋代是中國的「近世」),這個「中國」既具有安德森說的那種「傳統帝國式國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國家」的意味。作為一個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國家,漢族中國很早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空間的邊界,它甚至比那些較為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朝鮮)還清楚地認同這個空間作為民族國家的不言而喻,但是,作為一個邊緣相對模糊的「中華帝國」,它的身後又拖著漫長的「天下中央」、「無邊大國」的影子,使它總是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遍性的大帝國。
因此,對於複雜的中國,後現代歷史學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未必就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有合理性。
六、如何在中國歷史中理解歷史中國?
西川長夫曾經歸納道,現代國家作為國民國家,與傳統帝國的區別有五個方面,一是有明確的國境存在(國民國家以國境線劃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空間,而古代或中世國家雖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機構,但是沒有明確的劃定國家主權的國境),二是國家主權意識(國民國家的政治空間原則上就是國家主權的範圍,擁有國家自主權不容他國干涉的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理念),三是國民概念的形成與整合國民的意識形態支配,即以國家為空間單位的民族主義(不止是由憲法、民法與國籍法規定的國民,而且由愛國心、文化、歷史、神話等等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四是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空間的國家機構和制度(不僅僅是帝王或君主的權力),五是由各國構成的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的存在表明民族國家之主權獨立與空間有限性)。
這是一個日本學者的說法,但卻是以歐洲為思考背景的定義。然而,歐洲的定義並非來自亞洲資料而是來自歐洲歷史,尤其是近代歐洲的歷史,並不一定適用於東方諸國特別是中國。我一直很反對把本來是來自歐洲歷史的描述方式作為普遍歷史的統一尺度,儘管16世紀以後,歐洲的「國際秩序」和「近代性」逐漸取代東方「朝貢秩序」和「傳統性」,並獲得了「普遍性」,但是那種本來只是區域的經驗和規則,在解釋異地歷史時,總有一些圓枘方鑿之處。和歐洲不同,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心向邊緣瀰漫開來的,即使不說三代,從秦漢時代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語言文字、倫理風俗和政治制度就開始把民族在這個空間中逐漸固定下來,這與歐洲認為「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晚近的新現象」不同,因此,把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代的理論,並不符合中國歷史,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在中國,並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從而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
也許,很多人會想到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與「朝貢體制」,覺得古代中國以朝貢體制想像世界,並不曾清楚地意識到「國家」的邊界。但是,仔細考察可以知道,這種「天下」常常只是一種觀念或想像,並不一定是實際處理「中國」的國家與國際問題的制度或準則。這當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過程,如果簡單地說,大體上可以注意三點:首先,中國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與國家,由於在空間上的重疊,使得這一民族和國家的「邊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來。從宋代起,在遼夏金元壓迫下的勘界行為、海外貿易確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識與財富的自我與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戰之間的外交談判,已經使宋代中國很早就有了國境存在和國家主權的意識;其次,由於漢族同一性倫理的逐漸確立,宋代以來建立的歷史傳統、觀念形態和文化認同,已經很清楚地形成了漢族中國自我確認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謂「華夷」之辨、所謂「正統」之爭、所謂「遺民」意識,在宋代以後的形成,本身就是這種國家意識的產物;再次,從宋到清,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國際關係已經形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後,明清王朝、朝鮮、日本等國家之間的互相交涉,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國際」,只是這個「國際」原本是有一套秩序的,但是,後來卻在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衝擊下逐漸崩潰,終於被取代和遺忘而已。
很多人相信理論彷彿時裝,是越新越好,也有很多人總是把是否認同新理論與「政治正確」聯繫起來,當來自西方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研究新理論與新方法一經提出,曾經引起研究視野的變化,人們不僅對這種時尚的理論和方法相當贊許,而且常常不由自主地對堅持「國家」這一研究空間的歷史學有一種不恰當的鄙夷,覺得在今天仍然進行這種近乎「前近代」的研究方法,好像不僅「落後」,而且有「國家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嫌疑。可是,這種新理論總是來自歐美等西方世界,它的歷史依據和思想背景常常和我們不一樣,人們反過來可以追問的是,歐洲歷史可以這樣理解,非洲歷史可以這樣理解,亞洲和中國的歷史可以這樣理解嗎?特別是,當這個「國家」一旦形成「歷史」,當這個民族和國家不僅有一個共同的空間,而且有一個共同的生活倫理,有一個共同的政治體制,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習俗,這種倫理、體制和習俗又有了一個漫長的歷史傳統,那麼,這個傳統是否會使歷史敘述本身,很自然地環繞在一個社會、經濟、政治和觀念的共同體展開呢?漢族中國文明在很長歷史時期中的延續,是否使圍繞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敘述,比起另外選擇和組合的空間的歷史敘述,更加有明顯的內在脈絡呢?
結語 歷史、文化與政治:中國研究的三個向度
當然,我們應當承認,無論是「地方」或者「區域」的論述、「亞洲」或者「東亞」的論述,「台灣中心」或者「大汗之國」的論述,還是所謂「複線歷史」的論述,都給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多點透視」的新視角,使我們意識到,有關「中國」的歷史的複雜性和敘述的現實性,彷彿「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樣,讓我們這些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意識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接受這些挑戰和超越這些理論,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就是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的理論話題。在這樣一個既涉及理論又涉及歷史的領域中,我以為,有三點特別值得重視:
首先,在歷史意義上說,談論某某「國家」往往等於是在說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認,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反映的各個時代的中國。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反觀歷史中國,高句麗不必是「唐王朝管轄下的地方政權」,吐蕃也不在當時「中國(大唐帝國)版圖」,現在的東北、西藏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範圍內,但是,歷史上它們卻並不一定全是古代中國的領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簡單地以歷史中國來看待現代中國,不必覺得歷史上安南曾經內附、蒙古曾經由清帝國管轄、琉球曾經進貢,就覺得無法容忍和理解現代越南的獨立、外蒙古與內蒙古的分離,和琉球最後歸於日本,同樣,也不必因為原來曾經是高句麗的東北地區,現在歸入中國版圖,而覺得傷害了朝鮮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義上說,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它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尤其在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是相對清晰和穩定的,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後的中國,具有文化上的認同,也具有相對清晰的同一性,過分強調「解構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是不合理的,歷史上的文明推進和政治管理,使得這一以漢族為中心的文明空間和觀念世界,經由常識化、制度化和風俗化,逐漸從中心到邊緣,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層到下層擴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經漸漸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實際的,而不是「想像的」,所謂「想像的共同體」這種新理論的有效性,似乎在這裡至少要打折扣。
必須再次明確說明的是,從政治意義上說,「中國」常常不只是被等同於「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權是否可以等於「國家」,國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祖國」?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確的概念,一些政治認同常常會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同,甚至消泯人們的歷史認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過去,「朕即國家」的觀念曾經受到嚴厲的批判,人們也不再認為皇帝可以代表國家了,可是至今人們還不自覺地把政府當成了國家,把歷史形成的國家當成了天經地義需要忠誠的祖國,於是,現在很多誤會、敵意、偏見,就恰恰都來自這些並不明確的概念混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圖書 |
 |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1-03-2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52頁 / 22.7*15.2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3 |
中國歷史 |
二手書 |
$ 283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中國史地評論 |
$ 308 |
中國歷史 |
$ 308 |
人文歷史 |
$ 308 |
聯經出版 |
$ 332 |
科學科普 |
$ 343 |
中文書 |
$ 351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葛兆光,
一位身在「中國」的學人,
應當如何既恪守中國立場,又超越中國局限
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本書通過兩個歷史角度,
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關於「中國」的思想史,
一個是關於「中國」本身的學術史,
重新建構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論述。
「宅茲中國」用的是1963年在陜西寶雞發現的周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
「宅茲中國」可能指的是常被稱為「天之中」的洛陽。作者借它來象徵,不僅因為「中國」一詞最早在這裡出現,而且也因為「宅」字既像「定居」,又似「墨守」。
這新舊兩重意思,讓我們反省:什麼是中國?
1895年以後,
大清帝國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
原來動輒便可以「定之方中」(《詩經》)、自信「允執厥中」(《古文尚書》語)的天朝,
漸漸被整編進了「無處非中」(艾儒略語)、「亦中亦西」(朝鮮燕行使語)的世界,
便不得不面對諸如「亞洲」、「中國」和「世界」這樣一些觀念的衝擊。
爲什麽是「亞洲」?
究竟什麽是「中國」?
中國如何面對「世界」?
看似平常的常識背後,
潛伏著一個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本書討論「世界」、「東亞」與「中國」、「學術」與「政治」、「認同」與「拒斥」、「國別史」與「區域史」,雖然聚焦的是「中國」,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於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討論什麼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十七世紀以後,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到民族、國家和歷史;而民族、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又會涉及到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而周邊的話題,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歷史等問題。
葛兆光通過本書,提出了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應從有關「中國」、「亞洲」或者「世界」的認識的歷史資料,包括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歷史資料中出發,把問題放在思想史脈絡或學術史語境中去討論,而不應該是從來自西方的「理論預設」下去倒著看歷史,或者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證據」似的歷史論證。他提出了「從周邊看中國」,既包含了「中國觀」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也涉及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同時強調在歷史中研究「民族國家」,而不是把歷史從「民族國家」中拯救出來。
本書體系完整,一氣呵成,論證之細緻,說理之透徹,令讀者由衷敬佩。
作者簡介:
葛兆光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著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
章節試閱
引言:「中國」作為問題與作為問題的「中國」
也許,「中國」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冠以「中國」之名的著作,僅僅以歷史論著來說,就有種種中國通史、中國政治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等,在我們的課堂裡,也有著各式各樣以中國為單位的課程,像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文化等等。通常,這個「中國」從來都不是問題,大家習以為常地在各種論述裡面,使用著「中國」這一名詞,並把它作為文明的基礎單位和歷史的論述前提。
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質疑說,真的有這樣一個具有同一性的...
也許,「中國」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冠以「中國」之名的著作,僅僅以歷史論著來說,就有種種中國通史、中國政治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等,在我們的課堂裡,也有著各式各樣以中國為單位的課程,像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文化等等。通常,這個「中國」從來都不是問題,大家習以為常地在各種論述裡面,使用著「中國」這一名詞,並把它作為文明的基礎單位和歷史的論述前提。
可是如今有人竟然質疑說,真的有這樣一個具有同一性的...
»看全部
作者序
這本書討論的是「世界」、「東亞」與「中國」、「學術」與「政治」、「認同」與「拒斥」、「國別史」與「區域史」這樣一些大問題。最初,我並沒有想過要寫這麼小的一本書,來討論這麼大的一些問題。自從進入學術世界以來,我大都是在古文獻、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學史等古代中國的具體研究領域中打轉,儘管也不時關注西洋東洋的新說,偶爾涉足近世日本和朝鮮的歷史和文化,有時也忍不住發一些高屋建瓴的議論,但落筆成文的時候,總是覺得想要「言之成理」還是先要「持之有故」,沒有文獻支持好像理不直氣不壯,憑理論說大問題彷彿空口說白話...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緒說 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
引言:「中國」作爲問題與作爲問題的「中國」
一、從施堅雅到郝若貝:「區域研究」引出中國同一性質疑
二、從亞洲出發思考:在亞洲中消融的「中國」
三、臺灣的立場:同心圓理論
四、大汗之國:蒙元與滿清帝國對「中國」歷史的挑戰
五、後現代歷史學:從民族國家拯救什麽歷史?
六、如何在中國歷史中理解歷史中國?
結語:歷史、文化與政治,中國研究的三個向度
【附記一】
【附記二】
第一章:在歷史中理解中國
第一節:「中國」意...
緒說 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
引言:「中國」作爲問題與作爲問題的「中國」
一、從施堅雅到郝若貝:「區域研究」引出中國同一性質疑
二、從亞洲出發思考:在亞洲中消融的「中國」
三、臺灣的立場:同心圓理論
四、大汗之國:蒙元與滿清帝國對「中國」歷史的挑戰
五、後現代歷史學:從民族國家拯救什麽歷史?
六、如何在中國歷史中理解歷史中國?
結語:歷史、文化與政治,中國研究的三個向度
【附記一】
【附記二】
第一章:在歷史中理解中國
第一節:「中國」意...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葛兆光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3-29 ISBN/ISSN:978957083778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