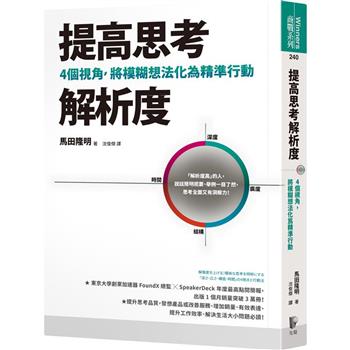此中譯本以權威之《集注版》為底本迻譯,
採英漢對照,
是中文世界裡第一次將鄧約翰《哀歌集》細譯詳注的成果。
譯文力圖保留原詩「英雄雙行體」之格律與形式,
每兩行換一韻,每行譯文控制在10-12個漢字。
注解亦廣納400年來各家之說,以求排除障礙,並補譯文未盡之處,
又時而輔以中國古典詩詞為注,以求中西互參。
本書有余光中教授的手書序文、
挪威音樂家Ketil Bjørnstad的譜曲CD及專文解說,
兩位大師皆為鄧約翰而特地動筆。
中、挪、英三巨人聚於一堂,美序、妙樂、奇詩融於一冊,藝術之臻已盡在其中。
※ 隨書附贈挪威大師畢揚斯達 (Ketil Bjørnstad)親自授權的四首鄧詩譜曲CD一張
《哀歌集》共收約20首各式情詩,屬鄧約翰少作,大多成於「林肯法學院」時期(1590年代)。本集風格多變,從戲謔怒罵的〈臂鐲〉,到憤恨難消的〈天生的憨呆〉,再進入情色不覊的〈床戰〉、〈勸女寬衣〉,及〈愛的巡航〉,令人目不暇給。此外,集中亦有成熟嫵媚的〈秋顏〉、搞怪胡鬧的〈變臉〉和〈香水〉、真情撼人的〈別離〉與〈臨別贈像〉,也有同性愛憐的〈薩孚致情人菲蘭妮絲〉,亦可見社會批判的〈不從〉和〈倫敦市民與其妻〉。《哀歌集》是一窺鄧詩多樣的萬花筒、開啟鄧詩廟堂的叩門磚,嚴厲如姜森(Jonson),也把〈臂鐲〉牢記在心,前吟後詠,並稱鄧氏在25歲前已寫下傳世之作,足堪世界級的大詩人。
作者簡介:
鄧約翰(John Donne, 1572-1631)
生於倫敦,長於天主教家庭,後入英國國教,仕途起少伏多,1621年始任聖保羅大教堂教長(Dean of St. Paul’s Cathedral)。文學上,鄧氏開英國17世紀「形上派詩人」(或「玄學派詩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之先河,詩風詭譎雄奇,意象新鮮突出。其情詩,捨蜜糖文字,取邏輯辯證,以剛勁代柔情,化學識為音韻,實為詩壇異種。20世紀初,受艾略特(T. S. Eliot)等人大力推崇,沉寂百年後,其大詩人之地位已再次確立。世俗詩歌外,其宗教哲理散文亦為瑰寶,名句no man is an island傳頌四百年,至今仍鏗鏘貫耳。鄧氏1631年3月31日死於教長任上,後葬於聖保羅大教堂,堂中一隅立有大理石雕像一尊。
譯者簡介:
曾建綱
祖籍湖南邵陽,1970年生於中壢,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1992)、政治大學英研所碩士(1995)、英國新堡大學英國文學博士(Newcastle University, 2007)。研究興趣多集中於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之詩歌,專攻John Donne及英詩中譯。酷愛電吉他、70年代搖滾樂與當代挪威音樂大師畢揚斯達(Ketil Bjørnstad)的作品。除參與各種學術活動外,亦是業餘吉他手及填詞人。任職文藻外語學院。
E-mail: chienkangtseng@gmail.com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513213114#!/
blog: http://chienkang.pixnet.net/blog
章節試閱
第1首 〈臂鐲〉
記女友遺失的手鏈,
並補償其全額損失。
並非因其色澤與妳髮色相仿
那般臂鐲妳大可給我戴上;
也非因臂鐲不時將妳手擁吻,
這等福氣它常享,我常飲恨,
不為其上的銘文,既酸又愚
說,這鏈不斷,此愛必不渝。
我弄丟了妳的七環之鏈
不嘆命苦,只嘆其價之不賤。
哦,十二枚天使金幣,此時尚無
劣等合金之酵母從中攙入;
尚未受到沾污,亦未偏離
造化最初創造他們之本意;
天使金幣,上天遣爾下凡支付
我一切所需,做我忠心導護
與新識結交,同強敵言息兵
於夙興夜寐之間,慰我心靈。
十二位頂罪天使,判官太可畏,
非要他們負累我犯之重罪?
真要遭銷毁,且投入熔爐
為他人之過失受此懲處。
我得不到救贖,痛苦亦無減輕
縱使他們在陰間大綁加火刑。
倘若他們只是法國錢幣,算了
多少法國佬,這民族天生沉痾
早已上身,他們且流落在我邦
何等憔悴,消瘦,跛腳,淪喪。
儘管法國君王篤信基督
其王冠仍從猶太之割禮習俗。
或如西班牙錢幣,流通無間
與其國王一般,隨處可見,
金幣待銼圓,如未成型之幼熊,
其威力更勝火砲,可守可攻,
粗工未磨圓,其型狀有如
大法師書中之多角星圖
其魔力足使大自然失調
一如這般金幣走旁門邪道;
如靈魂激發頭腦,雙腳,與心房
似河流,像血管,貫穿八方,
金幣以其詭詐亦遍布列國
縱絢爛之法蘭西亦分崩敗落,
而蘇格蘭,國不成國,乍榮乍亡
比利時十七邦,邦不成邦;
亦或正是此等唬人的金屬
本由大能術士取自各式礦物,
再以文火萃取其精髓而成,
是它使術士敗德、妄想、遭愚弄:
我不願以唾沬為術士滅火,
因他們身負駭人的罪過。
但要良善金幣平白送命?非要
我將平安,快活,衣食,盡拋?
多少雄心,受其撫育,都將消亡
連我那青壯活力與血氣方剛
也將消散,要愛,就看輕財富,
以免我財盡,妳的愛就此裹足:
哦,且找個大嗓門的宣事公差
即便錙銖之資也能令他開懷,
他可像惡魔嘶吼於大街小道
折煞拾獲者的良心,給他撞著。
占星師令人退壁,我且叩訪
他以精巧之天宮圖布滿紙張,
以諸多居室來劃分蒼穹
拿娼妓,竊賊,殺手,填塞其宮,
他雖居眾惡之首,唯居室擁擠,
連自己也苦無餘地可供身棲,
若他已黔驢技窮,曠日不尋,
說臂鐲難有下落,你也要甘心。
這等厄運你要由衷接納,
因為命運之聲靠他傳達。
妳說,哎,金幣價值絲毫不少
不過是改頭換面,打成了鏈條。
如首批沉淪天使,雖心術已偏,
智慧與知識仍存於其間;
正如天使金幣本當行善,供給
所需,如今勢必助長妳的傲氣。
沉淪天使形仍在,金幣已無軀;
形式決定內涵,金幣外形已去。
眼下且體恤天使金幣,其品級
遠非「道德」,「掌權」,與「權天使」可比。
但妳心堅意定,旨意必達,
我雖痛徹心扉,一如瑪利亞
將其獨子埋入飢腸之墳,
仍將金幣交付火窟,為道獻身。
良善之靈,你們賦萬物以生息,
良善神差,好消息經你們傳遞,
命中,你們本可歸屬一人
他將喜好與崇拜全給你們,
寧可勒緊褲帶,衣不覆體,
賠上性命,一個子也不能棄。
你們慘遭銷熔,罪由我擔
願少數倖存的同仁,常做我伴。
但,哦,可憎的拾獲者,我恨之深
竟對你的處境起了憐憫;
黃金在金屬中最具分量,
願最嚴厲之災禍降你身上。
活著時,腳上鐐,手上銬,頭上絞
先這般整肅,再大綁押送陰牢。
或是你收受敵國佣金,出賣
祖國,願你賣國不成,佣金沒來,
願你隨後俯身拾起之物,內附
毒物,迅速氣化直搗空空腦部;
願你詆毀之言,或某樣違禁品
一時不察手邊留,把大禍帶進:
願色慾之惡疾腐蝕你,久纏不放
要你情慾搔身,且無力行房。
願一切黃金引起的傷害,
所有惡魔苦思而得之禍災,
由富轉窮,老來淒涼又痛風
旅人、愛情與婚姻的苦痛
折磨你,並於你彌留之際
願你孳生的罪孽個個出席。
但我寬恕;以期正人君子悔悟:
黃金助元氣,且將金鏈歸主。
你若心有不甘,不願將它捨
黃金主強心,願它攻你心舍。
第1首 〈臂鐲〉
記女友遺失的手鏈,
並補償其全額損失。
並非因其色澤與妳髮色相仿
那般臂鐲妳大可給我戴上;
也非因臂鐲不時將妳手擁吻,
這等福氣它常享,我常飲恨,
不為其上的銘文,既酸又愚
說,這鏈不斷,此愛必不渝。
我弄丟了妳的七環之鏈
不嘆命苦,只嘆其價之不賤。
哦,十二枚天使金幣,此時尚無
劣等合金之酵母從中攙入;
尚未受到沾污,亦未偏離
造化最初創造他們之本意;
天使金幣,上天遣爾下凡支付
我一切所需,做我忠心導護
與新識結交,同強敵言息兵
於夙興夜寐之間,慰我心靈。
十二位頂罪天使,判...
推薦序
【中譯導讀】
「翻」來覆去、一「譯」孤行(文摘)
詩家總愛西崑好,
獨恨無人作鄭箋。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十二
一、鄧約翰:生平與家世
鄧約翰(John Donne, 1572-1631)生於倫敦麵包街(Bread Street),父親也叫約翰,母親伊麗莎白,母系的遠祖則是《烏托邦》(Utopia)的作者湯馬斯‧摩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鄧約翰13歲時與弟弟亨利入牛津大學的Hart Hall讀書,1592年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習法,期間,亨利因遭人密告在寢室窩藏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後病死於牢中。鄧約翰長於一個天主教家族,除了弟弟之外,舅舅賈斯柏也因耶穌會教士身分一度流亡法國,後死於那不勒斯。
1596年,他隨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遠征西班牙西南角的加地斯(Cadiz)。1597年,他又隨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出海,此次遠至北大西洋上的亞速群島(The Azores)。不久,他榮任掌璽大臣Sir Thomas Egerton的秘書。
1601年12月他與大臣喬治‧摩爾(Sir George More)的愛女Ann More秘密結婚,喬治爵士向Egerton施壓,讓鄧約翰丟了職,且於1602年2月入獄(Fleet prison),後獲釋。
鄧約翰於1621年11月22日被任命為聖保羅大教堂教長,直至1631年3月31日死於任上為止。他死時得年60,安葬於聖保羅大教堂。隔年,他的紀念雕像就已立於大教堂內,基座上還有自己寫的拉丁文墓誌銘。詩作於1633年由倫敦書商John Marriot與Richard Marriot出版,這是鄧詩第一次成書問世。
二、鄧約翰詩歌之品名及概述
鄧約翰的詩作共約180餘首,作品的體裁幾乎涵蓋當時流行者,分類整理如下:
(一)《短歌與十四行集》(Songs and Sonnets),共55首,作於1590-1611年間,多為愛情短詩,名作如The Flea等,皆出自此集。
(二)《祝婚曲》(Epithalamions),共三首,作於1592-1613年間,應酬作。
(三)《警句》(Epigrams),共約20首,最短2行,最長6行,諷刺味十足,創作年代約在1587-1595年間。
(四)《諷刺詩》(Satires),作於1593-1598年間,共5首。18世紀的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曾改寫其中兩首。
(五)《哀歌集》(Elegies),本譯注本之主角,共17-20首,詳解於後。
(六)《詩體書信》(Verse Letters),對象多為好友或贊助人,年代不一。
(七)《送葬詩與訃詩》(Epicedes and Obsequies),真正的「哀歌」,年代不一。
(八)《周年誌》(The First and Second Anniversaries),兩首,悼念早逝的少女Elizabeth Drury(1596-1610)。Elizabeth是要臣Sir Robert Drury(1577-1615)之女,Sir Robert則是鄧約翰的贊助人。
(九)《靈魂之進展》(The Progress of the Soul,又名Metempsychosis),作於1601,長520行,但未寫成,內容複雜難解。
(十)《十四行聖詩》(Divine Poems),共有22首十四行詩,其中有19首通稱the Holy Sonnets,名篇如〈死神別神氣〉(Death be not proud)。鄧約翰亦寫了一組宗教十四行詩,名為《冠冕》(La Corona),共7首。
三、《哀歌集》創作年代與現今版本
鄧約翰現存的「真跡」非常稀少,目前學術界所得之鄧式親筆手稿,在詩作中僅有一首「詩體書信」(A Letter to the Lady Carey, and Mrs. Essex Riche, From Amyens)。今日的鄧詩版本來源有二:17世紀古本與各家抄本。
目前學術界認為,《哀歌集》應寫於伊麗莎白一世晚期,時值1590年代,鄧約翰當時約20-30歲間。
根據《集注版》,共有17首詩列於《哀歌集》名下,共得1,014行。〈薩孚致情人菲蘭妮絲〉(Sapho to Philænis)有64行,但標題前並沒有冠以Elegy一字。《集注版》視〈茱莉亞〉(Iulia)與〈倫敦市民與其妻〉(A Tale of a Citizen and his Wife)兩首為「疑作」(Dubia)。因古本不易尋得,故譯者僅能單就二十世紀以來之主要版本,做一簡述:
(一)Grierson版(1912):詩全集,公認之權威版,採「舊式拼法」,Grierson可謂將鄧約翰帶進20世紀之第一人。
(二)Hayward版(1942):採「現代拼法」,收詩全集與散文選集(含部分書信),以1633年版為底本,全書近800頁,注解僅35頁。
(三)Gardner版(1965):採「舊式拼法」,收錄《哀歌集》與《短歌與十四行集》,全書370餘頁,注解占122頁。附多首樂譜,底本為1633年版,亦參照多組抄本。
(四)Shawcross版(1967):詩全集,並譯有鄧氏拉丁文詩。採「舊式拼法」,來源亦為1633及1635年版,並對照多種抄本,亦附多首樂譜。書後有詳盡的「校訂注記」及「鄧詩創作年份表」,為專家所引用之極佳版本。
(五)Smith版(1970):詩全集,以1633年版為依據,厚679頁,注解達315頁,是初學者最佳之「上手版」。1996版加附「進階書目」,另附「格律」,指導讀者精準「讀出」鄧詩。
(六)Craik版(1986):詩與散文之選集,僅選12首〈哀歌〉,編者並未點明所參考的底本,採「現代拼法」。注解詳實,有多處以現代英文「改寫」難句。書後「術語表」列舉261個鄧氏常用的字彙,並加以解釋,儼然一小型「鄧氏字庫」。全書299頁,注解87頁。
(七)Carey版(1990):詩全集、文選集,收15首〈哀歌〉。詩文皆按創作年代排序,採「現代拼法」,取材自1633年版。全書長488頁,注解僅59頁。
(八)Patrides版(初版1985,新版1994):詩全集,以1633及1635年版為底本,採「現代拼法」,注解詳盡,特點如下:其一,附1633年版的詩作排序表;其二,附波普改寫的鄧約翰二首《諷刺詩》;其三,厚達54頁、共1,034條的參考書目(至1991年),且按「體裁」分類,並以數字編號,專論《哀歌集》者共34條。序文長51頁,見解獨到。
(九)《集注版》(2000,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try of John Donne, 簡稱DV,主編是Gary A. Stringer):預計出版8大冊,是歷來規模最大的鄧詩編輯工程,也是此中文譯注本的主要依據。文本採「舊式拼法」,全書厚1,046頁,評注前後400年,是「美國現代語文學會」(MLA)認可的「學術版本」。《集注版》對每一首〈哀歌〉之評注皆劃分為Dates and Circumstances等項目,參考書目長27頁,700條。特色在於以手抄本為主要底本。本版共收17首「哀歌」,以數字加以編號,而視〈薩孚致情人菲蘭妮絲〉為第18首(但無「哀歌」字樣,亦無編號)。第1至12首哀歌大多以名為「威斯特麥蘭手抄本」(Westmoreland ms.)為底本,編者「推論」其中錯誤應是各種抄本中最少者。其餘的6首哀歌則取材自不同的手抄本。此外,編者更以碳14分析紙張上的浮水印,藉此精確定位其年代。本版已窮盡各式人文與科學的方法,確為近年來學界之典範。
(十)Dickson版(2007):詩選集,共選14首《哀歌集》詩作,其餘重要作品多半收錄。文本主要是依據《集注版》,採「現代拼法」。本版有240餘頁的評論,其中多半為新近研究。
(十一)Robbins版(2008):上、下兩巨冊,詩全集,僅將14首詩作列於《哀歌集》名下,
名為「愛情哀歌」(love-elegies)。注解詳盡,引用之詩文常異於前述各版,對鄧詩可能之 「源
頭」用力甚深,是英國方面近年來「鄧學」的大成。
四、「哀歌」一詞釋義
「哀歌」(elegy,希臘文elegeia,拉丁文elegia)是希臘詩歌的一種體裁,其主題多為悼念逝者。希臘的「哀歌」在形式上非常明確,通常以對句(couplet或distich)為一單位,前一行六音步(hexameter),後一行五音步(pentameter)。
「哀歌」傳到羅馬詩人的手中,其「六五對句」的形式不變,我們以馬羅的譯文為例,看看奧維德(Ovid, 43 BC-AD 17)在《戀歌集》(the Amores)中所說的「哀歌對句」為何:
Far hence, ye proud hexameters, remove,
…
While in unequal verse I sing my woes
遠離我,你這崇高的六音步詩行,走開,
……
我要以不公整的詩句唱出我的悲傷。(1.1.31, 34)
所謂「不公整」(unequal)指的是對句中的第二句,因為只有五個音步(foot),故與前一句的六音步比較起來顯得「不公整」。
形式上,羅馬人沿用希臘的「哀歌對句」,但在內容上,奧維德要跟史詩劃清界線。奧維德誓做「情人的導師」(praeceptor amoris),他的「哀歌」多遊走於飲食男女之間。當時,類似的愛情哀歌詩人(love elegist),在古羅馬尚有卡圖魯斯(Catullus)、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及提布魯斯(Tibullus)。
五、《哀歌集》的明顯風格
(一)模仿古羅馬哀歌詩人
羅馬的哀歌詩人是鄧氏最現成的描紅簿,這當中又以奧維德對他的影響最大。
「金錢與女人」之為題,常見於奧維德《戀歌集》,其中第1卷第8首,鴇母Dipsas就告誡旗下姑娘:
有人送好禮,荷馬妳也不用瞧
(聽我的)送禮你可得送得妙。
……
人長得俊,妳也別求和他共枕,
先看他的出手,妳好打起精神。 (1.8.61-62; 67-68)
鴇母的「處世之道」(worldly wisdom)亦可見於稍早的普羅佩提烏斯:
細看送上的黃金,別理送上黃金的手。
聆聽詩詞何所得,不過支字片語? (4.5.53-54)
提布魯斯也說:
時代墮落,只見鈔票不甩愛情:
但是鈔票罪惡何其多。 (2.3.39-40)
鄧約翰《哀歌集》第1首〈臂鐲〉就說到金錢在大都市裡之妙用:
天使金幣,上天遣爾下凡支付
我一切所需,做我忠心導護
與新識結交,同強敵息兵
於夙興夜寐之間,慰我心靈。 (13-16)
詩中人弄丟了女友的金鍊,心想一旦負擔賠償,則下場極為難堪:
多少雄心,受其撫育,都將消亡
我那青壯活力與血氣方剛
也將消散,要愛,就看輕財富,
以免我財盡,妳的愛就此裹足。 (51-54)
鄧約翰與大多數的「林肯法學院」學生一樣,並非富公子;馬斯頓就笑他們是「窮酸的法學院傢伙。」因此,創作愛情哀歌一來既是模仿奧維德,藉此顯露自己的文學品味與時尚,二來又可用文字反擊勢利眼,最後再刺刺倫敦拜金女,一舉三得。
其次,辛辣的「詛咒」也是鄧氏常常借力於羅馬詩人之處,其中有一種詛咒以仇敵之「死狀」及其過程為樂。卡圖魯斯在《詩集》(Carmina)第108首中,對柯米尼烏斯(Cominius)之死狀有以下的「期待」:
我深信,先是你的舌,善人之敵,
會被剪掉,再丟給餓鷹吃了;
黑喉烏鴉刨出你的雙眼,一口吞下,
腸子給狗吃,其餘的給狠吞。 (《詩集》,108.3-6)
在《哀歌集》第16首〈奉勸〉(The Expostulation)裡,詩人詛咒洩漏其戀情的密告者:
讓他遭天譴,竟把我愛情扼殺,
要他漂泊世間,如該隱受重罰,
淒慘至此,他卻不值絲毫同情;
為折騰他,叫「苦難」也變得機伶:
叫眾目閃避他,他亦閃躲眾目,
直到其身與惡名同般臭腐;
願他連三回不認主,毫無悔恨,
不再受人信任,縱他賭上靈魂;
受盡自我折磨,他一命嗚呼,
叫野狼扯其心,讓兀鷹刨眼珠,
五臟餵野豬,那舌尤其虛假
無所不洩,只管扔了給烏鴉,
他的腐屍,不讓其他畜生嚐,
獨給國王的獵犬久餐飽皮囊。 (39-52)
讀者可見,無論在受虐器官或施虐禽獸上,兩詩極為雷同。
另外,在拉丁哀歌中,讀者常見「被愛/愛神奴役」之說(servitium amoris, slavery of love),有時詩人臣服於天上的邱比特:
噢,這下慘了,邱比特箭無虛射,
我為愛灼熱,他統領我空洞心舍。(《戀歌集》,1.1.29-30)
詩人在細究其得失後,反倒甘為情擄:
確實,他以輕巧之箭將我刺傷,
愛神狠心,騷亂我受擄的心房。
我該屈從,還是抗拒讓他更猛,
稱臣吧,重負巧擔亦感輕鬆。(《戀歌集》,1.2.7-10)
鄧約翰顯然熟讀《戀歌集》,「被愛/愛神奴役」之說也現身於第5首〈不從〉(Oh let not me serve so)。單從標題中的「侍候」(serve)一字就可看出,他沿用此一主題;不同的是,標題中的not一字也表明,詩中人對「愛必為奴」有不同的見解。〈不從〉一詩說的是詩中人從前待女友如朝臣侍君王,後來查覺該女不貞,後悔昔日對她的服侍:
噢,別指望我侍候妳,如那般人
榮寵的煙霧令其忽飽忽昏;
拿宦達的言色來打腫充數;
可別把我列名妳的風流簿
如馬屁精崇拜偶像,他們不厭
以空邦來滿足君侯的稱銜,
儘管那兒不進貢,亦不稱臣。(1-7)
奧維德的「自我奴化」(self-enslavement),到了鄧氏之手竟成恨意四射的「懺情錄」,但愛意全消,且順道諷刺宮中朝臣,這些都是鄧式作風。
奧維德認為,愛情涉及諸多「技術層面」,非得有專人傳授。基於「愛情技術論」,奧維德寫了《愛之技藝》(Ars amatoria, The Art of Love),開班授徒。全書一開頭就確立「技術本位」的基調:
羅馬城裡要是有人不諳愛的技巧
則該細讀本書,讀後必然有一套。
搖櫓操帆把船駛,也得靠技術,
駕車要有方,談情也得有譜。(1.1.1-4)
隨後,他自命為師:
阿奇里斯受業於奇龍,我則是愛情的導師。(1.1.17)
「我則是愛情的導師」(ego sum praeceptor amoris)一副「專業」的自信,清楚點明了拉丁哀歌中「愛情導師」這個主題,詩人私設「愛情學院」。這個主題,也被鄧約翰直接模仿,第4首〈嫉妒〉就直接切入偷情的「技術面」:
我倆別再如昔,公然譏笑,
以輕蔑的暗語,他的醜貌;
也不要再與他同桌共進,
別因交談、碰觸,而面露姦淫。
在他鼓脹大腹,酒足飯飽
打鼾、倒坐,陷身柳條大椅之交,
我倆絕不再私占其床榻,
亦不如昔,嬉吻於其屋下。 (17-24)
詩中人以老手之姿,指導有夫之婦如何於夫婿在場之際,仍可與地下情人眉目傳情。
(二)第13首〈秋顏〉(The Autumnall)的「皺紋」隱喻
鄧約翰在《哀歌集》中運籌各類隱喻,下面就以第13首〈秋顏〉為例,說明鄧氏之為隱喻高手。
自第13行起至22行止,可見詩人運用空間、大小隱喻:
別把這皺紋當墓穴;若當真
則為愛神之墳,祂無別處安身。
但祂並非橫屍,而是端坐其中,
誓守此紋溝,一如隱者遁於洞,
此處,於她在世時,祂無意掘墳,
祂意在為她建碑,以念其芬。
儘管於巡行途中祂散居各處,
於此永居之所,愛神則永駐。
於此,黃昏常在,不見晌午暗夜,
於此,無酒池肉林,卻歡喜愉悅。(13-22)
這張「入秋和顏」最大的特徵落在皺紋上,因此詩人就以中年婦女的皺紋為此段隱喻的圓心,向外波及其他一連串的隱喻。單就象徵意義而論,皺紋象徵抽象的歲月在具象的肉體上留下的痕跡。此外,〈秋顏〉裡的皺紋亦可比喻人生中段的百般歷練。首先,他將焦點由第1-2行的臉孔轉到皺紋,將空間由整張臉濃縮至額頭上,因為皺紋是臉上最顯著的歲月之痕,並藉此引出下一個隱喻:皺紋之為或不為墓穴。在形象上,皺紋使臉上凹凸並存,一如原文graves一字,可指凹陷的墓穴,亦可指凸出的墳塚。如此,則「皺紋/墳墓」在形象上之對應構成了一個視覺隱喻。其次,就空間而論,此處將皺紋比做墳墓,明顯將前者放大,與前述「臉/皺紋」的縮小形成對比,但在性質上仍屬空間隱喻。
(三)性愛 + 宗教 + 煉金術 = ?:鄧約翰的「萬花筒詩學」(poetics of kaleidoscope)
性愛與宗教顯然隸屬兩個極端,然而,這種看似「異質組合」的手法,在藝術創作中卻屢見不鮮,鄧約翰也常在詩中鋪陳此法。若以第6首〈天生的憨呆〉(Natures Lay Ideott)為例,讀者可察覺此言不虛:
……我以情愛的細活
將妳精煉成極樂之天國。
我一手打造妳的本領與談吐,
妳的見識與生命樹亦我植入。(23-26)
原文中的字眼,如blissful、paradise、graces、creatures、knowledge、life’s tree等,皆常見於《聖經》中,特別是第26行的knowledge及life’s tree極易使人聯想到《創世記》中的「善惡知識樹」。第26行明顯在說:「是我〔詩中人〕啟迪了妳的性知識」,而life’s tree則是指詩中男子的陽具。
這種「性愛、宗教」互為表裡的現象,亦可採理論解釋。姜生在《考利傳》(Life of Cowley, 1779)中分析「機智」(wit)時,有以下論調:
姑且不論它〔機智〕對聽者產生之效應,機智……可視為一種「和諧之衝突」(discordia concors);此法或是結合各種互異的意象,或是發掘明顯相異之物中奇特的雷同。在這個定義之下的「機智」,他們〔指「形上派詩人」〕的作品中多得是。所謂機智,就是用硬扯的方法,將極為異質的想法統籌於一軛之下。如此一來,為了舉例、比較及引喻之故,自然法則與藝術被洗劫一空;此派作家的學問足以令人受教,其精妙亦使人驚喜;儘管讀來受益,讀者卻也常感吃力;同時,此法雖不時令人仰慕,但讀起來卻難使人愉悅。
所謂「和諧之衝突」原是拉丁文discordia concors,是指詩人於創作過程中,在「相沖」的事物中間,挖掘出相似點。以第6首〈天生的憨呆〉及第8首〈勸女寬衣〉為例,則可見其中揉合這異質的「性、教」二元。
文學、藝術與煉金術的結合亦可歸在姜生「異質想法」的條目下。鄧約翰不時提及煉金術,且以此來分析愛情,這就體現了姜生「異質想法」(煉金術 + 愛情)。第6首〈天生的憨呆〉第23-24行可見:
……我以情愛的細活
將妳精煉成極樂之天國。
「精煉」一詞為煉金術用語,是煉金過程中的一環。鄧約翰用此字來暗指詩中女主角原是粗劣的「卑金屬」(base metal),詩中男子則是煉金術土,將此村姑「提煉」成黃金般的貴婦。
譯者常將鄧約翰這種「性愛 + 宗教 + 鍊金術 + 各式學問」的詩法稱作「萬花筒詩學」:筒內裝有既定的材料,不增不減,但逆時針轉與順時針轉、角度的變化都會帶出全新的組合。
六、《哀歌集》之翻譯
(一)《哀歌集》與鄧詩的歐語版
目前譯者所知的鄧詩歐語版如下:
荷文版:譯者為Constantijn Huygens(1596-1687),Huygens身兼詩人與作曲家,與鄧約翰本人有私交,選譯了19首鄧詩,其中有數首選自《哀歌集》,這可能是鄧詩最早之歐語版本。
義文版:選譯15首《哀歌集》,請參考網站www.johndonne.org,或連至http://www.johndonne.org/docs/Elegie.pdf。
法文版:編譯者為André Souris,書題為Poemes de Donne, Herbert et Crashaw mis enmusique par leurs contemporains(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1)。
挪威文版:當代作曲家畢揚斯達(Ketil Bjørnstad)的專輯《恩典》(Grace, Universal, 2001)以鄧詩譜曲,原有挪威文之譯文,由畢揚斯達友人移譯,但未附於專輯內。
(二)《哀歌集》的中文版
傅浩於1999年出版了第一本鄧詩中譯集《艷情詩與神學詩》,其中收錄約百餘首鄧詩,是歷來最完備者。可惜,傅譯本身的漏洞不在少數。以下分成數點說明。
首先,傅浩的譯文,長短嚴重失控。《哀歌集》的原作以「英雄雙行體」寫成,除極少數破格外,每行皆為10個音節。以傅譯〈哀歌1:嫉妒〉(本書第4首〈嫉妒〉)之第29-30行為例,原文如下:
Into another country, and do it there,
We play’in, another house, what should we fear?
此兩行各有10個音節,相當工整,但請看傅浩的譯文:
放逐到另一個國家,而在那裡為所欲為似的
我們在另一所房屋裡玩樂,還有什麼可怕的?(傅浩,頁123)
這兩行譯文各長18個字,以18個漢字來對付10個音節,有散文化之嫌,只能算是「釋義」。傅浩失控的譯文同樣出現在〈哀歌2:字謎〉(本書第10首〈變臉〉)的第45行:
She, whose face, like clouds, turns the day to night,
她保衛著自己,她的臉彷彿烏雲,把白晝變成黑夜(傅譯,頁125)
她那張臉,如烏雲,令日頭黑沉(曾譯)
傅譯共用20個字,已是原文的兩倍,不論視覺或聽覺上,都不值得鼓勵。「她保衛著自己」五字,其實出現在原文的第43行:
So doth her face guard her…
此處傅浩把第43行的內容「拖曳」至第45行,顯然不妥。在〈哀歌4:香料〉(本書第3首〈香水〉)的第14行,傅浩的譯文卻又過短,僅得8字:
Still buried in her bed, yet will not die,
永遠躺著,卻不會死—— (傅譯,頁130)
雖不死,卻總是埋臥床榻 (曾譯)
「控制句長」,余光中教授說,乃「英詩中譯的起碼功夫。」因此,我以至多12個、至少10個漢字來對應原文之10個音節,可免譯文流於散文。
其次,傅浩的譯文多半向韻腳投降。以〈哀歌9:秋季的容顏〉(本書第13首〈秋顏〉)為例,原詩共50行,25韻,但傅譯僅得12韻。再以〈哀歌11:手鏈〉(本書第1首〈臂鐲〉)為例,原詩共114行,57韻,但傅譯僅得32韻,而且有兩組對句以同一字做韻腳:
它們所應滋養的許多希望都將死去。
如果你,愛人,撒手不管隨它們去。 (51-52)
你們命裡本可以屬於那麼一個
只熱愛和崇拜你們,一個。 (85-86)
以同一字互押,過分牽強。理想的譯文,應兼顧意義與形式。
在「達意」上,傅譯也多有爭議,以下以〈哀歌8:比較〉(本書第2首〈對照〉)為例,此詩開頭四行的原文如下:
As the sweet sweat of roses in a still,
As that which from chaf’d musk cat’s pores doth trill,
As the almighty balm of the’early east,
Such are the sweat drops on my mistress breast.
傅浩將這四行譯成:
好像蒸餾萃取的玫瑰花的芳香汗滴,
好像躁怒的麝香貓毛孔滲出的東西,
好像早晨東方的萬能的甘露,
這就是我女友酥胸上的汗珠。
「好像」兩字過分白話,在譯文中不妨適時地「古」一點。若以「如」替換「好像」,可更精練。其次,第1行the sweet sweat of roses中的sweat是指香精油(attar),故the sweet sweat of roses可譯成清楚的「玫瑰香精油」。傅譯「玫瑰花的芳香汗滴」一則詞義不明。
七、鄧詩之音樂與電影
「鄧學」同「莎學」或「紅學」一般,若非長期投入,恐難因一時之衝動可得。譯者建議,有志一窺鄧詩的初學者,不妨從相關的音樂與電影起步。
挪威當代鋼琴家、作曲家畢揚斯達,發行的專輯已超過40張(1973-2008)。在他眾多的唱片中,有三張專以鄧詩為題材,分別是《影子》(The Shadow)、《恩典》(Grace)和《光亮》(The Light: Songs of Love and Fear)。為方便讀者一探其內容梗概,此處我以《光亮》中的〈跳蚤〉(The Flea)為例,簡略分析畢揚斯達「含字吐樂」的法術。
他對〈跳蚤〉一詩的處理,仍以他見長的「五幕結構」為主體,我戲稱它為「畢式定理」:鋼琴前奏、(人聲)第1節詩、(人聲)第2節詩、中提琴間奏、(人聲)第3節詩。女中音Randi Stene以深鬱的嗓音唱出第1、2行詩:Mark but this flea, and mark in this / How little that which thou deny’st me is。畢揚斯達以「低盤」開出此曲,因為儘管全詩讀來語多戲謔,但開頭的對句卻也故作正經,因詩中人很嚴肅地要其女友「細看」且「思量」其拒絕求歡之不智。動詞 mark在首行中連用兩次,皆為重讀音,詩人一開頭就下如此「重手」,作曲家也以低沉對之。低沉外,女中音Stene在每一節的3、7、8行將聲音拉高。以第1節為例,第3行的first、第7行的woo及第8行的two如伏流沖向天際,Stene毫不吃力地就讓這幾個音符騰空俯看低盪的首行。這些關鍵音與詩行之出現,皆與跳蚤之動作有關:第3行的suck’d、第7行的enjoys與woo,以及第8行的pamper’d(過去分詞當形容詞用)與swells。這拔高的嗓音正是詩中人高分貝的「控訴」。
電影部分首推Mike Nichols執導的《心靈病房》(Wit, 2001),女主角兼編劇是英國女星艾瑪‧湯普生(Emma Thompson)。電影《心靈病房》由湯普生改編自同名的舞台劇劇本Wit,原作者是美國劇作家瑪格麗特‧艾德生(Margaret Edson)。
《心靈病房》主角貝玲教授(Prof. Vivian Bearing)專攻鄧約翰,其學術生涯正如日中天時,發現自己得了末期卵巢癌,立即接受化療。其間折磨,讓她不斷沉吟鄧約翰的〈死神別神氣〉(Death be not proud)。此刻,她必須借重詩中的哲理,好讓自己「準備」臨死。全片以〈死神別神氣〉為主軸,其中結尾兩行最令人深省:
One short sleepe past, we live eternally
And Death shal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l dy.
短淺的休眠一過,醒來既永存
屆時死神不復在,你必滅亡,死神。
貝玲教授死時的面容,除了面無鬍鬚外,酷似鄧氏生前請人為自己畫的遺像。原來,生與死,一如地圖的東與西,看似兩個極端,在地球儀上實為同一點。
八、結語:「但開風氣不為師」
「無論那一國文字,不是為了翻譯而存在的」,這是梁實秋的話。這個《哀歌集》中文譯注本是個全新嘗試,我身為譯注者,希望譯文能保留原著的風格與語言的力道。
最後一點補充。《集注版》中,〈茱莉亞〉算不上好詩,且作者不明,因此我並未將它譯出,純因考量鄧氏固有的風格與高標。
【中譯導讀】
「翻」來覆去、一「譯」孤行(文摘)
詩家總愛西崑好,
獨恨無人作鄭箋。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十二
一、鄧約翰:生平與家世
鄧約翰(John Donne, 1572-1631)生於倫敦麵包街(Bread Street),父親也叫約翰,母親伊麗莎白,母系的遠祖則是《烏托邦》(Utopia)的作者湯馬斯‧摩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鄧約翰13歲時與弟弟亨利入牛津大學的Hart Hall讀書,1592年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習法,期間,亨利因遭人密告在寢室窩藏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後病死於牢中。鄧約翰長於一個天主教家族,除...
目錄
目次
余光中推薦序
譯注者序
感謝
凡例
中譯導讀:「翻」來覆去、一「譯」孤行
第1首 〈臂鐲〉
第2首 〈對照〉
第3首 〈香水〉
第4首 〈嫉妒〉
第5首 〈不從〉
第6首 〈天生的憨呆〉
第7首 〈床戰〉
第8首 〈勸女寬衣〉
第9首 〈善變〉
第10首 〈變臉〉
第11首 〈勸愛人〉
第12首 〈臨別贈像〉
第13首 〈秋顏〉
第14首 〈愛的巡航〉
第15首 〈別離〉
第16首 〈奉勸〉
第17首 〈變換〉
〈薩孚致情人菲蘭妮絲〉
〈倫敦市民與其妻〉
引用及參考書目
鄧約翰大事年表
我如何替鄧詩譜曲:畢揚斯達談專輯唱片The Shadow
「手執胡本,口宣秦言」:翻譯在臺灣學術界的處境與展望
目次
余光中推薦序
譯注者序
感謝
凡例
中譯導讀:「翻」來覆去、一「譯」孤行
第1首 〈臂鐲〉
第2首 〈對照〉
第3首 〈香水〉
第4首 〈嫉妒〉
第5首 〈不從〉
第6首 〈天生的憨呆〉
第7首 〈床戰〉
第8首 〈勸女寬衣〉
第9首 〈善變〉
第10首 〈變臉〉
第11首 〈勸愛人〉
第12首 〈臨別贈像〉
第13首 〈秋顏〉
第14首 〈愛的巡航〉
第15首 〈別離〉
第16首 〈奉勸〉
第17首 〈變換〉
〈薩孚致情人菲蘭妮絲〉
〈倫敦市民與其妻〉
引用及參考書目
鄧約翰大事年表
我如何替鄧詩譜曲:畢揚斯達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