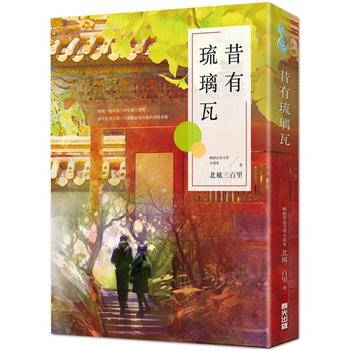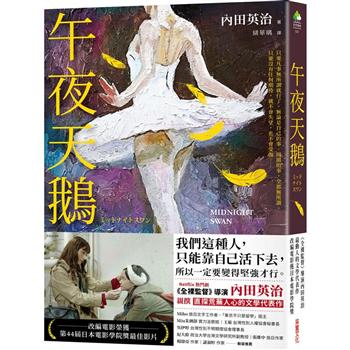編者序
楊煉
所有無人 回不去時回到故鄉
說出 說不出的恐懼
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
2010年一月四日是高行健七十歲生日。這一天,一群旅居海外的中文作家朋友、以及從不同國家專程飛來的譯者研究者們,假倫敦大學為他舉行慶賀活動。我的發言,以上面那三行詩開始。選擇它們,是因為這短短三行裡,涵括了當代中文作家從生存到寫作的精神里程。第一句濃縮流亡的兩個層次:當肉體回不去故鄉,精神上卻銜接了古往今來一切漂泊者。第二句把握思想和創作的內在動力:面對難以說出的恐懼,必須堅持去說,直到「立言「本身成為言之真意。第三句完成一種綜合:我們從現實到文學的四海漂泊,其實是一場不間斷的內心之旅。其景象,猶如一個人站在岸邊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出海。那個地平線上的遠方不在別處,正在他(她)的自我之內,把每天人生的風雲變幻,納入一個不停拓展的精神縱深。高行健的創作,令這一生命定位歷歷在目,同時也給當代中文文學指出了一種境界、一個高標。那只鳥,哪裡僅僅呻吟無根的苦楚?他的根──我們的根,從來帶在飛翔的體內,變被動的漂泊為主動的遨遊,盡情盡興無界無涯,堪稱逍遙,堪稱幸福!
給一位哪怕深受自己尊敬的作家朋友「祝壽」,總讓人略感局促。因為非親非故,加上大陸背景的影響,別人不說,自己也會覺得這個舉動帶點「官味兒」。即使為人、為文純正悠然如高行健,平時暢談人生創作,一無掛礙,但說到慶生,心中首先泛起一串問號:第一,為什麼慶?只因為他是首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如果那樣,他功已成名已就,何須吾等錦上添花?第二個問題接踵而來:怎麼慶?羅列履歷評價榮譽?來一番高雅的吹吹打打?倘如此,這「日子」有何與眾不同?我們慶祝它,除了對老高一人,有什麼更深刻廣闊的意義?
同樣刺激的提問是:高行健的七十歲生日,確實與眾不同。他這七十年,猶如一隻小船,鑽過的是中國歷史上、文化上最污濁血腥的驚濤駭浪。五四一聲「全盤西化」,開國人對自身傳統草率摒棄之先河。由蘇俄輸出的「國際共運」,又搶佔歷史進化的制高點,把任何獨立思考滌蕩殆盡。他降生的一九四零年,中日戰爭的烽煙裡,「救國」群情已常常混淆甚或覆蓋「救人」的冷靜(想想胡適先生關於「主義「和「問題「的微弱呼籲吧)。可歷史從不留下反悔的機會。他九歲時,一定也瞪著眼睛,跟在敲鑼打鼓的隊伍後面慶祝過「建國」。十九歲時,卻已經品嘗過出身異類和家有「右派」親屬的苦味。二十九歲,「文革」開場時像正劇、高潮中如喜劇、水落石出無非鬧劇,一場噩夢已經在書寫那部《一個人的聖經》了。八十年代大陸文化反思中,他用《彼岸》向自我深處追問;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發生,他用《逃亡》攥緊人生無路可逃的絕境。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受控的權貴市場經濟,迷惑國人也迷惑了世界。一個人得有怎樣的定力,才能不為這個詞義徹底分裂、且無視自相矛盾的世界所動,而堅持做一個「主動的他者」,拒絕任何意義上的隨波逐流?高行健的七十歲,確實值得慶賀。因為他用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在當今中國語境下,保持人格的完整、思想的健全是可能的。他這只小船,沒在激流中傾覆,在礁石上粉碎,或在安寧中腐朽,有幸運,更因為清醒。正是這自覺,不僅創造了璀璨的文字,更把他整個人生錘煉成一部傑作。由是,2010年一月四日,當朋友們聚集到倫敦,心中真正的慶典是:朝向一種獨立思想的禮敬。
基於這個想法,我們在倫敦舉行的,與其說是一次生日慶賀,不如說是一個「思想──藝術項目」:以高行健藝術為貫穿線索、對中國和人類當下處境深刻反思。我不得不說,我在世界上參加過無數文學節、藝術節,但這次活動,是令我最為心動的一次。請想像,華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七十誕辰,沒有中國的官方、沒有法國的官方──沒有任何官方──出面,就那麼幾個相識已久的老朋友,在幾乎全無經費(除了倫敦「華商報」、獨立中文筆會、作家張戎的合計一千來英鎊贊助)的情況下,純粹私人聯絡,私人出錢出力,「半地下」地把仍在聖誕假期宿醉未醒中的倫敦大學,變成了一個藝術盛會。我們是把它當作一首詩來構思、當作一件作品來精心完成的。從這裡饋集的節目資料可以看到:兩天的活動,既嚴肅又絢麗。倫敦大學校長的致辭,關於高行健思想藝術的專業研討會,朗誦他的最新劇本《夜間行歌》,高行健水墨繪畫大螢幕投影展,特別是集中放映三部高行健的電影:《洪荒之後》,《側影或影子》,《八月雪》(高行健編導、臺灣國家劇院演出的紀錄片),或許是世界上首次聚焦於他這一類相對不為人知、卻同樣特立獨行的創作。活動的地點,選在倫敦大學的布魯裡涅畫廊劇場,連續兩天,三百餘人的場地座無虛席。觀眾華洋參半,問答漢英疊加,台上台下一片交流互動。我的感慨也來自這裡:誰說這世界不需要思想?恰恰相反,在空話假話一統天下、思想極度匱乏的今天,每個人潛意識裡最為饑渴的正是思想。一枝藝術家的筆,只要能探入生命幽邃的痛處,就一定能喚起深藏的激情。倫敦曾經以「難懂「為由謝絕過老高劇本的劇場經理們,真該來這個活動看看,體會感動,也體會一點兒遺憾。
呈獻給讀者的這本書,就是上述「思想──藝術專案」的一個記錄。作為老高七十歲壽賀活動,這是一個小結。而作為在藝術家追問中必須反思自身的中國與世界,這只是一個開端。說到底,高行健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當代文化案例。他不僅僅在指點我們,一個中國藝術家的成功之途是什麼?相反,他恰恰在告誡,一個藝術家最根本的成功,正在於不追隨任何現成的「途徑」,無論那來自中國的物質誘惑、還是西方異國情調、「政治正確」的說辭。這本書裡的文章作者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歷和背景,但無論是和老高一樣經歷過文革又經歷過流亡的中文作家、或純然從藝術角度研究他」。真誠地面對內心,不虛張不矯飾。純粹地面對藝術,不奉迎不媚俗。藝術的境界,從來是藝術家自覺把自己寫至俗世「受不了」的地步,由此獲得的孤獨,才配得上高貴一詞。今天中國的文化生態,就是這樣一個「俗世」。但它遠比冷戰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嚴酷,因為口號之外,它更通過全球化的利益貪欲,腐蝕著脆弱的人性。直至把大多數「文學藝術」,也變成空洞現實的無聊裝飾。當我們的眼睛滑過那麼多詩歌、那麼多繪畫、那麼多「藝術」,心底卻冒出一句「可有可無」的評價,我們不得不自問:什麼是今天詩歌存在的理由?事實很簡單,比可見的經濟危機可怕得多的,是滲透世間人心的思想危機。利益硬通貨,在「共產黨」和資本主義間暢行無阻時,我們唯一能做的,或許只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一種個人的美學反抗。不過,可別把這理解為顧影自憐。此一舉,其實是找回了一個精神血緣,遠銜屈原、杜甫,近接卡夫卡、喬伊絲,並和五十年代蓬勃於臺灣的第一次中文大規模流亡文學一脈相承。一件件作品中,只見人性之高潔、詩歌之超越,而何哀之有?
真誠和純粹,換個古典的說法,就是「修身」。每一個人,經由生命和作品的本質合一,持續賦予中文傳統以高度創造性。高行健以自己的思想和創作,激起這長河中一朵璀璨的浪花。朋友們為他舉行的賀壽活動,在熱切肯定他所秉持的精神原則。現在,這本書出版,則是以另一個形式,讓這次思想和藝術的慶典,在讀者中延伸。此書最後截稿之際,高行健發來他今年赴台訪問的演講大綱,題為《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他開宗明義,指出這些思考,既源於文學,又遠不止於文學。而是通過對「深度」的追求,重建人和文的根本聯繫。「從二十世紀的陰影走出來,回到人和人性。」一語破的,他反思的是包含中國在內的一條歷史彎路:強迫人屈從某些大而空的觀念,經由切斷人性活生生的感受,而終於徹底取消了人。這解釋了站在二十世紀的終點,我們親見的人性和文化的滿目貧瘠。也因此,壯哉「走出陰影」!他這篇歸納一生思考的大綱,堪稱一篇最佳的「生日感言」,給朋友們一個熱情的回答。他證實了自己的話:「認識再認識,永無止境」。這正是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文化的生命本義。再一次,我想到他那首詩《逍遙如鳥》。茫茫天際,外在更內在,他說:「往昔的重負 / 一旦解除 / 自由便無所不在」。是的,正是這個詞:自由。浩浩七十年,雲煙掠過。心存此念,則永遠「僅僅是只鳥 / 迎風即起 / 率性而飛」。這樣的人,蒼老乎?青春乎?鬱鬱蔥蔥,下臨無地──
何其心熟乃爾!這不就是當代版的「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