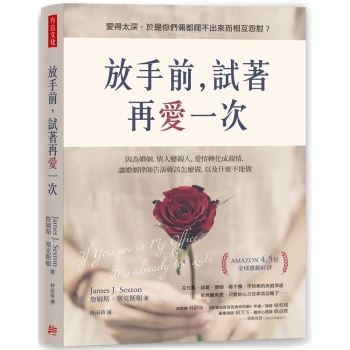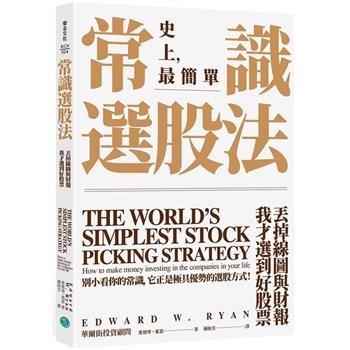序
我走過的路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餘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曆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余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