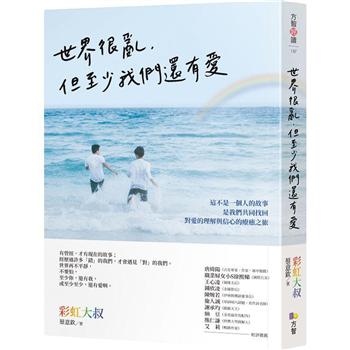第一章 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
引言
漢末佛教自天竺入華夏,是中國固有文明近代以前所接受的最主要異域文化。其影響被於藝苑,抒情傳統亦由此嬗變。觀察山水詩之發生,或許是探討嗣後詩學觀念一系列轉變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山水之在中國詩歌中出現,其意義遠非只是開拓一亞文類或新題材,而是使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性格也發生轉變。謝靈運(385-433)及其作品為佛教與山水詩關係之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此位歷代論者視為山水詩之不祧之祖的詩人,同時即湯用彤所謂南朝佛法之隆盛三時之一元嘉之世的佛學「巨子」,亦是饒宗頤所謂「第一個懂梵文的中國詩人」。然而,與王維(701-761)山水詩和禪宗的關係已成定論的情形不同,謝靈運的模山範水是否出自佛教影響?山水詩之發生,是否乃佛教東漸與中土文明合流的產物?對這些問題,學界遠未達致共識。近五十年來有關中國山水詩發展的主要論著有如下幾種:日本學者小尾郊一的《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1962)、臺灣學者王國瓔的《中國山水詩研究》(1985),德國學者顧彬(Wolfgang Kubin)的《光明的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1985)、中國大陸學者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1990),李文初等的《中國山水詩史》(1991)、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1993),美國學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中國上古和中古早期的風景鑒賞:山水詩的誕生》(1996),以及陶文鵬、韋鳳娟主編的《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2004)。上述專著對佛教思想催生山水詩發生這一問題多持漠然態度。只有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和陶、韋主編的《靈境詩心》和在談論山水詩起源時對此稍有涉及。前者在〈山水田園詩溯源〉一章中回顧了老庄心游自然和道教思想之後,以寥寥數語泛泛提到佛理和玄言結合。後者則只在<魏晉玄學的影響>為標題的一節中,提到佛教徒如玄學家一樣將山水當作領悟佛性的「言象」,并由宣宏佛教而強調形象。而在二書論述謝靈運的專章中,佛理的話題則不再出現。著名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ieville)的〈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山巒〉一文索性直接否認謝靈運山水詩與佛教的關聯。上述著作的一般思路為:追溯中國詩歌中自然描寫從《詩經》、《楚辭》到魏晉的發展,再從玄學和神仙家解釋山水詩在東晉出現的思想背景。然而,漠視了佛教這一重要因素,這一解釋裏所還原的歷史邏輯極不完整,且很難由此去探討中國詩歌審美性格所發生的變化。
這種情況在單篇論文中有所不同。美國著名漢學家馬瑞志(Richard Mather)的〈第5世紀詩人謝靈運的山水佛教〉可稱是本論題的篳路藍縷之作。該文發表於1958年,是筆者所見英語學界最早以佛教背景討論中國山水詩發生的研究論文。其貢獻是以謝靈運與幾位名僧如慧遠、曇隆的關係,以及謝氏有關佛學的論著證明這位詩人的大乘佛教信仰。尤有進者,該文以〈山居賦〉〈佛影銘〉為根據,提出了「山水佛教」(landscape Buddhism或可譯作風景佛教)這一頗具創意的命題。然而,作者卻并未進一步去論析此一「山水佛教」如何鑄造了謝靈運的藝術世界。馬瑞志的觀點直接影響了藝術史學者蘇珊•布什(Susan Bush)二十二年後發表的〈宗炳論山水畫與廬山『山水佛學』〉一文。此文借鑒日本學者的成果,集中討論見證東晉山水詩畫藝術萌生時期的兩篇重要文獻宗炳的〈畫山水序〉和廬山諸道人的〈遊石門詩序〉與大乘佛學的關係。象馬瑞志一樣,布什非常關注廬山佛影。然而,二人卻皆未曾探究此一佛影的特殊性與中土文化的關聯,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此外,布什論文的焦點是山水畫而非山水詩。馬瑞志還可能影響了佛諾德山(J.D.Frodsham)以翻譯為主的有關謝靈運的著作。
得益於東瀛深厚的佛學傳統,日本學者近年討論謝靈運山水詩的論文大都注意到其大乘佛教的背景。在這些論著中,志村良治1976年發表於《集刊東洋學》的〈謝靈運與宗炳──從〈畫山水序〉談起〉和〈山水詩轉變的契機──謝靈運的個案〉對本章而言,最爲重要。作者以〈遊石門詩序〉、宗炳〈畫山水序〉以及大謝的詩文為資料,考察了謝靈運與慧遠僧團的思想聯繫,從而确立了謝靈運山水詩的佛教背景。
中國大陸學界自八十年代後期起對佛學與山水詩發生的關係問題開始注意。比較重要的論文大致有張國星〈佛學與謝靈運的山水詩〉,錢志熙〈謝靈運《辨宗論》和山水詩〉,高華平〈佛理嬗變與文風趨新──兼論晉宋間山水文學興盛的原因〉,李炳海的〈慧遠的凈土信仰與謝靈運的山水詩〉,和普慧的〈大乘涅槃學與謝靈運的山水詩〉等等。多數文章是在謝靈運的山水之作中求證佛學的某個概念,它們可能給人啟發,但未能從更廣闊的背景去考察文化現象。
依上所述,現今對佛教與藝文中山水主題興起關係之研究,單篇論文尚限於各類個案──如支遁、慧遠僧團、宗炳──的相對孤立的研究,缺乏更恢宏的歷史目光。而能對山水詩發展作縱橫考察的大部論著,卻基本漠視佛教因素。這一對比說明了:佛教與藝文中山水主題興起之關係迄今僅為某些研究者的看法,而未成為學界之共識。而幾乎所有研究都未能回答:究竟大乘佛教、特別是慧遠僧團的佛學觀念,怎樣轉化為被歷代視為山水詩開山者謝靈運本人詩學觀念這一問題。
本章擬在中國文學諸自然觀念比較的視野裏,全面考察大乘佛教思想對山水詩興起之特殊意義。並循馬瑞志、布什、志村等學者的思路,探討佛教山林化運動在東南和中南的兩支──會稽支遁和廬山慧遠僧團的思想和著述與謝靈運山水詩的關聯。本章要證明的是:不止是大乘佛教,而是中土對大乘佛教某些觀念的容受,即基於中國文化對大乘的詮釋包括誤解,創造了「山水佛教」。廬山這一個案恰恰為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典型。而此「山水佛教」所賦予山水的獨特精神意義與其特別的「視感文化」(visual culture),皆為慧遠的兩位俗家弟子──畫家宗炳和詩人謝靈運所繼承,而在中古藝文領域大放異彩。本章的討論最後將進入謝詩的藝術層面,并視大謝所創造的某些藝術形式為其觀念的投射。因此,本章的關注將主要不是其作品內容的解讀,而是其詩學(poetics)觀念的問題,以及此一新的詩學觀念對确立中國山水詩傳統的意義何在。但作者應著重申明的是:本章並不是對山水詩發生學的全面探討,它注重的只是佛教在其中的貢獻,而無意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2卷):佛法與詩境的圖書 |
 |
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二卷:佛法與詩境 作者:蕭馳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07-1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76頁 / 21*14.8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85 |
古典文學 |
$ 435 |
華文文學研究 |
$ 435 |
佛教 |
$ 435 |
中國文學總論 |
$ 435 |
聯經出版 |
$ 468 |
小說/文學 |
$ 484 |
中文書 |
$ 484 |
Others |
$ 49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2卷):佛法與詩境
「境」的觀念如何逐漸進入中國詩和詩學?
「境」指示出詩中哪些新特徵?
「境」在詩學中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麽?
佛學的「境」如何與中國傳統融合?
蕭馳通過本書,帶您進入中國傳統詩
重新發現「詩境」
漢末佛教自天竺入華夏,影響被於藝苑,抒情傳統因之而嬗變。《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 第二卷:佛法與詩境》圍繞「詩境」,通過六個重要個案,歷史地考察了東晉至晚唐五代間抒情傳統與佛教的關聯。作者蕭馳論述了佛教觀念如何在文學中與中國傳統融合,又如何進入了詩和詩學的過程。展現了由來自內典之「境」所標示的中土文學匯入了新因素後的發展。其中主要有:確立非對待的、私情凈盡的無相自我,開發個人感覺中的獨得自識,以及截斷眾流之後生命景象的孤清夐絕。
作者簡介:
蕭馳
曾於中國大陸修讀中國文學批評史。1987年負笈北美。先後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修讀比較文學。1993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入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是濫觴北美而流播亞洲「中國抒情傳統」學術型態中重要學者,多年來致力其發展。所撰《中國抒情傳統》(臺北:允晨,1999)對此作初步理論思考,The Chinese Garden as the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密歇根大學,2001)探討此傳統在明清文人生活文化和近代小說世界中的延伸。與柯慶明合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上、下冊,臺大出版中心,2009)回顧此學術四十年發展。上世紀末以來,傾心研究中國主要思想背景下抒情傳統的觀念史。本書三卷:《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聖道與詩心》是歷時十二年研究的成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
引言
漢末佛教自天竺入華夏,是中國固有文明近代以前所接受的最主要異域文化。其影響被於藝苑,抒情傳統亦由此嬗變。觀察山水詩之發生,或許是探討嗣後詩學觀念一系列轉變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山水之在中國詩歌中出現,其意義遠非只是開拓一亞文類或新題材,而是使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性格也發生轉變。謝靈運(385-433)及其作品為佛教與山水詩關係之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此位歷代論者視為山水詩之不祧之祖的詩人,同時即湯用彤所謂南朝佛法之隆盛三時之一元嘉之世的佛學「巨子」,亦是饒...
引言
漢末佛教自天竺入華夏,是中國固有文明近代以前所接受的最主要異域文化。其影響被於藝苑,抒情傳統亦由此嬗變。觀察山水詩之發生,或許是探討嗣後詩學觀念一系列轉變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山水之在中國詩歌中出現,其意義遠非只是開拓一亞文類或新題材,而是使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性格也發生轉變。謝靈運(385-433)及其作品為佛教與山水詩關係之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此位歷代論者視為山水詩之不祧之祖的詩人,同時即湯用彤所謂南朝佛法之隆盛三時之一元嘉之世的佛學「巨子」,亦是饒...
»看全部
推薦序
本卷撰寫的目的,是嘗試歷史地考察東晉至晚唐五代之間中國詩學觀念與佛教的關聯。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而言,這無疑是最棘手、亦是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但這卻曾經是筆者多年來希圖迴避的問題。個中原因即如當世第一高僧印順大師所言:「佛法甚深」。佛法甚深而生年無幾,於是在不甚了了、卻無法不去面對之時,以幾句陳言去敷衍,就成爲包括筆者在内的許多人的應付之道。這樣做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在多年後令自己汗赧。因爲在學術上投機取巧決無勝算可言。
筆者真正決定正視此一問題,是在寫作《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一書(經...
筆者真正決定正視此一問題,是在寫作《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王夫之詩學發微》一書(經...
»看全部
目錄
導論
第一章: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
引言
一、佛教觀念中的「清曠山川」
二、佛教山林化與支遁的山林詩境
三、慧遠和廬山僧團的「山水佛教」
四、「山水佛教」廕庇下的大謝山水詩學
結語
第二章:如來清靜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
引言
一、輞川時期王維的禪學背景
二、王維晚期山水小品的獨特文類品質
三、王維禪學背景下的輞川詩境
結語
第三章: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
引言
一、境 對禪法意義之轉變與 詩境 的出現
二、皎然詩論之é詩境û觀平議
三、孤峰頂,秋月明 :晝公禪中境
結語
第四章:洪州...
第一章: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
引言
一、佛教觀念中的「清曠山川」
二、佛教山林化與支遁的山林詩境
三、慧遠和廬山僧團的「山水佛教」
四、「山水佛教」廕庇下的大謝山水詩學
結語
第二章:如來清靜禪與王維晚期山水小品
引言
一、輞川時期王維的禪學背景
二、王維晚期山水小品的獨特文類品質
三、王維禪學背景下的輞川詩境
結語
第三章: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
引言
一、境 對禪法意義之轉變與 詩境 的出現
二、皎然詩論之é詩境û觀平議
三、孤峰頂,秋月明 :晝公禪中境
結語
第四章:洪州...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蕭馳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7-19 ISBN/ISSN:97895708403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7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