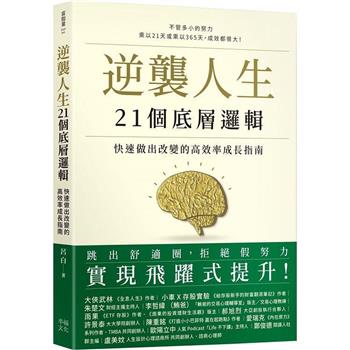如果要定義什麼是離死亡最遙遠的事,那會是什麼?
在生與死之間,距離究竟有多遠?
2013年台北國際書展訪台作家
芬蘭紀錄片導演、小說家 艾琳娜.希沃寧
長期關注非洲議題,挖掘生命勇氣與愛
摸索存在契機的深情之作
一場心繫非洲女童的愛與冒險──
她不僅描寫克服死亡恐懼,也書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與重。
《離死亡最遙遠》是一本關於人們如何被過去記憶啃蝕的小說,敘述著惡夢般的殘酷現實,破碎不堪的夢想,以及一種近乎救贖般,想要彌補過去錯誤的渴望。小說故事地點發生在作者最熱愛的非洲國家之一尚比亞,小說也是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完成。
艾琳娜.希沃寧以跨越國境的生動描寫,刻畫人尋找活下去的勇氣與力量,一個渴求心靈慰藉與新生的溫暖故事──
「死亡的恐懼,像所有偉大的情感般,會隨時間逝去而被淡忘。」
「最使我們著迷的事物,往往會使我們犯下最愚蠢的錯誤。那樣的事往往都存在著死亡的陷阱。」
生命的脆弱總是與恐懼緊緊牽連著,痛苦總是清楚的提醒我們,健康,青春,慾望,身體等種種的一切,都在等待著我們,當然也包括死亡。
事實上我們永遠不是存在我們身處的現在。躺在柏油地上女孩,即使有更多晾衣架圍繞著她自己,自己的存在清楚的與充滿香氣的香草共存著,但似乎也得同時經歷那些分解過的葉子,所散發出來的死亡氣味……
2009年,一個遠離歐洲社會與破碎婚姻的芬蘭男子保羅,離開芬蘭,再度回到他曾居住過、艷陽高照的非洲國度,想在此結束生命。
艾絲特,尚比亞女子,在聯合國國際救援組織工作,她摯愛的男人,因捲入暴動昏迷至今,眼見尚比亞的孩子經常得面臨悲慘的遭遇,她希望奮力守護好友貝西的女兒蘇珊順利長大。故事在兩人的觀點中穿梭鋪陳……
多年前他們在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遇害的地點相遇,當時他們都希望可以徹底的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不見──面對死亡的態度從一種渴求,到一種逃離……
遠離死亡只是浪漫的想法,還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孤獨的人生能否尋得慰藉與依靠?
作者簡介
艾琳娜.希沃寧(Elina Hirvonen)
生於一九七五年,芬蘭赫爾辛基新銳作家,紀錄片電影導演,電視節目主持人,新聞工作者,同時也非常熱愛旅行,足跡踏遍三十餘國。作品中常見對於非洲文化與歷史,移民議題,以及非洲與歐洲不同種族間的關係等的關注。
第一本小說《當我遺忘時》(Etta han muistaisi saman, 2005)曾獲芬蘭最大文學獎項「芬蘭文學獎」(Finlandia Palkinto)的提名;紀錄片作品《天堂樂園:在這個世界的三段旅行》(Paratiisi: kolme matkaa tassa maailmassa, 2007)也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
譯者簡介
陳(糸秀)媛
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曾於荷蘭萊頓大學及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從事文學及電影相關研究。目前為芬蘭土爾庫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班學生,論文主要關注喬伊斯之尤利西斯與電影美學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