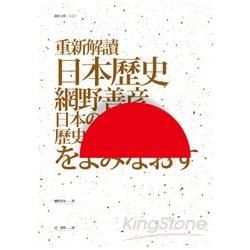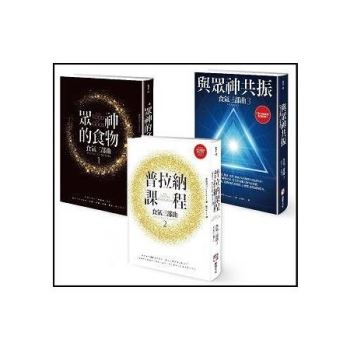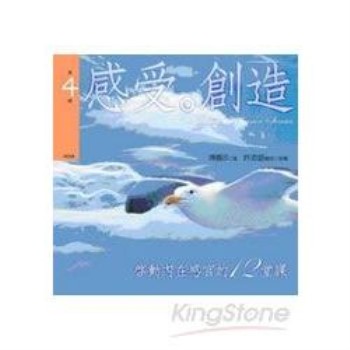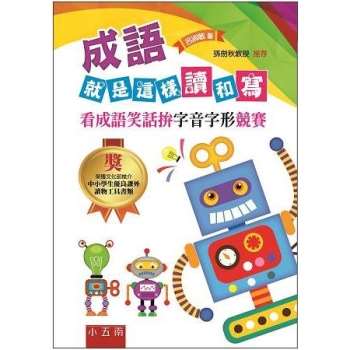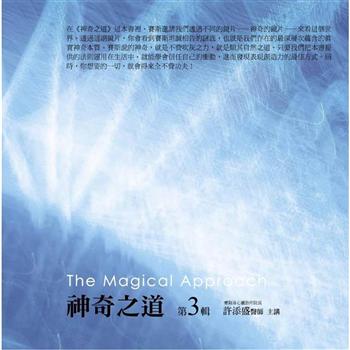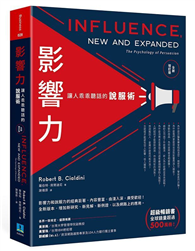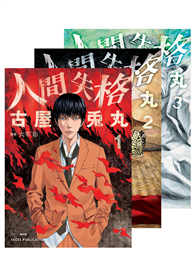前言
之一
我在短期大學任教已經接近十年了,這期間經常碰到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事。雖然我也知道學生和我大約有四十歲的年齡差異,不過還是不時會感受到他們的基本生活型態和我完全不同。例如這兩、三年來,我使用宮本常一所著的《被遺忘的日本人》(『忘□□□□日本人』,岩波文庫叢書)一書作為討論課的課堂教材,在課堂上和學生一起讀這本書時,常常會感到我這個世代和二十歲左右學生的差異──差異的產生與其說是知識上的歧異,不如說是我們兩者的生活本身迥異,因此很多對事物的基本看法都不相同。
如果要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譬如書中提到「苗床」(培育植物秧苗的小塊土地,待秧苗成長後再移植於大田)這個詞。我以為「苗床」當然是大家所熟知的概念,但竟然沒有一個學生知道。
另外書中還出現「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一詞,也沒有任何學生知道。他們也沒有看過牛或馬在工作的姿態。牛可能頂多只看過擠牛奶的乳牛、荷蘭乳牛等,馬則只有看過賽馬等供人騎乘的馬。
宮本書中也提到了「麻瘋病」或「麻風病」這幾個詞。甚至直接使用「韓森氏病」一詞,但學生們對這個病也毫無概念。即使換成「癩病」,他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疾病。如果說到愛滋病,當然大家都很瞭解,但是癩病這個詞就鮮少人知,也不知道它是一種什麼病。現在的學生不知道在世界上,甚至就在日本,還有人正深受這種疾病所苦,或因得這種病伴隨而來的歧視所苦。因為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我才被迫瞭解到:日本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在很多方面都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一般來說,現代人的技術較諸以往已發生相當大的質變。人類由大自然中開發出足以毀滅人類自己的力量,這件事至關重大,而且毫無疑問是人類史的問題,但是還不僅如此而已。特別是如果從日本社會的角度來看,有一些概念從江戶時代開始,到明治、大正、甚至是我們這輩還年輕的戰後時期,都被認為是普通的常識,但現在卻幾乎變得完全不適用,這些現在正在發生的變化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們也可以用廁所為例,現在的年輕一輩大概已經很難想像廁所的惡臭,但我們人小時候應該都有「覺得去廁所很恐怖」的經驗,現在一般家中幾乎沒有陰暗的角落,因此年輕世代沒有體驗過我們對黑暗的恐懼。現今這個時代反而會對其他形式的東西──例如剛才舉的愛滋病的例子──感到強烈的恐懼。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更深入思考這種變化的意義。
我們習慣將過去的日本歷史依時代區分為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與近代,從中掌握時代的變化,這是基本的架構,但就像剛才提到的,如果考量到人類和自然的關連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再沿襲以往對歷史的時代區分方法,很可能會碰到一些無法說明的變化,如果忽略這點,我們將很難真正掌握歷史。
在理解日本社會的歷史時,我們也必須想想是否有別於用原始、古代、中世等時代區分的方式,在目前為止都是用社會構成史的觀點加以區分,但相對於此,也有被稱為是民族史或文明史等視角的區分方式,姑且不論這是否為好的表現方式,但是如同前文所說,既然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聯已發生重大轉變,對日本社會的歷史加以區分也絕對有其必要。
那麼,因為現在的轉變期而逐漸被遺忘的社會──也就是那個和漸漸變得過時或消失的我們幼時經驗相連在一起的社會,究竟可以往回追溯到那一個時代呢?至今為止的研究常識都認為可以追溯到室町時代左右。換句話說,大約在十四世紀時發生了南北朝(日本的南北朝時代,發生於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年,當時日本同時出現南、北兩個天皇,之前為鎌倉時代,之後為室町時代)動亂,歷經此次大變動之後的時代和十三世紀之前的局勢有非常大的不同。我們這個世代的常識大致可以理解十五世紀之後的社會狀態,但是我們的常識卻好像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十三世紀之前的問題,那對我們來說幾乎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也就是說,和現在的變化同等重要的轉變發生在十四世紀的南北朝動亂時期,如果把該次轉換時期的意義和現在新的轉換時期相比擬,重新思考它的意義,應該會對從今往後人類應該選擇的道路、日本的文化或社會問題都有新的啟發。因此,本書想要討論這個十四世紀的變動時期,具體而言究竟是用怎樣的形式展現出來的?
之二
最近,關於「日本人是什麼」這個問題,不論在日本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討論。例如,一九九三年九月在澳洲的坎培拉召開了由澳洲國立大學主辦的「鐙.帆.鋤」國際研討會。除了澳洲學者之外,還有相當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印尼、韓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學者參加,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出席者大約有四十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日文研」這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大家各自針對日本人的認同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我不太會聽或說英文,所以是用日文報告,最後大家討論了些什麼,我也不太了解,不過從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報告開始,最後一直到日本軍隊中的慰安婦問題為止,有各種各類的問題都被提出來討論。特別是好像針對日本軍人的強暴問題,引發了很激烈的辯論。
其實,如果從分配給我的題目是「天皇.米.百姓」這件事來看,大概可以知道對於歐美人來說,他們所關心的是和自己很不一樣的日本人的特質究竟是什麼,但如果是印尼人或韓國人,就可以深切感覺到他們對於日本人不好的一面,以及因為這種不好的一面而造成的日本軍隊的殘暴行為(例如從軍慰安婦、強暴問題等),想要嚴厲追究。所以,其實這個研討會也讓我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很多刺激。
《年鑑(Annales)》這本著名的法國歷史雜誌也在一九九五年首次刊登了日本特集,總之可以知道,外國人其實對日本有很高的興趣。這也代表在這個時代,我們自己對於日本人究竟是什麼,也需要認真考慮一下,我們之前可能都不需要面對的敏感問題,之後也一定會不斷地朝我們迎面而來。不過就算不是這樣,我在這時候也深深感覺到,日本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和社會,其實都沒有辦法正確地掌握。
當然,其實對於自己的社會和歷史,日本人的觀點也多少發生了變化,像在前文所提到的澳洲研討會中,從彼此的討論中也可以感覺到這種變化。只不過,一般來說,日本是島國,被周圍孤立起來,是一個封閉性的社會,單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知道它不太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因此足以蘊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化。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因為這樣,所以日本的文化對於外國人來說十分難以理解,從這個觀點來看,就會覺得日本的社會十分特殊,這種觀點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日本人之間的主流想法。
而這種文化的支持力量就是以水田為中心的農業,從彌生文化進入日本列島之後,一直到江戶時代為止,日本的社會基本上都是農業社會,到明治之後才轉型為工業社會,甚至是在高度成長期(指日本的經濟規模大幅度成長的時期,對於日本高度成長時期有幾個不同的說法,不過大致是指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間)之後,才進一步進入真的工業社會。
一般的日本人都認為:因為日本人是在這樣的島國生活,所以才擁有均質、齊一的語言和文化,日本的社會也是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則是以水田為中心,並且以米為主食;用這種脈絡養成的日本人在日本列島中慢慢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即使是明治之後一直到現在的政治體系,也都是用這樣的想法在掌握日本社會,經濟政策也是這樣。而像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這些處理人類問題的學問,大概也都沒有逸脫這個常識的大框架。
但是,這種對於日本社會的理解,真的是正確的嗎?關於這點,我從以前就一直感到疑問,而且也用各種形式的發言提出疑問,下文想要集中在幾個問題點上,對日本的社會重新加以思考。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從「日本社會真的是農業社會嗎?」開始討論。
後記
之一
從很久以前開始,就有許多人對我說,應該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對年輕一輩說明,而早在三年多之前,「□□□□□□□□□□□」(筑摩書房精選叢書)就已經開始跟我邀稿。
不過,我現在在短期大學教授一般教育(相對於「專門教育」而言,約相當於通識課程),平常上課也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但是好像很少真正成功地感到學生們專心在聽我講課。只是在短大的課程結束之後,偶爾還是會有學生跟我說:他們聽到了和在高中學到的不同歷史,所以感到很有趣,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敢寫出這本書,向年輕一輩說說我的想法。
如果有人讀了這本書,因此對歷史稍感興趣,或是多多少少感到歷史和現在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我的書只增加了一小部分這種人,我還是會感到莫大的幸福。也請大家對我不吝賜教。正是因為有這些批評和感想,讓我一步步地更加努力,才能寫出更淺顯易懂、立場更堅強的著述。
這本書讓我有五次機會可以和筑摩書房的員工對談,而有了大幅度的修正。除此之外,本書的編輯、插圖等也承蒙筑摩書房的各位鼎力相助,在此深表謝忱。
之二
我在今年三月辭去了任教十五年的神奈川大學短期大學部,轉任該大學的特任教授,而用這種「退隱」的身分出現,倏忽間已經接近一年了。
辭去短大教職的時候,和《重讀日本歷史》出版的時候比起來,我已經或多或少比較習慣和年輕人交談了,但是從反面來說,也常常感到學生們和我這個老人的基本生活體驗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例如學生們完全不瞭解木炭的相關知識,也不知道「石」是什麼單位。反過來說,我對於電腦也完全沒概念。
因為這充分展現出現在的社會轉變是多麼劇烈,所以在授課結束時,其實我對於自己講授的內容到底被學生吸收了多少,常常感到很沒有把握。不過,由測驗的結果可以知道,學生對於其中幾個主題的確有某程度的反應。
本書也是立於這些細微的經驗之上,與前一本書相同,承蒙筑摩書房的各位職員們聚集在一起,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到九四年的五月之間舉辦了四次座談,將這些內容經過整理再匯整出書。
不過在完成之後,我又覺得在不同地方所寫的、所說的好像有許多重複。對於這點,我打從心裡感到十分慚愧,可是這本書的用意是要針對至今為止都被認為是「常識」的觀念,也就是廣泛被承認的日本史圖像、對日本社會的印象,指出其中根深蒂固的重大偏差或明顯的誤解,並加以矯正,讓我們對現代的社會不至於再有誤解,為解此當務之急,雖然我知道一定會有人批評本書的內容過多重複,但我仍在有此覺悟的前提之下,決心出版此書。
如果有人在讀完本書之後,願意拋棄大家都熟知的「常識」,用自己的想法,重新思考日本社會的實際狀態,只要有一位年輕人願意這麼做的話,那就是我莫大的榮幸了。
與前書相同,本書可以出版,也是承蒙編輯部的土器屋泰子小姐的辛勤工作,土器屋小姐一直鼓勵我出版這本書,而且在編輯方面也給予我許多幫助,在此深表謝忱,而對於其他在上班時間仍然撥冗與我座談、給予激勵的筑摩書房的其他員工,在此也一併致上最深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