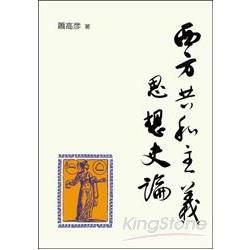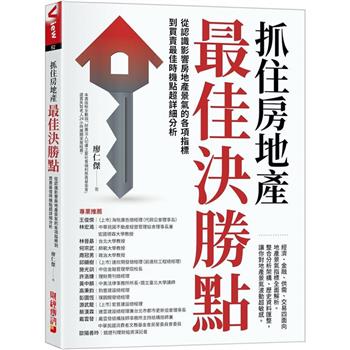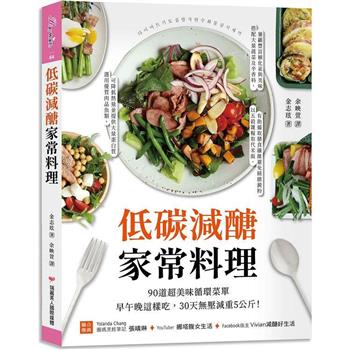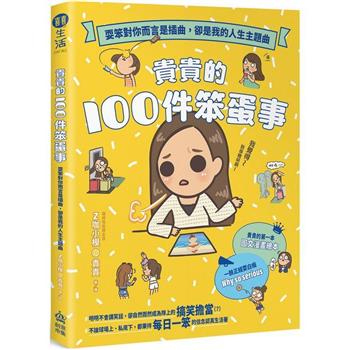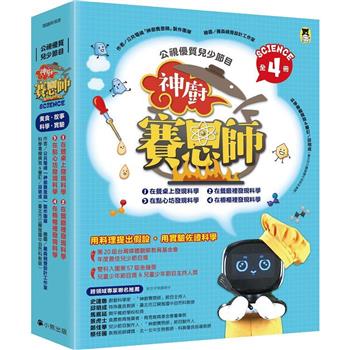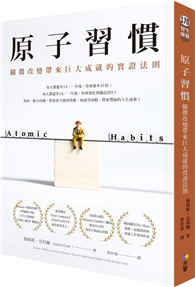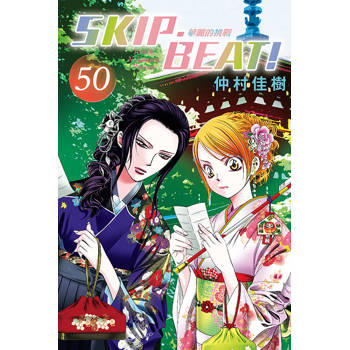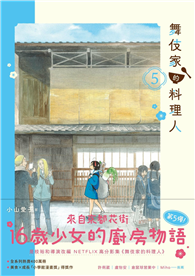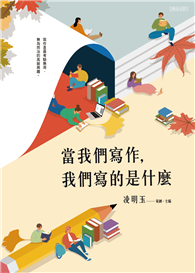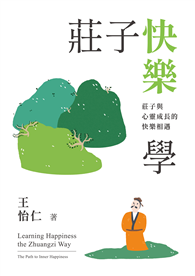自序(節錄)
本書的主旨是對西方共和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史典範,提出政治哲學的分析。所謂的「典範」(paradigm)意指大型的觀念叢結(complex of ideas),源於思想家對形上學、倫理觀、人性論、行動理論乃至政治制度等議題深入探究後,所產生的巨型論述系統。它們會形成核心的觀念詞彙以及政治想像,並構成政治場域的意義脈絡。雖然西方的政治思想流派繁多,但真正具有「典範」意義的,並不多見。
史學家波考克在其振興當代共和主義學術研究的鉅著《馬基維利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一書的第一部份,以宏觀的視野分析中古後期政治論述的競爭典範,作為理解共和主義興起的背景。他指出,在公民人文主義勃興之前,中古後期西方的兩大政治論述典範,其一以「習俗」(custom),另一則以「神恩」(providence)為核心。所謂的習俗,其實便是社會學家韋伯所提出的傳統統治形態,中古後期以普通法為最重要的代表。政治社會習俗之所以被接受並服從,在於其為傳之久遠的祖宗常法。而由於長期以來對於特殊環境與問題的回應,使得這些習俗累積了無數代人們的經驗,並形成了實踐智慧的來源。另一個政治論述典範,則是以救贖為核心的基督教,基於上帝統治世界的神恩概念而開展出的神學政治論。基督教雖然以上帝之城的終極降臨為唯一關懷,但由於上帝支配世界,所以俗世的事件仍然會以上帝的意志為基礎,而開展出一種此世時間的序列。也就是說,基督教以彼世的救贖角度,建構了一種具有連貫意義的俗世史(saeculum)。
共和主義者在現代初期所帶來的人文主義轉向,將西方人的注意力自傳統習俗或神學的俗世史,轉而關注此世政治社會自身的獨特意義。關於共和主義的最初發展,波考克認為可追溯到西元1400年前後,米蘭大公維斯康地(Giangaleazzo Visconti)家族勢力急速擴張進入托斯卡尼區域,對佛羅倫斯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威脅,並運用凱撒主義與王權觀點來證成其政治擴張。與之對抗的佛羅倫斯人文主義者遂重新發現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的價值,建構行動生活(vita activa)的政治理想,倡議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公民身份、公民德行以及政治參與等理想,以共和價值來對抗維斯康地家族的霸權論述,促成了共和意識的萌芽。承繼此公民人文主義傳統,馬基維利建構了第一個現代共和主義體系,之後通過英國內戰以及美國、法國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逐漸產生了與古典時期完全不同的現代共和主義論述,基本精神在於強調公民參與對於政治價值創新以及秩序興革的重要性。波考克認為,在現代政治思想中,能夠與共和主義相抗衡的唯一典範,只有後起的自由主義。
本書以共和主義思想家理論體系的闡釋為主軸,並且輔以思想史脈絡以及時代問題意識背景。對於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全書分析了亞里斯多德、西塞羅、波利比烏斯、馬基維利、孟德斯鳩、盧梭、美國與法國大革命的共和論述、康德與黑格爾,以及當代共和主義者鄂蘭與史金納的理論,最後並以共和主義角度剖析台灣的憲法政治。大部分篇章雖曾陸續發表於專業的學術期刊,但在本次集結成書的過程中,筆者除了對歷年的論述去蕪存菁、匡漏補遺,並特別為本書撰寫第一、二章,以強化古典共和主義的比重。另外,也對比較早期所撰有關黑格爾的兩篇論文大幅增刪,合併成第九章,以期符合共和主義的詮釋觀點。〈導論〉則對全書的基本論旨提出提綱挈領的說明。在書末參考書目中附有相關論文的原始出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比較。
學術研究有多種可能取向,筆者個人則以耙梳政治思想的內在理路為職志。所以,相較於一般歷史敘述,本書對於個別思想家將提出篇幅較長的理論分析。這或許是筆者早期研究黑格爾思想所形成的習慣。對黑格爾而言,思想之目的是將經驗系統化,是以,後起的哲學家需要對之前的思想掌握其整體精義,方能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哲學體系。筆者雖注重經典作品的義理闡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方法層次固守傳統的經典注疏派的觀點,或主張經典的神聖性。筆者並不認為共和主義(或任何政治思潮)是思想家在面對某些永恆的問題(例如「何謂正義?何謂自由?」)加以提問並做哲學思辯。相反地,筆者在研究共和主義的過程中,受到「劍橋學派」史學家波考克與史金納的影響,認為政治思想必定根源於特定歷史環境中的重大議題,並且會受到同時代先後的競爭論述的交互影響。然而,筆者主張,一流的政治思想家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在於,面對同樣的歷史情境時具有高屋建瓴的觀照能力,建構典範並創造政治觀念,對於當時的政治論述乃至其後的政治想像產生影響。一流的思想家既然具有此種系統化的能力,後進研究者在仰之彌高之餘,自然應力求鑽之彌堅、深入理解。
筆者在耶魯大學所完成的博士論文處理德國思想家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分析取向以二十世紀八○到九○年代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辯為基礎。返台初期自然也順著這樣的學術取向繼續研究,並將注意力轉到當代社群者如泰勒、麥肯泰以及沈岱爾的相關理論。然而,大約在九○年代末期研究馬基維利思想時,在廣泛閱讀相關文獻之後,逐漸脫離原來感興趣的馬基維利與現代「國家理性」的議題,而確立了以共和主義作為研究的主要課題。目前所集結的各篇章,便是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至於歷年來其他研究方向的學術論文,如社群主義、國家認同以及多元文化論等議題,為求全書意旨的統一性以及篇幅所限,並未收錄進來。
本書的主旨是對西方共和主義思想提供全面性的觀照以及系統性的分析,但由於各章均係可以獨立成篇的學術論文,對個別議題有興趣的讀者不一定需要從頭到尾通讀全書,而可以獨立閱讀各章,並參考註釋中所引用的其餘章節及相關文獻。另外,本書大部分內容都是對經典的疏義,分析時不可免地需要預設對於原始文本具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讀者若對原典有所理解,將有助於瞭解本書的意旨,並形成個人批判性的反思。全書處理的內容包含了許多西方重要思想家,若論述有疏漏之處,敬祈方家不吝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