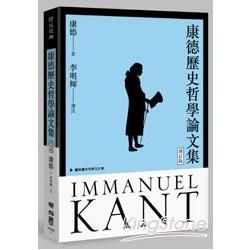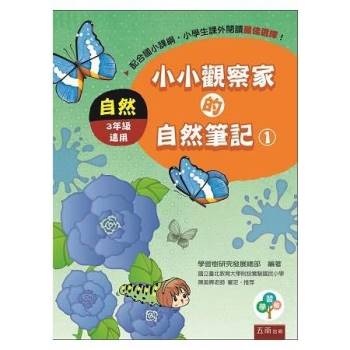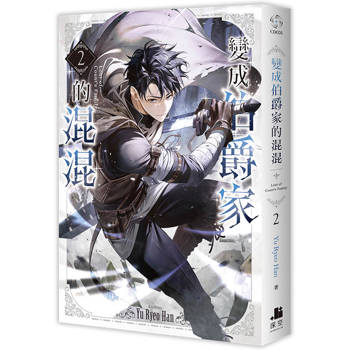前言(節錄)
康德底「歷史」(Geschichte)概念與歷史哲學對於中國的知識界而言,甚為陌生。中國的知識分子談起西方人底「歷史」概念與歷史哲學,首先一定想到黑格爾和馬克思,也許還會想到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乃至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儘管康德在中國的知識界中名氣不小,但是很少人了解他的歷史哲學,更不用說去討論了。在西方,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德國學者朗格雷貝(Ludwig Land- grebe)在其五十年代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便指出:在有關康德研究的眾多文獻當中,討論康德歷史哲學的極少;甚至連新康德學派試圖根據康德哲學底基本方向發展出一套文化哲學及關於歷史知識的理論時,也不重視康德底歷史哲學著作。
康德歷史哲學之所以未受到重視,其部分原因在於康德本人並未撰寫一部討論歷史哲學的專著,譬如《純粹理性批判》之於知識論,《實踐理性批判》之於道德哲學,《判斷力批判》之於美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之於宗教哲學。康德只有幾篇短文,專門討論歷史哲學底問題,其篇目如下:
1)〈在世界公民底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1784年發表)
2)〈評赫德爾《人類史底哲學之理念》第一、二卷〉(1785年發表)
3)〈人類史之臆測的開端〉(1786年發表)
4)〈萬物之終結〉(1786年發表)
5)〈重提的問題:人類是否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1797年所撰,收入次年出版的《學科之爭論》一書)
此外,其《論永久和平》一書(1795年出版)及〈答「何謂啟蒙?」之問題〉(1784年發表)、〈論俗語所謂: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不適於實踐〉(1793年發表)二文,亦部分或間接地涉及歷史哲學底問題。又由於其歷史哲學預設一套目的論,故欲了解其歷史哲學,亦不能不參考其〈論目的論原則在哲學中的運用〉(1788年發表)一文及其《判斷力批判》(1790年出版)第2卷〈目的論判斷力之批判〉。最後,康德還有一些未發表過的札記,亦涉及歷史哲學底問題。
康德有關歷史哲學的論著之所以如此分散,實有其進一步的原因。這是由於歷史哲學在其整個哲學系統中居於幾個主要領域交界之處:大略而言,其歷史哲學涉及形上學、知識論、道德哲學、宗教哲學及法哲學。因此,除非對康德底哲學系統有完整的理解,否則幾乎不可能正確地把握其歷史哲學,遑論對它提出恰當的評價。舉例而言,英國史學家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在其《歷史之理念》一書中對康德歷史哲學所提出的批評便無多大的價值,因為他竟然將康德哲學中「現象」(Erscheinung)與「物自身」(Ding an sich)之區分誤解為「自然」與「心靈」之區分。
康德歷史哲學之所以遭到忽視,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朗格雷貝還歸因於一種流傳已久的看法,即是認為:康德哲學是「非歷史的」,而其歷史哲學係停留在啟蒙運動及其理性樂觀主義之基礎上。由於這種成見,康德歷史哲學之光彩遂為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所掩蓋。再者,由於康德底歷史哲學包含一套目的論的歷史觀,不少學者往往未加深究,便將它與黑格爾和馬克思底歷史哲學歸於同一類型。這使得康德底歷史哲學始終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之故,本文擬透過對康德底「歷史」概念之勾勒,凸顯出其歷史哲學之特點。
在進一步討論康德底「歷史」概念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澄清「歷史」一詞所包含的歧義。在德文中,Historie和Geschichte 這兩個字都可譯為「歷史」。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德國的人文學界逐漸將這兩個字底意義加以區別,以前者指關於人類過去活動的記錄,以及這些記錄之編纂,以後者指存在於人類底精神或意識中的「歷史本身」。其實,這種用法上的區別可溯源於康德。他在其〈論目的論原則在哲學中的運用〉(以下簡稱〈目的論原則〉)一文中,為了界定「自然史」(Naturgeschichte)--有別於「對自然的描述」(Naturbeschreibung)--底意義,寫道:「人們將Geschichte一詞當做希臘文中的Historia(陳述、描述)之同義詞來使用已太多、太久了, 因而不會樂意賦予它另一種意義,這種意義能表示對於起源的自然探究〔……〕」康德所理解的「自然史」是從人類理性底有限觀點對於自然世界底起源所作的追溯;它不是「神祇底學問」,而是「人類底學問」。為了追溯自然世界底起源,它必須引進目的論原則。對康德而言,我們之所以必須將目的論原則引進自然研究中,正是由於我們人類底理性是有限的;反之,在上帝底全知觀點之下,目的論原則根本是不必要的。
同樣的,康德亦將目的論原則引進其歷史哲學中,而言歷史底目的。這種意義的「歷史」是依人類底有限觀點來理解的歷史,因為依其看法,「人類是地球上唯一擁有知性--亦即為自己任意設定目的的一種能力--的存有者。」康德與黑格爾底「歷史」概念正好在這一點上顯示出其根本歧異。因為依黑格爾底理解,世界史是「絕對精神」(或稱為「絕對理性」)在時間中的展現,換言之,是全知觀點下的歷史。這點分判至為重要,因為它不但有助於把握康德底「歷史」概念,亦有助於區別康德與黑格爾底歷史目的論。儘管康德在實際的語言使用上未必嚴格遵守Geschichte與Historie之區別,但其歷史哲學係以Geschichte為主要對象,殆無疑問。
若說康德所理解的「歷史」是依人類底觀點來理解的歷史,這項觀點是什麼呢?他在〈在世界公民底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以下簡稱為〈普遍歷史之理念〉)一文開宗明義便寫道:
無論我們在形上學方面為意志底自由形成怎樣的一個概念,意志底現象(即人類底行為)正如其他一切自然事件一樣,仍然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則而被決定。歷史以記述這些現象為務,而無論這些現象底原因隱藏得多麼深,歷史仍可使人期望:當它在大體上考察人類意志底自由之活動時,它能發現這種自由底一個有規則的進程;而且在這種方式下,就個別主體看來是雜亂無章的事物,就人類全體而言,將可被認為其原始稟賦之一種雖然緩慢、但卻不斷前進的發展。
根據這段說明,歷史係以「人類意志底自由之活動」為主要探討對象,而它依據的觀點即是「人類意志底自由」之觀點。如果人類像其他的自然物一樣,不具有自由意志,便無歷史可言。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並非歷史底直接對象,而是形上學(更精確地說,道德底形上學)之對象。歷史所要探討的主要對象是「意志底現象」,亦即人類的自由意志在現象界中的表現。這種「歷史」概念預設了現象與物自身之區分,以及人之雙重身分說。因此,我們可以說:康德底歷史觀是從人作為物自身的身分(自由的主體)底觀點來看他在現象界中所表現的行為。
在〈重提的問題:人類是否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以下簡稱〈重提的問題〉)一文中,康德以另一種方式來說明其歷史觀。他開宗明義表示:「我們期望有一部人類史,而這並非關於過去、卻是關於未來的人類史,亦即一部預測的(vorher- sagende)人類史。」但是所謂「預測的人類史」可以有不同的意義。如果這種預測並非以已知的自然法則(如日蝕和月蝕)為依據,便構成「預言的(wahrsagende)、而卻自然的」人類史;如果它是以超自然的感通或啟示為依據,便構成「先知的 (weissagende)人類史」。康德自己舉古希臘德爾菲神廟底女祭司與吉卜賽女卜者為前者之例,或許我們還可以將中國歷史上的讖緯、推背圖、燒餅歌也歸於此類。後者之例則如《新約.啟示錄》中的「千年至福說」(Chiliasmus)。這兩種人類史都預設一種決定論(determinism),乃至於命定論(fatalism)。康德在此文中所要討論的雖然也是「預測的人類史」,但完全屬於另一種形態。他寫道:
〔……〕如果問題是:人類(大體上)是否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這裡所涉及的也不是人底自然史(例如,未來是否會形成新的人種?),而是道德史,並且不是依據種屬概念(singulorum),而是依據在地球上結合成社會、分散為部族的人底整體(universorum)。
因此,康德所理解的「歷史」並不是以作為一個生物種屬的人類為對象,而是將全人類當做整體,來探討其自由底進展。這便是他所謂的「普遍歷史」。這種「歷史」可以預示:人類就整體而言,在道德上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
然而,這種預測如何可能呢?或者用康德底話來說,「一部先天的 (a priori) 歷史如何可能呢?」康德自己回答道:「如果預言者自己造成並且安排了他事先宣告的事件。」換言之,這是因為人是行為底主體,可以藉其行為產生一定的結果;既然這種結果是他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他自然可以預測。康德在此舉了三個例子:一是猶太先知預言以色列之滅亡,二是當時的政治家預言人類之冥頑不靈與反叛成性,三是當時的教士預言宗教之沒落與反基督者之出現。在這三個例子當中,預言者本身必須為它所預言的結果負責,因為正是他的行為造成了這些結果。這便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底殷鑑」或「歷史底教訓」。為取得歷史底殷鑑或教訓而撰寫的歷史,康德稱為「實用的歷史」(pragmatische Geschichte)。康德在此強調人在歷史中作為主體的地位,即是承認人在歷史中的自主性,這其中便隱含著一個非決定論的觀點。
然而,縱使我們承認人在歷史中的自主性,我們是否能對「人類就整體而言,在道德上是否有進步」這個問題有所論斷呢?這就要看我們從什麼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有三種可能的答案:一是認為人類日益墮落;二是認為人類日趨於善;三是認為人類永遠停頓在目前的狀況,或者是始終繞著同一點兜圈子。康德稱第一項看法為「道德的恐怖主義」(moralischer Terrorismus),稱第二項看法為「幸福主義」(Eu- damonismus)或「千年至福說」,稱第三項看法為「阿布德拉主義」(Abderitismus)。依康德之見,這三種看法都無法直接從經驗得到證明。「因為我們所涉及的是自由的行動者;他們應當做什麼事,固然能事先規定,但是他們將會做什麼,卻無法預言。」康德底意思是說:我們無法根據經驗法則去預測人底行為,因為這無異於否定人類意志底自由,而陷於決定論。
但是,承認我們無法根據經驗去預測人底行為,是否即意謂人類史是一齣荒謬劇,其中毫無道理可言?康德當然不會接受這種看法。他建議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正如他在知識論中一樣,他在歷史哲學中也提出一種「哥白尼式的轉向」。他寫道:
或許這也是由於我們在看待人類事務底進程的觀點上作了錯誤的選擇,而使這個進程在我們看來是如此荒謬。從地球上看來,諸行星時而後退,時而停止,時而前進。但若從太陽底觀點來看(唯有理性才能做到這點),根據哥白尼底假說,它們始終有規律地在前進。但是有些在其他方面並非無知的人卻喜歡固執於他們說明現象的方式,以及他們曾採取過的觀點--縱使他們在這方面會糾纏於第谷之圓與周轉圓,而至於荒謬的地步。但不幸的正是:當問題牽涉到對於自由行為的預測時,我們無法採取這項觀點。因為這是神意(Vorsehung)底觀點,而它超出人底一切智慧。神意也延伸到人底自由行為上面。人固然能見到這些行為,但卻無法確切地預見它們(在上帝眼中,這其間並無任何區別);因為他要預見這些行為,就需要有合乎自然法則的關聯,但對於未來的自由行為,他必然欠缺這種引導或指示。
換言之,人類史中的預測不但不能根據自然法則,亦不能根據超自然的啟示或感通。因為前者意謂對人類底自由的否定,後者意謂一種僭越,即以神明自居。這兩種預測雖有不同的依據,最後必然流於決定論,乃至於命定論。因此,康德視為可能的「預測的人類史」顯然不屬於波柏(Karl R. Popper)所批評的「歷史預定論」(historicism)。然則,我們還能依據什麼觀點來建立這種「預測的人類史」呢?康德底答案是:依據目的論底觀點。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康德對於目的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