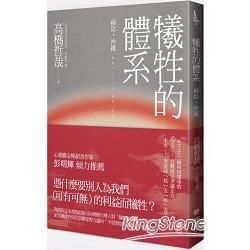憑什麼要別人為我們(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
從福島核電廠與沖繩的美軍基地談起,
探討無所不在的犧牲體系。
從小我們就認識到「不要損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別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等普世價值。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誰還敢坦然要求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甚至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從這最樸實的角度出發,確實難以想像為何還會有人被犧牲,甚至有人膽敢公然要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但是,福島核電廠的慘劇卻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被犧牲的一群人。而看著福島,很容易想起台灣……
我一直期待著這本書的中譯本,
不只是因為它說出福島核災之後許多不為人知的悲哀,
更期待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充滿台灣的各種「犧牲的體系」……
我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喚醒台灣人對「犧牲的體系」的反省,
並且讓政府與民眾願意努力邁向「不需要別人犧牲」的社會。
── 心靈勵志暢銷書作家 彭明輝 傾力推薦
人類的知識,不,人類的存在本身,即帶有光明與黑暗兩面。……
在這個晦暗中必須力求光明,是製造出黑暗的我們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為什麼是福島與沖繩呢?
日本1945年敗戰後,至今都一直被稱為「戰後日本」。
而這兩個地方正代表了在戰後日本,被編入國家體制內的兩個犧牲體系。
福島的核能事故,暴露出了在推展核能政策中所潛藏的「犧牲」;
而沖繩普天間的美軍基地問題,則凸顯了關於日美保安機制中的「犧牲」。
這些問題在日本全國皆知。但是,為了經濟成長與安全保障的大眾共同體全體利益,就可以犧牲某些人而將這體系正當化嗎?
這本書是由孩童時期在富岡町──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警戒區域度過、目前在東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的高橋哲哉,
以被犧牲者、獲得利益者雙重身分縝密省思後寫就的。
作者簡介:
高橋哲哉 (Takahashi Tetsuya)
1956年生於福島縣,1983年東京大學研究所哲學專攻博士課程修畢。歷任南山大學講師、法國巴黎國際哲學研究院客座教授等,現為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教授。
專精西歐當代思潮,同時富於社會實踐。對二次大戰前後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投以批判性眼光,從歷史認識的角度討論日本戰後責任、慰安婦問題、靖國問題等,長期關注「犧牲」的議題,並以此觀點討論國家權力收編個人的邏輯與修辭學。
主要著作有:《逆光的邏輯》(逆光のロゴス,未来社、1992)、《記憶的倫理學》(記憶のエチカ,岩波書店、1995)、《德希達:解構》(デリダ―脱構築,講談社、1998)、《戰後責任論》(戦後責任論,講談社、1999)、《歷史/修正主義》(歴史/修正主義,岩波書店、2001)、《靖國問題》(靖国問題,筑摩書房、2005)、《國家與犧牲》(国家と犠牲,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等。
譯者簡介:
李依真
台灣高雄人。2010年獲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赴日留學,2013年取得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表象文化論碩士,目前為同研究所博士生。在高橋哲哉的指導下研究法國當代思潮、犧牲、暴力、殖民歷史等課題。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提出大家必須要有什麼樣的覺悟
By unun
一如報紙上的評論,這本書簡潔的整理出下列問題:談到了福島與沖繩的共通點,也重新思考了地方與都會間的關係。同時更詳盡提出了當我們在談論停止利用核能、要求美軍基地撤退,以及此後該如何走下去之時,各方面都必須要有什麼樣的覺悟。我覺得本書相當好看。
沒有犧牲者的社會的可能性
By hanaohanao
本書是以犧牲的體系這個框架來討論福島與沖繩。作者一邊對照著日本的近現代史,一邊從受益者與負擔者間的權力關係來解讀這兩個事例,以尋找打造沒有犧牲者的社會的可能性。正如同本書作者及其他論者所指出的,福島事件在許多方面都很類似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本書引用了河上肇的「日本獨特的國家主義」,以及雅斯培的「問罪於戰爭」作了最佳論述。只是不論怎麼說,構想打造出沒有犧牲者的社會,都是最困難的難題。在書的最後,也以「我們必須以此為目標」作結。雖然我與作者在思考上的立場有些不同,但至少我們同樣都想站在犧牲者那方。
這場震災是天罰嗎?
By chogai
這本書,讓我特別有興趣的部分就是圍繞在震災上的「天罰論」與「天惠論」。比起前東京都知事石原等政治人物的發言,我對宗教界人士及知識分子的發言更抱持著疑問。尤其是對專門研究佛教學、佛教史學的末木文美士先生所提出的「天罰論」感到非常疑惑。在關東大地震時內村鑑三先生發表了〈天災、天罰與天惠〉這篇文章,用他的思想來檢證上述的問題,便能清楚看見潛藏在「天罰論」、「天惠論」之中的「犧牲的理論」。我認為,這就是這本書的精義所在。
福島,你好嗎?(彭明輝)
福島電廠核災事故距今三年了,很多人已經把它當作一個早已過去的歷史悲劇,不再關心並逐漸地淡忘了。事實上,福島電廠還在把含有核汙染的水排進海洋,並且讓洋流帶到全世界,又隨著海洋的食物鏈進入我們的身體。只不過,在媒體沒有持續報導的情況下,我們對於這場悲劇的持續發展已經沒有感覺了。
但是,福島的悲劇不僅止於土地、海洋與食物的汙染。在日本導演船橋淳拍攝的紀錄片《核能國家》裡,福島核災滿一年之後,被迫撤離的一千四百名居民還被安置在一間高中的廢棄教室內,所有家當都在一張榻榻米上,既回不了家又沒有工作,整天除了三餐排隊領便當之外,兩眼空洞無神地無事可做。看到這一幕,我心裡不禁浮現一個驚駭的聲音:好悲慘!他們人生竟然從此停格在三一一的那一刻,再也找不到出路了!
看著福島,很容易想起台灣。台北附近的兩座核電廠持續地在運作,安全性備受爭議的核四也在搶建與積極準備運轉,我們每天都活在核災的陰影下。當政府準備要用核災的風險來換取經濟發展機會時,你知道這到底是怎樣的風險嗎?譬如說,我就很想知道紀錄片裡的那些福島人,如今他們過的又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很想問:「福島,你好嗎?」
然後,有人寄來高橋哲哉這本書《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的譯稿。看完之後我發願要促成中譯本在台灣上市。因為,要深入談福島事件,除了這本書的作者之外,絕不做第二人想。
高橋哲哉教授出生於福島,福島既是他的故鄉又有著他的童年和玩伴,因此他對福島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有機會比外人更深入去了解、體會核災對福島的各種傷害。另一方面,他長大後就離開福島去東京,在那裡唸書、就業、結婚與安家,成為東京人。而福島電廠是為了供應東京的用電而設立的,福島人也可以說是為了東京人而被犧牲的,因此他又為此深刻感到歉疚與不安。不僅如此,高橋的專長是哲學,長期研究的主題是「犧牲」這個概念,以及「犧牲」的邏輯與倫理,因此他有能力深刻而細膩地去分析福島事件背後的決策與邏輯,以及各種參與決策者所必須要負起的道德責任。而且,他又是一個擅長分析時事的哲學工作者,在日本出版界享有極高的聲譽與影響力,因此有能力把他對福島事件的情感與理性分析用大眾能理解的方式陳述出來。
這一本書用福島電廠與沖繩的美軍基地為例,探討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憑什麼要別人為我們(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
從小我們就認識到「不要損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別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等普世價值。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誰還敢坦然要求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甚至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從這最樸實的角度出發,確實難以想像為何還會有人被犧牲,甚至有人膽敢公然要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犧牲。
但是,福島核電廠的慘劇卻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被犧牲的一群人。福島事件並非預料之外的悲劇,而是早就已經預見的劇碼:需要核電的是東京人,但是電廠卻蓋在福島而非東京,因為主事者早就預設了「不得已時福島可以被犧牲,但是東京不可以被犧牲」這樣的邏輯;許多專家都早已指出福島電廠無法抵擋海嘯的衝擊,但是東電卻以「發生的機率太低」為藉口而堅決不肯加強各種安全防護措施。書名「犧牲的體系」點出一個事實:有「被犧牲的人」,就有「從別人的犧牲獲得利益的人」,後者必須對前者負起道德上的責任。但是,福島被犧牲了,許多東京人卻從頭到尾都不曾問過自己:憑什麼要別人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不僅如此,福島核災之後,東京人既不曾派人去救援,還在災後對福島的農牧產品與居民百般歧視。這豈不是比「占盡便宜還賣乖」更可惡?
我們憑什麼要別人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只是因為少數必須為多數的利益而犧牲?還是說,給個補償費就可以將這犧牲合理化?
就算要別人犧牲,最起碼我們也總得要確實了解:為了我們的利益,別人到底必須做出什麼樣的犧牲。「犧牲的體系」之所以能夠在現實世界裡存在,首要原因就是:我們不願意去了解別人的犧牲,甚至根本就不想知道有人會為我們(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我們自己先從「犧牲的體系」上逃遁,再用「核災的機率小到可以忽略」的藉口遮掩被犧牲者的存在;當整個犧牲的體系都隱形後,所有的人都可以逃脫一切的責任,而安然享受(可有可無)的利益。「犧牲的體系」變成了沒有人需要負責的「無責任體系」。
高橋哲哉教授的這本書,就是要從各種角度揭露「犧牲的體系」,讓所有獲得利益的人清楚看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該逃避的責任,希望藉此讓日本人決心戒絕各種「犧牲的體系」,積極朝向「不需要犧牲別人」的社會而邁進。
在本書裡,他先讓讀者看到福島居民不為外人所知的各種慘痛犧牲:許多人被迫離開世居的美麗故鄉,再也回不去;農民與牧農因為看不到產業的未來而自殺,福島青年的婚約遭受反對(擔心他們的精子與卵子不正常),連掛著福島汽車牌照的卡車都被拒絕;而網路上各種對福島與東北居民的歧視言論,更是讓人痛心。
接著,他細數政府、學者、東京居民、福島居民各自要負的責任,並且一一駁斥各種想要將災難合理化、無責任化的辯辭。
讓福島居民冒著這麼大的風險與災難,東京的人沒有責任嗎?是不是給了補償金就可以抵清東京人的責任?還是說,福島人是自願接受核電廠與補償金的,因此他們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起所有的責任?其實,福島居民並沒有「選擇」接受核電廠:他們未曾被忠實告知核災的機率與後果,因此談不上「選擇」;而福島之所以會被補償金誘惑,是因為政府一開始就漠視福島經濟發展的需要,「迫使」他們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得不接受自己不了解的風險。高橋哲哉教授甚至明白指出,福島與沖繩在日本的地位根本就形同「殖民地」:他們先是在經濟發展上被漠視,繼而在「犧牲的體系」裡扮演著要被犧牲的角色。
從這角度看,我們真的也該問自己:我們是不是把蘭嶼、石門、金山、恆春、貢寮當作台灣的殖民地,先是在經濟發展上漠視他們,繼而準備在「不得已」時犧牲他們?更蠢的是,我們是不是也因為無知而把台北這個首都當作要被犧牲的對象?
我一直期待著這本書的中譯本,不只是因為它說出福島核災之後許多不為人知的悲哀,更期待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充滿台灣的各種「犧牲的體系」:苗栗縣政府的大埔案犧牲了兩條人命,以及無數農民的家園和生計;全省各地的都更案毀人家園,桃園航空城一案更已犧牲一條人命;TPP打算要犧牲四○%的農業來換取特定產業的利益,服貿則為了特定產業想像中的利益而準備讓許多弱者生計頓失。政府對這一切的犧牲從來不曾負起任何道德上的責任,從中獲利的財閥、居民更是蠻橫指責被犧牲者:「不要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社會發展與多數人的利益。」
今天,「經濟發展」已經變成「必要之惡」,心懷不軌的人用它遮掩一切蠻橫的殺人事件,以及毀人家園、奪人生計的惡劣行為,並且將各種「犧牲的體系」轉換成「無責任體系」。被愚弄的民眾則在「經濟發展」的口號裡,變成麻木不仁或窮凶惡極的附庸。
但是,絕大部分的「必要之惡」都是無能、怠惰與卑劣的藉口。以核電為例,雖然火力發電害死的人更多,而且台灣發展綠能的空間非常狹小,但核電仍舊不是非要不可的「必要之惡」。台灣過去因為過份的電價補貼而鼓勵浪費,使得我們在節能減碳上有非常大的潛力。根據一份國科會委託國內外專家的研究,台灣節能減碳的空間高達一.五六座核四廠,而且節能減碳會減少電廠燃料費,因而扣除節能設備的投資之後還淨餘一○六三億美金。節能減碳又賺錢,還可以不需要任何人為核電而冒著被犧牲的風險,何樂而不為?
不只核電如此,只要我們認真思索較佳的替代方案,就有機會在都更、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過程避免沒必要的犧牲,或者至少把犧牲的規模大幅減少。
我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喚醒台灣人對「犧牲的體系」的反省,並且讓政府與民眾願意努力地邁向「不需要別人犧牲」的社會。
名人推薦:提出大家必須要有什麼樣的覺悟
By unun
一如報紙上的評論,這本書簡潔的整理出下列問題:談到了福島與沖繩的共通點,也重新思考了地方與都會間的關係。同時更詳盡提出了當我們在談論停止利用核能、要求美軍基地撤退,以及此後該如何走下去之時,各方面都必須要有什麼樣的覺悟。我覺得本書相當好看。
沒有犧牲者的社會的可能性
By hanaohanao
本書是以犧牲的體系這個框架來討論福島與沖繩。作者一邊對照著日本的近現代史,一邊從受益者與負擔者間的權力關係來解讀這兩個事例,以尋找打造沒有犧牲者的社會的可能性。正如同本...
章節試閱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
四月十七日,我人在福島縣川町山木屋地區的山木屋小學。那所小學距離福島市的東南方約三十公里,比阿武隈山地還要更深入山區。為我開車的友人曾在這裡工作過,在那之後,他仍繼續與這裡的孩子們保持聯繫,因此就由他為我帶路。
山丘上,校舍、體育館、中庭等皆整備得宜。從中庭便能眺望四周的群山翠巒,感覺很清新。友人暑假時會與學生們在這裡夜宿,享受觀覽滿天群星的樂趣,這一點很令人稱羨。
跟著校工E先生,我們環繞了中庭及建築一周。中庭的地面四處都是裂痕,校舍的壁面也有些地方出現裂紋,那是三一一大地震的爪痕。但是這些都還好,只要進行修復,學校就可以回復到原本安全的狀態。真正的問題是眼睛所無法看見的輻射。福島第一核電廠的重度氫爆等所釋出的大量輻射物質隨風飄散,連距離核電廠約三十公里的這個地區也遭受了汙染。根據四月十三日發表的福島縣調查結果,從這所山木屋小學的土壤中所檢測出來的數值(一公里五九○五九貝克),在縣內十六個市町村的二十所小學中是最高的。
從我拜訪的翌日起,山木屋地區約百名的中小學生與幼稚園學童,便開始坐巴士到距離約十公里遠的町中心學校、幼稚園上課。政府公布該地區全體皆為計畫性避難區域,所以在一個月內,所有成人也必須離開此地到其他地方避難,不過首先還是從容易受到輻射影響的孩童開始執行。據說在家長會裡,教育委員長發言說:「孩子們什麼罪都沒有!山木屋地區也什麼過失都沒有!這真是教人痛恨至極!」的確,若是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沒有發生事故,對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來說,核電廠大概是相當遙遠的存在。為了在相距甚遠的核電廠所發生的事故,他們竟然必須要離開自己熟悉的土地,這件事想必任誰也沒有想過。
在山木屋地區之後,我接著進入飯舘村。即使是在這種狀況下,山木屋地區的居民還勉強可以在同地區的川吴町內避難,但是鄰近他們東邊的飯舘村,卻必須全村遷移到別處去找尋避難場所。因為這片面積廣大的村落,全都被指定為計畫性避難區域。
飯舘村相當秀麗,山林、耕地與牧草區波狀似地蜿蜒成一片,隨處都有知名的「飯舘牛」在悠閒吃草。如果有人對輻射汙染毫不知情而來到此地,大概完全不能理解為何六千多位村民全都必須要離開這個美麗的村莊吧。而村民們自己大概也無法相信,為何在這片與核電廠完全不相干的土地上,經營在地農業與畜牧的自己竟突然得要離開村落?而且,還是在發生核電事故後又過了一個月的現在……
我接著向東前往南相馬市。它的市中心位於離核電廠二十∼三十公里的區域內,是被指定為在屋內避難的區域。大概因為這樣,在市內幾乎看不見人或車,在像失去了什麼的藍天下,燦爛綻放的櫻花似乎顯得很落寞。市政局一樓聚集了些災民,他們或是在窗口前排著隊,或是看著公布欄上的死者名單或從全國各地匯集而來的聲援留言。
從國道六號南下,向著核電廠前進。一如預期,在距核電廠二十公里遠處,豎立著「禁止進入」的告示牌與「停止通行」的光電板,警察封鎖了道路。「警戒區域」告示牌雖沒有強制力,但我並不逞強進入,而是掉頭北上。我在南相馬市與相馬市之間步行,勘查了海嘯留下的痕跡。
我是在福島縣長大的,父母皆是福島市人,但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我出生於現在的磐城市,只在兩歲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在東京度過,到高中畢業為止,則都是在濱通、中通、會津等地的學校間輾轉來去。至於小學,則是在福島第二核電廠所在地的富岡町就讀。在那裡,我住了四年。
因為這個緣故,對我來說,不論是這次的大震災還是福島核電事故,都不是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在那塊土地上,仍舊殘留著我人生中最初的記憶,而今它的自然環境與人民,正苦悶地發出悲鳴。而不可思議的,在我的體內,彷彿也能夠聽到這些難以言說的呻吟。那場事故是車諾比級「七級」的大事故,不僅富岡町會變成幽靈城市,說不定連整個「福島」都會消失。
從雙葉町、富岡町、南相馬市、飯舘村、磐城市以及福島市等縣內外聚集而來的「核電難民」有數萬名,其中還有數千名的孩童。每次透過媒體得知這些消息時,我總是難以克制的投入其中。
我追著連日來傳達事故惡化及災害擴大的報導,心中夾雜著不安、悲傷、困惑、憤怒以及罪惡感──我感到有股難以言喻的某種情感被撩起。
我們何時才能解決這個事故?在根本上,它可以說是能夠解決的嗎?雖然電力公司發表了「工程進度表」,但卻不可信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我上述的那些理由,以及我難以公開的(私人)部分,我對於此次事故的感想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化為語言表達出來?而化為語言表達出來又真的妥當嗎?縱使我已提筆至此,卻仍然有著些許躊躇。
從責任中脫逃
至少我能說的是,核能發電是一個犧牲的體系。在那裡,有要求犧牲的一方,以及被犧牲的另一方(在核電的情況中,前者指的是人,但後者不只是指人)。要求犧牲以及被犧牲的兩方的關係,確實並不單純。這點與其他犧牲的體系相同。但是,儘管如此,這仍舊不能抹滅掉要求犧牲以及被犧牲者這兩者間的關係。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們)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而且,當隱蔽或正當化發生困難,或犧牲的不當性被揭穿時,要求犧牲的那方總是會規避自己的責任,並從責任中逃脫。這個國家的犧牲體系,是蘊涵著「無責任體系」(引述自政治思想學者丸山真男)而成立的。
在三一一之後,「無責任體系」持續發揮它那空虛的本質。
四月十九日,文部科學省發表了在福島縣內中小學及幼稚園裡使用校舍與中庭的基準,並規定年間輻射曝曬量超過二十西弗、中庭輻射量超過每小時三.八毫西弗
以上才限制戶外活動。根據這一基準,除了福島市、郡山市、伊達市的十三個設施,一般的學校活動都變成在認可的範圍中(在這之後,幾乎所有的限制都被解禁)。
這是充滿疑問的措施。根據福島縣的調查結果,縣內約七五%是法令規定的輻射管制區域,而二○%則是必須更加嚴格控管的個別受曝管制區域。即使用大人的基準來看,這樣的輻射量也是極高的,讓幼稚園兒童與中小學生在這樣的場所中活動,真的可以嗎?因為政府一直無法標明基準,就造成了縣內幾乎全部的區域都要避免在戶外活動。再者,核能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在四月十三日發表了孩童年間受曝基準量「應該規範在大人基準量一半的十西弗程度」這樣的見解。但是,這個見解在翌日即以「不是委員會的決定」而被撤回,文科省二十西弗的基準於是取而代之。
一般成人的受曝基準量是年間一西弗!對於更易受到輻射影響的孩童,政府竟然容許其受曝基準要比一般成人還多上二十倍,這到底是什麼狀況?雖說這是非常時期所以才緩和基準,但是一開始,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才設定基準的?是誰,用什麼理由,以這種輕忽的態度設定了如此危險的基準?
四月二十一日,要求撤回此基準的市民與政府展開交涉,核能安全委員會與文科省的負責人皆出席了。但是,令人啞然的事實卻被攤開在眾目睽睽之下。文科省負責人竟然不知道輻射管制區域的意義,也不知道禁止未滿十八歲者進行勞動的區域有哪些,更不知道福島縣內有許多學校是符合輻射管制區域及個別受曝管制區域的數值。而他也回答不出來,為何從三月二十三日起才開始測量累積輻射量,之前的累積量卻不包含在內?核能安全委員會並沒有召開正式的會議,他們對決定基準量是二十西弗的審議過程也毫不知情。即便「(安全委員會對文科省)只是提供建議,並沒有決議」,但他們到底提供了什麼建議?五位委員到底各自提出了什麼意見?既沒有紀錄,也無法回答。對於市民所提出的問題,他們幾乎完全回答不了。
福島孩子們的未來,有可能因為這項決定而改變。不僅是健康災害,他們也有遭到各種歧視的危險。這件事到底誰要負責?許多父母過著無法入睡的夜晚,到了早上,又要將孩子送往學校。這樣真的可以嗎?身為父母,這樣難道不是在對自己的孩子做出無法挽回的事情嗎?應該要有人來回應這種不安,但卻看不見負責的人在哪裡。深刻的不安,竟被放置在完全的無責任之中(四月三十日,內閣官房參與小佐古敏莊批判了政府對核電事故的應對措施並辭去官職。這位輻射安全專家決定辭任的理由之一是:「『文科省所採用的年間二十西弗的這個基準』簡直是高到不像話,如果採納了這個基準,我的學者生涯將就此告終。我絕對不想讓我的孩子遭到這種待遇。應該要採用接近普通輻射防護基準的年間一西弗才對。」他如是說)。
前福島縣知事佐藤榮佐久的著作《扼殺知事──被捏造的福島縣貪汙事件》,此書的〈第三章 圍繞核電的抗爭〉、〈第四章 停止核電所有機體〉,可說是為推行核電的國策與實際執行部隊電力公司如何輕視當地居民安全的這件事,提供了珍貴的證言。
根據佐藤前知事的說法,在核電事故中,縣與自治團體沒有任何權限,只有袖手旁觀的份。例如,一九八九年一月所發生的福島第二核電廠三號機的事故,東電不顧反覆出現的警報,連續數天隱蔽了機體異常的事實。即使在終於報告了事故的當天,仍舊放任警報作響,任機體持續運轉七小時。而且在這個時候,「事故的消息是從福島核電傳到東京的東京電力總公司,再傳到通產省,然後再回傳到福島縣,拖拖拉拉繞了一大圈,最後在地的富岡町才終於從縣廳得到消息,實在是離譜。」福島縣也曾向通產省要求過要分擔責任,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因為,「應作為核能發電國策的第一當事者──國家」,已經變成了「在安全對策上不執行任何主導權」的「完全無責任體制」了。
二○○二年八月,東京電力長年以來為了隱蔽在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內的過失而竄改檢查紀錄的事實,因內部人員的告發而浮上了檯面。而且,這個告發信件兩年前就早已被投遞到核能安全.保安院去了,但保安院不但沒有深入追查,亦沒有聽取告發者敘述事由及情報,反而通知東電告發的內容和告發者的姓名。根據前知事的說法,雖然「國家與東電是一丘之貉」,但是「國家才是真正的『貉』」。
無法再信任國家的前知事,退回了本來已允諾的混和氧化物核燃料計畫,並與國家、東電全面抗爭。但是,二○○五年十月,在內閤會議中決定的「核能政策大綱」,卻完全沒有反映福島縣所提出的意見,國家開始著手回收核燃料這個實際上根本沒人相信可以順利進行的計畫。
前知事說:「在這個看不見負責人的臉、誰都不負責的日本型社會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下定決心要像旅鼠般全力朝向自我毀滅奔馳。狀況就如同約六十年前,向著既沒重要意義也沒勝算的戰爭突進一樣。所以我才稱它為『日本病』。」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認為,這裡似乎已正確「預寫」了三一一之後的破敗嗎?又有誰能夠否認,福島縣民是因「完全無責任體制」而最早被犧牲掉的事實呢?
在地自治團體根據電源三法而獲得了巨額的補助和恩惠。沒有什麼大型產業的地方能夠收到幾億元經費的支助,勞工的雇用也因此增加,大大潤澤了當地居民的經濟。難道該地不是在一開始時就視經濟發展為目標,而招攬核電廠進駐嗎?既然如此,那麼現在他們就沒有權利演出「被背叛了」、「不可原諒」的無辜受害者戲碼。類似批評,以及像是「自作自受」等的粗暴言論也同時並存。
但是,經產省與東電從以前開始,就藉著各種機會、使用各種手段,不斷宣稱「核電是多重防護系統」、「絕不可能因自然災害而導致核能事故」。「如果只聽到這些話,鄉鎮地區會相信也理所當然」(佐藤前知事)。就像以前的戰爭一樣,要想從輿論炒作以及投下巨大經費推行的國策中全身而退是非常困難的。的確,「被騙」也有「被騙的責任」。但是,比起補助金或其他,對當地來說,「安全」是首要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不會有願意接受核電的住民。重大事故與補助金的「等值交換」是不成立的。
在這個意義下,為「絕對安全」宣傳背書的核能科學專家、學者、技師們的責任非常重大。如果沒有那些在經產省所召集的無數委員會、審議會中擔任職務,並接受電力公司巨額研究經費而被收編到國策裡的學者們,「核電安全神話」是不可能成立的。而那些為了廣告費就氾濫播放「安全」宣傳片,並排擠持批判立場的學者或記者的電視等大眾媒體,也犯了同樣的重罪。
被犧牲的是誰?
聽說在第一核電廠發生第二次氫爆的三月十四日至隔日,政府與東電間出現了相當緊張的對峙。十四日晚間,東電命令事故現場的職員全員撤退,並試探性提示了善後收拾將委任給自衛隊與美軍的處理方針。翌日,菅首相衝進東電總公司,駁回東電的這項方針,並怒斥:「現在只剩下你們了不是嗎?撤退實在太不像話了!你們必須要覺悟!一旦你們撤退,東電絕對百分百會垮台。」然後脅迫:「這不是東電垮台的問題,而是日本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問題。」
真相到底為何並不明確。據一部分消息指出,東電幹部的說詞是:「我們商討著要撤退部分員工是事實,但要全員撤退則絕對不是事實。」如果東電真的有打算要撤退全數員工,那大概再也沒有什麼是比這作法更不負責任的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依舊會很安全」,東電用這種花言巧語哄騙當地居民並獲取龐大利益,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卻說沒有能力處理而丟下問題逃亡,這種卑怯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這麼一來,被留下來的當地居民該怎麼辦?生命與生活皆暴露在危險中的人們該怎麼辦?
另一方面,從東電的角度來看,「真正的貉」其實是國家。難道國家打算要將所有責任都推到大企業但在法律上也不過是民間企業的東電身上,然後逃脫嗎?東電大概是這樣想的吧。這就是「一丘之貉」的同志們在相互推卸責任。
問題是,菅首相說「現在只剩下你們了」的那個「你們」指的到底是誰?「必須要覺悟」的到底是誰?聽說東電認為「(首相)說『不許撤退』,就好像是在說『到受曝、死亡為止,都要給我繼續下去』一樣」,因而感到不滿。但是,被要求「到受曝、死亡為止都要繼續下去」的人,既不是東電的會長,也不是社長或副社長,而是核電內的現場工作人員。況且,他們之中的大多數甚至不是東電員工,而是通過子公司、孫公司雇用來的非正規勞工。再說,聽說現在在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擔任危險任務的作業員中有八成都是在地居民(來自擔任作業員健康檢查的醫師證言)。核能事故的災民,竟要自己擔任收拾善後的殘酷基層勞動。
也有些報導稱他們為「敢死隊」、「福島五十」,把他們當成英雄看待。終於,必須開始進行會受到大量輻射照射的工作時,該怎麼選擇「平成特攻隊」才「公正」一事也被拿出來討論。無論是志願還是命令,如果產生了受曝死者,那就應該像靖國神社的「英靈」一樣,把他們當作「為國家」、「為國為民」、「為日本」而奉獻出生命的「尊貴之犧牲」來表揚,只要給家屬〈如果有家屬〉精神上的安慰與經濟上的補償就好。他們難道是想講這些嗎?這樣的現實狀態,難道不是要為在「完全無責任體制」下推行的核電政策,以及享有它利益、權力的政治人物、官僚、電力公司幹部、核能學者與技師〈有人將他們總稱為「核能村」〉的怠慢、欺瞞、特權意識所招致而來的淒慘失敗收拾殘局嗎?這難道不是在上演現代的代罪羔羊〈scapegoat〉戲碼嗎?被災難襲擊的社會,為了從自身的罪惡中脫逃,而將全部責任推卸給沒有力量的羔羊,把它當作犧牲。就這樣,社會將羔羊視為解救自身的存在而崇敬奉仰著。
在福島核電的危機裡,媒體報導了核電基層作業員的部分工作實況。一天兩餐,吃的是乾燥的米飯與罐頭、礦泉水一瓶、穿著防護衣、戴著特殊口罩勉勉強強降低輻射量的輪班作業、無法洗澡、在防震大樓的大房間裡打通鋪等等。但是,關於遭受輻射的工作實況,東電卻幾乎完全沒有公開,媒體也不去報導。無論是在福島核電或其他的核電廠,甚至不僅是在這次的危機裡,事實上,在「平時」就一直存在著受曝於輻射中的基層勞工。而且這些勞工縱使被懷疑因受曝於輻射而產生的疾病與死亡案例多不勝數,但至今真相仍不見天日。所謂的「被懷疑」,指的是這些人就算是因白血病或癌症去世,也會因為「無法證實其與受曝之間的因果關係」,而無法被認定為勞災。在樋口健二所著《被抹煞在闇黑中的核電受曝者》〈闇に消される原発被曝者,二○○三年〉一書中,就以真實姓名介紹了像這樣「因不明原因死亡」的四則福島核電勞工及其家屬的案例。
我們可以說,核電是一種必須要在其內部和外部都同時預設犧牲才能成立的體系。無論是在日常或是在危機中,核電在其內部都需要受曝勞工的犧牲。若一旦發生大事故,首先被犧牲掉的就是當地及其周邊的人們、環境。接著,由於輻射物質的擴散,超越縣界、國界等其他更廣大區域的人們與環境也將被犧牲。所謂的核電,就是這樣的犧牲體系。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
四月十七日,我人在福島縣川町山木屋地區的山木屋小學。那所小學距離福島市的東南方約三十公里,比阿武隈山地還要更深入山區。為我開車的友人曾在這裡工作過,在那之後,他仍繼續與這裡的孩子們保持聯繫,因此就由他為我帶路。
山丘上,校舍、體育館、中庭等皆整備得宜。從中庭便能眺望四周的群山翠巒,感覺很清新。友人暑假時會與學生們在這裡夜宿,享受觀覽滿天群星的樂趣,這一點很令人稱羨。
跟著校工E先生,我們環繞了中庭及建築一周。中庭的地面四處都是裂痕,校舍的壁面也有些地方出現裂紋,那是三一...
作者序
紀念福島核電事故三週年(高橋哲哉)
從發生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事故以來,已經過了三年。在這段期間裡,災民們被迫承受了多少苦難?直到現在,他們仍舊被多少的不安與困苦侵擾?這些都超越了我們的想像。
事故後,我從二○一一年四月十七日初次走訪災區以來,每月都會固定返回福島一兩次。因為如果不站在災區的立場,我們又如何能夠去談論事故或核電問題呢?對在福島縣出生成長的我來說,現在只希望先將理論、邏輯都放到一邊來陪伴故鄉的人們。
我在事故發生後,產生了相當強烈的愧疚感。為什麼自己在熟知蘇聯車諾比事件、東海村
JCO事故等海內外核電相關事故的慘痛教訓下,還讓自己故鄉福島的人們去背負如此重大的風險,而自己卻在東京悠哉享受著福島核電廠所供給的電力呢?我感覺在我的心中,自我分裂成了兩半,其中一半無法冷眼旁觀福島居民的苦悶,就像自己也受到傷害般;但另一半卻是個從福島的犧牲中獲取利益的加害者。
在這種糾結的情緒下,將核電視為「犧牲的體系」的觀點,逐漸在我心中成形。所謂的犧牲,第一,是安全神話的崩潰。嚴重事故隨時都可能會發生,一旦發生將出現無法估量的犧牲。第二,核電體系若沒有在輻射曝曬下、從事勞動的工作人員就無法運作。第三,從採掘核電燃料鈾礦的時候開始,就已經產生受到輻射曝曬的勞動與環境的汙染。第四,核電的「核廢料」等放射性廢棄物也將帶來災害。
核電是若沒有這些犧牲就無法運作的體系,而這種將某些人的利益建築在其他人的犧牲之上的「犧牲的體系」,既無法從現代憲法的人權原則上獲得正當化,更無法在人道倫理上獲得正當化。基於這些理由,我於是認為應該盡快廢除核電體系。
事故發生滿三週年的今日,我更堅信核電本身就是一個「犧牲的體系」。因為即使福島為了這個事故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日本政府卻仍棄災民不顧,還計劃著要再度運轉核電、將核電事業輸出國外、增設核電廠等。福島的犧牲彷彿是早已被計算在這些政策之中,政府竟還打算若無其事地繼續維持這個體系。
目前,日本列島上設置有五十四座核電廠,以及「高速增殖爐文殊廠(Monjyu)」、「六所村核廢料處理廠」。核廢料處理廠若發生事故,其危險性遠不是核電廠可以相較的。一旦有狀況,不要說日本全島了,連整個北半球都會瀕臨危機。而這麼多的核電相關設施竟已經被設置在這麼狹窄的日本列島上!這只表示了,「戰後」的日本在追求經濟成長以及為保持潛在的核武軍備平衡上,親手製造出了連自己都束手無策的負面遺產。
人類為了生存,是絕對需要大地、水源及空氣的。在地球這個受到大地、海洋、空氣包圍的環境下,人類被賦予生命並得以生存。人類若要繼續生存下去,這些條件缺一不可。這些條件最根本的意義,就是我們的環境、生命的環境。
人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勞動,以人為的方式整頓自然。不僅是農業或都市文明,即使只是挖掘洞穴、組裝家屋來抵擋風雨,也都是在改變自然環境的行為。但是,人類的這些行為應以不傷害大地、水源、空氣等環境為前提。因為要是破壞了這些生命生長最根本的條件,將得不償失。破壞最原本的自然環境,將使我們無法再為了生存而進行任何作為。
近代之後,科學技術的發達使人類不斷改變自然環境,也使我們忘了人類的這些作為必須要節制。在日本,戰前曾發生過足尾礦山礦毒事件,戰後則爆發水俁病(汞中毒)以及大氣汙染等一連串的公害,這些事件都在警告著我們,破壞環境最後只會造成人類自己的損失。
接著,發生了福島核電事故。在這次事故中,我們見證了核電這種科技一旦引發了大事故,將使土地不再適於人居。不僅是土地,水、食物、空氣都不能為人所用……我們了解到核能汙染傷害了所有原本的環境。
在東亞,推行核電政策的不只有日本,韓國、中國及台灣也一樣有核電。製造出這些核電廠的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們。我們在追求更富裕、更便利,享受更舒適生活的戰後經濟活動中,追求著恐怕是關係到開發核武器的技術,因而從自己手中製造出了對世界環境、對自己的生存來說非常危險的事物。我們一味追求慾望的後果是大量製造出無法讓自己生存下去的事物,這正是我們深刻的自我矛盾。我認為將此稱為「罪」也絕不誇張。在第一次核爆實驗成功之後,物理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曾說:「物理學家們知道了什麼是罪,而這是他們不能喪失的知識(the physicists have known sin; and this is a knowledge which they cannot lose.)。」人類的知識,不,人類存在的本身,即是帶有光明與黑暗兩面的。
日本列島現在正處於深邃的晦暗之中,我們在這個晦暗中必須力求光明。這是製造出黑暗的我們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帶給居住在擁有核電廠的台灣讀者們一些參考。
最後,由衷感謝東京大學研究所博士生李依真為本書翻譯及出版中文版一事貢獻己力。同時我也要向彭明輝先生致上敬意,感謝他在對本書的深刻理解上,撰寫了珍貴的推薦序。
二○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後滿三週年之日於東京
紀念福島核電事故三週年(高橋哲哉)
從發生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事故以來,已經過了三年。在這段期間裡,災民們被迫承受了多少苦難?直到現在,他們仍舊被多少的不安與困苦侵擾?這些都超越了我們的想像。
事故後,我從二○一一年四月十七日初次走訪災區以來,每月都會固定返回福島一兩次。因為如果不站在災區的立場,我們又如何能夠去談論事故或核電問題呢?對在福島縣出生成長的我來說,現在只希望先將理論、邏輯都放到一邊來陪伴故鄉的人們。
我在事故發生後,產生了相當強烈的愧疚感。為什麼自己在熟知蘇聯車諾比事件、東...
目錄
推薦文:福島,你好嗎?(彭明輝)
台灣版序:紀念福島核電事故三週年(高橋哲哉)
前言
第一部 福島
第一章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
輕忽釀大禍
身為福島之子
身為首都圈的一員
我該如何討論核電事故?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週刊朝日 緊急增刊 朝日新聞》)
第二章 再論核電犧牲體系
何謂「犧牲的體系」
第一重犧牲──嚴重事故
暴露在輻射線下的不安
對當地產業的重創
對福島縣民的歧視──「輻射會傳染」
「要把福島縣民丟去哪裡?」
歷史性歧視的殘存──「東北土人」
自然環境的汙染
絕非意外的大事故
第二重犧牲──曝露在輻射下的勞工
需恆常暴露在輻射下的工作
雙重受害
第三重犧牲──採掘鈾礦時所伴隨的問題
第四重犧牲──核廢棄物該如何處理?
將「核廢料」丟到國外
三一一之後的日本課題
殖民主義
日美安保體制與「浮在海上的核電廠」
從核電到「核能的軍事利用」
核電是「核能的潛在相互制衡力」?
第三章 核電事故與震災思想論
(一) 思考核電事故的責任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第一義的責任在「核能村」
政治人物‧官僚的責任
學者‧專家的責任
迷失方向的安全基準
山下的發言哪裡有問題?
河上肇「日本獨特的國家主義」
市民的責任
曾漠不關心的責任
在地居民的責任
政治責任
(二) 這場震災是天罰嗎?圍繞震災的思想問題
石原都知事的天罰論發言
震災是上天的恩惠?
宗教人士的發言──天主教
宗教人士的發言──基督新教
知識分子的發言
內村鑑三的天罰論
墮落的都市‧東京
犧牲邏輯的典型
承擔國民全體罪惡的死
〈反戰主義者的戰死〉
為死賦予意義的問題
天罰論與天惠論的無法確定性
核爆是天罰還是天惠?
天罰論為什麼會變成天惠論?
為什麼這個震災是天罰?
對震災的牽強附會
「日本」意識形態的表現
因為危機所以法西斯?
第二部 沖繩
第四章 「殖民地」沖繩
何謂普天間基地移設問題?
政黨輪替中顯現的戰後日本之犧牲
沖繩是日本的墊腳石
天皇的訊息
戰後沖繩的命運
如果沒有沖繩的犧牲,戰後日本將無法成立
○‧六%的土地,七四%的負擔
無意識的殖民主義
可見的犧牲體系
因為可見所以要表示「感謝」
沖繩並沒有沉睡
第五章 與沖繩對照的福島
「殖民地」福島
沖繩與福島──相似點與相異點
援助金‧補助金的利益勸誘
真的對該地有貢獻嗎?
看不見的前提──地域的貧富不均
將殖民主義正當化的神話
另一個神話──民主主義
全民公投的危險
是誰成為犧牲者?
是誰決定犧牲?
沒有犧牲者的社會是可能的嗎?
後記
附錄:高橋哲哉訪談紀實(李依真)
重要引用‧參考文獻
推薦文:福島,你好嗎?(彭明輝)
台灣版序:紀念福島核電事故三週年(高橋哲哉)
前言
第一部 福島
第一章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
輕忽釀大禍
身為福島之子
身為首都圈的一員
我該如何討論核電事故?
〈核電,一個犧牲的體系〉(《週刊朝日 緊急增刊 朝日新聞》)
第二章 再論核電犧牲體系
何謂「犧牲的體系」
第一重犧牲──嚴重事故
暴露在輻射線下的不安
對當地產業的重創
對福島縣民的歧視──「輻射會傳染」
「要把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