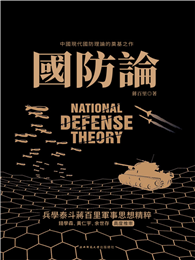戰爭如何創造歷史?戰爭如何孕生社會?戰爭如何形塑人們的主體經驗?
克勞塞維茲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由汪宏倫主編,朱元鴻、汪宏倫、姚人多、莊佳穎、彭仁郁、黃金麟、趙彥寧、鄭祖邦、藍適齊等專家學者所撰寫
《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
則是指出:「社會是戰爭的延續」
戰爭是形塑人類歷史的重要力量,也是探討現代性(modernity)不可或缺的一環。《戰爭與社會》共分十章,是台灣社會學界對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集體努力成果,十篇專文從理論、歷史、到主體經驗,次第開展,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思考圖像。
《戰爭與社會》結合台灣、東亞與世界的脈絡,為相關議題的探究,開啟新的方向。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汪宏倫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社會系兼任副教授,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與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研究涉及台灣、中國與日本民族主義,致力探討東亞現代性中戰爭、情感與價值觀諸問題。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與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作者簡介
汪宏倫(導論、第三章)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曾任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訪問學者。研究涉及中、日、臺民族主義,探討東亞現代性中戰爭、情感與價值觀諸問題。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與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鄭祖邦(第一章)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社會學理論、政治社會學。目前主要研究重點為戰爭與現代社會理論、九○年代以來台灣的國家構成與民主發展之研究。
朱元鴻(第二章、第六章)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以及約廿餘篇期刊論文,編有《孔恩:評論集》(與傅大為合編),主編《理論與當代戰爭》麥田翻譯書系(2003-2010),《文化研究》創刊主編(2003-2011)。研究興趣包括社會思想史、當代社會文化理論、都市民族誌。目前在撰寫《自閉症與我們的時代》,一個醫療概念史的跨文化研究。
黃金麟(第四章)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學理論、近現代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身體社會史、戰爭與現代性等。著有《歷史、身體、國家》(2001, 2006),《政體與身體》(2005),《戰爭、身體、現代性》(2009)等書及相關論文。
姚人多(第五章)
英國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領域為歷史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目前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台灣人第一次遭遇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經驗。
藍適齊(第七章)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日本東京大學。主要研究興趣爲台灣史、近現代東亞史、民族主義╱歷史記憶╱認同建構。研究成果曾發表於positions: asia critique, China Journal,『軍事史学』(日本)等期刊。
彭仁郁(第八章)
巴黎狄德羅大學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博士。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認證之精神分析師。博論於2007年獲法國「研究世界」獎後,改寫為專書《亂倫試煉》(PUF, 2009)。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嘗試探討精神分析之當代性、人為暴力創傷與療癒。
趙彥寧(第九章)
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歷年來研究主題包括性/別與酷兒、國族主義、國家暴力、國境管理與跨境遷移。著有專書《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巨流,2001),與數十篇國內外期刊及專書論文。
莊佳穎(第十章)
莊佳穎,英國蘭開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 UK)社會學博士,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同時兼任台師大國際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及東亞流行文化學會理事長。學術研究興趣為民主化與消費社會、國家認同與每日實踐、流行文化等,目前正在執行的研究計畫為「可愛文化的台灣實踐」。(FB:laalaapiano@ntnu.edu.tw;網站:http://www.xiaoying.idv.tw)
章節試閱
導論: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
汪宏倫
凡是認真思考歷史與政治的人,莫不留意到暴力在人類事務所扮演的巨大角色,但乍看之下令人訝異的是,暴力很少被單獨挑出來特別討論。……這顯示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遭到忽略;沒有人質疑或探究這看起來眾所周知的事。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1970)
上述這段話,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在其膾炙人口的小書《論暴力》中提出來的。鄂蘭引用列寧,指出二十世紀其實是個暴力充斥的世紀,而她所針對的,除了左翼與後殖民的暴力反抗理論(如馬克斯與法農)外,也包括了戰爭與革命的集體暴力。這段話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東亞來看,同樣也十分貼切,發人深省。環顧四周,當前東亞區域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點,幾乎都與國家的集體暴力極端形式──戰爭或戰爭遺緒(即戰爭所創造或殘留未決的問題)──有關。即以各國內部的基本重大社會分歧來說,台灣所謂族群、國家認同與統獨問題,說到底,其實是個戰爭遺緒的問題;韓半島的分斷體制與反美民族主義,是個戰爭遺緒的問題;日本的「新民族主義」、「歷史修正主義」、「和平憲法」與沖繩美軍基地爭議,也是戰爭遺緒的問題;中國內部的「新民族主義」、新疆與西藏問題,不同程度上也是戰爭遺緒的反映。除了內部的社會分歧外,在各國之間存在的重大爭議,也幾乎都和戰爭遺緒有關,包括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日韓之間的領土糾紛與仇恨記憶、中日之間有關歷史記憶的爭議(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等),乃至近年來牽涉中、日、臺三方的釣魚台/尖閣諸島紛爭等。這些爭議或問題,究其源頭,無一不指向戰爭,尤其近代(十九世紀以來)發生在這個區域的各個大小戰爭。
何以說這些問題都和戰爭有關?以台灣社會最為切身的統獨問題或國家認同問題為例,其實這也是從十九世紀以來一連串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後果。如果不考慮鄭成功擊退荷蘭人與施琅攻台之役,和台灣歷史地位命運息息相關的戰役就有:中日甲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包含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乃至韓戰。這裡面只要有任何一場戰爭的勝負逆轉或是未曾發生,今天的台灣社會內部的主要分歧(無論是統獨、族群、民族主義、國家認同等),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樣貌。每一種有關台灣地位與前途的論述,幾乎都是在肯定或否定前面戰爭的結果,或對之進行片面的歷史闡釋。在此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國族問題本身即是東亞戰爭遺緒的一環。再以中、日之間紛擾多年的所謂「歷史認識」問題為例,幾乎所有的爭議,都是集中在如何記述(與紀念)中日戰爭的問題,因此所謂「歷史認識」,其實是個「戰爭認識」的問題。同理,兩岸之間其實也是「戰爭認識」問題,也就是如何詮釋戰爭(國共內戰)的意義、如何看待與處理戰爭結果的問題。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背後都隱含著對戰爭及其後果的態度與評價,雖然這些態度與評價在大多時候並沒有言明。
過去十多年來,我們也觀察到關於戰爭遺緒的研究與討論──如戰爭記憶、戰爭責任、創傷與賠償等問題──陸續增加。即使在非學術的文化與媒體領域,我們也看到關於戰爭及戰爭遺緒的文學、報導、戲劇、電影與藝術創作越來越多。控訴國家暴力與戰爭傷痕的論述與活動日益頻繁,例如原殖民地出身的日本兵與慰安婦向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與賠償。在當前的東亞社會,從台灣、中國、日本、韓國、沖繩等地,處處可見戰爭所留下來的遺緒與國家暴力的傷跡,人們忙著撫平傷痕、保存記憶、控訴迫害、要求賠償、反抗壓迫。這個趨勢的背後有幾個成因,其中之一是冷戰體制的瓦解。1989年之後世界局勢劇變,東歐與蘇聯共產政權一一解體,美蘇兩大陣營相互頡頏的局面不再,使得冷戰體制在東亞也產生鬆動,區域局勢重整,許多原本被壓抑凍結的戰爭遺緒問題逐一浮現。另一方面,歷史週期感與世代意識也是刺激戰爭記憶論述與研究的因素之一。所謂歷史週期感,指的是人們對於特定數字的週年總是存著必須特別加以紀念的心理傾向,而戰爭記憶便會被週期性地反覆炒熱。至於世代意識,牽涉到的是某些參與或經歷過重大戰爭的世代,當人們意識到這個世代逐漸開始凋零時,產生一種「留下歷史見證」乃至「搶救歷史記憶」的努力。這種趨勢在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在近二十年來的日本尤為明顯。由於敗戰之故,日本社會對戰爭與軍人的評價在戰前戰後完全逆轉,許多曾經參與「大東亞戰爭」的士兵在返回故里之後絕口不提戰場經歷,成為一個噤聲沈默的世代。直到最近,這些逐漸凋零的沙場老兵開始發聲訴說自己的故事,有些為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惡行道歉反省(最知名的是前幾年過世的東史郎),有些則嘗試撫平戰爭創傷,乃至為自己與昔日同袍平反,嘗試挽回「大東亞戰爭」的榮光。
的確,環繞著戰爭與戰爭遺緒的論述與實作正在大量增加中,但令人好奇而不滿的是,除了少數的例外,少有人反省戰爭作為集體暴力的本質,或深入探討戰爭對近現代東亞的意義。如鄂蘭所指出,從克勞塞維茲到恩格斯,從左派到右派,大部分的論者都只是把戰爭視為政治或經濟的延續,因此主要的分析概念語彙仍是帝國、殖民、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鄂蘭指出,戰爭與暴力的任意性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遭到忽略;但在當前的東亞,戰爭所造成結果的任意性並沒有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是不斷受到來自不同陣營與立場的人持續挑戰,也因此引發種種爭議。所謂歷史認識問題,很大一部份是如何詮釋戰爭,如何合理化暴力的問題;而所謂記憶與遺忘的政治,則無非是戰爭以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因此戰爭的記憶,很容易就變成記憶的戰爭。在此意義下,戰爭從未結束,只是從軍事場域進入到符號象徵的場域。因此,在歷史認識的爭議中,我們只看到不同立場的人們把戰爭從軍事場域延伸到象徵場域,然而這些爭議所缺乏的,卻是對戰爭或集體暴力自身的反省。難道戰爭只是個隨機的變數,而歷史的闡述,居然只是這些隨機變數的函數結果?
上面的考察使我們發現,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看似和平的年代,但無論從時間或空間來看,戰爭離我們其實不遠;更重要的是,我們一直生活在戰爭遺緒當中。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當代的社會,某種意義下其實可說是「戰爭所孕育出來的社會」(荻野昌弘2013)。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在主流社會學中,戰爭似乎是個不受重視的研究領域,這個狀況直到近年來才有所改變。的確,戰爭可說是人類社會恆常存在的現象,它的歷史幾乎和人類的歷史同樣悠久。戰爭是形塑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探討現代性(modernity)問題時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相較於其他現代性的議題領域(例如資本主義、工業化、官僚化等),當前的社會科學對於戰爭的探討與研究卻相當地少,關於戰爭的理解也仍舊處於低度理論化的狀態。主流教科書中的古典社會學幾乎不處理戰爭,孔德與史賓塞等人甚至認為現代工業社會與過去的軍事社會不同,將逐漸遠離戰爭、邁向和平。社會學家缺乏對戰爭的關注,這似乎已經是個「共識」;晚近幾乎每一位觸及戰爭此一研究主題的社會學者,都會肯認並檢討這個事實。然而,從社會學的發展史來看,早期的社會學者並不缺乏對戰爭的關注,但耐人尋味的是,在社會學建制化的過程中,歷經兩此世界大戰,那些戰爭與軍事的主題反而被逐漸篩選過濾掉,尤其二戰以後,以美國社會學為首所建立的主流社會學對戰爭的議題並不重視,甚且在理論與研究中有意無意忽略。這背後有著看似弔詭的知識社會學原因:提倡和平價值的自由主義,以武力擊敗了尚武的法西斯主義。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發展出來的美國主流社會學,有意無意地貶抑暴力與戰爭,具有代表性的結構功能學派,明顯地流露出將社會和平化(pacifying)的傾向。即使與結構功能學派對蹠的衝突學派,所關注的也是微觀或個人層次的衝突,而較少關注宏觀層面的國家暴力與武力衝突。
另一方面,英語的主流社會學界其實不乏「戰爭社會學」或「軍事社會學」的傳統,例如國際社會學會便有「Armed Force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而美國社會學會也有「Peace, War and Social Conflict」的研究分支(section)。就像社會學中大部分的次領域一樣,「戰爭社會學」與「軍事社會學」這樣的次領域,主要關注的是戰爭與軍事本身,而他們所做的研究,不外乎是採用社會學的理論、概念與研究方法,分析戰爭、和平、衝突、以及與軍事相關現象與課題。
然而,與前述「戰爭社會學」或「軍事社會學」的傳統有所不同的是,本書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戰爭與軍事本身,毋寧說是嘗試將戰爭納入社會學的整體思考中,除了「將戰爭問題化」之外,更企圖探討戰爭與其他社會現象(例如宏觀層次的歷史社會變遷、人口遷徙流動、政治治理、以及微觀層次的個人生命經驗、記憶與創傷等)之間的關聯──一言以蔽之,即戰爭的非軍事面向(non-military dimensions of war)。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關懷,和歷史社會學中所謂「新韋伯學派」較為接近,但企圖更為寬廣一些。簡單地說,所謂「新韋伯學派」,是把權力、暴力與衝突帶回被帕森思所「結構功能化」的韋伯理論中,探討暴力與衝突在大規模歷史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代表性的學者,如Theda Skocpol(1979),Charles Tilly(1985, 1992),Michael Mann(1986, 1988),Anthony Giddens(1985)等人,都曾在他們的歷史研究或理論著作中將戰爭納入分析。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把戰爭與暴力納入視野,尤其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對戰爭與暴力的關注明顯增加,而探究的主題,除了國家形成與國族建構等典型議題外,還包括了將平民納入戰爭體系的動員過程、敵我關係的建構與處置、以及戰爭中的意義追尋、認同與記憶的建構等議題;重新將戰爭帶入理論思考與模型建構,也成為新的趨勢(Kestnbaum 2005, 2009, Joas 2003, Malešević 2010, Joas and Knöbl 2013, Wimmer 2013)。
把視野拉回與台灣較為接近的日本來看,日語學界向來不缺乏對戰爭的思考與反省,與戰爭相關的研究也極為豐富,這和日本特殊的歷史脈絡與國族情境有關。由於戰敗的經驗、以及特殊的和平憲法,日本的知識思想界對於戰爭(與和平)的探索可說不遺餘力。不過,過去大部分的著作,多集中在人文學科領域(例如史學、文學、哲學等),相對來說,社會學(或廣義的社會科學)的研究還是較為少見。近年來,社會學界也有逐步將之理論化與系統化的努力,其中較值得矚目的是關西學院大學社會系的荻野昌弘所主持的「戰爭所孕育的社會」研究計畫的系列成果(荻野昌弘2013,島村恭則2013),以及年輕一輩的社會學者近年來所提倡的「戰爭社會學」,例如野上元與福間良明(2012)所編的《戰爭社會學書籍導讀:解讀現代世界的132本書》,以及上述二人結合其他學者所編的《戰爭社會學的構想:制度、體驗、媒體》(福間良明、野上元、蘭信三、石原俊2013)等。顯然地,如何把戰爭適切地納入社會學研究視野,並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專長來對戰爭及其相關現象進行分析,在當前的日本學界也是個方興未艾的主題。
在台灣,情形多少有幾分類似。雖然近年來也開始有不少歷史學者針對台灣的戰爭記憶與戰爭遺緒從事整理考掘的工作,但主流社會學對「戰爭」這個主題仍大多保持緘默。社會學界將戰爭當成研究主題的努力並非完全沒有,但相較於其他蓬勃發展的領域與主題(如經濟社會學、階層化研究等),畢竟仍屬於零星少數。黃金麟與朱元鴻都曾經針對「戰爭與現代性」以及「戰爭/內戰」等主題,舉辦過研討會,黃金麟(2009)的歷史社會學專書,也突顯出戰爭作為主題之一。鄭祖邦(2006)的博士論文,則可說是第一本以戰爭為主題、嘗試將戰爭理論化的博士論文。這些先驅性的努力,為本書奠定了基礎,而上述的學者們,也都成為這本專書的貢獻者。
在上述背景下,這本書可以說是台灣社會學界(或廣義的社會科學界)嘗試將戰爭主題化(thematize)與理論化的集體努力。它並非只是一般的「會議論文集」,而是具有清楚而強烈的研究議程設定(research-agenda setting)的意圖。雖然限於時間與人力,我們無法窮盡所有與戰爭相關的可能議題,但以目前的論文組成來說,已經相當完整地涵蓋了在台灣從事戰爭與社會的研究時,應該碰觸到的層次、面向與議題。而這樣的研究議程,也反映在本書的章節安排上。
這本書呼籲「把戰爭帶回來」,意思當然不是要重啟戰端、也不是要宣揚什麼尚武精神或軍國主義。這句話的靈感來自1985年出版的《把國家帶回來》(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一書。在這本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社會學文集導論中,編者之一的Theda Skocpol呼籲把長期受到社會學與政治學者忽略的「國家」帶回社會科學的分析,進而提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Skocpol 1985)。同樣地,把戰爭帶回來,意思是把戰爭重新帶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當成一個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線索來看待。這條線索,可以追溯到克勞塞維茲的經典命題,也就是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在其經典名著《戰爭論》中,克勞塞維茲提出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命題:「戰爭無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續」(Clausewitz 1976: 87)。這個命題長久以來影響人們對戰爭的思考:戰爭只是一種手段、一個政策工具,政治才是最後的目的。或許是因為如此,戰爭一直被視為是個暫時的過度階段,而不是恆常狀態。然而,一個多世紀之後,傅柯將克勞塞維茲的命題做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為戰爭與政治的關係開啟了新的詮釋空間。傅柯宣稱:「政治乃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Foucault 2003: 48)。這個翻轉命題並非只是玩弄花俏的概念修辭或語言遊戲,而是富有深刻的寓意與洞見。傅柯的這番話隱含著「對內」與「對外」兩層解讀的意義,而這兩層意義,都牽涉到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在對內的層次上,戰爭指的不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一種「社會內戰」;這種社會內戰指的也不是實際發生的戰爭,而是指不同個體與群體之間蘊含的內在衝突狀態。換句話說,這裡的戰爭作為一種隱喻被擴大解釋,用來描述權力的運作模式。在此,「政治乃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其實呼應著韋伯對國家與權力的界定:國家是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社群,而權力則是在即使面對抵抗的情況下也能使他人參與共同行動的實現意志能力(Weber 1958: 78, 180)。如果我們對照克勞塞維茲把戰爭視為「以暴力迫使敵人屈服於己方的意志」的行為(Clausewitz 1976: 75),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傅柯把政治視為戰爭的延續──戰爭與權力都是要屈服對方的意志,僅僅是形式不同而已。然而,正是這種混淆了權力與暴力的觀念,引發鄂蘭的不滿與抨擊。對鄂蘭來說,權力指的是人類群體協調行動(to act in concert)的能力,是共同生活必然的產物,因此權力並不屬於個人,而屬於群體。權力並不需要被正當化(justified),但需要合法性(legitimacy)。相對地,暴力只有可能是一種工具,使用暴力必須有正當的理由,因此暴力必須被正當化,但暴力毫無合法性可言。對鄂蘭來說,現代政治最根本的謬誤,就反映在韋伯對國家與權力的界定上:暴力不可能是「合法」的,而權力也不是暴力,並不以屈服別人的意志為行使條件。傅柯把政治視為戰爭的延續,從經驗現實的意義上來說,的確相當精準地捕捉了現代政治的現況;但從規範意義來看,這無疑是現代政治(或者廣義地說,現代性)的問題根源之一,也正是鄂蘭在《論暴力》的第二節中所尖銳批判的(Arendt 1970: 35-56)。
在對內的層次上,傅柯的翻轉命題主要聚焦在「治安的裝置」,也就是國家如何透過生命政治的統治技藝來壟斷暴力與行使權力;在對外的層次上,傅柯則是討論了「軍事─外交的裝置」,所謂「安全體系」(2007: 296-7,另參見本書第一章)。在此,我們回到了傳統或一般意義下的戰爭,也就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傅柯翻轉克勞塞維茲命題,是在1976年的課堂演講《必須保衛社會》(Foucault 2003)中,而他聚焦討論「領土、人口與安全」的議題,則已經到了1978年(Foucault 2007)。此時傅柯已經不再強調「政治是戰爭的延續」,而是在國家主權的戰爭中再次肯認了克勞塞維茲的命題(2007: 305-6)。然而,恰恰是在這點上,傅柯錯失了擴大他自己的理論洞見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正是本書想要進一步深化與挖掘的。政治是戰爭的延續,這裡的戰爭不僅僅是個隱喻,而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歷史上的戰爭。如本文一開始所述,當今東亞各國內部與外部之間所存在的重大分歧,其實都與十九世紀以來的各場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當前的各國內部(國族)與外部(國際)的政治,都是過去戰爭的延續。台灣內部的藍綠/族群問題是如此,海峽兩岸的統獨問題是如此,中日、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與歷史記憶問題,莫不都是過去戰爭「透過其他手段的延續」。更進一步說,由於國家的擴張滲透使得政治權力在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戰爭也就透過政治而變得無所不在。在此情形下,我們想要探討的是:戰爭透過什麼樣的手段、如何被延續?這些延續中的戰爭,對於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與樣態,有何關聯或啟發?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導引下,本書各章的主題與安排,背後有一定的脈絡可循。戰爭對社會的影響是廣泛全面且深刻久遠的,但在不同的階段,其作用與效應有所不同,我們嘗試以「戰爭」與「戰爭遺緒」來加以區分。質言之,若以「戰爭的發生與終結」來作為分界點,則本書的前五章所處理的,主要可說是「戰爭本身」(war itself),而後面五章,處理的則主要是「戰爭遺緒」(war legacies)。換句話說,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戰爭卻創造出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使得戰爭以其他方式延續著。當然,這樣的劃分並非絕對,例如第三章所提到的「戰爭之框」,其實也在戰後成為一種戰爭遺緒,繼續形塑人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整體而言,這十篇文章所設定的研究議程,可以總括在四組座落在不同層次的問題意識之下:
第一組問題,主要關切的是理論與宏觀歷史(macro history)層次的問題:如何將戰爭理論化?戰爭在過去的社會理論中曾經被如何概念化?戰爭與現代性有何關聯?作為「壟斷合法暴力」的現代民族國家如何出現、與戰爭的關聯為何?從十九世紀以來,環繞著戰爭與國家暴力的現象與概念,歷經了什麼樣的變化?什麼樣的理論概念或分析架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戰爭及戰爭遺緒?而戰爭與戰爭遺緒,又如何形塑、框架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本書的第一、二、三章,可說分別從不同的理論層次與面向,嘗試對上述問題提出答案。
第二組問題,則是對戰爭期間(wartime)與戰爭狀態(the state of war)的具體分析。處在戰爭期間的國家,如何遂行動員、並進行統治?而長期處在「戰爭狀態」之下的社會,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戰爭與治理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國家如何兩面作戰,一邊對付「外部敵人」,一邊對付「內部敵人」?在什麼意義下,我們可以像傅柯一樣翻轉克勞塞維茲的命題,宣稱「政治是戰爭的延續」,甚至如第五章所宣稱,「社會是戰爭的延續」?這是第四與第五章所探討的主題。
第三組問題,則是戰爭所牽涉的倫理問題,包括終戰之後的正義,以及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戰爭是一種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展現,要訴諸戰爭,必然牽涉到「是否應該使用暴力」、「如何正當化戰爭」的倫理問題,而這也是「正義戰爭」這個古老概念所探詢的課題。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還有更為複雜而艱難的倫理問題等待解決:戰爭犯行如何界定?戰犯要由誰、如何審判?正義如何恢復、或得到確保?我們是否應該寬恕、又該如何寬恕?戰爭應該如何被人們記憶、或不被記憶?哪些人與事被記憶,又有哪些人與事被排除在記憶之外?戰爭的記憶與權力及認同之間,構成了什麼樣的回路?對照於記憶所造成的負擔,遺忘是否更好、甚至必要?本書的第六、七、十章,便專注探討上述有關戰後正義與戰爭記憶的問題。
第四組問題,則是從微觀或個體的層次,探索戰爭之「零餘主體」與負面經驗。所謂「零餘主體」,是相對於冠冕堂皇的「戰爭之框」所建構出的國族主體(見第三章),指那些被排除在框外、或是被壓抑忽視的主體。這裡面包括被國家利用後卻遭到拋棄的戰犯(第七章)、慰安婦(第八章)、以及因為戰亂所造成的流亡主體(所謂「外省人」,第九章)。這些零餘主體,在戰爭期間與戰爭之後所經歷的是什麼樣的生命經驗?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戰爭其實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現象,通常由男性所發起,被動員到戰場上從事戰鬥行為的也絕大多數是男性。那麼,女性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體驗過的經歷,又是如何?性與性別,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戰爭與戰爭遺緒?戰爭對個人所造成的種種創傷,又該如何理解、如何療癒?第八章與第九章,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省思。
循著上面四組不同層次的問題意識,本書各章的論證次第開展,從理論、到歷史、再到主體經驗,彼此之間形成了有機的對話。第一章從宏觀歷史與理論的層次,為我們梳理了戰爭與現代性的關聯,並探討社會理論中的戰爭如何被概念化。鄭祖邦追本溯源,從馬基維利與克勞塞維茲開始爬梳戰爭與現代性的接合點。馬基維利對國家理性的強調,預示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將會取代過去羅馬帝國的統一權力,而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尤其是「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此一知名命題,則是為民族國家使用武力的正當性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與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深刻影響了韋伯對現代國家與地緣政治的思考,尤其反映在他〈就職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等前後期著作中。對韋伯而言,現代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的特殊性是建立在「合法暴力的壟斷」上,因此武力的運用,便成了思考政治倫理的關鍵,而韋伯也據此發展出他知名的「支配類型」與政治倫理學說。韋伯對國家理性與正當暴力的強調,長期主導了學界對戰爭與民族國家的看法,也啟發了後來被稱為「新韋伯學派」的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不過,傅柯權力理論的出現開始改變了這樣的局面。馬基維利與克勞塞維茲的影響再度浮現,但也得到了新的闡釋與修正。傅柯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知名命題,強調「政治是戰爭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傅柯以「戰爭狀態」來認識權力關係的特性,而藉由翻轉克勞塞維茲的命題,傅柯也批評了霍布斯的「契約─壓制」權力模式,強調「戰爭─鎮壓」的權力模式。另一方面,傅柯的「生命政治」與「治理性」的概念,同樣也翻轉了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後者僅強調了「國家的保存」,而前者更關心的是「力量關係的保存、維持與發展」。鄭祖邦對馬基維利、克勞塞維茲、韋伯與傅柯四人的理論影響與對話的考察,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將戰爭理論化」,而近年來恐怖主義與去疆域化的戰爭,也使理論化的工作面臨的新的挑戰。
第二章幫我們梳理了過去一百年來關於戰爭與革命相關現象與概念的改變。朱元鴻首先批評了諸多作者與理論家將19世紀視為「和平的世紀」的盲點,指出其背後帶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進入二十世紀後,隨著兩次大戰的開展與落幕,西方與全球對於戰爭的觀念與態度也有所轉變,使得戰爭更為「文明化」或「人道化」。朱元鴻也引用了鄂蘭,指出戰爭與革命可以說是現代世界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催化因素,而戰爭與革命之間密切相尋的組構關係,也切入了兩者之間所有暴力或非暴力的反抗/鎮壓形式。本章進而探討了1918年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的「戰爭共產主義體制」(War Communism)模式,以及其後藉武裝衝突而蔓延興盛的戰爭革命模式,包括毛澤東時期的中國、1975年後的越南、以及波帕的赤柬政權等。相對於此一戰爭革命組態,則是一種非暴力的政治鬥爭模式,作者稱之、為「公民抵抗」。這種強韌的模式,可見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希臘、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國家在之後的八○年代相繼跟進的民主化革命,八○─九○年代中東歐推翻共產政權的社會革命,乃至2011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從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來看,可以發現「戰爭共產主義」的模式逐漸減少,而「公民抵抗」的模式增加。這一消一長之間,作者歸納出其背後的條件與背景,包括農民戰爭的消失、殖民主義的終結、烏托邦的失落、選舉權的普及、全球治理機構的介入、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全球媒體的即時報導、以及互聯網的政治動員潛力。
第三章處理的則是處理戰爭如何改變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而人們又如何感知戰爭的問題。汪宏倫結合了社會學者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與Judith Butler的同名書,提出了「戰爭之框」之框的概念,藉此說明戰爭如何框構世界(framing)以及被框構(framed)的過程與作用。戰爭之框主要的作用在區辨敵我、劃分出「可悲傷的生命」與「不可悲傷的生命」。一場戰爭可能創造出新的認知框架,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而這樣的框架可能延續到戰爭結束,成為國族之框,繼續形塑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在所有的民族主義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戰爭之框。本章進一步分析了存在於日本、中國與台灣等地的不同的戰爭之框,指出這些戰爭之框如何被塑造出來,又如何形塑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本章嘗試指出,這些不同的戰爭之框,除了造成社會內部的分歧(如日本與台灣)之外,同時也造成不同社會之間的對立、導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本章的結論則是再一次碰觸到戰爭與現代性的問題,指出東亞的現代性與戰爭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國,人們都是透過戰爭(或戰爭威脅)來認識「何謂現代」的,在他們認識到西方現代文明之前,先見識到了西方的船堅砲利,而整個現代化的過程,可以說是伴隨著戰爭的經驗(無論戰勝或戰敗)一道開展的。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成了戰爭下的犧牲品,其主權歸屬也隨著不同戰爭的結果而有所變動。因此,本章主張,要理解東亞現代性,解開當前民族主義的死結,必要先從反省戰爭、清理戰爭遺緒著手。這是個難以迴避也無法繞開的問題。
第四與第五章的共同主題,是戰爭與治理之間的關聯。不過,兩篇論文的視角卻有明顯不同,提供了我們思考戰爭與治理之間關係的兩個不同面向。如標題所提示,第四章的重點放在統治技藝。黃金麟以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台灣稱為「韓戰」)為例,探討此一戰爭在中國國內的經營歷程(包括台灣問題在動員過程中的「隱形」)和其所涉及的戰爭動員技藝(如控訴會、決心會、愛國公約和各種革命競賽的進行等),如何與共產黨的建國(state-building)需要緊密相連。黃金麟斷言,如果沒有朝鮮戰爭,共產黨還是會以特定的方式從事建國工作,但肯定會和愛國主義高張,反美帝動作頻仍下的結果有所不同。「前方打美帝,後方挖美根」,成為中共建國初期營造統治權的有利基點。而以日本侵華的路線,做為美帝即將透過朝鮮侵略中國的比照路線,以此(歷史記憶和想像的恐怖結合堆砌)凝聚集體的意識和愛國情操,也分明表現在當時的群眾意識生產上。本章從理性與情感政治的分析,切入戰爭與治理的關聯。作者指出,就功能關係和因果角色而言,戰爭與治理有如連體雙胞胎,只顧及一方而忽略另一方,都無法對其中任何一方作清楚的分析。
第五章同樣也探討戰爭與治理的關聯,但切入的角度和第四章明顯不同。從表面上來看,這章似乎不是處理戰爭本身,而是把戰爭當成一種比喻,探討國家如何對付內部敵人,但事實上,我們不要忘記,其實本章所處理的兩個時期──日治初期、以及1991年以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兩場具體的戰爭是確確實實存在著的:日本殖民政府的征台之役,以及國共內戰。這兩個戰爭又分別具有不同的理論意涵。就前者來說,日本雖然在甲午之役打敗清廷,並根據馬關條約「獲得」了台灣這塊殖民地,但對於日本帝國來說,要接收這塊土地,還需要另一場戰爭。這說明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即使以武力擊敗一個「前現代帝國」,並依據現代國際法訂立了條約,但在接收一個「前現代」的戰利品時,仍要透過武力征服(對內壟斷暴力)的過程,而不識「現代國家」為何物的「無識土匪」林少貓與日本殖民政府的交涉過程與下場,竟透出幾許荒謬的喜感與悲涼!至於第二場戰爭──國共內戰,同時提醒我們戰爭對台灣的影響如何深遠巨大。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能夠以「敵人」的方式來處理「匪諜」,原因恰恰不是戰爭是一種「隱喻」,而是台灣的確處在戰爭狀態(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中。姚人多凸顯「戰爭狀態」以及「敵我區辨」等因素在決定台灣社會基本樣貌時的支配性力量,分析一個永恆處於戰爭狀態、被戰爭原則所支配與分化的社會,如何不斷地在內部搜捕「國家的敵人」。姚人多提出「社會是戰爭的延續」的主張,其實為傅柯翻轉克勞塞維茲命題,做了最佳的詮釋。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章與第五章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架構值得分析──冷戰。換言之,台海兩地的政權對峙,長達四十多年處在隱形的戰爭狀態中,其實是冷戰結構下的產物,而韓戰即是開啟冷戰序幕的關鍵一役。冷戰是另一個值得分析的議題,本書雖然沒有一篇論文是直接處理冷戰,但第四與第五章所處理的議題,其實也提醒我們,不該忘記冷戰的存在。
本書的後半部(六至十章),處理的主要則是戰爭遺緒。第六章探討了困難但重要的終戰正義的問題。戰爭結束了,但戰爭所創造與殘留下來的種種問題,才正要開始。朱元鴻指出,在每一場戰與內戰之後,總會衍生諸多關於正義、寬恕、和解、記憶、遺忘與否認等問題。尤其二戰以後的戰犯審判,更為戰後正義掀起了一番全球性的高潮。儘管正義與寬恕依循的是不同的邏輯,它們卻都同樣要求記憶的義務,因此也無可避免牽涉到歷史否認的問題。本章以尼采和魯迅作為引子,探討遺忘的力量,和操作化的正義與儀式化的寬恕形成對比。朱元鴻批判地檢視了對記憶的過度沈溺,以及將過去的苦難作為一種累積政治資本的盛行作法,認為以苦難悲情的記憶(大屠殺、二二八等)來作為國族經驗的基礎將導致難以解決的困境。本章最後對「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讎」這句出自魯迅《題三義塔》的著名詩句的另類解讀,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想像空間的可能。本章的結尾為讀者提示了戰爭終結的可能性,而其所碰觸到的記憶與遺忘的問題,則構成了第十章的主題。
第七、八、九三章,則可說是戰爭的「零餘主體」,他們是被主流的戰爭之框(或其後的國族之框)所排除或遺漏的。台籍戰犯、慰安婦與外省老兵,看似三個不同群體、不同屬性的人,但他們都是被主流的戰爭之框所形塑的國族敘事所排除、壓抑甚至刻意遺忘的一些人。他們都曾被不同的政權所動員、利用,但最後也都遭到被背叛的命運,成了零餘的主體。第七章的台籍戰犯,呼應了第三章「戰爭之框」以及第六章「戰後正義」的概念。什麼樣的正義才是正義?被不同國族的「戰爭之框」所排斥的群體,要向誰請求正義?本章同樣也使用了Judith Butler的「戰争之框」概念來探討台籍戰犯的問題。藍適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超過了二十萬名的台灣人被徵召到亞洲各地的戰場,其中超過三萬人喪命於戰場,更有上百名台灣人在戰後接受了各個盟國所進行的B/C級戰犯審判。但是在戰後的歷史書寫和集體的戰爭記憶中, 台灣人和臺灣本土的戰爭經驗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遭到邊緣化甚至忽略。作者分析戰後各盟國在其東南亞殖民地所進行的B/C級戰犯審判的審判紀錄、相關外交文件、和已經出版的口述歷史紀錄,發現在發還原籍執行刑期、赦免減刑、以及釋放及遣返等諸多「跨國性」的議題中,臺灣戰犯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國籍身份的界定等方面出現了許多的爭議。這些爭議過程凸顯了在多國和跨國的脈絡之下所進行的臺灣戰犯審判中, 臺灣戰犯的身份是處在一種矛盾而同時不穩定的狀態。在他們的身上,國家主權界限之間產生了彼此重疊和滲透的情況。更重要的是,上述的幾點爭議呈現出了二戰之後——在戰後新的國際環境、去殖民、和冷戰的脈絡之下——臺灣人及其戰爭經驗的「國族屬性」無法被清楚界定的情況。透過對台籍戰犯歷史的研究, 藍適齊指出,由於其「可悲傷性」未受到認定, 經歷過戰爭經驗的臺灣人他們的生命價值也未曾受到肯定, 進而導致了在戰後的戰爭記憶中對臺灣人及其戰爭經驗的忽略。
同樣處理的是「零餘主體」,第八章與第九章則把我們進一步帶入了微觀層次的分析。這兩章有不少共通的主題,其中之一是戰爭所帶來的創傷,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共同主題,則是戰爭中的性別與性。自古以來,發動戰爭、上戰場打仗的,絕大多數是男性;雖然歷史上不乏「巾幗英雌」或「聖女貞德」之類的記錄或故事,近年女性從軍也被常態化,但無可諱言地,從事軍事活動的仍是以男性為主,而戰爭也充滿了被視為「男性特質」的陽剛暴戾之氣。在此性別脈絡下,女性在戰爭與戰爭遺緒中扮演什麼角色?起過什麼作用?相對於男性的戰場經驗,女性在戰爭中又遭遇過什麼?彭仁郁與趙彥寧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十分不同的圖像。
彭仁郁的論文處理的是棘手而複雜的慰安婦問題。在以男人為主的戰場上,女人的身體被物化成洩慾的工具,藉以滿足無數男性士兵的生理需求。這種看似體貼士兵的「人道關懷」,卻導致了極度非人道的後果。日軍在二戰期間設立的「慰安」制度,可以說是「戰爭性產業」的極致,如同彭文指出,國家機器透過直接或間接暴力的手段取得性服務提供者的來源,不但剝奪人身自由,且對受害者的身體、心理施予折磨酷刑,而戰場上的殺戮氛圍所挑起的權力慾與面對死亡的焦慮感,更可能導致戰士以性暴力的形式作為發洩管道。這個由多重不平等所形成的暴力結構,在慰安婦的身心留下巨大深刻而難以磨滅創傷。彭仁郁也引用了Butler的「戰爭之框」概念,來說明這些女性的生命如何被排除在戰爭主事者的認知框架外。弔詭的是,戰後有關慰安婦的討論,卻在一度冷漠沈寂而又重新公開訴說後,引發種種爭議與議論,造成了這些阿嬤在生命暮年面臨二度傷害。透過心理創傷的精神分析研究,本章嘗試指出,創傷分析療癒的終點,可以是為主體社會實踐的起點,對主體特異性和詮釋權的重視,有助於使創傷憶痕表徵化,一方面協助敘說主體化的生成,令個別經驗敘事在匯入大歷史的同時,也能保留挑戰主流敘事的異質力量。這也是精神分析與社會學可以彼此銜接對話之處。
第九章處理的是因為戰爭而流亡的人們,尤其一般俗稱的「外省老兵」。雖然這群人和慰安婦所處的脈絡完全不同(曾經上戰場的男性士兵),但性、性別與創傷也同樣構成了趙彥寧這篇論文的主題。透過引人入勝的民族誌敘事,作者向我們展示了國共內戰及其後長達四十年的兩岸分隔,對當年隨著國府來台的底層士兵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創傷。這種創傷的核心情感有兩種來源,一是與母親/原鄉的強迫分離,二是被抓兵與從軍期間的苦痛與憤怒。創傷並非唯一的戰爭/流亡情感主軸,現代性的文化媒介(如電影、歌曲與象徵文字)不僅創發了新興多元的感知能力,更為個人所挪用以表述創傷情感。然而,經過四十年後,母親/原鄉雖然「失而復得」,卻不見得保證流亡身份的終結,反而可能引發另一段扭曲的生命歷程。透過分析榮民照顧體系中諸多看似瑣碎、服膺黨國霸權且違反「工具理性」的日常實作,趙彥寧分析了這些從沙場退下來的老兵如何建立起一種主流社會所難以理解的親密關係,成為自我滿意的照顧者。本章另一個值得留意的貢獻在於,一般對台灣所稱「外省人」,經常將之放在政治社會學的脈絡下以「省籍問題」或「族群矛盾」來理解。然而,如果放在戰爭與流亡的脈絡下來看,我們可以發現1949年隨國府遷台的「外省人」,其實是因躲避戰亂或政權更迭所造成的離散流亡者(diasporists),這樣的現象放到國際中極為常見,而這個以流亡主體作為戰爭遺緒的研究視角,也擴大了外省人研究的視野與可能的對話對象。
第十章處理的是另一種常見的戰爭遺緒,也就是戰爭記憶的問題。莊佳穎以2008年以後在台灣造成話題的三部電影──《一八九五》(2008)、《海角七號》(2008)、與《賽德克‧巴萊》(2011)──來探討戰爭記憶如何在新生代影視工業的文化生產中,被再現、再製和浪漫化。莊佳穎指出,戰爭在台灣社會具有三種層次的意義:存在於歷史和集體記憶中的戰爭、遍佈日常生活中的戰爭隱喻、以及影視文化商品中各種真實與虛擬的戰爭。在全球化風潮及消費主義興起之後,多年來盤旋於台灣人心底,長達半個世紀悠長而隱晦的戰爭記憶,逐漸幻化為透過科技和符號美學所呈現的表意系統。對於年輕世代而言,戰爭不再是一個具體、二元和絕對的概念,而是一個可被再製與消費、可供表述填充和組裝的流動意符。年輕世代透過一種由文化商品所建構的機制,去認識、揣摩和感受他們未曾經歷的戰役;在層疊的符號所交織的片刻虛擬實境中,動容於戰爭本身的殘暴和人類普遍的不幸。在此脈絡下,上述幾部由年輕世代所生產的電影,挪用了日本文化元素和好萊塢的文化生產格式,重新定義戰爭的記憶,並因此重新塑造了台灣電影文化的地景。這些被「輕盈化」的戰爭記憶,反襯出戰爭經驗本身的不可承受之重;而作者在最後提出的「歷史記憶的集體民主化」,也讓我們回想到第六章的沈重扣問:在「記憶─權力」的回路之外,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找到一種「不受仇怨禁錮的、不再教條僵化的、放下牽掛的、無憂的、不一樣的回憶」?
讀完這些篇章,讀者可能會恍然悟出,原來戰爭與戰爭遺緒,在我們生活的社會中幾乎無所不在。在台灣這樣一個深受重層戰爭遺緒影響的社會,忽略戰爭所留下來的深刻印記,是一件多麼令人惋惜的事。或者,換個角度說,對於過去歷史上多重戰事所留下的種種印記,在台灣社會並沒有完全受到忽略;從較為沈重的台籍日本兵、慰安婦、外省老兵與流亡經驗,到已經逐漸融入大眾文化與消費社會(尤其近年蔚為潮流的「文創產業」)的戰爭記憶電影、眷村懷舊文化、金馬戰地觀光,再到每日爭吵不斷的統獨議題等,台灣社會以不同的節奏、頻率、強度與比重,處理面對著這些不同的戰爭遺緒。然而,遺憾的是,人們很少把這些看似紛雜的現象與議題,系統性地放到戰爭與戰爭遺緒的脈絡下來整體觀照。把戰爭帶入我們的思考中,對於擴大視野、重新省察台灣與東亞的歷史脈絡,有著深刻的啟發與幫助。
本書各章所帶出來的研究議程,有一般性的普遍理論意涵,也有東亞與台灣脈絡的特殊性。這些篇章分別處理了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彼此之間可以形成有趣的對話,交織出不同的主題,本書目前採取的組織編排方式僅是眾多方式中的一種,讀者可以自行根據興趣作不同的創意組合。雖然單憑著一本書,很難完整呈現和台灣與東亞相關的戰爭與戰爭遺緒全貌,但無論就議題或主題來說,本書已經相當程度涵蓋了相關領域,包括戰爭與社會理論、戰爭組態樣貌的歷史演變、大東亞戰爭、國共內戰、韓戰(抗美援朝)、正義與寬恕、台籍日本兵、慰安婦、外省老兵、大眾媒體中的戰爭記憶等。這些論文,雖然不能說面面俱到鉅細靡遺,但基本上能夠反映出台灣(社會)學界對戰爭問題的集體努力的成果。這本書雖然不敢誇稱是「第一」,但至少是台灣社會學界少有的針對「戰爭」此一主題進行全盤思考與系統性考察的論文合集。我們期待它能夠具有開拓議題的作用,啟發學界對戰爭與戰爭遺緒的進一步思考與討論。當然,這背後還有許多未能提出深究的問題,例如冷戰結構的影響、反戰和平運動等,這些都有待未來研究者的進一步探索。
回到傅柯的翻轉命題:「政治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如果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是「政治無所不在」,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戰爭無所不在」──無論是作為隱喻的戰爭,或實際發生過的戰爭。重新審問戰爭,探索戰爭與政治間的複雜關係與多重變貌,將是反思台灣與東亞目前高漲的國族主義的一個契機。「把戰爭帶回來」,並不是要從事戰爭,而是要把戰爭帶回到當代政治與社會的討論核心之中;我們不僅要反省戰爭,更要反省戰爭在現代政治運作與社會形構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本書所要提倡的,不是一個新的「戰爭社會學」領域──這樣的領域在英語學界的主流社會學早已存在,我們的關心也遠比戰爭社會學來得廣。毋寧說,我們希望能夠這本書能幫助讀者們重新思考戰爭、認識戰爭、反省戰爭與各種形式的暴力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誠如Owens(2007: 149)所指出的,戰爭帶來許多迷思幻想,因為關於它的神話與謊言是如此強而有力;戰爭可說是眾多事物之根源,因為戰爭既破壞又創新、集毀滅與新生於一旦;戰爭刺激人們最大極限的想像,因為它把最為對立的事物壓縮到最短的時間與最小的空間內,把生與死的問題推到極限,逼使我們不得不去面對許多關於人類社會存在的根本問題。環繞著戰爭所引發的種種問題與現象,同時涵蓋了經驗的、歷史的、與理論的層次,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本書的標題幾經周折,最後仍定為「戰爭與社會」,便是著眼於戰爭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廣泛、全面、久遠且複雜。事實上,「戰爭與社會」在英語學界其實已經是個稍具歷史且半制度化的研究領域,不少大學設有相關的研究中心或學程,甚至有以此為名的學術期刊。不過,上述領域還是以歷史學的研究為主,社會學涉入極少,理論化的程度也較低。台灣也有不少歷史學者從事戰爭相關議題的研究,但似乎仍缺乏一個以「戰爭與社會」為整體觀照的問題意識。本書嘗試建立「戰爭與社會」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涵蓋理論、歷史與主體經驗,除了可以和國外既有傳統對話,也希望能號召更多不同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參與,共同開發此一課題。期待本書的面世,能為台灣學界對於戰爭與戰爭遺緒的整體思考,開啟新的視野與方向。
導論: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
汪宏倫
凡是認真思考歷史與政治的人,莫不留意到暴力在人類事務所扮演的巨大角色,但乍看之下令人訝異的是,暴力很少被單獨挑出來特別討論。……這顯示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遭到忽略;沒有人質疑或探究這看起來眾所周知的事。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1970)
上述這段話,是知名的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在其膾炙人口的小書《論暴力》中提出來的。鄂蘭引用列寧,指出二十世紀其實是個暴力充斥的世紀,而她所針對的,除了左翼與後殖民的暴力反抗理...
作者序
一本嚴肅的學術專書,頂著「戰爭」如此沉重的題目,似乎不該以過於輕鬆的話語開場,否則易顯突兀,反損整體價值。尤其這是一本集體創作,若是染上過多個人色彩,難保不招來居功掠美之譏。不過,每一本書的背後總有些緣起軼事,若不趁著寫序的時候交代,將來恐怕再無機會。
幾年前,在一個學術討論的場合,我力陳戰爭對理解當代社會的重要性,一位同事(顯然他沒有被我說服)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戰爭?我對戰爭沒興趣。我這個人熱愛和平,討厭戰爭。」
是的,我們假設大部分的人都熱愛和平,討厭戰爭,我自己也不例外。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心理傾向,使得我們有意無意忽略戰爭在日常生活與(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低估了戰爭對社會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和平據說是當今世上的主流價值,但人們似乎也因此不願正視戰爭。戰爭所引發的種種負面意象與聯想──殺戮、殘酷、死亡、動盪、離亂、悲慘、創傷──也使得人們易於壓抑與戰爭相關的記憶或想法。當我剛開始轉行投效社會學時,從來就沒想過有一天我的研究會碰觸到戰爭這個引人不快的幽暗題材。
戰爭作為學術研究的題材,並非完全不曾被碰觸過。在歷史學、政治學乃至文學與藝術,都不乏處理戰爭的研究。然而,在社會學界,這樣的研究尚不多見,也還缺乏系統化與理論化的知識努力。這本書,正是嘗試填補這樣的空缺。
上述的空缺也反映了一種普遍印象: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的,而戰爭並不存在於社會的日常運作中,因此社會學鮮少碰觸戰爭議題,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一個看似承平的年代,戰爭經常被視為是一種「例外狀態」。戰爭只發生在特定的時空脈絡,被鎖在某個記憶的角落。只有關心某一特定時空(例如研究戰時歷史的文史學者)或特定議題(例如軍事專家與國際關係學者)的人才需要關心戰爭,否則的話,戰爭和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實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這本書,便是嘗試扭轉這樣的印象。戰爭和社會的關係,其實遠超過一般的想像。許多人都曾聽過這麼一句話:「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本書則試圖告訴讀者:政治是戰爭的延續──不,不僅如此而已。整個社會都可說是戰爭的延續。你我生活所在的當下台灣社會亦然。
在研究東亞民族主義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戰爭對理解當代社會的重要性,而近年來國外社會學界出版的幾本英文專書,也印證了我的看法。然而,戰爭所牽涉的問題太多、影響層面太廣、太複雜,我發現一個人不可能處理周盡,非集體智慧不為功,因此興起了結合同道共同創作的想法。此時正好社會所蕭新煌所長責成我為所內籌辦一個小型研討會,我便利用這個機會,集結分散各地的朋友們,開了一場工作坊。這便是這本書的由來。
不過,要提醒讀者的是,這不是一本「會議論文集」,甚至不是一般意義下的「論文集」。這裡面的各篇論文並不僅僅因為在同一場會議發表而收錄在一起,也不是處理相近的題材而已。它們各篇之間彼此呼應,相互唱和,主題環環相扣,論證層層開展,從理論、到歷史、再到主體經驗,為「戰爭與社會」這個尚未完全成型的研究領域設定議題架構,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與其說是一本論文集,不如說是一部結合眾人心力、由九位作者共同譜寫的學術專著。
本書所收錄的各篇論文,是以2011年12月9日中研院社會所主辦、東海大學社會系協辦之「戰爭與社會」工作坊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另外再加上朱元鴻的《正義與寬恕之外:戰爭、內戰與國家暴行之後的倫理》一文而成。在工作坊的前後,我和各篇作者也曾在東海大學舉行過「會前會」與「會後會」,針對各篇的主題設計、寫作方向與全書的整體性,反復琢磨對話。當時參與工作坊的各場次主持人、評論人、以及現場聽眾都提供了具有啟發的意見,這些人包括了李丁讚、黃崇憲、蔡英文、柯志明、張隆志、陳永發、吳乃德、吳介民、黃丞儀、張茂桂、范雲、蕭阿勤、蘇碩斌等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同儕先進,在此重申謝忱。
這本書能以目前的樣態問世,要感謝許多人。首先是中研院社會所的蕭所長,如果不是他當初的督促與支持,我一開始的「集體創作」夢想大概沒有實現的機會。感謝《文化研究》期刊編委會,尤其是主編劉紀蕙與執行編輯陳惠敏,在原已繁重的編務之外願意接下額外的代審專書工作,幫忙覓得稱職的審查人選。感謝兩位細心負責的匿名審查人,接下吃力不討好的包裹審查工作;他們仔細閱讀了全書每一篇章,逐篇提供了許多精彩的洞見與建議,也給〈導論〉的寫作帶來許多靈感啟發。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慨允出版本書,從最初的工作坊籌備到最後的定稿成書,助理張育齊一路任勞任怨,協助整理文稿與所有煩瑣庶務,是幕後功臣。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每一位作者的貢獻與付出。如果沒有他/她們前後一貫的持續參與、以及對我這個主編的信任與包容,這個集體創作無法克竟全功。
過去幾年,我曾在台大與清大開設「戰爭、記憶與認同」的課程,原本以為是個冷門的題目,沒想到意外引來超乎預期的學生,其中不乏來自日本的同學。顯然地,戰爭看似離我們漸遠,但關於「戰爭與社會」的探究興趣,正方興未艾。最後,容我重複〈導論〉中的籲求:期許本書的面世,能讓「戰爭與社會」成為一個引發正視的研究領域,吸引更多研究興趣的投入,同時能為台灣學界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帶來刺激,開啟新的研究方向。
「把戰爭帶回(研究視野中)來」!
一本嚴肅的學術專書,頂著「戰爭」如此沉重的題目,似乎不該以過於輕鬆的話語開場,否則易顯突兀,反損整體價值。尤其這是一本集體創作,若是染上過多個人色彩,難保不招來居功掠美之譏。不過,每一本書的背後總有些緣起軼事,若不趁著寫序的時候交代,將來恐怕再無機會。
幾年前,在一個學術討論的場合,我力陳戰爭對理解當代社會的重要性,一位同事(顯然他沒有被我說服)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戰爭?我對戰爭沒興趣。我這個人熱愛和平,討厭戰爭。」
是的,我們假設大部分的人都熱愛和平,討厭戰爭,我自己也不例外。然而,或許正是因...
目錄
序
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
第一章 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鄭祖邦)
一、前言
二、戰爭與現代性的思想入口:從馬基維利到克勞塞維茲
三、戰爭與民族國家:韋伯的理論創始
四、戰爭與社會治理:傅柯的理論翻轉
五、結語:邁向一種戰爭的社會理論
第二章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朱元鴻)
一、百年和平
二、歐洲公法的輓歌
三、兩種革命/戰爭的場景
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
五、世界的內戰,冷戰
六、阿拉伯之春,公民抵抗的淵源與前景
七、世紀展望:相互依存的複雜性
八、結語
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
一、導言:東亞的國族問題與戰爭遺緒
二、理論與概念:戰爭、「戰爭之框」與國族建構
三、東亞的「戰爭之框」:日本、中國、台灣
四、結語:重審現代性——戰爭、國家與「合法暴力」
第四章 以戰為治的藝術:抗美援朝(黃金麟)
一、戰場與戰略
二、歷史的意義
三、競賽與公約
四、另類的交戰
五、戰爭與治理的辯證
六、結論
第五章 社會是戰爭的延續:日治時期以來台灣「國家的敵人」之歷史考察(姚人多)
一、傅柯的問題
二、敵人與戲碼
三、什麼東西沒變?
四、土匪與治安戲碼間的認知落差
五、土匪與良民
六、什麼東西變了
七、結論
第六章 正義與寬恕之外:戰爭、內戰與國家暴行之後的倫理(朱元鴻)
一、戰後正義(Jus Post-Bellum)
二、戰犯審判:歷史的判讀
三、戰犯審判:確立真相的檔案或是歷史否認的包裹?
四、寬恕:另一個全球化的劇場?
五、記憶與遺忘的政治?
六、遺忘:與時俱逝的腐朽或是迎展生命的能力?
七、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寬恕?還是遺忘?
第七章 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台籍戰犯(藍適齊)
一、前言
二、民間活動
三、中華民國政府的參與和立場
四、民間 VS. 國家
五、結論:戰爭記憶與台灣的身分認同
第八章 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彭仁郁)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意識
二、創傷研究的倫理質疑:方法論問題
三、戰爭與性/別
四、戰爭創傷的臨床論述
五、創傷主體真實的可共享性
六、說不可說、傾聽瘖啞
七、歷史銘印、共享記憶:真相版本之戰
八、結語:戰爭創傷敘事的歷史銘印
第九章 親密關係倫理實作:以戰爭遺緒的男性流亡主體為研究案例(趙彥寧)
一、導論
二、重建美好烏托邦的未來:照顧蔣公與懷念母親
三、國家給予的私下授受:延續生命的倫理實作
四、永續創傷化的流亡主體?:瀕死倫理實作的意義
第十章 浪漫的虛擬史詩:2008年後台灣電影中的戰爭記憶(莊佳穎)
一、前言:電影作為戰爭記憶書寫的所在
二、台灣,戰爭記憶小故事的漂浮之島
三、來自戰地的明信片
四、帶著戰爭傷痕的台日情意結
五、結論:在開放的歷史書寫空間裡自由飛舞
作者簡介
序
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
第一章 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鄭祖邦)
一、前言
二、戰爭與現代性的思想入口:從馬基維利到克勞塞維茲
三、戰爭與民族國家:韋伯的理論創始
四、戰爭與社會治理:傅柯的理論翻轉
五、結語:邁向一種戰爭的社會理論
第二章 百年來戰爭與革命組態的改變(朱元鴻)
一、百年和平
二、歐洲公法的輓歌
三、兩種革命/戰爭的場景
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
五、世界的內戰,冷戰
六、阿拉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