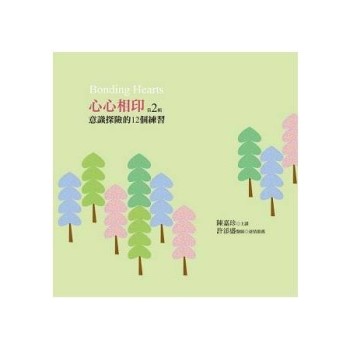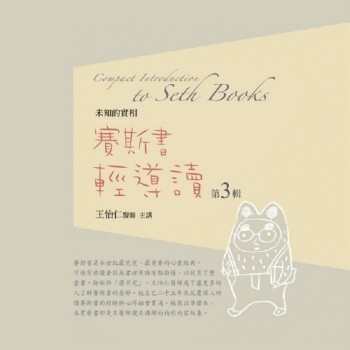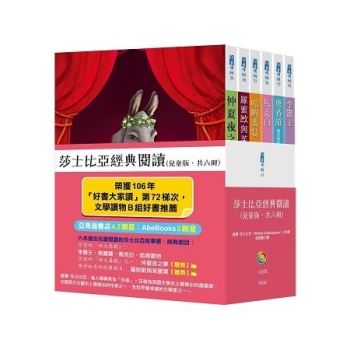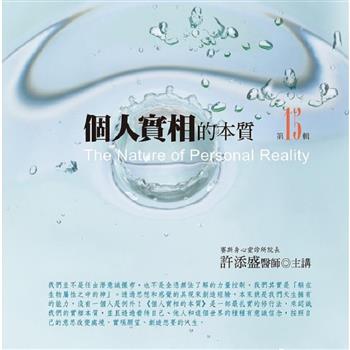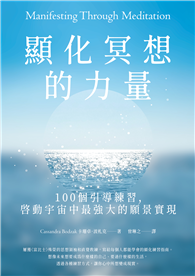第一章 還給荀子公正的評價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歷史、史學的存在若有意義,最主要應該就是提醒我們:不要把我們所過的現代生活,視之為理所當然。
一項簡單的事實:目前地球上有七十億人口,很多,空前的多、空前的擁擠,一個龐大、恐怖的數字,然而放入人類文明與歷史經驗中看,我們這六十億人都還是少數。光是從兩千多年前,幾個大文明在「軸心時代」燦爛開展算起,曾經在地球上活過的人口總數,是七十億的七到十倍。
死去的人比活著的人,多得多。他們死了,卻留下了他們如何過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處理自我與其他人關係……的種種痕跡。當前的七十億人不可能過著單一、同樣的生活,有其多元差異;曾經活過的五、六百億人,他們擁有的人間經驗自然更多元、有著更複雜的差異。歷史,保留了部分的多元、差異,在我們眼前顯示人是多麼奇特的動物,從個人到社會,存在著近乎無限的可能性。
面對這些歷史材料,尤其面對記錄古人智慧的經典,我盡量不做「古為今用」的解讀。不把這些文獻讀得好像他們是針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處境而寫的。「古為今用」是強調古代經典之現實意義的讀法,對我來說,一方面是一種「以少數扭曲多數」的霸道態度,另一方面更抹殺了在漫長時間中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關鍵訊息──別自大、別太自以為是,你的現實生活方式,不過是人類豐沛多樣經驗中的一種,在人類的可能性中只占據了很小很小一塊領域。自滿於這種現實視野,只會讓你錯失了原本存在於你身體裡、存在於你可以繼承的文明經驗裡的眾多其他可能性。
把古人說的話,改成像是我們自己講的,好像古人是在我們身邊一起搭捷運一起看電視一起和老闆開會的人,用我們熟悉、容易接受的詞語、觀念說話,這種作法既不公平,也不聰明。所以我選擇盡量(當然不見得一定做得到)將經典放回歷史中,理解經典的作者處於怎樣的時代,面對怎樣的環境,困擾於怎樣的問題,又努力試圖要尋求怎樣的答案。還有,他的所思所言,又是用怎樣的形式記錄下來,在時空變化中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才存留顯現在我們眼前。
把經典擺放回歷史中,於是經典和經典之間就產生了時代性的關聯,而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帶著時間、歷史概念讀經典,經典與經典之間就產生了「互文關係」,讀這本會幫助我們理解那本,或讓我們用不同眼光來看待那本。
例如說,讀過《戰國策》,對「縱橫家」的風格與行事有了確切的印象,知道了他們如何靠口舌的「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操弄外交與內政,於是閱讀《孟子》或《莊子》時,我們就會恍然大悟發現:雖然分屬於儒家和道家,兩人的想法、主張天差地別,但他們兩人表達想法、主張的方式,卻都是「雄辯」式的。在表達風格上,孟子、莊子和蘇秦、張儀有著高度親近性。
又例如讀過《禮記》之後,我們會對於周代的「禮」有較深入的了解,也就能從「禮」的角度去看待《孟子》書中關於「性善」的主張,體察出「性善論」和周代「王官學」傳統之間的密切關係。更進一步,當我們接觸到《荀子》的「性惡論」時,我們就知道這不單是荀子和孟子兩人在人性論上的主觀概念差別,後面更有著對於「王官學」傳統的大檢討,「法」逐漸取代了「禮」,成為社會組織的核心紐帶。
兩千年儒學真正的主流
由孟荀差異還原了孟子的思想大綱大本,我們就能看得清楚,孟子這種強調個人內在自主醒覺力量的看法,在中國傳統中,從來都不曾真正是主流。宋明「理學」中有「程朱」和「陸王」之爭,「程朱」強調的是「格物致知」、是「學」,「陸王」主張的則是「明心見性」。取徑上,「程朱」接近荀子,「陸王」接近孟子,兩派相持,勢力較大的,明顯是「程朱」一派,而且「程朱」還攻擊「陸王」「流於狂禪」,不是中國孔孟的正統,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禪宗影響的產物。
事實上,「理學」運動就是在佛教的刺激下產生的,「程朱」一派說「性」、說「理」、說「氣」,何嘗不是從禪宗那裡得了許多啟發?「程朱」攻擊「陸王」的理由,與其說顯示了「儒」和「佛」的差異,還不如說反映了長期以來不了解孟子、不能接受孟子理論的態度。
從政治上看,孟子更是邊緣。我們幾乎找不到哪個皇帝是真正相信孟子學說,遵從、實踐孟子政治理論的。雖然語言文字上都說「孔孟」、「孔孟」,然而若細究其內容,我們找到最明確的,往往是荀子的主張、教導。「性善」的啟發,明顯沒有外鑠教誨、訓誡來得重要。對必須統治龐大帝國的皇帝來說,當然也是藉由「學」讓人民行為統一乖順,要比保護人民、讓人民回歸自我本心,來得既容易又有利得多了。
許多被視為中國文化的長處,語言文字上歸於「孔孟」,實際上功勞應該追溯到荀子才對。同樣的,許多中國文化中被強烈批判攻擊的缺點,語言文字上也習慣怪罪於「孔孟」,其實往往「孔孟」是替荀子背了黑鍋的。
明明來自荀子的思想、學說,為什麼後來都不提荀子的名字呢?一個重要的理由,歷史上的理由,是:荀子去除了「禮」和「法」之間的絕然劃分,同時也就去除了原本儒家和法家之間最清楚的區別。孔子、孟子的思想絕對不可能和法家有所混同。荀子的「性惡論」實質上將「禮」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也就使自己的立場朝向當時日益壯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
荀子教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後來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發揮了極大作用,就是李斯;荀子思想還強烈影響了一位同時代的論著者,那是韓非。李斯、韓非都不是儒家,都和儒家沾不上一點關係,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從「秦王政」到「秦始皇」,從秦國到秦朝,荀子的聲望、地位一直很高。但也因為如此,到了秦滅亡之後,荀子的聲望、地位也就隨著秦及法家,快速崩落。
漢朝成立之後,花了六十年的時間,不斷摸索統治的方式。這六十年,可以用太史公司馬遷的一句話統括:「漢承秦弊」。六十年,唯一不變的政治價值是:秦朝是個鮮明的錯誤示範,如果秦朝不是那麼糟、不是錯得那麼厲害,那也輪不到沛下無賴劉邦取得天下。漢朝新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檢討秦的錯誤,無論如何不能重蹈秦的覆轍。
漢文帝時形成的「與民休息」原則,就是檢討中產生的初步答案。秦之所以滅亡,就是使民過度,讓人民受不了,紛紛揭竿而起。反其道而行,那就盡量不要擾動,盡量安靜,盡量少做。
漢武帝時終於建立起了漢朝自身的帝國統治法則,那是一套名為「儒術」實質上摻夾了許多陰陽概念的「天人感應論」,但既然名義上「獨尊儒術」,那當然還是把孔子抬了出來。孔子一時間幾乎都被神化了,然而相對地,曾經和秦朝、和法家有過密切關係的荀子,在這種氣氛下就不可能沾邊得到甚麼好名聲、好地位。
漢朝以降,雖然荀子思想的影響極大極深,卻因為和法家的歷史糾纏,使得他無法在儒家傳統中得到太多的肯定。荀子的影響作用和名聲地位之間,一直有著很大的落差。
第二章 儒者的變貌
賤儒和君子儒的分別
「古之所謂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可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古代有資格出來做官的士大夫,有這幾種基本的品質──老實忠厚,和合群眾,懂得選擇尊重對的價值,樂於和他人分享,遠離犯罪錯誤行為,認真探求事物的基本道理,而且視獨享富貴為羞恥。
「今之所謂仕士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以古代理想標準對照看,現今出來做官的士大夫,具備的品質卻是──骯髒隨便,破壞規矩,放縱慾望,貪圖私利,觸犯法令,心中沒有「禮」與「義」,只想著要享受權勢而已。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古今不出來做官的士大夫也有相異的品質。古代「處士」具備的品質是:道德高尚,安於平靜平淡,行為端正,不貪求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物(不做官是因為明白有些事是無法強求的),以自己的行為示範宣揚正確的道理。
相較之下,「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今天不出來做官的士大夫是這樣的人──用不做官不做事來掩飾自己沒有能力、沒有知識,在不受考驗的情況下宣稱自己有能力、有知識。明明利慾薰心貪得無厭卻假裝清心寡慾,行事虛偽汙穢卻硬是標榜自己謹慎誠實,故意凸顯自己不合流俗來取得流俗認同稱讚,不腳踏實地站好(「離縱」,離開了直線、正道)卻故意墊起腳尖來(「跂訾」)把自己裝成比別人高。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而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接著荀子就古之處士「知命者」的特性進一步發揮,探討甚麼是「士君子」自己能做能控制的,甚麼不是。君子可以自我控制、自我修養,給自己值得被人尊重的高貴特質,但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尊重他。他可以自我修養到值得信賴,卻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信任他。它可以自我修養到能夠發揮作用,卻沒有辦法保證、更沒有辦法強迫人家一定要重用他。
「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因而君子不在意人家攻擊、毀謗,卻極度在意自己身上有修養不夠的缺點。不在意人家不信任他,卻極度在意自己身上有不值得信任之處。不在意人家不重用他,卻極度在意自己能力不足。所以外界的讚美對他不構成誘惑,外界的批評詆毀也不會讓他擔憂害怕。他是個內在自足的人,依照自己相信的正確原則行事,嚴格要求自己,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傾斜偏離正道。這樣才是「誠君子」,真正由內修養的君子。
「《詩》云:『溫溫恭人,為德之基』,此之謂也。……」《詩經‧大雅‧抑》篇中有這樣的句子:看起來寬厚溫和,恭敬待人,能有這樣的外表,一定是因為內在有深厚的品德為其基礎吧!形容的應該就是這種「誠君子」。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真正的君子,內在修養會顯現在外表,從晚輩、子弟的眼中看去,他的模樣是:帽子高高的,衣服寬大,表情溫和,三項配合得很自然。給人的感覺是:嚴正、安詳、寬舒、包容、廣大、明亮、坦率。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暓暓然,是子弟之容也。……」從長輩、父兄的眼中看去,他的模樣是:帽子高高的,衣服寬大,態度樸實。給人的感覺是:低調、善良、容易親近、端正、勤勉、恭敬、忠誠、謙下。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官俛,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形容過真君子的模樣之後,荀子語帶不屑地說:接著讓我為你們描述一下今天這些號稱有學問的人又長甚麼樣子。他的帽子戴得低低的而且前傾,他的帽帶(「纓」)和腰帶(「禁」)都綁得鬆垮垮的,他的表情看起來很傲慢。真君子給人的感覺是一致的,今天「學者」給人的感覺卻是矛盾多變的:有時遲鈍得好像不會走路,有時又蹦蹦跳跳安定不下來;有時一句話都說不完整,有時又吱吱喳喳饒舌不停;有時面露恐懼、有時消沉沮喪、有時瞪著眼睛發呆。缺乏內在修養,因而外在也就沒有定性定貌。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訽。是學者之嵬也。……」在有吃有喝有聲色娛樂的場合中,他很容易就沉醉、迷亂了。在莊重的場合,他顯得慌張不自在或嫌惡不耐煩。遇到有事必須負責、必須工作時,他的態度是怠慢的、逃避的。既懶惰又懦弱,偏離正道,沒有廉恥之心不怕人家嘲笑辱罵,唉,這就是今日「學者」的鬼樣子啊!
「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荀子罵的這些「學者」是誰呢?會稱他們為「學者」,因為激起他心中最強烈不滿的,是和他同屬「儒家」,但不同派別的那些人。
老是把帽子戴得歪歪扭扭,說話平淡無味,和古代聖人僅有的相似之處在於走路像大禹一樣跛著(傳說與因為長年治水辛勞,到後來腿都壞了、跛了),像舜一樣低著頭不往上看往前衝(傳說舜因為謙下,所以總是低頭疾走),這是子張氏「賤儒」的模樣。
把衣服帽子穿戴得像模像樣,隨時維持莊重神情,擺出謙恭外貌卻一整天不說話,說不出甚麼有內容的話,這是子夏氏「賤儒」的模樣。
懶惰懦弱怕事,缺乏廉恥之心喜歡大吃大喝(「耆」同於「嗜」),老是掛在口中說:「君子本來就應該不勞動不勞累。」來自我掩飾,這是子游氏「賤儒」的模樣。
最後,荀子以自己、自己這派「君子儒」的對比性質當作結語:「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那種真正的君子不是這樣,安然自在卻絕不懶惰,勤勞不懈怠,掌握根本原理來應付不同的變化,不論如何變都能做得合宜,這樣才是學習、追仿聖人的正確方法。
由王官學向諸子學轉移
〈非十二子〉藉由批評、攻擊其他學說來凸顯荀子認定的儒家基本立場,描述了理想中「士君子」的內在與外表。除此之外,荀子還要藉由這篇文章顯現、確立他所繼承的子弓這派,才是儒家的正統。子思一派、子張一派、子夏一派、子游一派,都不符他認定的儒家標準。子思一派,因為前有孟子的張揚提倡,在那個時代影響特別大,就被荀子格外標舉出來,列在「十二子」之間。
第一個層次,在建立儒家核心價值上,〈非十二子〉言簡意賅地傳達得清清楚楚。「古之所謂仕士者」、「古之所謂處士者」,都有陳述,也碰觸到了「命」,討論了「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
第二個層次,在攻擊儒家以外的門派一事上,荀子的表現相對就沒那麼精確、精彩了,只是三言兩語快速帶過。說得那麼簡略,有立場上的不得已。若是真要好好評論各家學說,那就非運用「辯」的方式與技巧不可。但整體上,荀子又是反對「辯」,視之前的戰國雄辯風格為敗壞世局的罪過。他不願辯、不能辯,只願、只能以直白、強烈的口吻指責錯誤,卻沒有展開鋪陳真正的論理。
第三個層次,內鬨批判儒家其他派別上,荀子顯露出了最刻薄、最不容忍、最無法說理討論的一面。在文字中,我們毫無疑問感受到了他對子思、孟子、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的痛恨,卻沒有看到他解釋痛恨情緒的來源。顯然,在儒家核心價值上,這些人、這些派別不可能和荀子真的有巨大、根本的差異。然而正因為核心類似,內部的角力競爭就使得許多枝節、意氣長期糾結,那是講不明白的,那也是無從排解的。於是就只能訴諸於一些醜化的描述,充當這些其他儒家門派的罪狀。
荀子的目的,對外讓儒家成為諸子言論競爭中最值得信賴、採納的主張,對內讓自己所繼承的子弓這支凌駕其他派別,成為儒家的唯一代表。
從孔子到荀子,兩百多年時間,儒家有了很大的變化。今天我們無法確知儒家是如何得名的。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例如「儒」是用來指稱主持喪禮的人,「儒」是形容特別恭敬、格外柔軟柔弱的人等等,但從史料上看,這些說法都不是很有說服力。從史料上,我們比較有把握的認識是:第一,儒家的思想內容和西周封建制度中的「王官學」有密切關係;第二,儒家的建立,孔子是關鍵人物。
孔子的理想,是回復周代封建成立之初的秩序,所以他的信念和西周貴族教育很接近。不過孔子將這套貴族教育普及化,擴張成人格與品德的基本養成,又將這套貴族教育的外在儀式(「禮」)予以內在化,強調人的自我精神醒覺與修養鍛鍊。
因而,從教育內容、運用的材料上看,儒家沒有自己新創的東西,孔子的態度是「述而不作」,堅持自己只是將本來就有的「王官學」傳統予以恢復並發揚光大,不管詩、書、禮、樂、易、春秋,都不是儒家專有的,是所有其他家派也可以選擇汲取、繼承、運用的共同遺產。但是在解釋、看待這些共同遺產時,尤其彰顯其內在原則、根本道理上,從孔子以降,儒家卻有一種和傳統「王官學」很不一樣的立場與態度。
儒家因而具備了特殊的雙面性格。從一個方向看,儒家是新版的「王官學」,是傳統已有內容的轉化;換另一個方向看,儒家又是因應東周新環境新困擾而產生的「諸子學」中最早的一家。其回歸「周禮」的主張,不是單純的繼承,而是來自於對應春秋變亂,認為解決變亂、使人安居,最好的策略就是從精神層面復興已有的傳統。「王官學」和「諸子學」,前後兩種不同的知識潮流,在儒家身上奇妙地統合了,在儒家身上,「王官學」和「諸子學」沒有絕然的界劃,而是一體兩面。
不過隨著時序由春秋遞移到戰國,周封建結構進一步陵夷沒落,傳統周文化愈來愈不受重視,儒家原有的雙重性格也就不得不隨著位移。繼承「王官學」的部分愈來愈淡薄,相對地,與其他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學說並立的「諸子學」部分,愈來愈濃厚。
在一個意義上,儒家逐漸喪失了其獨特的地位,變得和其他各家平起平坐。在另一個意義上,我們卻也看到儒家具備了足夠的彈性,能夠適時和舊傳統拉開距離,才能存在發展幾百年,沒有跟著舊傳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裡。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儒學主流真正的塑造者:荀子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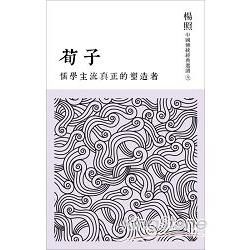 |
儒學主流真正的塑造者:荀子 作者:楊照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144 |
中國哲學 |
$ 190 |
中國哲學 |
$ 190 |
其他國學 |
$ 211 |
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0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儒學主流真正的塑造者:荀子
孔子以畢生之力守護「禮」,
在他傳下的「儒家」這塊招牌底下,
卻存在著許多門派,各自詮釋孔老師。
戰國末年,動盪時代即將結束,
百家爭鳴的盛況已走向法家一統的局面,
荀子身處這般情勢之下,
合理的選擇,就是重新思考禮與法的關係。
孟子堅持「法」的層次低於「禮」,只是不得已的輔助手段;
荀子認為「禮」與「法」沒有明顯的區隔,只是程度上的問題。
孟子相信人性本善,只要盡力發揚本心,就能達成好禮的理想社會;
荀子主張人性原本渾渾噩噩,不學則無從明瞭聖人制禮以規訓人心的用意。
荀子淡化了儒家與法家的界線,因而不受後世儒者推崇。
事實上,相較於講求個人內省功夫的孟子來說,更關注於如何合理安排
整體社會秩序的荀子,才是兩千年來儒學實踐的主流。
拋開冷硬的課文題解,穿過層層的過度解讀,
楊照以平易的文字、扎實的分析,
打破時空限制,直接從原典之中汲取千年智慧。
透過「歷史式讀法」和「文學式讀法」,
帶你一次讀懂兩千年前的中國傳統經典!
‧楊照全程領讀、解讀,中國傳統經典完全解碼
‧台灣新品種文庫版,隨身伴讀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明日報》總主筆、《新新聞》總編輯、總主筆及副社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已出版數十部文學創作及文化評論著作。長期於「誠品講堂」、「敏隆講堂」開設人文經典選讀課程。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還給荀子公正的評價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歷史、史學的存在若有意義,最主要應該就是提醒我們:不要把我們所過的現代生活,視之為理所當然。
一項簡單的事實:目前地球上有七十億人口,很多,空前的多、空前的擁擠,一個龐大、恐怖的數字,然而放入人類文明與歷史經驗中看,我們這六十億人都還是少數。光是從兩千多年前,幾個大文明在「軸心時代」燦爛開展算起,曾經在地球上活過的人口總數,是七十億的七到十倍。
死去的人比活著的人,多得多。他們死了,卻留下了他們如何過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處理自我與其他人關...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歷史、史學的存在若有意義,最主要應該就是提醒我們:不要把我們所過的現代生活,視之為理所當然。
一項簡單的事實:目前地球上有七十億人口,很多,空前的多、空前的擁擠,一個龐大、恐怖的數字,然而放入人類文明與歷史經驗中看,我們這六十億人都還是少數。光是從兩千多年前,幾個大文明在「軸心時代」燦爛開展算起,曾經在地球上活過的人口總數,是七十億的七到十倍。
死去的人比活著的人,多得多。他們死了,卻留下了他們如何過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處理自我與其他人關...
»看全部
作者序
一
二○○七年到二○一一年,我在「敏隆講堂」連續開設了五年、十三期、一百三十講的「重新認識中國歷史」課程。那是個通史課程,將中國歷史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紹過去一百多年來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許多重大、新鮮發現與解釋,讓中國歷史不要一直停留在「新史學革命」之前的傳統說法上,所以叫做「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這套「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的內容,最先是以接續「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課程形式存在,因而在基本取徑上,仍然是歷史的、史學的,等於是換另一種不同的方式,重講一次中國歷史。
...
二○○七年到二○一一年,我在「敏隆講堂」連續開設了五年、十三期、一百三十講的「重新認識中國歷史」課程。那是個通史課程,將中國歷史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紹過去一百多年來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許多重大、新鮮發現與解釋,讓中國歷史不要一直停留在「新史學革命」之前的傳統說法上,所以叫做「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這套「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的內容,最先是以接續「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課程形式存在,因而在基本取徑上,仍然是歷史的、史學的,等於是換另一種不同的方式,重講一次中國歷史。
...
»看全部
目錄
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總序
第一章 還給荀子公正的評價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以禮為核心的孔孟哲學
各自詮釋孔老師
向「大勢底定」的時代轉變
重新思考「禮」與「法」的關係
兩千年儒學真正的主流
第二章 儒者的變貌
荀子重視位分和實用
治國之道:群天下之英傑而教之以至順
禮之不及,以法續之
賤儒和君子儒
由王官學向諸子學轉移
第三章 儒家有什麼用
不實用就淘汰
大儒典範──周公
儒者無所不適
評量、選擇和分配的藝術
人皆可以為堯舜──靠的是學習
荀子的理想社會──恰如其分的安排秩序
儒者積極進取
...
第一章 還給荀子公正的評價
在歷史脈絡中掌握經典
以禮為核心的孔孟哲學
各自詮釋孔老師
向「大勢底定」的時代轉變
重新思考「禮」與「法」的關係
兩千年儒學真正的主流
第二章 儒者的變貌
荀子重視位分和實用
治國之道:群天下之英傑而教之以至順
禮之不及,以法續之
賤儒和君子儒
由王官學向諸子學轉移
第三章 儒家有什麼用
不實用就淘汰
大儒典範──周公
儒者無所不適
評量、選擇和分配的藝術
人皆可以為堯舜──靠的是學習
荀子的理想社會──恰如其分的安排秩序
儒者積極進取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楊照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20 ISBN/ISSN:978957084442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開數:25 開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