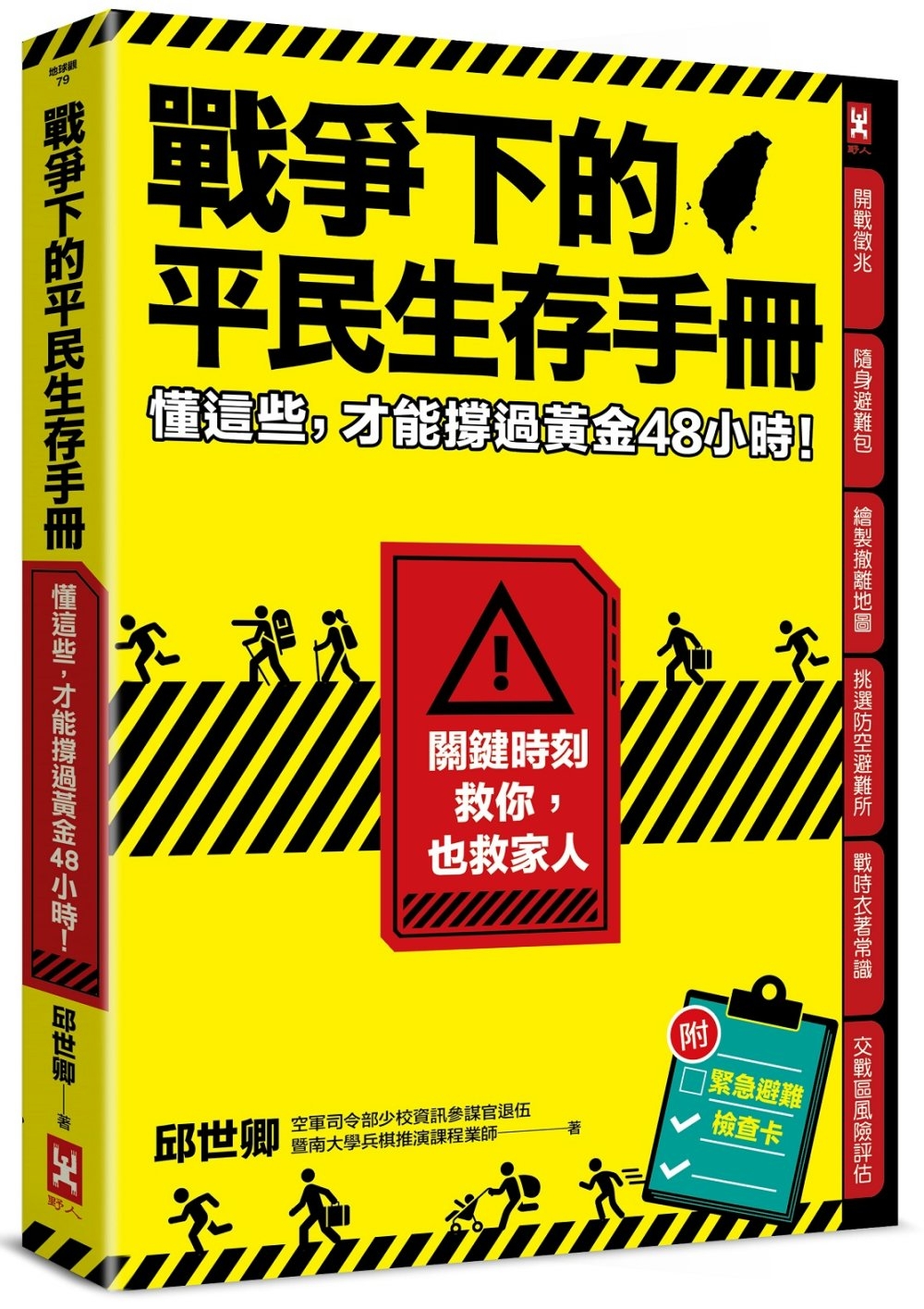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大海浮夢的圖書 |
 |
大海浮夢 作者:夏曼‧藍波安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9-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我從大海來,大海是我的家!
帶著夢想,游向最遠的深藍
海洋是男人說故事的源頭,波浪是學習成熟的草原
金鼎獎、多項文學大獎得主 夏曼‧藍波安
寫作以來最受期待的長篇小說
航海大冒險、木舟橫渡南大平洋、摩鹿加海峽
歷經陸地與海洋的五十餘載豐富人生
2014年,我們終於讀到最動人的海洋文學鉅作!
這個灘頭,從偷吃芋頭莖的那個小孩起到今天,是我們部落建立和諧的源頭,
堅持吧!學習寧靜,在海上,我的孫子希‧切格瓦,我的孩子夏曼‧藍波安。
穿越蘭嶼與台灣的今昔、獨特而豐富的航海記事、廣納海洋與南太平洋眾多小島的見聞,夏曼‧藍波安最新長篇小說力作《大海浮夢》,以原住民的開創性格與敏銳觀察,達悟族對人事物的獨到美感,敘述了整個家族的歷史,人生歷經陸地與海洋的實地冒險,堪稱21世紀的「海人與海」!
《大海浮夢》共分四章,呈現了夏曼‧藍波安生命與大自然接觸的軌跡:
‧蘭嶼的童年生活所見,廢核運動,與不同領域的海洋被剝削的真相
‧驚險的南太平洋海上木舟冒險,青年離家重返故鄉,重拾斷裂的根源
這部長篇小說表達了夏曼‧藍波安半世紀以來對自我與家園的探索與感悟,更寫及庫克群島國,斐濟、印尼群島,巴布亞、大溪地、菲律賓,廣及南太平洋的諸多群島的探險,是台灣海洋文學的經典之作,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美學的新里程!
浮夢的海上旅程,如作者夏曼‧藍波安筆下生動地浮現:「不同國籍的人要長期共生在沒有船艙的仿古船,長時間曝曬在赤道的艷陽下是需要耐力、深厚的心理素質的。你也會發現每天睜開眼睛、閉目睡覺都在海上,夾在黑色的星空下與無情的波濤上,船隻的脆弱如一片樹葉……」
作者簡介
夏曼‧藍波安
1957年生,蘭嶼達悟族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集文學作家、人類學者於一身,以寫作為職志,現為專職作家,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的負責人。身為台灣原住民唯一的海洋民族,海洋的變幻莫測孕育出達悟人獨特、優美而亙古的文化,也成為他取之不竭的創作泉源。他離開故鄉島嶼,在台灣求學、工作多年,1980年代末毅然返回蘭嶼,從最基本傳統營生方式學習,重建自己蘭嶼人的認同與尊嚴,以身體力行和生活實踐,深入達悟文化、海洋哲學,並化為優美動人的文學呈現。其筆調深情內斂、詩意,隱含達悟特有的語法,敘事抒情自然、寓意深遠。
在他細膩優美、詩意的筆下,海洋、飛魚、傳統達悟人的生活智慧和現代衝擊下的悲喜,皆成了他創作的核心,出版以來獲獎不斷,1992年《八代灣神話》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1999年小說《黑色的翅膀》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央日報年度十大本土好書,散文《冷海情深》獲1997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海浪的記憶》獲2002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漁夫的誕生〉獲2006年九歌年度小說獎,並為同年第23屆吳魯芹散文獎得主,並以《老海人》獲2010年金鼎獎。2012年出版小說《天空的眼睛》,並獲該年度中時開卷好書獎。2014年推出最新力作《大海浮夢》,寫下他終於實現童年的航海夢的珍貴旅程,本書獲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