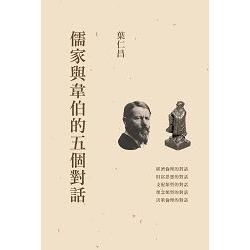經濟倫理的對話
財富思想的對話
支配類型的對話
理念類型的對話
決策倫理的對話
財富思想的對話
支配類型的對話
理念類型的對話
決策倫理的對話
《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為跨越政治、經濟、宗教與方法學等領域的思想史學術創作。葉仁昌教授累積了將近三十年的思考與體會,很大膽並充滿創意地,對儒家與韋伯(Max Weber)開展了五個批判性的對話。包括了清教徒與東亞的經濟倫理、欠缺無限利潤心的儒家財富思想、道德型正當性的支配類型、義利之辨的四種理念類型,以及何不曰利的決策倫理省思。藉此,不只重構了韋伯若干論述的框架,也爲儒家提供了新視角下的不同詮釋。
韋伯是一位經典的大師,葉仁昌教授卻不只具體地指出韋伯對儒家的理解盲點,還應用韋伯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家,更試圖補足韋伯對儒家在研究上的遺漏,完成韋伯未竟的探索,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家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了不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