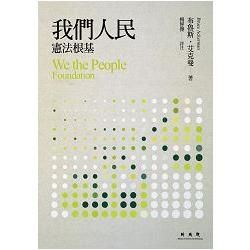什麼是代表人民的憲法價值?
台灣的憲法時刻是否已經結束?還是即將開始?
立法院各政黨無法提出修憲案,是否不正當性阻礙人民發聲?
各政黨又如何動員民眾,廣泛而全面地展開思辨,推動台灣新修憲?
美國耶魯大學布魯斯‧艾克曼的憲法時刻理論,非常值得我們借鏡!
台灣的憲法時刻是否已經結束?還是即將開始?
立法院各政黨無法提出修憲案,是否不正當性阻礙人民發聲?
各政黨又如何動員民眾,廣泛而全面地展開思辨,推動台灣新修憲?
美國耶魯大學布魯斯‧艾克曼的憲法時刻理論,非常值得我們借鏡!
日常政治的決定,不可違背憲政時刻的人民決定
布魯斯‧艾克曼在《我們人民:憲法根基》一書中
對美國憲政發展經驗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解釋
布魯斯‧艾克曼綜合了美國歷史、政治學與哲學,探討了美國人民主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其提出美國憲政發展的三個重要憲法時刻:制憲建國期、戰後重建期、新政時期。並提出二元民主論,認為日常政治的決定,不可違背憲政時刻的人民決定。其亦主張,法官在解釋憲法時,必須先找出憲法時刻的抽象化原則並將新政時期的新價值,與制憲建國時期和戰後重建時期的價值予以整合,以解決當前的憲政爭議問題。
艾克曼的二元民主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想探討非正式修憲程序的問題,並不是探討憲法解釋的問題,但實際上,他仍然是參與了美國憲法學界對憲法解釋方法的爭論。尤其,他的理論,正是要為華倫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提出辯護。
這本《我們人民:憲法根基》,主要是提出美國經驗的憲法理論。他的理論,是認為政治可以分為常態政治和憲法政治或稱憲法時刻。在憲法時刻下,由於高度動員全國人民,所制定出來的憲法,需要我們尊重與維持。而常態政治下國會以多數決做成的決定,卻可能是一時激情,而違反了憲法時刻下制定的憲法根基。
由於艾克曼教授是法律學者,這個憲法理論,最終的關懷,還是為了解決法律學者所關心的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由於司法違憲審查,由少數幾個大法官,可以透過投票否決國會議員通過的法律,故一直以來,都有所謂反多數決的疑慮。而且大法官在解釋憲法時,似乎也有很多種解釋憲法的方法,有的強調基本人權,而會將自己的人權價值,放入憲法解釋中,而屢遭批評。艾克曼在本書提出的理論,也是想提出一個大法官解釋憲法的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