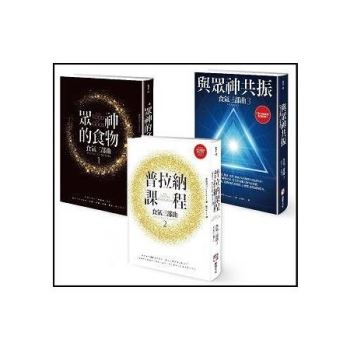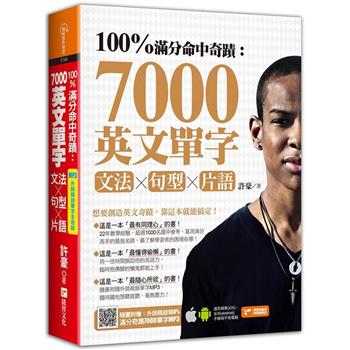聯經中文版序
《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中文全譯本即將出版。首先我們要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同時必須感謝幾位細緻嚴謹的翻譯者:劉倩、李芳、王國軍、唐衛萍、唐巧美、趙穎之、彭淮棟、康正果、張輝、張健、熊璐、陳愷俊、梁淑雯、劉威廷、楊華慶。他們的譯文大都經過了作者本人的審核校訂。復旦大學古籍所的吳冠文先生也指出一些錯誤,並予以更正,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他。此外,對於兩位在百忙中努力堅持自譯(即使是部分自譯)的作者──李惠儀和奚密──我們也要獻上謝忱。
必須說明的是,當初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而且我們請來的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雙重影響,因此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思考與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將把《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出版構想和編撰原則簡單介紹給中國讀者。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學部主編琳達.布瑞(Linda Bree)於二○○三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時刻。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於二○○一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E. J. Brill)也正在計畫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劍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們編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巧我們當時也正在考慮著手重寫中國文學史,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
《劍橋中國文學史》乃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與該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劍橋義大利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劍橋德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相同,其主要對象是受過教育的普通英文讀者。(當然,研究文學的學者專家們也自然會是該書的讀者。)然而,劍橋文學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年代上大致與劍橋世界文學史的歐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與一些學界的文學史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參考書,而是當作一部專書來閱讀。因此該書盡力做到敘述連貫諧調,有利於英文讀者從頭至尾地通讀。這不僅需要形式與目標的一貫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互相參照,尤其是相鄰各章的作者們。這兩卷的組織方式,是要使它們既方便於連續閱讀,也方便於獨立閱讀。卷上和卷下的導論就是按照這一思路設計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需要之外,《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面對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讓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換言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並撰寫出一部既富創新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
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還有以下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它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genres)的做法,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種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為此,需要對文化史(有時候還包括政治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當然,文類是絕對需要正確對待的,但是,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將成為文化討論的重點,而這在傳統一般以文類為中心的文學史中是難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問題重重。《劍橋中國文學史》並非為反對標準的慣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許多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也已經意識到,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著根本的缺陷。但習慣常常會勝出,而學者們也繼續按朝代來分期(就像歐洲學者按照世紀分期一樣)。在此,《劍橋中國文學史》嘗試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蹤不同時期思想所造成的結果和影響。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把初唐與唐朝其他階段分開處理。此外,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鑑。在卷上、卷下的導論中,我們都對分期的理由做了說明。
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這當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間進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後來文學非常活躍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當然,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的方法。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他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
有關過去如何被後世重建的現象,還可從明清通俗小說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有關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還是詩文的寫作。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關文學的改寫。人們通常認為,〈漢宮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並不在元朝。根據伊維德(Wilt Idema)的研究,許多現在的元雜劇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寫」的。至於改寫了多少,很難確定,因為我們沒有原本可以參照。當然,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有人認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成就,主要來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劇本改寫得生動傳神,其實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對於這種所謂創新的「改寫」(rewriting)跟作者權的問題,我們自然會想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後來改寫者的貢獻有多大?版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又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
此外,必須向讀者解釋的是:我們這部文學史後面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只包括英文的資料,並未開列任何中文文獻。首先,如前所述,本書乃是一個特殊情況的產物,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所以有關讀者對象(即非專業英語讀者)有其特殊的規定,同時出版社對我們的寫作也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我們所編寫的「英文參考書目」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準備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將來能繼續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英文書籍。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寫作文學史首先要參考的是原始文獻,其次才是二手文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獻的影響。事實上,在撰寫每一章節的過程中,我們的作者都曾經參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他許多語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一一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篇幅將「浩如煙海」,會無限增大,所以劍橋大學出版社完全支持我們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選擇性的英文書目。同時我們覺得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現在我們既然沒有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也就沒有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
總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敘述的整體連貫性,又要涵蓋多種多樣的文學方向。希望中譯本能夠傳達出我們真誠的努力。最後有兩點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書由十餘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譯本又經過了多位譯者的參與工作,故而每一章的學術與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必然帶有各自作者和譯者各異其趣的風格印跡;第二,從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簡體中譯本的下限時間只截至一九四九年。但這次聯經出版公司終於能出版「全譯本」,這真是對本書的最好補充。因此我們要對聯經的胡金倫先生特別獻上衷心的感謝。
孫康宜
英文版序
這部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橫跨三千載,從上古時代的鐘鼎銘文至二十世紀的移民創作,追溯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久遠歷程。在全書編寫過程中,作者們通力合作,對主題相關或時段交疊的章節予以特別的關注,力求提供一個首尾連貫、可讀性強的文學史敘述。我們亦認真考慮了每個章節的結構和寫作目標,並斟酌在何處分卷以便讀者的理解。
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浸潤於兩種傳統之中:其一為中國古典學術範疇;其二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史書寫。出於對學術習慣的尊重,當代西方學者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往往襲用中國學界術語,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語彙常常難於理解。本書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採用更為綜合的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視角,特別避免囿於文體分類的藩籬。對中國早期和中古文學而言這種方法較為適用,但應用於明清和現代文學則多有困難。雖然如此,通過清晰地架構總體文化史或政治史,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例如,卷上的唐代文學一章沒有採用「唐詩」、「唐代散文」、「唐代小說」、「唐代詞」等標準範疇,而是用「武后時期」、「玄宗時期」等主題,敘述作為整體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文、筆記小說等作品。與此相似,卷下關於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分為「明初─一四五○」、「一四五○─一五二○」及「一五二○─一五七二」,分別關注諸如「政治迫害與文字審查」、「對空間的新視角」、「貶謫文學」等文化主題。文體問題當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對於以文體本身作為主題的敘述,文體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更能體現其文學及社會角色。這種方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作品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因而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屬於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學,就文本流傳而言它們出現較晚,但是卻擁有更久遠的淵源。伊維德在卷下第五章處理了這個問題,將他自己的寫作與其他章節的歷史敘述融合起來。
由於這項工程的規模和複雜性,我們決定不提供冗長的情節概括,只在必要的時候對作品進行簡短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文學史寫作通常圍繞作家個體展開,其他劍橋文學史作品同樣如此。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實與否)已經與其作品的接受融為一體。
隨著文學作品本身及其傳播途徑的多樣化,明清和現代文學更難以用統一的方式敘述。篇幅所限,我們決定暫不討論當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時,基於我們的歷史維度,我們也不得不排除韓國、越南以及日本境內的漢文作品。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則適當予以關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學史寫作無疑還會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和標準範疇的約束。就中國文學而言,年號、人名、文體以及中文語彙的傳統漢學翻譯方式都可能對歐美讀者造成閱讀障礙。鑑於此,我們努力保持術語翻譯的一致,儘管我們要求作者根據各自時代的需要選擇最恰當的英文譯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現時都給出英文譯名,並在括弧中注出中文拼音,漢字原文則收入書後詞彙表。除特別說明外,本書所引中文資料的英語譯文均為作者自譯。同樣由於篇幅所限,引文出處一般隨文提及,未以注釋形式標出。本書的「書目」所列出的英文參考文獻也只選擇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鑑於中文出版物數量之龐大,作者們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說,我們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是永遠充滿感激的。
孫康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卷上導言(節錄)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其他文化,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現代中國政治邊界內的所有文學,這一邊界內有多種語言,還有一些完全獨立於漢文學之外的古老博大的文學傳統。在本書中,我們的研究領域採用的是一個較為有限的定義:即在漢族社群中生產、流通的文學,既包括現代中國邊界之內的漢族社群,也包括那些華人離散社群。儘管本書所論的作者不全是漢人,卻都參與了漢文化。
這一表面上顯得很簡單的定義引發很多問題。這一定義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多個社群的種族自我認同,而這些社群有數千年的發展變化歷史;二是多種語言之間具有共通身分的假定,而這些語言在語言學家們看來是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如同所有這類「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質上都與某一政體密不可分,這一政體在今天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中國政體與外在於該政體的華人社群的關係,還有這些社群自己與該政體的關係,依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無論我們如何試圖給文學史劃出範圍,比起這一學術體裁在十九世紀初首度成熟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變得遠遠更為複雜。兩個世紀前,對文學史家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事實還是作為一種理想,語言、種族、民族國家,這三者之間的同一性都是不證自明的。即便在當時,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往往也有使用其他語言言說──而且常常也使用其他語言書寫──的社群。現在,我們意識到問題要複雜得多。過去有一些古典語言──有時與口語截然不同──構成了文學生產的主體,卻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各個「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的歷史之外。從過去到現在,都存在混合式的語言(macaronic languages),因翻譯的壓力而發生變化的語言,在殖民地與前殖民地、在離散人群與多種族移民中傳播、變異的國家語言。
所有這些現象都為文學史帶來了難題;這些現象清楚表明,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的文學史,在何種程度上與民族國家及其利益綁縛在一起,為民族國家提供一部連綿不斷的文化史。如果沒有民族國家的形成,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學史往往就變成了對一個「人民」的文化史的確認,和一種特定的語言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語言為這一情況的可能性提供了根據。
儘管早在現代時期之前,中國文學就已服務於為一個社會階級建構一個共同的文化身分這一目標,中國文學史的現代書寫,從一九二○年代首次全面成熟之後,卻一直持守著十九世紀對語言、種族、政體的同一性的信念。從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不斷重述一個漢民族的史詩,重述從遠古到現代、散布於極其廣闊的地域的中國文學文化的歷史與連續性。
這把我們帶到漢語語言的問題,思考二十世紀的「語言政治」(language politics)所發生的變化如何產生了這兩卷本的《劍橋漢語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一卷稱為《劍橋古代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一卷稱為《劍橋白話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ture)。在西歐,這樣的兩卷書不會只用同一個字:卷上會用「拉丁語」,卷下則會使用歐洲「地方語言」(vernacular)中的一種──這裡且以「義大利語」為例,直到很晚,義大利語都還不是一種民族國家語言,而是「地方語」,「volgare」。在中國,兩卷可用同一個字;在歐洲,兩卷須用不同的兩個字。這一事實是「政治性的」──既在通常的意義上,也在文化的意義上。
眾所周知,漢語是一種以字元為基礎的語言。這一事實帶來的種種後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同一個字的讀音,在語言史上,包括了各種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語言和方言的大語言區域內,都變化很大。此外,漢語只有上古語言形態變化(morphology)遺留下來的辨認不出的痕跡,它的單詞似乎沒有屈折變形(uninflected)。如果說書面語語法的最初功能是為了控制語言的區域差異和歷史變化,那麼,漢語並不需要書面語語法,因為漢字發音有各種變化,而且從表面看來明顯缺乏形態學。如同所有語言一樣,字詞和句式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讀音的變化,使得以上古語言為基礎的一種簡單的「文言」看上去不過是口語的正式的書面形式。在一九二○年代的語言改革之前,中國的狀況近似於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的美式英語寫作練習:gotta(代表口語),got to(轉化為書面語的口語),have to(非正式用語,但在某些場合的書面語中可以接受),must(正式用語,「正確得當的」書面用法)。的確,就承認各種差異不過是語言修辭層次(register)的問題而言,漢語與英語極其相似,它們皆承認所有這些變化都屬於同一種語言(「漢語」或者「英語」)。
宇文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