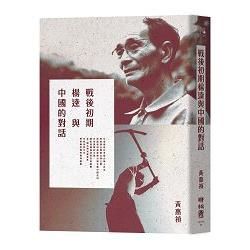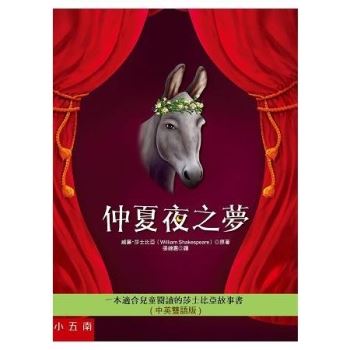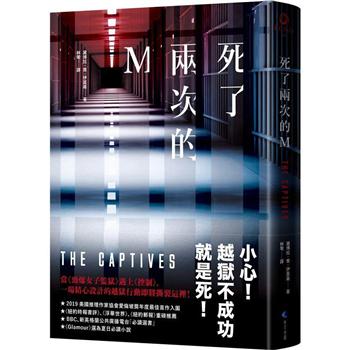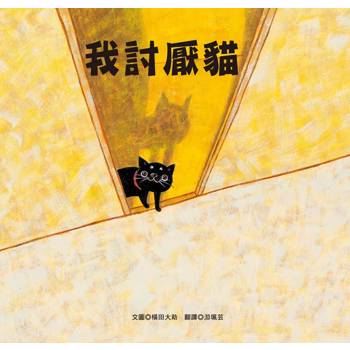借助多種新出土的第一手史料,
勾畫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政權、中國現代文學、中國來台人士間的對話,
呈現楊逵在爭取台灣人自治與重建台灣新文學之際,
面臨當局亟欲將台灣全盤中國化時有所選擇的立場,
藉此填補楊逵研究的罅隙,
並一窺台灣知識菁英在政治與文化雙重轉型期的精神圖像。
戰後初期(1945-1949)是台灣歷史上最為複雜,社會變動也最為快速的時代。短短四年間,台灣由日本統治轉為中國接收,台灣人並因此經歷語言轉換與政治壓迫的雙重困境。其間,以日文為書寫載體的作家如何堅持其文學志業,如何回應政權遞嬗與文化變遷,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屹立於台灣文壇的楊逵,無疑是觀察台灣作家如何面對戰後初期的風雲變幻時,一位具有指標性的重要人物。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主要藉由相關文獻資料的爬梳,從幾個層面進行探討。首先,楊逵從積極組織自己的政治團體,到配合中國政府的接收,以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進行政治啟蒙,並參與籌備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的原因。其次,二二八事件期間和中國共產黨員蔡孝乾有所聯繫的楊逵,與中共在台地下黨的關係。再者,楊逵傳播的中國文學包含的作家與作品,所選錄創作的內涵與共同特色,以及楊逵引介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之目的。最後是釐清楊逵與大陸來台作家合作交流的思想基礎,以及彼此在文學理念與文化立場上的異同。藉此呈現戰後初期楊逵在爭取台灣人自治,與重建台灣新文學之際,面對當局亟欲將台灣全盤中國化時有所選擇的立場,以填補戰後初期楊逵研究的罅隙,並一窺台灣知識菁英在政治與文化雙重轉型期的精神圖譜。
延伸閱讀: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
《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
《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
《美與殉美》
《空間╱文本╱政治》
《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作者簡介:
黃惠禎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職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曾任《楊逵全集》執行編輯暨「資料卷」責任編輯,協同主持「台灣客家文學數位資料庫建置計畫」、「楊逵文獻史料數位典藏計畫」。著有《楊逵及其作品研究》(1994)、《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2009),並負責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04‧楊逵》(2011)。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拋棄台灣人立場的心靈痛楚,相當程度地展現了中日戰爭時期成長的新世代,在日本人與台灣人兩條對立的路徑中掙扎的苦悶心境。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臺灣新報》報導了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領袖──杜魯門(Harry S. Truman)、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蔣介石聯合發表「對日共同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以及盟軍要求日本投降的八個條件,其中之一在於實施「開羅宣言」,將日本領土限定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被決定的其他諸島。據此,台灣人當已預見日本戰敗之後,即將迎向嶄新的政治局面。儘管曾經是中國領土,有眾多來自中國移民的後裔,戰爭時期除了物資被強徵以支應軍備之所需,文學藝術被迫協力戰爭之外,台灣也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到盟軍飛機的激烈轟炸,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更以軍屬、通譯等名義被送往前線,而與中國人站在敵對勢力的兩邊。夾處在交戰的日本與中國之間,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不難想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期待已久的和平終於到來時,臺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竟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靜觀」。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印證了這項記載的真實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描述與友人脫去衣裳,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各人朝向海面大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的狂喜之後,也記錄了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噫,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噫,感慨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
字裡行間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翌日,吳新榮既喜悅又不安的複雜心境。一方面,為漫長的戰事終於結束,台灣可望脫離日本統治而雀躍不已;另一方面,由於無法洞悉時局的趨向,對於台灣的前途充滿疑懼。
八月二十八日《臺灣新報》刊載蔣介石所發表,關於中國獨立達成的聲明,收回台灣及澎湖群島也列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隨著中國接收台灣的態勢逐漸明朗,得以擺脫日本殖民地歧視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被戰敗國日本支配的命運,轉而成為戰勝國中國之一方,台灣民眾迅速陷入歡欣鼓舞的慷慨激昂中。九月一日張士德返台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獲得包括舊台共成員謝雪紅、蘇新、簡吉,與作家張文環、呂赫若、吳新榮等眾多不分派別台灣民眾的踴躍響應。九月十日,由陳炘發起,葉榮鐘擔任總幹事,林獻堂參與領導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召開籌備委員會,正式推動相關事宜。國民政府軍接收時的熱情迎接,與國語(北京話)學習的盛況,體現了台灣人對這個新時代的熱烈歡迎,以及重新建設台灣社會的殷切期盼。其間,台灣人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台灣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為盡速重建戰後新台灣,台灣社會展現前所未見的活力。
戰爭末期在物資統制的前提下,台灣的報紙、雜誌各被統整為《臺灣新報》與《臺灣文藝》一種。日本戰敗後各種刊物陸續出爐,根據學者何義麟的統計,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為止,台灣島內新創刊的雜誌,至少有一百一十種以上。主導發行者大致可分為台灣文化界人士、官方機構或學校團體、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等三種。另有台灣人與大陸來台人士合作的刊物,《台灣文化》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報紙方面亦為數不少,主要有從《臺灣新報》改組而成,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臺灣新生報》、國防部宣傳處的《和平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華日報》,以及民間創辦的《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各自傳達行政機關、軍方、政黨、民間,分屬左、右翼等不同光譜的言論,一度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繽紛榮景。
由於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台灣與中國的社會型態及文化內涵,在戰後已經有了極大的差距。一九四四年四月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十月由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呈,並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核定。接收後陳儀政府即以此為方針,推動台灣文化的重建。其中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第四十四條中關於國語普及的「公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以及五十一條「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槪予銷燬。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等條文,不僅預告中國國語文時代的來臨,也以此宣示牴觸中國國民黨的言論,將運用官方的力量予以排除。
行政長官陳儀來台後,為執行中國化的政策,去除日本文化的影響,設立三機構以實踐〈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部分構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負責媒體的管制與法令的宣傳,「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運動,「臺灣省編譯館」從事刊物編輯,並接續日治時期的台灣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陳儀保護下傳播魯迅思想,希望藉由魯迅曾經參與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展開,發揚中華民族主義,藉以改造台灣人的國民性,由此掀起戰後台灣文化界的魯迅風潮。一九四六年二月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已出版者予以銷毀與取締。十月二十五日起廢止報紙雜誌的日文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禁用日文與日本圖書的查禁,在接收台灣僅滿一年的一九四六年間即已落實。台灣以「去殖民」(decolonization)與「中國化」為兩大前提,逐步邁向重建之路。
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
推薦序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楊翠
在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中,惠禎的風格,一向不與主流同道。在某個意義上,她有如孤鳥,長年固守被喧嘩群落遺忘的一小方天空,孤身靜飛。
這二十五年,我確實見證了惠禎的孤獨和執著。二十五年前,台灣文學研究尚仍一片荒蕪,中文系出身的惠禎,在主流的側身邊緣,一頭埋進去,靜靜開始研究楊逵;二十五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狀似繽紛,各種研究主題迸生,而惠禎,仍然蹲伏在這塊原初的土地上,一鋤一鏟,探掘楊逵。
回視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罹患集體創意焦慮症,從商品市場到文化場域,就連學術界也不例外,大家絞盡腦汁想著各種所謂「創新議題」、「先鋒研究」,議題一個個被快速生出來,又被快速消費掉。這些年台灣文學的研究主題,後殖民、後現代、全球化,早早就是民國舊事了,殖民現代性、空間與地方、移動與旅行、離散與認同、倫理、創傷、身體、飲食……,議題流行化,一時風潮,人人爭相競逐,卻又乍起乍落,不久前才充斥各期刊、研討會的研究主題,轉眼間就成為過時舊事。
研究主題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快速流掠,問題是研究者的創新焦慮症,執念於變化咖啡上面的拉花,卻失落了內蘊滋味。然而,惠禎卻是另一種執念。自從那一年的秋日午后,楊逵次子楊建同意把一大疊泛黃手稿交到她手中,午后的溫潤陽光與厚重的歷史氣味,互涉交織,滲入她的思想與情感紋理,此後,無論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景如何千變萬化,惠禎總是固守著楊逵這株花樹。
不同於追求時尚、創新、先鋒的媚俗性研究,惠禎的研究,特別有一種悠緩的節奏感,素樸而細膩的韻味,乍看沒有太多花俏的語言,然而,她通過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材料撥尋,細密的史料交叉比對,嚴謹的組織與詮釋,對每一個細節都再三推敲求證,對每一個歷史疑點反覆探察,體現了一個真誠學術研究者的風範。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仍是惠禎的一貫研究風格。延續她前一本書處理一九四○年代、二戰前後楊逵的思想與行動,本書所選擇的時間斷限,是一個更關鍵性的歷史切口。以台灣史來看,「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是一個獨特的,更是充滿「難題」的歷史時點。早期的台灣史研究,對這段時期有諸多誤識誤判,總是簡單以「苦悶」、「禁錮」、「沉寂」概括詮釋,我們知道那是一個變局,我們認為那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變局,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粗暴登臨台灣,而台灣人民憂苦噤聲,瘖啞無語。然而,事實不然,當更多史料被探掘,更多研究撥開歷史迷霧,我們才知道,台灣人民並沒有噤聲不語,有志者並沒有沉寂不前,那個時代的鮮活躍動,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楊逵就是其中一個不服從的台灣細胞。
因為各方細胞積極竄動,戰後初期的複雜性,也超出我們的一般認知。這短短幾年,台灣內部、台灣與世界的關係,不是簡單的重新洗牌而已,台灣與中國、左翼與右翼、國民黨與共產黨,各種權力交鋒,各種思想交雜,各種光影迸現,極其複雜,充滿疑團。
因此,探析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究竟面臨何種處境?如何在各種權力光影中左衝右突?如何在各種思想光譜中,尋找安置與實踐的位置?這是一個精神史的命題,更是一個艱鉅的難題。而我們之所以必須深入戰後初期的歷史荊棘,更因為這些難題,也正是現實台灣難題的歷史源頭。惠禎想處理的,因而不僅是楊逵,而是一個牽纏糾葛超過一甲子的台灣母題。
楊逵的思想經常被詮釋為「複雜」,從一九八五年他辭世至今,左右統獨爭相詮釋,或黨同,納為己方陣營,或伐異,斥為叛徒異端,不曾停歇。但楊逵還是楊逵。楊逵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林瑞明,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就清楚揭示:複雜的不是楊逵,複雜的,是他的時代。戰後初期最複雜、最艱難的課題,是台灣正在進行主體重建、世界觀重構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以「遷佔者政權」夾帶「祖國」的政治/文化符碼,強勢介入,干擾了台灣人對自身課題的思考理路。
正因如此,惠禎選擇從「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切入,剝解戰後初期千絲萬縷的複雜時代紋理,精確擊中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於刻劃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圖示,是很有效的路徑。
通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惠禎帶領我們重新認識楊逵──一個有著孤獨、結盟雙重性格的實踐者,一個跨界政治社會、文化文學運動場域的行動派。戰後初期,楊逵以「一匹狼」的孤身戰鬥性格,以及跨組織結盟的開放性格,跨界奔走於各種權力光譜之間,尋求交流、合作、協商、對話,全力投身台灣社會的重建工作。這短短四年,幾乎可以說是楊逵人生最活躍的四年,於是我們知道,在戰後初期那樣詭譎的時代,如此積極的行動者,終而走向禁錮的黑獄,也是得其所哉。
總體來看,在楊逵研究已然豐沛的今日,《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的價值,正是對於戰後初期的複雜歷史語境,有著深刻、多向度的掌握,正因楊逵堪稱戰後初期台灣最積極、活躍、跨界的行動者之一,因此,通過楊逵,惠禎所照見的,是整個時代的鮮明斷面。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從以下幾個面向,建構複雜的時代、簡單的楊逵。首先,惠禎清楚地指陳戰後初期楊逵在政治社會運動/文化與文學運動的多重實踐面向;跨界於兩重實踐場域,正是楊逵從日治時代以來一貫的運動性格。在政治運動方面,日本一戰敗,楊逵就開始著手準備,以嚴防接收政權的橫暴,他的動靜,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都觀察到:「只有楊貴……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對此的牽制策略是必須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在此意圖下,他採取了一些動作……」
楊逵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體質,這影響了他戰後初期所有的行動方向。無論是最初意圖組成的「解放委員會」,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新生活促進隊」,以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的下鄉組訓,宣揚挺身抗暴,宣傳加入「二七部隊」,還有一九四九年參與起草「和平宣言」等等,都顯示戰後初期他的抗暴行動,不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抗爭,甚至更加積極堅決。
在文化與文學運動方面,日本才剛投降半個月,國府接收工作尚未展開,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楊逵就創刊《一陽週報》,這是目前所知的戰後第一份刊物,其後他陸續創刊《文化交流》,策畫編輯出版「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主編《和平日報》「新文學」、《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等。以「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的出版歷程來看,可以觀察到楊逵的堅定意志;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由楊逵策畫編輯,並負責多數作品的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第一輯《阿Q正傳》出版後,楊逵即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八月出獄後,隨即繼續執行編輯計劃;而預計每月出刊一至二本的《臺灣文學叢刊》,雖因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經費籌措不易,一再延遲出版,但最終仍然出版了三期。可見楊逵即使歷經政治牢獄、經濟困局,在政治運動舞台失落之後,仍舊堅守文學實踐的崗位。
其次,惠禎總結了楊逵在戰後初期文學運動的幾個行動方向,這些方向,都與「台灣、左翼、民主」密切相關,而這也正是楊逵精神的總結。第一,他積極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與作品,企圖建構台灣文學發展的主體歷史脈絡。第二,他掀起、並積極參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論爭」,與一批對「台灣文學」無知、抱持偏見的中國來台作家打擂臺,捍衛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第三,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也都是在「台灣.左翼」的核心思想底下,包括他在「中國文藝叢書」的編譯策略,《臺灣文學叢刊》的選刊作品,都以具有關懷社會現實的作品為主。第四,惠禎指出,楊逵通過文學作品的選刊,以及序文、雜文的書寫,傳達了鮮明的「反抗意識」,如對國民黨接收官僚的批判,對台灣人反殖民抗日行動的刻劃,彰顯出對威權統治的反思,並潛藏著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
最後,惠禎對於楊逵與台共、中共地下黨是否有「組織關係」的爬梳,析辯精細,論證厚實,她明確指出,楊逵與台共、中共,有著個人性的交誼,有著行動上的合作,但並沒有組織性的關係。
這個結論,確實掌握了楊逵的基本性格與思想底蘊。這是由於她對楊逵已經瞭若指掌。如果不了解楊逵的一匹狼、孤鷹性格,很可能任意將他安置在某個特定的組織中,然而,楊逵遠非如此。戰後初期,中國、台灣、左翼、右翼,各方推擠,然而,對楊逵而言,最重要的是台灣主體、民主政治、階級平等,而這些目標,絕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運動團體可以達成的,他必須保持自由之身,跨界結盟,原因在此。
戰後初期,楊逵既結盟舊台共黨員、中共地下黨成員、中國來台左翼作家等左翼陣營人士,也結合中部青年、文化社群、文學社團等在地行動者,同時也試圖尋求與原日治時期右翼民族運動者如林獻堂、葉榮鐘等人的合作。他努力於尋求各種支援管道,以使戰後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文學,走上美麗的繁花盛景。如此孤鷹性格,如此多重關懷,他無法直接依附於某一個既定組織,當然更不會選擇「從政」。當日他的農組舊友劉啟光(原名侯朝宗),從中國返台後,被派任為新竹縣長,楊逵的昔日社會運動舊友如連溫卿、簡吉等人,都進入縣府工作,劉啟光也有意延攬邀楊逵入主縣府民政局或社會科,但楊逵以「要做事情不一定要做官」而拒絕了。
時代很複雜,但楊逵很簡單,只要能掌握他「台灣、左翼、民主」的一貫思想底蘊,就能掌握楊逵被時代光影覆蓋的內在肌理。惠禎的研究,正是既掌握了時代的複雜性,更掌握了楊逵的簡單性。而其實,楊逵,只是「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一個提喻而已。戰後初期,在各方勢力、各種思想、各種困境雜陳的複雜光影中,如楊逵這般的台灣知識分子,都在努力思索、抵抗、實踐,面對風險,承擔風險。
於是,用盡氣力想要重建台灣社會的一匹狼,終於入了黑獄。在詭譎的戰後初期,一個瘦削的台灣作家,奮力穿梭各種權力光譜,尋求建設更好的台灣,這段故事,從此被政治黑霧深埋。
數十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一隻孤鳥,遭遇了這匹狼。那一方天地間,歷史裡的這匹狼,固執地站到時代的浪頭上,然後被迫沉入霧霾,而現實裡的那隻孤鳥,從迷霧裡將他打撈上岸,一點一點,撥開重重霧障,拆解這道歷史難題。《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因而既是一本文學研究成果,也是一個研究者的自剖,安靜而熱情,素樸而真摯。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楊翠
在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中,惠禎的風格,一向不與主流同道。在某個意義上,她有如孤鳥,長年固守被喧嘩群落遺忘的一小方天空,孤身靜飛。
這二十五年,我確實見證了惠禎的孤獨和執著。二十五年前,台灣文學研究尚仍一片荒蕪,中文系出身的惠禎,在主流的側身邊緣,一頭埋進去,靜靜開始研究楊逵;二十五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狀似繽紛,各種研究主題迸生,而惠禎,仍然蹲伏在這塊原初的土地上,一鋤一鏟,探掘楊逵。
回視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罹患集體創意焦慮症,從商品市場到文化場域,就連學術界也不例外,大家...
作者序
安身立命之道
一九九○年十月,秋陽從窗外灑進車內,溫暖著初次見面的我和楊翠。當時的我們正從大甲火車站出發,並肩坐在開往外埔楊建老師家的公車內,愉快地聊著我即將進行的,以楊逵及其作品為主題的研究規劃。這一切的因緣來自於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撥了通電話到大甲高工給楊建老師,洽詢商借楊逵未曾公開面世的手稿。由楊翠陪同拜會過楊建老師後數日,楊翠的夫婿魏貽君先生載著我,從台北專程開車到他位於楊梅的老家,領取一大疊楊逵文稿資料。翌日,雙手捧著已然泛黃的手稿,步入中文系辦公室,一頁一頁小心翼翼地翻閱影印時,為了能親炙知名作家的第一手文學史料,竟不自覺地激動到幾乎要熱淚盈眶。那時怎麼也料想不到,楊逵研究竟會在日後的人生中,尤其在自我追尋的路途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多方蒐集研究資料期間,發生調查局人員進入清華大學,逕自逮捕歷史所研究生的事件。政大中文系位於百年樓,恰與歷史學系是上下層樓的近鄰。從助教處聽聞歷史學系輾轉傳來,該系與清大歷史所間的通話,早已被情治單位監聽,相關人士人人自危的傳言後,第一次莫名地感受到白色恐怖的肅殺之氣。儘管已經解除戒嚴,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進行針對楊逵文學的初步研究。坦白說,一九九二年七月獲得碩士學位時,被頻頻詢問「楊逵是那個時代的人?」的同學們連連吹捧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當年倒真的有點兒沾沾自喜。
一九九四年七月,碩士論文在行政院文建會的策畫之下,幸運地獲得正式出版的機會。經過兩年的沉澱之後,重新閱讀在參考資料上親筆寫下,充滿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眉批時,赫然發現過去深信不疑的台灣史,和研究中搜集到的史料間,竟然存在著嚴重的斷裂。那一刻才頓悟自己不懂楊逵,也不懂他生活過的時代。主要原因來自於過去接受的黨國教育,讓我與日治時期以來的台灣歷史近乎完全疏離。接下來的幾年間,經歷了與原本堅持的信念不斷衝突對抗的過程,不知道究竟能相信什麼,只知道對於從小生長的鄉土近乎無知。於是,舉凡台灣的文學、歷史、族群、民俗、建築,甚至台灣的植物、昆蟲、鳥類、哺乳類動物的入門書籍等等,幾乎是來者不拒地抓到就讀,一本接著一本快速瀏覽完畢。回想起來,那種心情簡直就像在贖罪一樣。
一九九四年起,透過指導教授李豐楙老師的引薦,協助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教授整理楊逵資料,參與規劃《楊逵全集》編輯與出版事宜。一九九六年再度回到政大就讀博士班,適逢「《楊逵全集》編譯計畫」在文建會資助下開始執行。由於李豐楙老師與編譯委員們的鼓勵,決定重拾楊逵研究,並聽取陳芳明教授的意見,以研究成果最為不足,社會變動最為快速與複雜的四○年代為範圍。九年間歷經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以及《楊逵全集》的全數出版完畢,二○○五年七月終於順利畢業。
獲得博士學位半年多後,從通識教育中心轉任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正式踏入台灣研究學界。面對研究績效純以數量計算的評鑑機制,學術事業已不再是單純的興趣或使命感,而是為了累積點數不得不做的差事。適應不良的我在痛苦中,重新摸索研究對於自己的意義。隔年,因為是系上唯一符合系主任資格者,在極力掙扎抗拒之後,仍然不得不違反生涯規劃,兼任行政主管職。在位期間系務繁忙,研究停擺,又遭逢最疼愛自己的父親驟逝,心力交瘁。苦撐完三年任期,以堅決的態度辭謝連任的選舉結果,終於得以卸下行政職。接著,我花了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去尋找原來那個快樂又單純的自己。這些年來由於健康情況欠佳,想要完成一篇論文都很困難的情形下,因為不忍見愛護自己的人失望,終究能督促自我,以蹣跚的步履持續前行。
已經是第三本學術專書了,仍舊以楊逵研究為題,或許在追求廣博與深入兼具的學術界,顯得有些奇怪。其實,不過是藉此回到從事研究的初衷,重溫與楊逵手稿第一次接觸時的感動。在此要特別感謝李豐楙老師、陳芳明老師、陳萬益老師、河原功先生多年來在學術上的指引,還有對我關懷備至的李喬老師與師母蕭銀嬌女士,從不吝於提攜我的黃美娥教授,以及總是站在我身旁的好友楊翠、雅芳、克明、舒亭,成為家人之外支撐我熬過來最主要的力量。當然不能遺忘了我最親愛的家人介人與易安,兩位不僅是我最可靠的後盾,也是我永遠的精神支柱。另外,這本書得以完成,必須感謝科技部提供專書寫作計畫的研究經費,全書出版及書中三章先前投稿學術期刊時審查委員的指正,聯經胡金倫先生與沙淑芬小姐的專業編輯,還有可愛的學生助理李彥陵、賴俊佑、陳冠如協助影印研究資料,俊佑、冠如並參與全書文稿的反覆校對。
長達二十五年的楊逵研究,緣起於楊建老師當年慷慨允諾出借楊逵手稿,以及身為政治受難者楊逵次子,一則則在困頓顛躓中辛苦走來的人生故事,逐步引領我走向認識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路徑,也促使我經由前輩作家的社會關懷,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意義。在楊逵的圖像因為統獨意識的不斷糾葛,依然模糊不清之際,我所從事的楊逵研究,不外是挖掘與整理史料,再把史料放回歷史脈絡中,仔細聆聽它們娓娓道來的故事。感謝楊逵家屬始終惠予必要的奧援,以及從不干涉論點的開放與理解,我才得以藉由戰後初期楊逵身影的描摹,逐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最後,謹將這本書獻給敬愛的楊建老師。
安身立命之道
一九九○年十月,秋陽從窗外灑進車內,溫暖著初次見面的我和楊翠。當時的我們正從大甲火車站出發,並肩坐在開往外埔楊建老師家的公車內,愉快地聊著我即將進行的,以楊逵及其作品為主題的研究規劃。這一切的因緣來自於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撥了通電話到大甲高工給楊建老師,洽詢商借楊逵未曾公開面世的手稿。由楊翠陪同拜會過楊建老師後數日,楊翠的夫婿魏貽君先生載著我,從台北專程開車到他位於楊梅的老家,領取一大疊楊逵文稿資料。翌日,雙手捧著已然泛黃的手稿,步入中文系辦公室,一頁一頁小心翼翼地翻閱影印時,為了...
目錄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 陳芳明
序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 楊翠
自序 安身立命之道
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二、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
三、相關資料與本書綱要
第二章 戰後初期的楊逵與「中國」
一、前言
二、楊逵對中國接收政府的態度
三、楊逵與中共地下黨員的關係
四、楊逵與大陸來台編輯的合作
五、楊逵對中國文壇的隔海呼應
六、結語
第三章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的時代意義
一、前言
二、發行概況與創刊之目的
三、宣揚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
四、楊逵有關台灣政局的立場
五、追求民主自治及其困境
六、結語
第四章 楊逵策畫「中國文藝叢書」的選輯策略
一、前言
二、入選的作家與作品
三、忠於原著的直譯法
四、策畫、出版與行銷
五、與《臺灣文學叢刊》之比較
六、結語
第五章 楊逵與大陸來台作家揚風的合作交流
一、前言
二、展轉流徙的文藝青年
三、戰後台灣的紀實報導
四、基於改造社會的合作
五、台灣文化與中國量尺
六、結語
第六章 結論
附錄一:戰後初期楊逵轉載中國新文學一覽表
附錄二:《一陽週報》現存各號刊載作品一覽表
附錄三:揚風作品目錄初稿
(一)戰後初期已發表作品目錄
(二)手稿目錄
參考資料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 陳芳明
序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 楊翠
自序 安身立命之道
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二、戰後台灣文壇與楊逵
三、相關資料與本書綱要
第二章 戰後初期的楊逵與「中國」
一、前言
二、楊逵對中國接收政府的態度
三、楊逵與中共地下黨員的關係
四、楊逵與大陸來台編輯的合作
五、楊逵對中國文壇的隔海呼應
六、結語
第三章 楊逵主編《一陽週報》的時代意義
一、前言
二、發行概況與創刊之目的
三、宣揚孫文思想與三民主義
四、楊逵有關台灣政局的立場
五、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