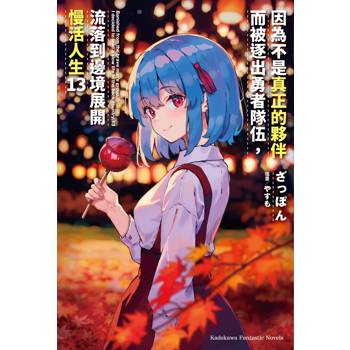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最佳藝術家獎」得主
潘國靈N年醞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我不僅關注書寫狀態,也關注文學在這世界的命運!」
王良和、李歐梵、洛楓、凌逾、張歷君、陳智德、葛亮、
董啟章、廖偉棠、鄧小樺、駱以軍、謝曉虹、聶華苓
── 台港海外文壇名家一致推薦!
一個作家消失了
一場漫長的解咒
一個文字女巫的生成
一段幽靈的召喚
一趟消失的旅程
思考寫作世界和消失的種種可能與命運。
《寫托邦與消失咒》有三個人物、兩段情感故事,作家遊幽為了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自行失蹤,他的愛人悠悠四處尋找,為了進入他的創作生命而來到了「寫作療養院」,療養院的看守人余心一邊帶領悠悠遊逛不同的房間和角落,一邊勾畫處身的城市景觀,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會鏡像與歷史命運,即「香港」!
悠悠被情人丟棄,失魂落魄地來到療養院,想找回男子遊幽,而遇到了解救者余心。為尋回這消失了的作家,余心引導悠悠,寫下遊幽莫名出走的過程,以便了解事故的真相。追求安樂窩、世俗幸福的女子,無法理解在寫托邦療養院沉潛寫作的男子。只有同樣進入寫作世界的女子,才能明白作家的魂去了哪裡。
小說穿梭於雙重世界間,沙城與寫托邦,此處與他方。以沙城的示範屋苑「華麗安居」為序,進入寫托邦的世界。一個作家驀地消失,女子悠悠追逐其作家情人遊幽於密室中,密室成了一所「招魂屋」。悠悠在寫,恍如尋覓也是與影子共舞,亦像把消失的對象埋葬,將之轉化為幽靈。消失的地方不在沙城現場,而把悠悠引至「寫托邦」國度──心靈鏡像投射或處於沙城內核縫隙的隱蔽處。在寫托邦,悠悠遇上看守人/文字巫師余心,在其召喚下一支流放的寫作族群展現眼前,「夜寫者」、「孤讀者」、「築居師」、「回頭者」、「失焦者」、「巫寫會」、「沉降者」等逐一登場,其中的空間幻景──「寫作療養院」、「回頭橋」、「刻寫板屋」、「消失角色收容所」、「修道院迴廊」等不斷變換。消失的遊幽也許在其中,又或者,他不過是她寫作時捲吐的香菸。
延伸閱讀:
潘國靈,《靜人活物》
陳智德,《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董啟章,《心》、《地圖集》、《夢華錄》、《繁盛錄》、《博物誌》、《雙身》
韓麗珠、謝曉虹,《雙城辭典1‧2》
廖偉棠,《異托邦指南/閱讀卷:魅與祛魅》
作者簡介:
潘國靈
小說家、文化評論人,兼任大學講師
著有小說集《存在之難》、《靜人活物》、《親密距離》、《失落園》、《病忘書》、《傷城記》,散文/詩集《七個封印》、《無有紀年》、《靈魂獨舞》、《愛琉璃》,城市論集《第三個紐約》、《城市學2》、《城市學》等。作品於兩岸三地發表及出版,部分被翻譯成外文。曾獲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香港文學雙年獎小說推薦獎、香港書獎等。2006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利希慎基金獎助金」,赴紐約遊學一年。翌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並赴伊雲斯頓西北大學參加該校首屆「國際寫作日」,及到芝加哥蕭邦劇院與當地作家交流。2009年,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室為潘氏舉辦文學展覽「莫『失』『莫』病:文學遊子潘國靈」。2011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
章節試閱
第一章【寫托邦】
寫作療養院
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期間,認識了不少院友,有的在這裡已住上百年了,有些新加入進來,各自有不同或共通的理由進來。他們有些是在外頭迷路,走著走著就走進來,覺得可以待下去,就一直留守下來,在外邊世界,他們也許被列入「失蹤人口」而不自知,然而這裡不是警察帶著巡邏警犬可以搜索得到的地方。這裡太過隱蔽,或者應該說,這裡的隱蔽性太過特殊,不是外邊世界所能輕易追蹤的。其中一些也不是慌失失誤闖進來的,而是在路上飄泊良久,一直在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應許地」,他們在路上顛簸多時,距離各自的家鄉出發地越來越遠,幾乎就要客死路上,幾乎就要放棄了,「應許地」尋找不果,卻中途來了這所寫作療養院。他們有些,只把這裡當作一個中途站,休息一會再上路,一些進來之後,卻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從此無法再寫,卻一直沒有離開。也有一些是被活捉進來的,進來的時候身體負傷著,或者精神已有點異常,好像隨時都有自毀的傾向,需要特別看護照料。有的留幾天就真的嚥下最後一口氣,終於得到永恆的安寧,療養院成了他們生命的墓地。有的帶著身心重傷,生命力異常頑強(還是折磨力異常強悍?),在療養院中活了很長很長的餘生。
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他們不需要入場券,交入院手續費,出示醫生紙,甚麼也不要,他們進來了的時候,就已經進來。門口是一道會變形的門口,只對屬意的人開啟。你若看到它緊緊封閉,如一堵石牆無異,那即機遇未到,你若看到它半掩,那你要自己作出抉擇,進還是不進。它真正開啟時會變身一道窄門,如門縫漏出一隙曙光,尋找的人可以輕身穿過如駱駝穿過針口,這樣的事已經發生了許多許多年。
這個自身可以不斷變形、重組的寫作療養院,會給每一位院友提供最適合他們的空間。院友一般都是獨立幽居的,他們不慣與人交流,偶爾療養院會安排一些放風活動,院友可自行決定參加與否,一點群體生活還是需要的。但整的來說,大部分時候,每人都踏著自己的影子走路。
在寫作療養院中,他們每天都要服用一定劑量的藥物「花勿狂」(Pharmakon)。每人服用的「花勿狂」配方都不同,它不是可口可樂有特定的方程式配方,可以大批複製。事實上,世上沒有兩劑「花勿狂」的配方是完全一樣的。即使是同一個人,昨天服的藥劑,跟今天服的藥劑,跟明天服的藥劑也不一樣,唯獨它的最基本組成元素是一致的,這組成元素叫文字書葉,需要「書寫者」按照自己的追求、口味、喜好自行採摘。他們每天啃掉一片片書葉,吸取書葉中的營養,經消化、反芻、轉化,吐出一串串透明游絲,服之,不為飽腹,而為一種精神靈氣。那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循環系統。
書寫的人
所有在寫作療養院中待著的人,都有一個寫的執念,他們來到此地是因為要寫作,他們各人想寫的東西都不同,而唯有把心目中要寫的東西寫出來,他們才有望被discharge(“discharge”不僅是「離院」,也是名副其實的dis-charge──充電的相反狀態)。進來的人不需要入場券,但出院的話則需要一份「出院書」,也就是他們在住院期間完成的作品。如果作品完成不了,他們一生都帶著一份虧欠的感覺,儘管他其實不欠任何人東西,也從來沒人宣稱是他們的債主。他們其實自身就是債主與債仔,另一種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循環。這些人中有些出了院又會再進來,因為他們完成了一個作品後又隨即將之捨棄,又往自己身上積累新的字債,必須離開喧囂的俗世找一張寧靜的書桌閉關修煉,也即是一再回到寫作療養中,儼如一個長期病患者般。但也有其中一些,回來的時候門不再向他們開啟,他們已經不再是病患者了。
這些懷著寫作執念的人,有人稱他們為「作家們」,但鑑於「作家」之名在外邊世界越發有氾濫也即空洞化、庸俗化的趨勢,這裡我們稱他們為「書寫的人」,你要是稱他們為「書寫動物」、「書寫者」、「文字族」、「寫字兒」也是可以的。在這裡,夢想、幻想、冥思與實錄、記述的邊界是十分模糊的,異國神遊與椅上神遊有時是同一狀態,也可以說,在文學國度,凡能構想的都是存在的,如果你找不到,只是在現實中找不到。
書寫族群
一切由流離失所開始。被放逐的命運是其開端。無論走到哪裡,都不會有一個他們感覺自在的家園。書寫者雖各為個體,但游離的他們,合起來也成一支流徙各地的書寫族群。這些生命離散者,彼此不認識彼此,但彼此又隱密中有所親緣,好像在他們額上烙了一個有待破解的蓋印W,像天生胎印又像因原罪太深而被縫在面皮上的刺青,榮譽與恥辱共存。他們各自在存在的荒漠上行走,孤獨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命運,但在冥冥中他們亦感到一種共生的聯繫,有一把時強時弱的聲音把他們召喚到一處不知實存還是虛構的「寫托邦」(Writopia)國度,這把聲音可能來自外在、高於他們的,也可能來自內在、不過是自我分裂的唇語和幻聽。
耶穌只以譬喻說道理,魔鬼也很會這一套。魔鬼的另一名字是折翼天使,他們墮落凡間,跌落於存在的高處。他們其中一些,在濁世中成為寫作的信徒,語言的囚徒,那受恩賜的,那受懲罰的,他們寧願膜拜九個繆斯的女神為偶像,也堅拒信奉一個單一的上帝。他們把隱喻的本領一一學過來,如天生本能,但他們不說導人向善的教訓。他們只說他們所真正看到的,並極度耽溺於美。他們的故事層出不窮,但既為族裔,也有著他們的生命密碼共通性。我將會把他們的殊異共生面相、處境、故事等,就我所知道的一一道出,如果你感興趣,不妨把他們當作這世上的一類瀕危生物般認識,因為世界的氣候越來越不利於他們的存在;他們無以人工複製如科學家拯救瀕臨絕種生物般,拯救他們於全然崩解的唯一之途,是寫出他們的故事。故事有續命,與死神對奕轉移其視線以延緩死期的作用,這是人類自古就知道的。但我不確定我能否有足夠力氣,說它一千零一夜,如果我中途力有不繼或命有不測,希望有後續的寫者替我接力。
被包圍的場所
那可能你會問,寫托邦到底在哪裡?問這問題的人我向你致禮,因為你不僅問「甚麼是文學」,還問「文學往哪裡找」這更加深問題,然而我同時也要向你致歉:這是不能直接言說的。如果你太刻意的找,我恐怕這會是無限延緩的路。一如所有的樂園(「寫托邦」也是一種樂園,即便是「失樂園」),其準確位置都必須有所隱藏,並與外邊世界有所隔絕,這樣才能確保居住其中的寫作者受到保護。它隱蔽、四周被包圍著,在未可知之所在。神祕性與神聖性不可分割。儘管世上的水上樂園和山中仙景傳說多的是,但我可以告訴你,寫托邦既不在水上,也不在山中。它也不在天邊,星星可以仰望,但畢竟太過遙遠。如果你必須問其所在,我唯一可告訴你的是:它在一個極限盡頭,但始終是與人類生活連結的一個地方。世俗的河流從上游流到這裡,但途中必然也有著天然的屏障,和人為的阻斷。來過這裡的人,離開後對它只有模糊的印象,除非他以真正的寫作折返,否則並無清晰指引路徑可依。它甚至缺乏固定不變的位置,「被包圍的場所」四圍立著圓錐形石堆,做為遷移時的標記。
這隱蔽的被包圍的被保護的場所,其在世位置我不能直說也無從說,但其地貌、景觀、人種我試圖給你呈現,事實上,這便是我最初來到此地的初衷,屬於我的寫作執念。現在也成了我這寫作療養院看守人的一份責任,看守人的職責之一,便是充當這裡的嚮導,尤其為新來者,也為始終懷有神遊異國夙願的人。他們本身也是半知情者或潛在知情者,否則便不會在這裡出現,也不可能留心聽我的話語。
悠悠我心
外邊世界每消失一個作家,我這裡就多一個成員。但最近走進來的一個女子,卻說自己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作家的情人。她情人自家中出走,本來這也不是太稀奇的事,但他出走的時間比她預計的長,前後總算起來,共有一千零一夜了。一千零一夜,我心想,這個女子說的可能也是心理時間,或文學隱喻;即使她說她本身不是一個作家,但能輕易穿越門縫走進來,應該是與寫作有點因緣的,即若她當下並不知道。
於是我問她:「你的作家情人在哪裡消失?又或者說,你最後一次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女子低著頭,皺皺眉頭說:「在家中。一夜醒來不見了。」(那你一定還在夢中。)「我沒想過一個人可以在家中消失的。嗯,其實也不,不完全是消失的,而是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他在另一個世界的自我放逐旅程中,也間歇傳來微弱音訊。我就是仔細聆聽著這些文字音訊,摸著摸著找到這裡來的。說不定他也曾經路過於此。」
「這樣吧,你暫時在這裡留下來,我給你準備一個空間,好好把你尋索的心跡寫下來。寫作的召喚能力,暫時你也許未能領會,但試著吧,看機緣吧,看天分吧,說不定你才是一個真正寫作的人。」
第一章【寫托邦】
寫作療養院
我在寫作的療養院中度過了若許年。
期間,認識了不少院友,有的在這裡已住上百年了,有些新加入進來,各自有不同或共通的理由進來。他們有些是在外頭迷路,走著走著就走進來,覺得可以待下去,就一直留守下來,在外邊世界,他們也許被列入「失蹤人口」而不自知,然而這裡不是警察帶著巡邏警犬可以搜索得到的地方。這裡太過隱蔽,或者應該說,這裡的隱蔽性太過特殊,不是外邊世界所能輕易追蹤的。其中一些也不是慌失失誤闖進來的,而是在路上飄泊良久,一直在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應許地」,他們在路上顛簸多...
推薦序
序一(節錄)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洛楓
有沒有一個文學作品曾經讓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茲在茲?然後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卻又無路可逃?法國文論家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曾經引述卡夫卡(Kafka)的書信,論析「殘酷閱讀」的境況,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災劫、如同自殺,沒有給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卻敲打腦袋致命一擊,情緒晃亂、思慮震動,片刻不能停止或靜止,然後重新發現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這樣的書才值閱讀(頁一七─一八)。說起來有點玄幻不可思議,閱讀是一個死亡和再生的過程,目的是讓我們醒悟於日常的慣性、沉冗與平庸,承受當頭棒喝,猛然驚醒於個體存在的形相及其卑微,這樣的書不容易尋找,這日子卻讓我碰到一本:潘國靈的首個長篇小說集《寫托邦與消失咒》,夜裡失眠的時空總會回閃那些片斷和字詞,明明那是一個基於現實的虛構世界,偏偏血肉相連,割不斷、理還亂,一切從「矛盾的悖論」(paradox)開始說起三個關鍵字:文本互涉、場所、書寫……
開放與私密:文本互涉
第一個關鍵字是「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法國文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俄國理論家巴赫汀(Bakhtin)的觀點,結合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有關「文本」(text)的闡釋,提出所有作品和言說都是一種文本互涉的存有,從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社會、從作家的書寫到讀者的閱讀,都是無數文本的轉化和嵌入(頁三五─三七)。克莉斯蒂娃論述的是文學原理和語言學(儘管許多人誤以為修辭手法或文學技巧),潘國靈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採用「後設」的策略,將「文本互涉」的情態轉換而成小說的構成,刻意大量的引用和鑲嵌幾達鋪天蓋地的程度,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浮出人物的性格、作者的言說,形成一個表面文本開放、內裡其實非常私密的書寫體系。是的,潘國靈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有三個人物、兩段情感故事,作家遊幽為了創作關於「消失」的小說而自行失蹤,他的愛人悠悠四處尋找,為了進入他的創作生命而來到了「寫作療養院」,療養院的看守人余心一邊帶領悠悠遊逛不同的房間和角落,一邊勾畫處身的城市景觀,於是,幾條線索扣在不同視點的轉換,共同砌出一座沙城的社會鏡像與歷史命運,它的「潛文本」(subtext)就是「香港」!然而,潘國靈又不在寫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個「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樓台或迷宮,層層疊起迂迴曲折的各式話語,通篇密佈古今中外的文學、哲學、心理學、繪畫、電影、神話、文學及文化理論的引述,包括波赫士、羅蘭.巴特、杜哈斯、吳爾芙、艾慕杜華、聖經、馬格列特、高達、米蘭.昆德拉、傅柯、西西、村上春樹、尼采、紅樓夢、王文興、尼金斯基、Ouroboros,Narcissus,Peter Pan……這些繁雜文本的穿插,是故事情節結成的部份,以很割裂的形式構成無法割裂的狀態,使《寫托邦與消失咒》變成了「文本萬花筒」,潘國靈把玩猶如七色玻璃的拼貼,旋轉幻變的流光!這樣的取捨,想像的原因有二:一是書中三個角色都是寫作人的身份,不能避免游弋於浩瀚的書海,二是作者本人除了文學創作外,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評論人,文字一直穿梭於古今中外的論述;基於這兩個設定,我便有理由相信,小說的三個人物其實都是一個作者的分裂化身,何況潘國靈互涉的文本還包含自己過去的創作如《親密距離》、《無有紀年》、《靈魂獨舞》,甚至早期的《病忘書》與《傷城記》!基於第三個邏輯論辯,我更確定《寫托邦與消失咒》其實是作者本人一次自我迷失與尋找的啟蒙旅程!
異質空間:寫托邦與沙城
第二個關鍵字是「場所」(locale),事件發生的所在地。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在論及「駁雜地形學」(heterotopology)的時候指出,理解當代世界的方法是從「空間」出發,探討空間如何形成?空間與空間之間怎樣連結?建構了甚麼人際關係?其中更提出「異托邦」(heterotopias)的混雜形態,它是一種「異質空間」(heterogenous space),跟「烏托邦」(utopias)是鏡像關係——如果說「烏托邦」是一個無何有之鄉,不存在現實卻又處處反映現實的匱乏和欠缺,藉此美化「理想地」的追求,那麼,「異托邦」就是鏡子的對立面,帶有「他者」(Other)的屬性,照見自我的存而不在,I find myself abs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I am(頁三五二),是鏡子的另一端,反照自我身處的真實所在,同時看見鏡中的自己及鏡面的存在,並在這虛擬的維度直視周遭的環境(頁三五二);「異托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以迥異的形相分佈不同的角落,有些是禁地,有些是異類場域,像墓塚、監獄、精神病院、療養院、妓院、博物館、殖民地等等(頁三五三─五六)。《寫托邦與消失咒》滿是異質空間,其中互相對照的是「寫托邦」和「沙城」,前者類近一個虛構地方,後者便是香港的「變體」。潘國靈在小說開首的章節即描述「寫作療養院」之所在,是一個「應許地」、「中途站」,隱喻「烏托邦」的色彩,裡面住著自願前來的作家,服用維持寫作慾望的藥物「花勿狂」,是一處「不知實存還是虛構的『寫托邦』(writopia)國度」,不在水上、不在山中,在一個極限盡頭、一個失樂園,寫作人寄居其中,以「文字」作為建築材料,搭建自己的房子和堡壘,是俗世無處可逃、最後匿藏的洞穴或迷宮,四周是房間與牆的幽閉空間,最後成為終老的棲居地;所謂「沙城」,是小說故事發生的現實與現世場景,根據作者的地貌描寫,依稀可以辨認旺角、油麻地、將軍澳等香港區域,到處都是鋼筋水泥的建築、遊玩的樂園、購物商場、公共交通樞紐,同時也是主角遊幽和悠悠日常生活的家和「華麗安居」,生活破碎,人際關係疏離,大眾遵行起承轉合的生命歷程,從出生、長大、工作、賺錢、置業、結婚、養家、生兒育女到老死,溢出這些規條的容易被視為異類,行動講求效益、生活追求舒適,在父母、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敵人的人際網絡裡,織縫牢不可破的身份分配和責任,是男主角遊幽極力逃逸的地方,也是一座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然而,另一方面,在我個人非常主觀的閱讀過程中,「寫托邦」與「沙城」還鬼魅地迴響了兩個經典的文學文本:西西的《浮城》與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作者繼承前者的寓言結構,以「他鄉」說「故地」,將「香港」化成隱喻的載體,同時又借用了後者的「二元結構」或佈局,以一虛一實的空間或世界共同顯影香港的社會實況。無論「寫托邦」還是「沙城」,都是傅柯所言的「異質空間」:一,隱伏危機,所以主角遊幽失蹤了、許多歷史事物被消失了;二,個體行為異常,像遊幽的反抗世俗、世俗者的功利主義;三,充滿禁忌,像對「六四」、「23」等數字的敏感和忌諱,從而消滅;四,矛盾並置,像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中與西、真實與類像、封閉與開放等等生活文化。從這些脈絡看來,潘國靈筆下的「寫托邦」和「沙城」其實也是一個鏡子的重像關係,彼此折射人處其中的欲求不滿與內外掙扎,以及生命的流離失所和自我放逐!
道成肉身:書寫與疾病
第三個關鍵字是「寫作」(writing),及其引發的疾病隱喻。西蘇認為「書寫」是一種爬落梯子底層的狀態,不斷下沉才能到達靈魂的深處、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尋覓並發見那些未可預知的領域,而且沉到底層必然轉身攀爬上去,這便是「昇華」的時候(頁五─六);西蘇又說「寫作人」必須活於極端的生命之中(live at the extremity of life),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才能超越常人不能超越的,以「我寫,故我在」來明證自己,因為「寫作」源於死亡與失去,失去至親、愛情,便以文字填補那些空洞和虛空,延續生命、克服恐懼、戰勝憂患和記錄傷痛(頁一○─一一)!此外,「寫作」必須幽閉,在高牆和樓塔之間禁錮靈感的思緒,忘情也忘我的投入筆下的世界,讓自己方生方死、輪迴再生,然後成就也留下作品(頁二七─二八)。《寫托邦與消失咒》是一本關於「寫作」的論述,以「作家」作為人物切入書寫的世界,揭開各樣因寫作而來的心理、生理、社群或人際糾纏,例如不能依靠「寫作」維生和界定自我,寫作人如何尋找身份、堅持意向、抵抗外來壓力?「作家」到底是甚麼人種或物類?在現實種種捆綁、扭曲、異化和妥協的規範下,寫作人的「烏托邦」究竟在哪裡?假如為了堅守寫作的陣地而脫離世界、傷害愛人,作為基本的「人」又如何取捨?書中的遊幽夾縫於城市生活的瑣碎與寫作生命要求的專注,選擇了離群索居,再自我流徙,「以四海為家,以四圍為界」;失去了愛人的悠悠留守「寫作療養院」,立意要將遊幽的情話寫成傳記,作為「重新擁有他的一個方法」!就這樣潘國靈展開一幅一幅「寫作」的版圖:它是一種執念,用以對抗世界的氾濫與庸俗,也是一種不能抵抗的慾望和誘惑,彷若藥物帶來的幻境和快感;它是一種儀式、信仰、救贖、自我構成,是生命書寫的附魔狀態,甚至是病、是身體的一部份,寫作跟身體息息關聯、呼吸與共也禍福相連,既可療癒又可戕害!此外,寫作猶如「愛情」,充滿徒勞與塗抹,不是能愛便能獲得,不是失去便可以彌補,用盡力氣與花盡心思可能還是一無所有,但仍然能夠寫下,卻是唯一擁有對方的憑藉,很矛盾和解構,卻是書寫與愛情共有的本質!最後,寫作其實是一趟自我消失的旅程,在迷途中掉進懸崖或囚室,或迷失於網絡世界,以書寫善終!
隨著「寫作」而來的是「病」(illness),各樣身體、心理、精神和社會的病,及其種種藥物效應,像因失眠而服用的「白瓜子」(安眠藥)、因抑鬱症而來的胃酸倒流,還有癲癇症與痙攣、亢奮與疲憊、Depression與脾臟沉降,還有菸葉、大麻、罌粟、酒精、咖啡和迷幻藥,甚至「寫作病」,一種自閉、自疑、焦慮、驚恐的症狀,體力與心力透支的盡頭是人的解體,肉身最後消失。美國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中說過,「疾病」通過身體言說,將精神和人性心理變成戲劇化的語言、一項自我表述,不同性格導致不同病理,於是疾病也宣示性情,另一方面,「流行病」是社會動亂的表癥,呈示宗教、道德與公共秩序的失衡(頁四四─五八)。《寫托邦與消失咒》呈現大量的「疾病」書寫,既聯繫個體的生理失調與生活壓力,也環扣社會、政治、經濟、人際關係的腐化和侵蝕結果,個體的病、群體的隱患、城市的不健全與病態,連成一線,牽一髮而動全身,而潘國靈筆下的沙城(或香港)充斥過度發展的消費與浪費、政治的壓抑與禁制、文化的稀薄和功利、社會的分歧和貧富不均、族群的決裂和孤絕等等積勞成疾的病變,而當這些人與城市的疾病變成絕症以後,便祗有消亡的終局,因此,在遊幽失蹤後也預示了「沙城」即將的殞滅!
潘國靈寫道:「他在,又不在。眼睛盯著前方,但又有一種渙散。渙散是於我而言,他其實在對焦另一個世界,或者可以說,生活在他方。」像這樣相反相成的「悖論」,貫穿了整個小說的核心與外圍,而當無數弧線重疊的時候,核心的外圍也是核心的內圍,於是,寫拓邦與沙城,書寫與疾病,潘國靈跟他消失的角色,還有我這個讀者(同時也是一個作家的身份),都被捲入了複像與疊影之間:「真身與影子、後方與前方、演員與觀者、光與暗」(書中悠悠的敘述)!正如傅柯所言:I see myself where I am not,如果「文學」也是一面鏡子,它的殘酷就是照見了眾生的極端生命!
序二(節錄)
開拓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凌逾
香港知名作家潘國靈已寫了十四部書,又經N年醞釀,第一部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終於在二○一六年問世。扉頁有「作家消失、解咒、文字女巫、幽靈召喚」等字眼,開篇就營造出詭異神祕氛圍,讓人好奇,這到底是奇幻、偵探、魔幻小說?還是雌雄莫辨、難以歸類的小說?
一、自創:寫托邦、寫作療養院
為打造首部長篇,潘國靈度身訂做了一批新詞。一開幕,獨特意象就登場亮相:「寫托邦(Writopia)、寫作療養院」。然後,愛情故事出場:悠悠被情人丟棄,失魂落魄地來到療養院,想找回男子遊幽,而遇到了解救者余心。為尋回這消失了的作家,余心引導悠悠,寫下遊幽莫名出走的過程,以便了解事故的真相。追求安樂窩、世俗幸福的女子,無法理解在寫托邦療養院沉潛寫作的男子。只有同樣進入寫作世界的女子,才能明白作家的魂去了哪裡。
潘國靈不斷嘗試給自創新詞下定義。寫托邦恰似寫作療養院,裡面住著一群懷著寫作執念的人:病人們每天要服用一定劑量的藥物,「花勿狂」,既是解藥也是毒藥,每劑配方都不同,但均為文字書葉,書寫者按需要採摘啃食,以實現自我完成的循環系統。筆者梳理一下「寫托邦」的理論譜系。烏托邦(Utopia),憧憬美好社會,中式有莊子的無可有之鄉,西式有柏拉圖、莫爾論述。今人讚新科技:米切爾認為,「伊托邦」(E-topia)從水井中心到水管中心,再進化到網路中心;凱文.凱利說未來科技是「進托邦」(protopia)。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科技文化有末世論(eschatology);安德魯.芬伯格認為,科技是歷史終結的元凶,詛咒惡托邦(dystopia)時代;這源於對戰爭的反思,赫胥黎、奧威爾的反烏托邦憂思,《駭客任務》、《全面進化》、《魔鬼終結者》等科幻都憂慮智慧型機器人過度進化。傅柯創設「異托邦」(heterotopia),描述監獄、瘋人院等處於邊緣和交界,不同於烏托邦的空存。董啟章《地圖集》寫殖民地香港的異托邦,認為地球實體空間幾近研究殆盡,唯有-topia想像之地,尚有文藝置喙可能。二○一六年初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zootopia),想像全新的動物烏托邦:肉食和草食動物和平共處,尊重多樣性和差異性,減少歧視和偏見。創客們日益喜歡創造「-topia」系列詞,大有「X托邦」情結。
潘國靈創設「寫托邦」王國,既烏托邦,也異托邦。這飄浮於沙城上的一方淨土,遠離人類,既開放又排斥、既打開又關閉,將本不能並存的幾個空間並置,不是幻想的而是補償的異托邦,既在此又在彼的鏡子烏托邦,內裡又有歷史堆疊的時間異托邦,即異托時,如博物館、圖書館,共時和歷時的異托邦共存。寫托邦恰似「異次元空間、多維空間」,次元即維度,一維線性、二維平面,三維立體,四維則超越了空間概念。寫托邦,也許不在三維空間,而立身於五維、六維等高維空間,存在於心靈、靈感空間,像靈魂的夢境,自由的天堂。
為什麼創設「寫托邦」新詞?寫小說的人寫小說,自曝虛構過程,這是西式後設小說。但《寫托邦與消失咒》既曝露作家寫小說的過程,也省思寫作本身,寫透創作病症的林林總總,彷彿寫作病理學專著。書寫者們在紙上搭建文字堡壘,我寫,我寫,寫進去,三重血淚;長年迷失在書屋和圖書館,在搬書勞苦中體驗生活;深知唯有書本,能把自己帶到應許地;陷入寫作的無限迴圈,像堂吉訶德,與自我的風車作戰。《寫托邦與消失咒》書葉以淚澆灌,書脊以血灌注,書寫者唯一的存在之高處在深淵,這深淵無法以「尺、米」記,只能以「尋」記,尋不完、沉不完。可謂一把辛酸淚,兩袖空空風。
二、迷宮文學:人際層次的多重鏡像、傳統與世界的知識迷宮
迷宮本指門戶道路複雜難辨,也比喻充滿奧祕不易探討的領域。全球善造迷宮文學的高手,有波赫士、卡爾維諾、納博科夫、普魯斯特等,搭建時間的迷宮、敘事的迷宮、自我的迷宮、記憶的迷宮……書寫本義隱匿纏繞,費人思量。潘國靈創設迷宮編碼,讀者破解編碼,發現新書的隱藏密碼,如何滲透出香港性、本土性、傳統化與世界性因素,也很有趣。
構築人物層次的多重敘事迷宮。全書開篇不久就直白以告,人名創設的緣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因有悠悠,而有余心,在遠古詩經就有了塵世的約定。無名無姓,任我命名,是為文字最初的自由。悠悠和遊幽有同音之名,卻有不同的性別身份,分裂為兩半,彼此尋找。只有男作家寫透女巫,女巫寫透男作家,悟透性別的奧妙;只有我心,才能凝聚神魂。悠悠、遊幽、余心實際是三位一體,互為鏡像。當男女分身完美地凝合為雌雄同體,性別和解,才能尋回最強大的自我。就像卡爾維諾的《分成兩半的子爵》,子爵被劈成善惡兩半,最終必須合體,才能成為完整的人。
搭建敘述者、人物與讀者的迷宮。不採取套盒結構法,而用旋轉木馬式輪軸轉法,讓三個人物各自吐露心聲,輪流登臺,好像話劇一般。三人都身兼多重化身:互為作家,又互為作家的筆下人物,又互為讀者;作者尋找人物,人物尋找作者,作者尋找讀者,種種苦情;他們結成一個個對子,複調對寫。後現代戲劇熱衷於實驗一人分飾多角,或是多人分飾一角。潘國靈的敘述者也不斷分身,從親歷者、旁觀者、中立者等角度傾訴,折射書寫者的所有悲喜。有時作家又兌換成書,書又兌換成作家,形成更撲朔迷離的關係。
再造香港本土文學迷宮,向前輩作家們致敬。潘國靈從西西的「我城、浮城」改寫起步,創設「沙城」書寫。二○○五年,向西西三十年前的《我城》致敬,寫〈我城零五〉之版本,串燒西西筆下子民,另炒出新家族關係圖:阿果女友悠悠,朋友麥快樂,麥快樂嫲嫲為白髮阿娥;還向西西〈浮城誌異〉取經,也借馬格列特超現實畫作想像,讓愛寫的悠悠代筆寫文:「悠悠的浮沉之城、眼睛之城、烏鴉之城、口罩之城」。新書讓前作的人物裂變;且對烏鴉城、口罩城有更深的發揮:提及當年寫〈鴉咒〉,將自己完全寫進去,迷狂體驗如邪靈附身。新書乘上想像的飛氈,也向西西《飛氈》致敬。
召喚前期作品之魂靈。如新書寫及人與櫥窗模特人偶互動,與作家的兩篇前文互涉:一是小說集《靜人活物》的〈不動人偶〉;一是《存在之難》中的〈兩生花店〉。新書再次寫及死魂靈出版社,也出自《靜人活物》。潘國靈說被《去年在馬倫巴》的謎打動,謎無法破解,如人生,也像其迷宮文學。
重構全球文化符碼,鑲嵌神話、傳說、小說、電影、戲劇等多元豐富元素,有高遠的世界情結。如寫月神娜娜(Nanna),抄寫女神妮莎巴(Nisaba);對比歐洲的木偶劇與中國的皮影戲映照,為了寫囚徒與影子人;提及杜哈斯《寫作》的洞穴隱喻,為了寫洞穴放映會,洞穴癖。寫蛇頭咬著蛇尾的傳說,為了引出麥克.安迪的《說不完的故事》,小男孩闖入文字叢林,進入忘我境地,自我消失,故事不止。西西也寫過〈永不終止的大故事〉。活在河的第三岸的父親消失了,這是向巴西作家若昂•羅薩的短篇致敬。西西也引用過此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心人總能在全球人、歷史人中找到靈魂感應對象,心有靈犀一點通。
創世紀的寫托邦。這本新書其實意在創建體系,作為階段性的寫作系統整合,這部集大成之作建立書寫者的寫托邦,視野宏闊。董啟章的《貝貝的文字冒險:植物咒語的奧祕》,自創少兒文學的創意寫作教材,小女孩咒語附身,必須寫作闖關,才能逃離困境。此書也像創意寫作小說教材:余心帶著悠悠,逛遊寫作遊樂場,讓其感悟寫作的祕笈,在文字中找回消失的情人,體驗寫作之痛。劉以鬯《酒徒》是對寫作進行酒徒式反觀凝思;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是對寫作進行失魂式招魂苦思。
三、暗黑的基因:消失的咒語
《寫托邦與消失咒》所憂思的,首先是對書寫的寫性體悟,其次是對沙城的城性界定,深層是對未來的憂慮。作家吹響了負能量詞彙集結號,從章節標題到具體文本,塗抹了大量的灰色,種下了暗黑的基因,描繪憂思:孤讀者、離鄉者、憂鬱者、失焦者、失神者、無適度者、書墓園、災難界、已死區、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場……人到中年的迷茫,極致的寫作體驗,陰森的寫作文風,讓人印象深刻。潘國靈讀卡夫卡感悟到,創意在陰溝、沼澤中滋生,正常,與文學無親,這也是藝術之難。在寒冰文風影響下,敘述者形象多變易變。
文學語言的執念者。這些人額上都有W印痕,這些文字問米婆、被閃電擊中的人,學徒階段多做抄寫員:把白粉牆當作塗鴉牆,從客廳到門再到塗鴉牆,從個人空間轉向公共空間,一步步略有成就;漸漸成為夜寫者,夜鶯族,受貓頭鷹智慧女神眷顧的人,像魯迅,張愛玲等。西西作品透光度高;潘國靈作品透夜度高,新書在班雅明城市蕩遊者基礎上,拓展書寫城市的夜遊者。
沙城空間的敏感症者。全書不僅描畫沙城外的空間:療養院、靜默迴廊、招魂屋、沙中城堡;也描畫沙城都市景觀:置身於周圍飆升的鉛筆高樓,沙城唐樓變成小矮人王國;住在華麗安居大廈的作家,卻要自行消失。身處其中,有築居師、離鄉者、回頭者。作家自己就是築居師,搭建語言的房子。筆者曾論述過西西《我的喬治亞》示範文學建築師的風采,搭小說如搭房子。潘國靈寫築居師自創文字迷宮,卻連建築的空殼都寫沒了。
消失人與消失美學。筆者曾論過,潘國靈創造了「蘋果、手機符號學、壓縮人、數字人、貧淚人」等新美學。如今新書又創造「寫托邦、消失人、消失美學」等物事。作家消失,不僅是大隱隱於市那麼簡單,消失四處蔓延。呈現作家思想來源;建造消失角色收容所;想像消失的十二種可能。書寫者經歷出走記,遍遊雕像界、災難界、書墓園、已死區、回收筒、自照湖、埋葬場,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的廢紙收購站老打包工,獨白其三十五年感受,控訴對踐踏人類文化的愚蠢暴行。書籍被棄,就像書寫者。讀者死了,因為人人都成為寫手,卻不願成為讀者,讀者稀缺,喪失了閱讀能力。書沒人讀,變成棄嬰。古往今來,消失咒陰魂不散。潘國靈創造「消失的作家」,像羅薩的「活在彼岸的男人」,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童話「穿紅舞鞋的女人」,都讓人過目不忘。
此書結尾也貫穿消失美學。寫作者被安排到沙中城堡,靜思寫作,想寫「出沙城記」者,以為自己走了很遠,但卻仍在沙城之內。就像《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寫現實與虛構雙聲道的難以打通,或然與實然世界的難以通約,《寫托邦與消失咒》寫生活與愛情的難以相容,深思消失的可能性,與實然性周旋拉鋸,鋪陳敘事。追尋沒有結局,因生活與小說有邊界,文字與愛情也有界線,將兩者消融雖是境界,但也危險,女子陷入悖論,無法解救。到最後,所有的人物、追尋的情節、寫作本身都消失了,這造就了懸念的保鮮術,懸念永不終止……
不同的作品,賜予人的力道是不一樣的:有些善講故事,善寫當下;有些有歷史的穿透力;有些善於頓悟,哲思;有些如沐春風;有些疾風驟雨。《寫托邦與消失咒》不是傷痕、反思、尋根、新寫實文學,而是苦吟、沙城、消失派文學,獨創「寫托邦、暗黑美、消失人、消失咒」等新美學。但此書本身卻絕不會消失,而會激發人產生評說、解釋的慾望。作家直面寫作的魔咒,以自身精采的創作,開拓「寫托邦」的創世紀文學,成功實現了解咒,獨一無二。該書乍看像言情、偵探、魔法小說,但實際卻不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通俗小說,而是讓人痛苦的小說,進入它,就像跌入了無法測底的思想深淵,難解的困境、人生的兩難、深刻的問題,像錐子一般刺痛著你,逼迫你思考不已。這痛並快樂著的書,昇華出哲學的韻味。
序一(節錄)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洛楓
有沒有一個文學作品曾經讓你失眠、心悸、坐立不安而念茲在茲?然後迷失在文字的苦海不能自拔卻又無路可逃?法國文論家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曾經引述卡夫卡(Kafka)的書信,論析「殘酷閱讀」的境況,一些作品彷若利刃一般插入心房,彷彿災劫、如同自殺,沒有給予任何甜美的快感,卻敲打腦袋致命一擊,情緒晃亂、思慮震動,片刻不能停止或靜止,然後重新發現了自己和生命的所在,祗有這樣的書才值閱讀(頁一七─一八)。說起來有點玄幻不可思議,閱讀是一個死亡和...
目錄
序一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 洛楓
序二 開拓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 凌逾
第一章【寫托邦】Writopia as Asylum
寫作療養院
書寫的人
書寫族群
被包圍的場所
悠悠我心
第二章【招魂屋】Apartment as Apart/ment
此處與彼處(悠悠)
夜寫者(余心)
睡房的共語(悠悠)
孤讀者(余心)
書房的回憶(悠悠)
築居師(余心)
客廳的塗鴉(悠悠)
離鄉者(余心)
華麗安居(悠悠)
回頭者(余心)
過渡空間(悠悠)
憂鬱者(悠悠)
第三章【消失咒】Disappearance as Character
交換故事.演員(余心)
抄寫員(悠悠)
消失札記(抄自「塗鴉牆」)
消失角色收容所(余心)
為了寫作的消失(遊幽.悠悠)
日落前讓捉迷藏終結(悠悠)
巫寫會(余心)
消失的十二種可能(悠悠)
消失的另種可能(余心)
第四章【附魔者】Writer as (Dis)illusionist
作家與編輯的相遇(悠悠)
被閃電擊中的人(余心)
文字與愛情的界線(悠悠)
阿菲西亞(余心)
給寫作附魔的人(悠悠)
無適度者(余心)
否定的人(悠悠)
文化醫生.一場文學的病變(余心)
文學助產士.書本與妊娠(悠悠)
一趟消失的旅程(悠悠)
修道院.迴廊(余心)
第五章【字畫像】Portrait as Effacement
失焦者(余心.悠悠)
失焦自畫像(悠悠.遊幽)
無所歸屬的人(悠悠)
一個書寫者的,不安之書(編輯:悠悠)(遊幽)
沙城前後(遊幽)
從那邊遙寄的放逐者遊記(遊幽)
名利場(悠悠)
一段關於自殺的對話(悠悠.遊幽)
互困亦是一種結果(遊幽.悠悠)
傳記作為情話、毀容與塗抹(悠悠)
幽靈的還原.文字問米婆(余心)
第六章【出走記】Exile as Return
飛鴿傳書(悠悠)
回歸之旅(遊幽)
第七章【洞穴劇】Cave as Theatre
沉降者(悠悠.余心)
洞穴放映會(洞穴癖.木偶劇藝人.囚徒.影子人)(悠悠)
災難現場(悠悠)
沙中城堡(余心)
序一 極端生命的殘酷閱讀──潘國靈和他的消失角色 洛楓
序二 開拓寫托邦與消失美學──論潘國靈首部長篇《寫托邦與消失咒》 凌逾
第一章【寫托邦】Writopia as Asylum
寫作療養院
書寫的人
書寫族群
被包圍的場所
悠悠我心
第二章【招魂屋】Apartment as Apart/ment
此處與彼處(悠悠)
夜寫者(余心)
睡房的共語(悠悠)
孤讀者(余心)
書房的回憶(悠悠)
築居師(余心)
客廳的塗鴉(悠悠)
離鄉者(余心)
華麗安居(悠悠)
回頭者(余心)
過渡空間(悠悠)
憂鬱者(悠悠)
第三章【消失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