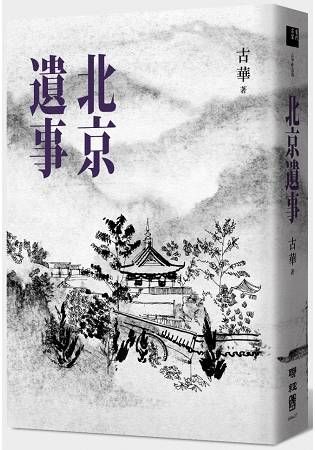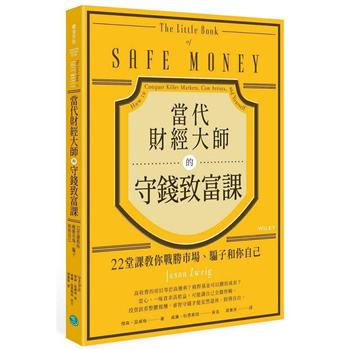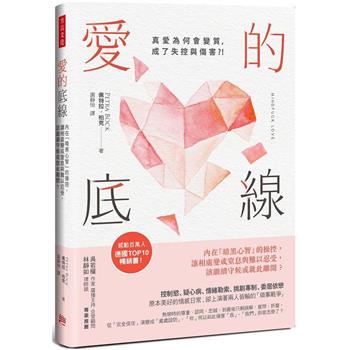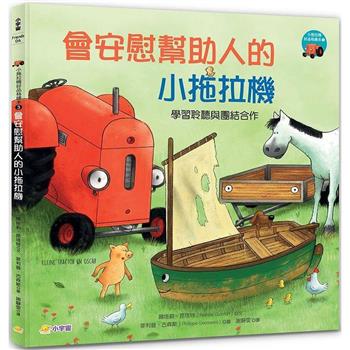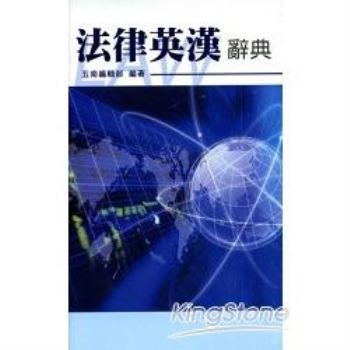1989年之前的北京是什麼樣子?
躍進或解放、鬥爭與災難、饑荒和瘋狂,教人連命也可以丟掉!
躍進或解放、鬥爭與災難、饑荒和瘋狂,教人連命也可以丟掉!
睽違26年,繼《芙蓉鎮》、《儒林園》之後
第1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中國當代知名小說家 ── 古華
蟄居10年完成,近20年最為費時費力,震驚全球華文讀者扛鼎之作
《北京遺事》為第1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中國當代知名小說家古華歷時10年完成、具史詩意識之長篇力作。內容超越時空,通過一城一鄉兩個家庭、一僧一俗一對戀人的命運傳奇,行雲流水、波瀾不驚且娓娓動聽地敘述神州小兒女們在大時代瞬息萬變、風雨雷霆中的悲歡際遇,生命無常。
古華在小說中時而春花秋月喁喁情話,時而鐵鐃銅鈸慷慨悲歌,時而談天説地臧否古今,涵蓋現代中國社會歷史、文化、教育、藝術、政治、經濟、科技、地理、交通、民族、宗教、法律、獄政等廣闊領域之風雲變幻,家國沉浮。世紀回聲綿綿不絕,實爲一部小百科式、精彩紛呈的文學讀物,更是以小見大的時代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