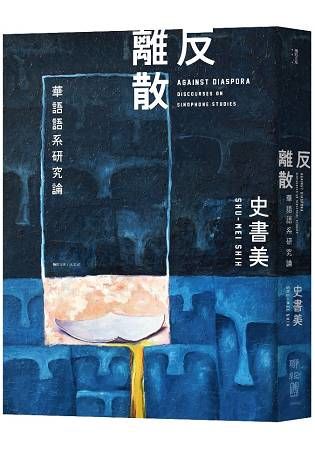比較文學家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最新成果
討論華語語系的概念、使用、方法與實踐
探討其歷史內容、語言的多樣性與作為理論的潛力
史書美最新論著《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提出了華語語系研究關注位處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以及霸權生產邊陲的華語語系文化,其焦點放置在因三個歷史過程而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大陸殖民、定居殖民、以及遷徙/移民。
華語語系研究瓦解自民族國家興起後語言、文化、民族與國籍之間形成的等價鏈,透過思考在地生產的獨特華語語系文化文本,探索中國與中國性、美國與美國性、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性、台灣與台灣性等邊緣如萬花筒般多變且具創造性地重疊交錯。
《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認為華語語系文化的形成包含許多不同標記,語言標記通常可作為其他隱含差異的縮影,因此對漢語族語系語言的基本知識是必要的。華語語系的概念顯現聲音和書寫上的多語性。例如華語語系香港文學藉由創造新興用語和文字,長期協商於粵語與北京話之間;主流華語語系台灣文學則是河洛語和北京話協商的場域,文字上也每有創新;華語語系馬來西亞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在文本和電影對白裡應用粵語、福建話、潮州話、北京話等不同元素的聲音和文字。因此,華語語系不只多音(polyphonic),也多文字(polyscriptic)。此外,華語語系的概念不僅表達語言的多樣性,同時也凸顯這些語言在特定地點與當地非華語的各種語言在地化與混雜化的過程。回族雖被視為中國境內漢化最深的少數民族,但華語語系回族作家仍常使用或借助阿拉伯語。以華語語系新加坡文學為例,作家們將各種華語和馬來語、英語,有時甚至和坦米爾語交混。同樣地,華語語系美國文學是一個已經存在超過百年的文學傳統,早年以粵語寫成,近年則更多標準漢語的運用,其長久以來的隱性或顯性對話者為位居主流語言的英語。
延伸閱讀: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
鍾怡雯,《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Ⅱ》
張小虹,《時尚現代性》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
作者簡介:
史書美(Shu-mei Shih)
出生於韓國,台灣讀大學,美國讀碩博士,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以及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從2013年到2015年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陳漢賢伉儷講座基金教授(專任),現為同職位的兼任講座教授。於2012年曾任臺灣大學文學院白先勇講座客座教授。也曾客座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義大利波隆納大學、加拿大卡爾頓大學、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等。
著作大多發表在美國,為華語語系研究的創建人及主要的立論者。其論文散見美國的主要學術刊物如PMLA等,部分論文有翻譯成華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土耳其文。
專著包括《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等,另合編Minor Transnationalism、Creolization of Theory、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Comparatizing Taiwan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
本章就「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定義提供一個概略性的、綱領性的視角,這一視角將後殖民研究、種族研究、跨國族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融會起來。華語語系研究是對處於中國和中國性(Chineseness)邊緣的各種華語(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體的研究。這裡「中國和中國性邊緣」不僅僅理解為具體的,同時也要理解為概略的。它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地緣政治之外的華語群體,他們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續幾個世紀以來移民和海外拓居這一歷史過程的結果;同時,它也包括中國域內的那些非漢族群體,由於漢族文化居於主導地位,面對強勢漢語時,它們或吸收融合,或進行抗拒,形成了諸多不同的回應。由此,華語語系研究整體上就是比較的、跨國族的,但它又處處與時空的具體性緊密相關,即依存於其不同研究對象而變動不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並不專門聚焦於文學,而是借助對「離散中國人」(the Chinese diaspora)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評,提出華語語系研究的粗略輪廓。在我看來,「離散中國人」這種提法是不恰當的。
一、「離散中國人」
數百年來,那些從中國遷徙出去、在全球範圍內散居各處的人們,對他們的研究作為中國研究、東南亞研究、美國華裔研究的一個子域而存在,同時,在美國的歐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中也有零星關注。此一子域,其邊界圈定在那些從中國移居任一他鄉的人們,故被稱為「離散中國人研究」。「離散中國人」被理解為中華民族在世界範圍內的播散,作為一個普遍化範疇,它以一個統一的民族、文化、語言、發源地或祖國為基礎。新疆的維吾爾人、西藏及其周邊地區的藏人、內蒙古的蒙古人,如果他們移民海外,通常並不被認作離散中國人的一分子,而移居海外的滿人則模棱兩可。涵蓋與否的標準似乎取決於這些民族的漢化程度,因為慣常被完全棄置不顧的事實是,離散中國人主要是指漢族人的海外流散。「中國人」,換而言之,本來是一個國家屬性標誌,卻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的、語言的標誌被傳遞,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漢族中心的標籤。而事實上,在中國由官方認定的民族就有五十六個,各民族所操持的語言更是多種多樣。通常被認定和理解的「漢語」不過是國家推行的標準語,即漢族之語,亦被稱為普通話;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很大程度上被限定為漢人;而「中國文化」指的也是漢文化。簡而言之,「中國人」這一術語作為一個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範疇,常常被限定於指稱漢族,而將所有其他民族、語言和文化排除在外。將域外的中國性簡化為漢族這一單一民族屬性,其實也只是類似訴求之翻轉(inverse)而已。歷史上,眾多民族對於形成今天的「中國」有著重要的貢獻,例如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滿族的重要遺產──他們擴充的疆域,被之後的中華民國以及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因此,這種將中國人視為漢人的民族簡化主義,與把美國人誤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並沒有什麽不同。在上述兩種情況中,都有一種貌似不同卻類似的民族中心主義在作祟。
中國海內外的各種因素究竟如何共同促成了一統的「中國人」觀念?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我們或許要追溯到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種族主義觀念體系,他們根據膚色來認定中國人,從而忽視了中國內部的豐富性和差異性。這就是中國人成為「黃種人」且被化簡為單一民族的開始,而事實上,在不斷變化的中國地緣政治的邊界內,歷史上一直存在眾多明顯存在差異的族群。中國人一統性的外在促成力量,與中國內部一統的訴求悖論地不謀而合,尤其是在一九一一年滿族統治終結之後,中國急切盼望著出現一個統一的中國和中國人群體,以凸顯自身在文化和政治上獨立於西方的自主性。唯有在這種語境中,我們才能夠理解在十九世紀末,由西方傳教士提出的「中國人的國民性」話題,何以同時在海內外的西方人和漢人中流行起來;我們也才能夠理解,這一觀念何以在當日中國對於占據主流的漢人一如既往地散發著魅力,如有關中國人的素質問題的討論。一方面,對於西方列強而言,它為一九四九年之前殖民中國找到理由,也使得十九世紀末到現在在這些列強國家內部實施對華人移民和華人少數群體的差別管理變得合情合理;不管出於哪個目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這一說法的用處都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和漢人而言,種族意義上的「中國人」至少出於三個不同的意圖:以統一的民族抵制二十世紀早期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主義;踐行自省(self-examination),這是一種將自我(self)這一西方概念內在化的努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除了給部分少數民族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之外,還要把少數民族的國家訴求和愛國奉獻精神調適到中國這一國族身分上。
以上對「中國人」和「中國性」術語問題簡要而寬泛的探討充分表明:這些術語被激活,乃是由於與中國外部其他人的接觸,以及與內部其他族群的碰撞。這些術語的意義並非只是在最一般層面上使用,同時也在最具排他性的層面上發揮著作用,它們兼含普遍和特殊於一體。更確切地說,強勢個體把自己仿冒成普遍性,這與外部因素施加給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性的粗糙的普遍化串通一氣。這種外部因素來自西方,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自亞洲其他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它們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抑制且抵抗著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日本和韓國明確地開展「去漢化」運動,定義自己國家的語言,以反抗中國文化的霸權,例如,在它們各自的語言中,消除日文漢字和朝鮮漢字的重要性。
人們從中國移居世界各地,在暫住國逗留,有時候也進行殖民開拓,例如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新加坡)。雖然離散中國人研究試圖通過對他們本土化傾向的強調,去拓寬中國人和中國性的問題,但「中國性」在這一領域依然占有主導地位。因此,審視「離散中國人」這個一統性的範疇在當下顯得十分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它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共謀關系──民族主義者習慣用「海外中國人」,而「海外中國人」這一提法假定這些人渴望回到作為祖國的中國,而且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服務中國──同時也由於它不知不覺地與西方和非西方(如美國和馬來西亞)國家對「中國性」的種族主義建構聯系在一起,且起著強化作用──在這些國家,「中國性」永遠被看做是外國的(所謂「離散的」),而不具備真正本土的資格。在東南亞、非洲、南美洲的後殖民民族國家裡,如果從歷史上說操持各種華語的人已經進入本土居民的行列,這並沒有什麽牽強之處。畢竟有些人早在六世紀就來到東南亞,比那裡民族國家的存在還要早得多,理所當然地足以經得起與國籍捆綁在一起的身分標籤。問題在於,誰在阻止他們成為一個泰國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度尼西亞人,或是新加坡人,和其他的國民一樣被認為僅僅是多語言和多文化的居民,只不過恰好有一個來自中國的祖先而已。情況相類,誰在阻止那些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他們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來到美國)成為「華裔美國人」(在這個複合詞中強調後者「美國人」)?我們可以細想五花八門的種族排斥的行為,諸如美國的《排華法案》,越南政府對當地中國人的驅逐,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反中國人的種族暴亂,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以及爪哇的荷蘭人對中國人的屠殺,菲律賓針對中國小孩的綁架,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案例。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人」這一具體化的範疇,作為一個種族和民族的標籤,是如何成全了諸如排外、替罪羊和迫害的各種企圖。當意大利人、猶太人和愛爾蘭人的移民逐漸成為「白人」,融入美國白人社會的主流之中,而作為華裔美國人的黃種「中國人」卻依舊還在為爭取認同而飽嘗艱辛。
第一章 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
本章就「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定義提供一個概略性的、綱領性的視角,這一視角將後殖民研究、種族研究、跨國族研究以及區域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融會起來。華語語系研究是對處於中國和中國性(Chineseness)邊緣的各種華語(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體的研究。這裡「中國和中國性邊緣」不僅僅理解為具體的,同時也要理解為概略的。它包括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地緣政治之外的華語群體,他們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續幾個世紀以來移民和海外拓居這一歷史過程的結果;同時,它也包...
作者序
華語語系的概念
中國迅速崛起成超級強權或許迫使我們當下重省目前關於帝國與後殖民性的論述,但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滿清征服「中國本土」北邊與西邊的大片疆域時,它便符合我們所賦予的帝國一詞的現代意涵。這段歷史因兩個不被承認的執迷而常被忽略:對西方帝國的迷戀以至忽略其他帝國擴張的模式與盛行的中國被列強欺凌之論述。若我們的視野沒有長期偏頗海洋(亦即西方)殖民擴張的模式,將西方視為知識勞動中最值得分析的對象,中國的崛起便不會引起這麼大的驚訝。若我們將中國今日的崛起與滿族對內亞的侵略視為一種殖民事業的繼承與強化,我們也不會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如此驚訝。當我們考量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東方主義的批判時所採取的立場,我們所理解的後殖民理論,特別是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可能無用武之地,甚至有共謀之嫌,因為此立場容易淪為缺乏內省的民族主義,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另一面。雖然不可否認在滿清帝國以降的中國在歷史上有一段承載受難者經驗的時期,但中國受西方帝國欺凌,幾乎可稱為受害學的受難情結論述有效地掩蓋了自身缺乏內省的民族主義。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是繼承或重新殖民滿清所占領的大片領域,包括西藏、新疆(其字面意思「新的疆域」明顯指示領土的擴張)、內蒙古與滿洲,將「中國本土」原本的領域擴張兩倍以上。現在,當中國對早期西方帝國侵略以一種彷似後殖民的立場宣稱對「領土完整性」的高度關切與批判時,此立場對被併吞領土的藏族、維吾爾族與蒙古族而言同時也是一種帝國的宣言。
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更需要復甦一個既有但卻長期被邊緣化的批判傳統,批判「中國性」(Chineseness)的霸權與同質性。以許多不同的邊緣形式存在於中國境內與其外的作家與藝術家早已批評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性的霸權,視之為強加在身分上的殖民枷鎖。此批判傳統在中國境內遭受意識形態的箝制,但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傳統在中國境外的命運更是悲慘:這個批判中國性的傳統基本上被視而不見或不予重視。在美國,左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浪漫情懷加上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機器因政治與經濟考量需安撫中國,此兩因素重重地打了批判《PMLA》中國中心主義傳統一個巴掌:這個批判傳統因為被忽略,進而淪為一個莫不相關的傳統。
對於某些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所謂的非漢族,因此不夠正統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中文──漢族的語言或漢語──是殖民強加上的語言,因此在少數民族之間,「中國人」通常只是護照上國籍一欄的稱號,並不包含對文化、民族或語言的指涉。中國官方認定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他們的文化工作者自其社群被納入中國後便長期將自己定位在中國性的邊緣。這些中國的內部殖民地,美其名被稱為自治區,其疆界實際上被肆意劃定,而自治也常常僅是名義上的自治。在地文化、語言與宗教信仰的消逝歷歷在目,從近來頻繁的西藏與新疆的各種騷亂及抗爭事件便可探知一二。位於中國西南部有些少數民族村落今日被定位成旅遊村,當地居民穿著傳統服飾敞開家門迎接好奇的遊客。日常生活商品化的極致表現,莫過於商品化個人生活中具異域風情的食衣住行等面相,日常生活竟然可以成為維生的工具。
在東南亞、澳洲、台灣、美洲、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華語語系作家與藝術家,一直都有拒絕被收編入中國性的框架的傳統。同時,他們所追尋的在地認同也通常與在地的強勢的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或種族主義的認同模式格格不入。從中國來的移民被加諸中國佬(Chinaman)、支那人(chino)與異教中國佬(heathen chinee)等歧視性稱謂,使他們與其後代無法完全認同他們歸化的土地。黃禍的種族主義論述在西半球對中國移民與其後代所加諸的歧視,也增加他們在認同上擁抱所謂的祖國的意願。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有效且持續地播撒「海外華僑」(overseas Chinese)此一具意識形態的身分認同,利用他們在異地遭受種族歧視與其他形式的歧視,將這些歧視有效轉化成有利中國的遠距民族主義,讓海外華僑們能永遠效忠中國。中國政府對海外華僑使用的名稱與法國政府對海外(outré mer)屬地使用的名稱幾近相似並不令人意外:如同法國政府對其海外屬地宣稱其主權,中國亦視海外華僑為必須效忠母國的屬臣。
華語語系研究關注位處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以及霸權生產邊陲的華語語系文化,其焦點放置在中國的內部殖民與從中國移民至各地區後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華語語系研究瓦解自民族國家興起後語言、文化、民族與國籍之間形成的等價鏈,透過思考在地生產的獨特華語語系文化文本,探索中國與中國性、美國與美國性、馬來西亞與馬來西亞性、台灣與台灣性等邊緣如萬花筒般多變且具創造性地重疊交錯。譬如,華語語系藏族文學與華語語系美國文學提供兩個在文學領域以華語語系研究的範例。若華語語系研究對中國中心主義有尖銳的批判,它同時也批判歐洲中心主義或其他任何中心主義,如在馬來西亞的馬來中心主義。簡單來說,其批判模式是多向批評(multi-directional critique)。
近幾年,學者們使用「Sinophone」一詞時多指其外延意義之中文言說或中文書寫。黃秀玲(Sau-ling Wong)使用該詞來指涉以華文而非英文書寫的華美文學;新清史學家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與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將使用中文為溝通語的穆斯林回族稱做說漢語的穆斯林,藉此跟說土耳其語的維吾爾穆斯林做區分。雖然這些學者主要以外延意義使用該詞,他們背後的目的是要以命名來釐清對比:黃秀玲強調華文書寫的華美文學,揭露學界以英語語系定義美國文學的偏見並呈現出美國文學多語的面向;柯嬌燕等人則強調中國的穆斯林民族中語言、歷史與經驗的分歧性。研究西藏文學的學者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和Laura Maconi則指出藏族作家使用漢語,也就是「殖民者語言」時,書寫的困境與身分認同和語言差異之間的糾葛。
華語語系的概念
中國迅速崛起成超級強權或許迫使我們當下重省目前關於帝國與後殖民性的論述,但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滿清征服「中國本土」北邊與西邊的大片疆域時,它便符合我們所賦予的帝國一詞的現代意涵。這段歷史因兩個不被承認的執迷而常被忽略:對西方帝國的迷戀以至忽略其他帝國擴張的模式與盛行的中國被列強欺凌之論述。若我們的視野沒有長期偏頗海洋(亦即西方)殖民擴張的模式,將西方視為知識勞動中最值得分析的對象,中國的崛起便不會引起這麼大的驚訝。若我們將中國今日的崛起與滿族對內亞的侵略視為一種殖民事業的繼承與強化,...
目錄
導論:華語語系的概念
第一章 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
第二章 有關華語語系研究的四個問題
第三章 理論‧亞洲‧華語語系
第四章 放回世界的台灣研究
第五章 性別與種族座標上的華俠文化:香港
第六章 思索華語語系文學: 馬來西亞、香港、美國
附錄一 跨國知識生產的時差:讀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蕭立君
附錄二 華語語系研究不只是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史書美訪談錄/許維賢
附錄三 不斷去中心化的旅程──專訪史書美教授/彭盈真、許人豪
附錄四 華語語系研究及其他──史書美訪談錄/單德興
參考引用書目
謝誌
導論:華語語系的概念
第一章 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
第二章 有關華語語系研究的四個問題
第三章 理論‧亞洲‧華語語系
第四章 放回世界的台灣研究
第五章 性別與種族座標上的華俠文化:香港
第六章 思索華語語系文學: 馬來西亞、香港、美國
附錄一 跨國知識生產的時差:讀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蕭立君
附錄二 華語語系研究不只是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史書美訪談錄/許維賢
附錄三 不斷去中心化的旅程──專訪史書美教授/彭盈真、許人豪
附錄四 華語語系研究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