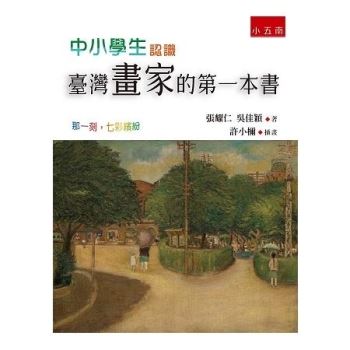王汎森新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包括兩部分文章,一部分是與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代的來臨」這個主題相關的文字,另外一部分則是闡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研究的方向與態度。
後者主張思想史亦應探討「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而因為本書中與「主義時代的來臨」有關的幾篇論文也刻意從廣義的「思想與生活」這個主軸出發,略有別於從政治角度去處理「主義」的問題。
作者王汎森教授並不主張將思想化約為生活,也不是在宣揚一種唯與生活發生關係的思想才有價值的想法,更不是認為重要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不値得用心研究。但誠如克羅齊所說的:「思想作為行動才是積極的」、「思想既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裝實在的容器」,同時他也強調「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職能」。那麼如果想了解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實際的樣態,則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種方式」。作者認為,「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以及這兩者之間往復交織,宛如「風」般來回有趣。此處所謂的「生活」,包括的範圍比較寬,包括有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
延伸閱讀: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作者簡介:
王汎森
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
章節試閱
古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
過去我曾多次使用「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交界」這個標題。但是近來我覺得以「交界」為題,仍將「思想史」與「生活史」想像得太區隔,是「一而二」,但我腦海中所構思的其實是一種「二而一」的現象。所謂「二而一」的意思是它既是思想的,同時也是生活的。譬如說在傳統中國,經學、思想與日常生活常常是融合無間的,只能以「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來描述。
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要先說明,本文並不是要刻意忽略歷史上的大思想家,或刻意將思想化約為生活。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把歷史上的思想家,如孔子、朱子等人從思想史上抽掉,東亞歷史將會變得非常難以想像。但是如果從歷史實際發展的角度出發,在談思想史的問題的時候,除了注意山峰與山峰之間的風景,還應注意從河谷一直到山峰間的立體圖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提法,便是想對這個立體的思想圖景進行比較深入了解的一條進路。它希望了解思想在廣大社會中如微血管中血液周流之情形,因而也提醒我們注意不能隨便將思想視為實際。
史家認為思想史著作是依據新創性原則所寫成的,與微血管遍布的部分脫節,以至於對歷史的實際發展變得不可解。因為忽略了上述的層面,連帶有許多通俗的思想文本、思想流傳方式與渠道、思想下滲之層次等被忽略了。結合前述,可以導出一種思想史的層次觀,即可以大略區分幾種不同層次的思想展現。再者,由「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推導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我思故我在」的層面。
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主題下,應該討論的問題非常多,本文只選擇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它們分別是:一、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二、「思想的存在」與「歷史的事實」;三、「降一格」的文本;四、思想史的層次;五、擴散、下滲及意義的再生產;六、百姓的心識與「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七、「我在故我思」的現象。
一、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
我們如果對思想史採取一個定義:思想像微血管般遍布於社會,有些地方比較稀疏,有些地方則非常濃密。人是會思想的動物,不管那是高深的玄思,或是一些傅斯年(1896-1950)稱之為「心識」的東西,它們都可稱之為思想(intellection),因此,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定義思想史為「history of intellection」。此處「intellection」的意思是指所有社會行動中有一個意義的層面,包括感知(perceiving)、辨識(discerning)、認識(discernment)、理解(understanding)、意義(meaning)、感覺(sense)、表示(signification)等。所有的社會行為,都有一個思想的層面賦予行為意義。如此一來,思想即與現實生活中的每一面都可能發生關聯,「我思故我在」與「我在故我思」都存在,二者可能周流往復,互相形塑。
處理所謂「面向思的事情」的歷史時,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取徑: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概念史、精神史等,不一而足。而且,不管是哲學史、思想史中的哪一種取徑,都可以有別的取徑所不能得到的好處。有些是高度理論、抽象的層面,或與生活不完全相干的層面,有些則是與生活踐履交織在一起的。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例,儒家思想特別重視踐履之學、是側近人生的,但是近代的思想史研究,一心以趨向哲學的抽象化、理論化為高,經此一番改變,思想史這門學問就像一具「頻寬」變得愈來愈窄的雷達。所以本文是想從史學的角度來恢復思想中的生活層面。
法國學者皮耶.阿道筆下所還原的希臘哲學,充滿了各種精神修鍊(spiritual exercise),更像是宋明理學強調的精神修鍊或自我的提升(「你可以比你自己所想的好」),要去除激情、欲望、奢華之念,宇宙及個人是一個整體,每一刻都要使自己更良善,保持快樂狀態,而哲學在其中要扮演角色。但歐洲的中古時代擺脫了這一面,中古人格部分的關懷被基督教吸收了,而哲學所賸下的是思辯的部分。18世紀以後大學興起,大學中的哲學教育是一種專業教育,故遺棄生活層面。因此皮耶.阿道說,18世紀有創發性的哲學是在大學之外。
我對傳統思想史研究的反思來自於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因為我覺得思想與歷史發展之間有一個重大的罅隙。一般思想史上所寫的內容,與當時一般社會思想所表現的現實裂開為兩層,現實如何?思想史如何?因何有互相合一之處、也有不合一處?在不合一之時,如果只注意較為抽象的思想概念的變化,那麼對歷史的實際發展往往無法理解。為了要了解現實中思想如何擴散、下滲,或思想與日常生活如何發生關聯,以及思想傳播的節點、渠道等問題,引發我思考本文中的種種問題。
因為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故它的範圍是立體的、非平面的。它的範圍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思想如何與生活發生關係?二、為使思想生活化,人們作了些什麼安排?這裡牽涉到自我技巧、自我修養的歷史。三、思想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形成什麼樣外溢的、氣質的、偏好的成分?因為思想影響涉及一般人(包括下滲)的歷史,因此涉及形形色色的文本、管道、節點、場合。思想的下滲究竟影響到何種程度?所謂的政治思想,除了各個高峰之外,山脈呢?生活與思想的關係為何?都是我下一節要談的問題。
二、「思想的存在」與「歷史的事實」
前面提到如果思想史的雷達「頻寬」不夠,歷史的實際發展會顯得有點莫名其妙。以政治思想史為例,如果不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會以為在思想史書中所出現過的即是歷史上的現實,因而困惑於這樣的問題:如果某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何以後來歷史的發展會是那樣?現代人撰寫的政治思想史(如蕭公權〔1897-1981〕),顯示出合乎近人「現代性」想像,或是自由主義的偏見(liberal bias),每每是因為其思想新奇有創見才被寫入,以至於讀者感到不解:如果那樣的思想曾深及民間,何以在歷史發展中找不到它們的蹤影?譬如史家一提到晚唐思想就列述羅隱(833-909)的《兩同書》,寫到明末清初思想就一定是黃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訪錄》。這當然是必要的,但他們的思想在當時是否生根,是否形成建置性遺產(institutional legacy),卻並未被好好地回答。以《明夷待訪錄》為例,相比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社會契約論》在完成以後即一紙風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長期影響甚微,並沒有產生建制性的遺產。所以如果一想到思想史上有《明夷待訪錄》,就誤以為它與清初以來的實際歷史密切相關,就會誤以思想的創新為實際發生的歷史。
《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偷偷流傳,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流行,一直要到清朝後期才逐漸產生重大影響。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1901-1995)曾經寫過〈明夷待訪錄當作集〉,指出這一部書在傳鈔過程中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錯訛,以及怎樣夾雜了傳鈔之時的俗語等等。可見思想在發展的過程中,從創生到在實際歷史中打開一扇門,也許要花一百年的時間,思想與現實生活之間往往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又如呂思勉(1884-1957)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書中講到宋代政治思想時幾乎只有井田與封建,問題是宋代政治思想只有這一點點嗎?井田、封建思想真的影響過宋代的政治運作嗎?它們曾經被相當程度的廣大官員乃至百姓所理解嗎?
古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
過去我曾多次使用「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交界」這個標題。但是近來我覺得以「交界」為題,仍將「思想史」與「生活史」想像得太區隔,是「一而二」,但我腦海中所構思的其實是一種「二而一」的現象。所謂「二而一」的意思是它既是思想的,同時也是生活的。譬如說在傳統中國,經學、思想與日常生活常常是融合無間的,只能以「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來描述。
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要先說明,本文並不是要刻意忽略歷史上的大思想家,或刻意將思想化約為生活。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把歷史上的思想家...
作者序
在進入正文前,我要先提幾點可能的疑問:我是不是在為中國沒有發展出抽象的哲學思維辯護?是不是傾向於將思想化約為生活?是不是在宣揚一種唯與生活發生關係的思想才有價值的想法?是不是認為重要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沒有價值,不必用心研究?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個人高度重視為何中國沒有發展出像希臘以來的那種抽象的思維。誠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說的:「思想作為行動才是積極的,思想既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裝實在的容器」,同時他也強調「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職能」。那麼如果想了解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實際的樣態,則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種方式」。至於本書的標題之所以僅取前者(「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只是為求簡潔方便而已。而不管哪一面,我所討論的都只是對傳統思想史視野的一種擴大,而不是對思想史工作的取代。
將近二十年前,我在〈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交界〉一文中,便提到對「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以及這兩者之間往復交織,宛如「風」般來回往復的現象的興趣。但當時的想像相對比較簡單,後來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宇宙如網」的意象經常出現在我腦海中。此處所謂的「生活」,包括的範圍比較寬,其中當然也包括社會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而我之所以特別強調「生活」這個面向,是因為即使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我所側重的也還是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層面。
一
在近代中國史學中,「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之所以被忽略,可能與西方「哲學」觀念的傳入有關。「哲學」高踞學問的寶座之後,人們有意無意之間認為,要經過幾度從生活世界抽離之後的哲學,才是最高的真理。但如果我們想了解歷史的發展,則僅注意歷朝各代比較抽象的哲學,往往又未必能解釋歷史的真正變動。本書所關心的是「intellection」,是廣義的思想活動,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現象。它們最初可能是來自一些具有高度原創性、概念性的哲學思想,但是它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像血液在微血管中流通,形成了非常複雜的現象。
對於了解傳統中國的歷史而言,「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似乎是難以迴避的面向。而且,在傳統中的許多文本帶有濃厚的生活性。儒家基本上是一種踐履之學,譬如宋明理學的文本,如果不在相當程度上從踐履的角度去把握,則必然會有所誤失。一直到近代反傳統運動之後,這個生活踐履的層面才被刻意忽略。近人研究歷史時,每每忽略傳統思想的生活性,也忽略了一旦加入生活的面向,思想史的理路便要相應地擴充及複雜化。譬如說其中有性質及內容的不同,光譜濃淡、思想高低之差異,或者說有不同的思想史層次(layers of concept)的存在。不同層次之間既有所區分,也有各種複雜的影響或競合關係。
談「intellection」時,絕不能抹殺大思想家的關鍵地位。試想,如果把孔子、孟子、朱熹(1130-1200)、王陽明(1472-1529)等人,乃至近代的胡適(1891-1962)與陳獨秀(1879-1942)從思想史上抽掉,歷史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如果將程朱或宋明理學諸大儒都抽掉了,整個東亞近八百年的歷史又會是哪一種景色?歷史上有許多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通俗文本或意識形態,往往是從具原創性的思想層層轉手而來的。譬如格林(T. H. Green, 1836-1882)的倫理學思想形塑了19世紀英國公務員的基本意識形態;又如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說過的,許多財政部長腦海中的東西,其實是從他讀過的經濟學教科書轉手而來的。所以在討論思想史時應該留意它有一個縱深,需要了解並處理思想在社會中周流的實況,免得誤將某種「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當作「歷史的現實」。
二
多年來我都這樣認為。第一,每一段歷史都不是單線的,其中都有各種力量同時在競合著,但並不表示當時沒有主旋律及次旋律之分,也不是沒有大論述與小論述之分。第二,我們應該從歷史中看出層次的分別。層次的分別當然不是像切蛋糕那樣整齊,各層次之間的分別與界域往往模糊難定,但是層次之分別多少是存在的,而且層次之別有時出現在相同人身上。譬如清代考證學最盛時,從事考證的人可能一方面作反宋儒的考證工作,但是在參加科舉考試時所攻習的仍是四書朱註。
層次之別有時出現在不同人群中。譬如在清代考證學當令之時,有一層官員、學者、地方讀書人是以生活化的理學作為其持身的標準,如唐鑑(1778-1861)《清學案小識》中所列舉的大量案例,或如清末民初沈子培(曾植,1850-1922)所觀察到的,即使在考證學盛行的時代,「乾嘉以來朝貴負時望者,其衣缽有二途。上者正身潔己,操行清峻,以彭南畇《儒門法語》為宗;其次則謙抑清儉,與時消息,不蹈危機,以張文端《聰訓齋語》為法。百餘年來漢官所稱賢士大夫之風氣在是矣。」
對不同思想史層次的了解有助於我們澄清一種誤會,誤以為思想史中所陳述過的即自然而然周流於一般人民腦海中,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斷裂(conceptual lags)。譬如說會誤以為清代中期以後,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凌廷堪(1757-1809)的新人性論已經是人們思想的公分母;或誤以為明清以來,既然有崇商的思想家,那麼廣大士大夫世界應當是已經採取了一種重商的觀點;或誤以為太虛法師(1890-1947)於民初提出「人生佛教」之後,當時廣大佛教信徒已經接受了這個概念,而忘了這是要等到幾十年之後,經印順(1906-2005)、證嚴等人提倡「人間佛教」之後,才得以下及廣大的群眾、並產生有力的行動。如果不分層次進行觀察,則往往會誤以為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然會被各個層次的人所接受,或誤以為浮在咖啡上淺淺的一層奶油,早已經滲透到整杯咖啡中。
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或「生活是思想的一種方式」這個大前提下,首先要考慮的是生活與思想/知識交織的現象。首先,關心「文本」的「生活性」這個問題,有好幾個方面,譬如古代有不少文本,本來就應該從「思想與生活」這個角度去領略。如果忽略了這一層,除了可能誤失它的意義,而且不能鮮活生動地理解文本及文本後面的活生生的意志與活動之外,也失去了揣摩、模擬它們的意義,失去了轉化自己心智與行動的機會。我個人所發表過的〈經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則是另外一種例子,它顯示在「使用」、「詮釋」等場合中,思想與生活交織的現象。我在這一篇文章中提到,抄《春秋繁露.祈雨篇》以祈雨,評論《春秋》以寓自己的出處進退等都是。又如明清學術轉型,一般多只將注意力集中在考證學的崛起,很少注意到迴向經典、迴向古代,在現實政治、人生態度及其他若干方面帶來的深刻改變。譬如它帶出一批新的政治語言、帶出一種新的想像政治的架構。在之前的一個階段可能是處於邊緣的,或陌生甚至不存在的語言及思考政治的架構,在此時來到歷史舞台中央,成為形塑輿論,合理化或排斥某種政治生活的態度。而這些影響,其實與考證學這種新學術的興起至少是一樣重要的。
歷代「經書」每每有其生活性,討論經書往往也同時在指涉現實。近代學者洪廷彥在〈經學史與歷代政治〉中討論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詁》。洪氏說該書的論點每每針對東漢末年社會政治的突出問題而發,如中央受宦官控制,如少數民族(羌族)的侵略。何休引用《公羊傳》的說法,認為應該要「先正京師」,即針對處理宦官專權的問題而發;何氏又說「乃正諸夏」,即是把首都以外的地方安定下來;最後是「乃正夷狄」,即是解決少數民族的問題。足見《公羊解詁》這一部書,既是東漢的,也是跨越時空的;既是生活的,也同時是一部經典注釋之書。每一次「用經」都是對自己生命的一次新塑造,而每一次的「用」,也都是對經書的性質與內容的新發展,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傳統」。所以,關於「用經」或「用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這個討論還可以延伸到另一個面向:「歷史的」與「思想的」是否必然處於互相排斥的狀態?我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事實上,從生活情境中所孕育出來的思想、哲學,也可能產生跨越時代的影響。宋明理學的產生與唐末五代以來的政治、社會、思想、人心有關,宋代大儒不滿唐末五代以來的亂局,並試著對此亂局提出解方,而宋明理學即帶有這個解方的某些藥性,然而這並不影響那一套思想後來成為跨越時空的思想資源。故一時的,也可能成為永遠的,而事實上所有永遠的,最開始也與一時的歷史與生活情境不能完全分開。舉例說,我們如果細看朱熹的生平的資料,看朱氏成書或醞釀思想的過程,就可以印證前述的觀點。
三
本書中所收的文字多與近代思想史有關,包括〈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這些文章所牽涉到的主題往往可以用許多不同的角度加以處理,但是收在這裡的幾篇文章往往傾向從存在的境遇、心靈氣質及心識感覺的層面入手。譬如本書中與「主義」有關的幾篇文章,「主義」當然是政治問題,但是在政治之外,它也與生活中實存的境遇、心識的感受密切相關。
如前所述,由於這幾篇文章多觸及近代中國的心靈危機與革命,所以我要在這裡略作一些申說。因為忽略了思想與生活面向的關係,所以我們對近代中國的心靈危機與革命也沒有足夠的把握。心靈革命當然與思想的變動密切相關,但兩者不總是同一回事。此處的「心靈」是指一些實存感受、生命意義、精神世界,甚至是一些尚不能稱之為思想的,佛家稱之為「心識」的東西。從晚清儒學解體開始,中國社會/思想產生了心靈(或精神)革命/危機。一方面是革命,同時是危機,是無所適從;是解體也是創造、啟蒙也可能同時有困擾,這些現象往往同時發生,有時候甚至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們一向把對心靈世界的探索交給思想史,但是思想史對這個不太抽象、不太概念化的實存層面,也就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的部分,往往過於忽略。這個心靈的、實存的世界不只是對個人生命有意義,它與整個時代的歷程與抉擇,甚至與現實的政治都有分不開的關係。我們也可以說,政治的世界從來都不只是政治的,它還牽涉到許多個人的、心靈的、實存的、情感的、人生觀的層面。這裡我要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介紹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學說的話:「知識裡面還有願望、意志,影響於他的『信仰的意志』」,而願望、意志、信仰,都是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現實活動不可忽視的部分。所以當我們想更深入了解近代的巨變時,不能不對這個領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譬如,想了解清代政治意識形態時,我們不能不深入了解理學與名教綱常、忠孝節義結合之後,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心靈或思想狀態。但我們很難在理學思想的研究中找到這方面的評估。有關這些大思想家的研究,大多在分析他們「理」、「氣」、「心」、「性」、「誠」、「仁」等方面的概念。
在探索五四之後的思想與日常生活世界時,我們便發現存在感受、生命氣質、人生態度、人生觀等方面的問題的重要性。〈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一文即是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如毛細管般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世界。〈從「新民」到「新人」〉則是討論個人的人生觀及內心結構,以及內心動力與態度之變化,如何與思想上的追求相互作用。〈「煩悶」的本質是什麼〉是在探討生命存在的感受、心靈的煩悶不安,如何成為時代思潮的「轉轍點」。這三篇文章最後卻都隱約指向一個關鍵的歷史發展:「主義時代」的來臨。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主義式的政治與思想對過去8、90年的歷史影響最大,「主義時代」的來臨最重要的背景當然是為國家、為政治找出路,或是年輕人為了生活「找出路」。但「主義時代」的來臨不只是一個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思想史上的重大變化。如果只從政治來談主義,或是從擁護或譴責某種主義來談論它,以至於忽略了從思想史及生命存在感受、心靈困惑、生命意義的追求或生活史等角度去研究它,都將有所缺憾。
本書中〈「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一文試著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時代集體的存在感受可能與政治有關?也就是為什麼心靈的、思想的與生命存在方面的問題會影響到政治思想的抉擇?它牽涉到生活與思想之間可能存在著介面與介面互相轉接的關係,在〈「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中討論透過「轉喻」或「轉轍點」,「生活史」與「思想史」或其他的介面套接在一起。每個時代的人都在體驗著他們的體驗,而如何體驗他們的體驗,便產生了介面銜接的可能。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轉喻」的觀念,即「意識到什麼是什麼」(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ing something)。譬如意識到現實生活挫折的本質是什麼、意識到煩悶的本質是什麼。在極度無助的時代,或在新思想活躍的時代,「意識到什麼是什麼」的「轉喻」式行為可能變得比較活躍,而且更容易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進而傾向於把體驗到「什麼」是「什麼」的第二個「什麼」用新思潮給填滿。煩悶、生活挫折、日常小事的不如意可能被聯繫到一套更具理論性、更有延展性的思想系統,形成介面與介面的轉接。透過「轉喻」,使得生活的可以連接上思想的、主義的,因而一切存在的困境與煩悶便與政治主義有了連接,而且與現實行動形成最密切的關係。在這個格局下,日常生活的感受都直接或間接、近期或長遠地聯繫到一個清晰的藍圖,使得人們內心的意義感得到一種滿足。討論「主義」何以吸引人時,政治的層面當然是首要的,但我認為心靈的、存在的感受的層面也不可忽視,它們最後都歸到政治,像纖維叢一般纏繞在一起,故「主義」的崛起與近代中國心靈世界的革命與失落、啟蒙與困擾等有不可忽略的關係。
更具體地說,我是在討論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近代主義式政治的興起,是一件非常關鍵性的大事。但是政治行動的主體是一個一個的個人,是我、是人生觀、是生命意義、是生涯規畫等,這是一個包括心靈、情緒、感覺、內在自我等等非常廣泛的世界(人的存在是什麼?人的心靈是一堆雜草?)。國民黨在「主義」與「人生」方面的論述非常少,國民黨的刊物中也不斷提到青年的「苦悶」,但是認為青年之所以苦悶是因為信錯了共產主義,或沒有堅定信仰所致。在三民主義陣營方面,比較像是國民黨為了適應「主義」的時代,而勉力撐持出一套體系來。國民黨不像共產黨,有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擴充到各個層面。〈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一文討論的是近代一種強大的「未來性文化」,還有這個強大的「未來性文化」對歷史解釋與歷史寫作的巨大影響,以及它對現代政治、文化所產生的超乎吾人所能想像的作用。
人的思想像風中飄逸的火焰,它很容易熄滅,或被各種思想或信仰的怒潮席捲而去,這個情形在下層生活世界尤其明顯。故本書中的另一條線索是如何了解下層生活世界的思想狀態,如〈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再來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篇文章除了是對思想與生活交光互影的各種面相的陳述之外,還講到「我在故我思」,即生活世界在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在文中特別強調了「轉喻」這一個觀念。人的大腦是一個最重要的「轉喻器」,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條件下,「轉喻」活動變得異常活躍,人們更靈敏地意識到「什麼是什麼」,在這種時候,生活中的挫折或生命中的煩悶,每每會「轉喻」成對形形色色的思想體系的迎拒或發展出新的詮釋。譬如前面提到的〈「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一文,我想用這篇文章來說明人如何「意識到什麼是什麼」,而將「生活」轉喻為「思想」,或將「思想」轉喻為「生活」。透過「轉喻」,「思想」與「生活」形成有機連結,不再截然二分。
本書的另一篇文章是偏於思想史方法論的反思:〈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乃是以思想「結構體」來思考晚清以來的一種思想複合性現象,而在無限多樣複合式的結構體之上有各種支配的理路,譬如愈來愈強的民族主義。
最後,在強調「思想」與「生活」時,不能不反省歷史寫作中「人的消失」的問題,故本書以〈人的消失?!〉一文作為總結。撰寫這一篇文章有一個最重要的機緣。我注意到,近百年史學思潮中有一條若隱若現的主線,便是否定「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而且近代歷史學太過傾向於從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抽離出來,太受過度抽象的、哲學化的思潮左右。沒有了「人」的歷史,也使得歷史這一門學問日漸遠離了它原初的任務。
在進入正文前,我要先提幾點可能的疑問:我是不是在為中國沒有發展出抽象的哲學思維辯護?是不是傾向於將思想化約為生活?是不是在宣揚一種唯與生活發生關係的思想才有價值的想法?是不是認為重要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沒有價值,不必用心研究?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個人高度重視為何中國沒有發展出像希臘以來的那種抽象的思維。誠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說的:「思想作為行動才是積極的,思想既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裝實在的容器」,同時他也強調「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職能」。那麼如果想了解思想在歷史...
目錄
序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人的消失?!──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
附錄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序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人的消失?!──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
附錄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