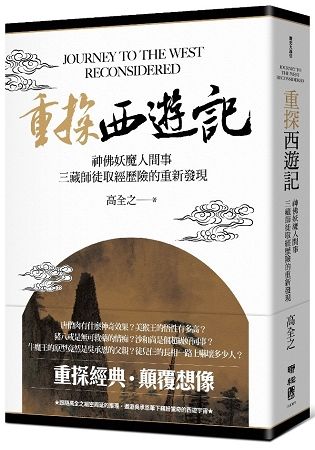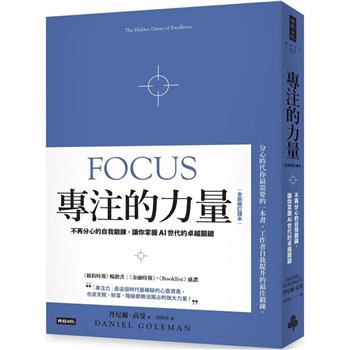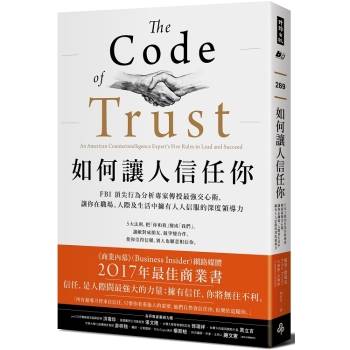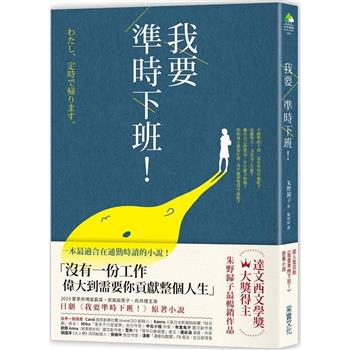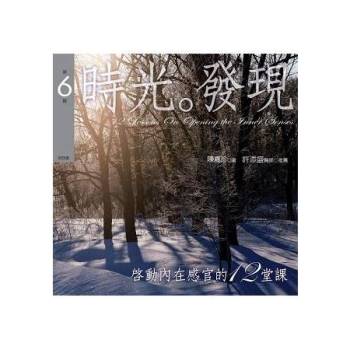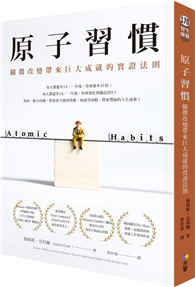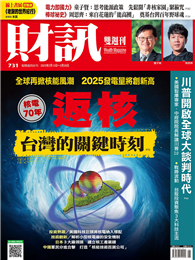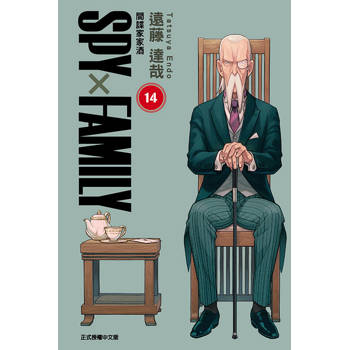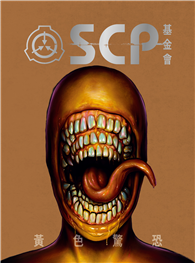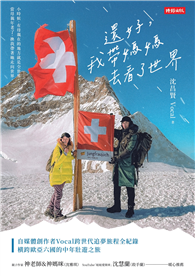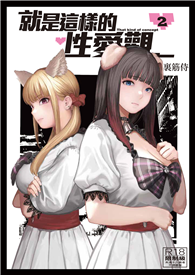豬八戒──無可救藥的情痴
一
豬八戒大概是中國小說最膾炙人口、搞笑、卻令人同情的人物。那不可能是個不經意的意外的文學效應。作者如何塑造這個繁複的角色?
史學家陳寅恪在漢譯佛教經典裡追溯《西遊記》故事成型初期的文學想像,歸納「故事演變」的規律(他的措詞是「公例」)。所提諸事都是小說角色有限的屬性或活動。有關豬八戒的部分,講有位天神為救驚犯宮女、困於豬窟的比丘,化身為豬自窟走出,引誘名叫「出光」的王追殺,那位比丘就趁機逃逸。陳寅恪建議這個佛經故事指向並演化成豬八戒。
不知為何陳寅恪認為:「驚犯宮女,以事相類似之故,變為招親。」八戒本是天界的天蓬元帥,因酒醉戲弄嫦娥而被貶下塵凡。所以佛典裡「驚犯宮女」實已與八戒在天界鬧事遙相指涉,不必攀爬到後來的招親情節。所謂「憍閃毗國之憍,以音相同之故,變為高家莊之高」,乃沒有必要的牽強。類似這種文學源頭的提法僅為推測,不具《三國志》和《三國演義》之間那樣確切的傳承關係,最好適可而止,以免爭議。這樣釐清之後,不講招親,陳寅恪找到的八戒佛典淵源就全都在八戒第一次會面觀音的表白之內,皆八戒出場之前的昔日舊事。佛典影響小說創作,說來就較為簡易,說服力強些。
值得注意陳寅恪沒說這部小說的「本源」僅只限於他所熟知的佛典。所以爬梳其他思維模式,也會帶來他所列舉的效益:「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能,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評論家常提醒我們《西遊記》的其他想像依據在於道教與儒家。那些建議絕非空穴來風。第四十七回,孫行者規勸車遲國王「三教歸一」,意思是以佛教、道教以及儒教治國。但我們必須防範這種解讀方式可能引致的兩種盲點。其一,我們追究釋道儒的牽扯,並非同意這種也出現於《紅樓夢》研究的思維完整解釋了中國社會的存活。白先勇認為中國社會得以長存下來,至少還得依賴法家。其二,《西遊記》在釋道儒之外,也格外注重與其沒有直接聯繫的俗世智慧。就以觀音菩薩與八戒初會對談為例,他們各自引用道家或儒家典籍的經句,但也另外加上冠以「古人云」或「常言道」的俗話。類似的例子相當多。在作者心裡,有些俗語雖然不具明顯的釋道儒色彩,但份量重,同樣具有言行規範的權威性。
作者藉用八戒與觀音的初會去界定情慾之外,其他兩項貫穿全書的八戒屬性。其一是食慾。八戒說皈依佛門會餓肚子,「依著佛法餓殺」。觀音勸說素食也能吃飽。八戒接受訓示,從此不再吃人度日。三藏的三徒在皈依釋門之前都曾吃人,都因觀音而開始齋戒。《西遊記》一再講觀音慈悲,這裡化度三個妖怪,並且拯救他們或會吃食的蒼生。但在八戒的案例裡,此時埋下種子,以便稍後一再重複他食量驚人和見色心動,以便體現儒家的基本人性認知:「食、色,性也」。三徒都是高度人格化的妖怪。食色本性的看法不離人性。其二是娶妻安家的偏好。八戒告訴觀音他在福陵山雲棧洞曾入贅,與卵二姐成婚,後來卵二姐過世。八戒喜歡成家。好色與成家相關,但有其區別,八戒這些想望顯示他是個沒有親屬聯繫的流浪者。稍後我們再簡略討論這些特質。
綜上所述,故事裡八戒一露面,作者就開宗明義交代了取經團隊裡唯八戒獨具的四項屬性:豬身、好吃、好色,以及樂於安家。
二
有個比元代更悠久的證據,支持吳承恩沒有發明豬八戒造型的提法。黃永武在敦煌資料裡見到一張唐人繪的大摩利支菩薩:「菩薩的腳踝前,有一頭金豬,豬不是被踏著作車乘,在唐代畫家的筆下,金豬已經是豬頭人身的形象,兩手架開,奔走飛快,造形非常活潑,正是法力無邊的樣子,那就是後代傳說豬八戒的雛形!」《西遊記》的八戒故事雖然未受唐人繪圖裡的佛教故事嚴格規範,但八戒形象確是吳承恩的主要小說策略之一。這個故事的天界神祇頻繁下界,但只有三個不可或缺、因犯錯而貶落麈世的案例:金蟬子(三藏)、捲簾大將(沙僧)、天蓬元帥(八戒)。金蟬子投生出世,忘卻前生,從嬰兒開始成長。沙僧和八戒都先挨打後遭逐,保持記憶以及魔法,在人間沒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兩人都說自己「變得這般模樣」。沙僧形像凶醜,想必與從前天界的捲簾大將英姿不同。八戒變形尤其劇烈,形同畜生。第十九回的八戒自白詩裡有句「我因有罪錯投胎」,行者也說八戒「錯投了胎」。那個「錯」字並非意外或錯誤,實為故意安排。第一百回如來佛祖說八戒「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貶」字清楚表明懲治。投入豬胎是處罰的一部分。在故事尾端,佛家持續了故事開始時候道家的制裁。
《西遊記》故事裡神祇們不但演示人格化的思維與言行,軀體也大都類同人形。天蓬元帥的情況應不例外。既然下界以後仍然記得前生,當然知道人豬有別,而且瞭解凡人為何驚嚇於自己的外表。豬悟能蓄意變成人形到高家莊騙婚,「模樣兒倒也精緻」,理由即在此,長相終究是討好丈人和妻子的方法之一。後來豬悟能自己疏忽而現出原形,又操弄法術,引起丈家排斥,算是得個教訓。取經途中八戒的外形始終是個問題。第廿回,行者教八戒如何「收拾」醜相。收拾意指特殊的五官掩藏動作。醜相有時壞事。第卅二回,八戒在平頂山遇到巡山的銀角大王,怕被認出,「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裡藏了」。那就是行者早先教的收拾動作之一。有時八戒竟然也善為利用醜相。第五十四回,師徒進西梁女國。為了消除該國國民對過境男性的興趣,三藏要徒弟們「切休放蕩情懷」。八戒「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唇,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諕得跌跌爬爬。」
我們在〈精英主義和宗教平權─—比較歷史玄奘和吳承恩的佛教思想〉已簡單討論取經任務完成,在接受封賞的大典裡,八戒當場抗議師父與行者受封成佛,自己只得個淨壇使者的職位。我們現在注意那個抗爭的其他細節。如來佛祖不嘗試,八戒也未要求,恢復天蓬元帥形象原狀。為何作者設套而不解套?那時候白馬得以重得龍體,但作者刻意讓八戒持續豬形去就任新職,那麼淨壇使者將會因為外觀而引起其他神祇側目。如來佛祖甚至為了因應豬身所持續的食量問題,特別告訴八戒:「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其實如來佛祖有所不知。三藏和孫行者也被蒙在鼓裡。第九十三回,舍衛國給孤布金寺的人都來看八戒吃飯狼吞虎嚥。沙僧立刻暗地裡勸阻,要八戒吃相斯文些。八戒隨即聽話停止進食。可見八戒可以適應調整吃相和食量。作者似乎在說八戒有學習的能力,可以瞭解吃食乃先天本性,可是過度的食量卻不是。第九十二回,四木禽星協助擊敗犀牛怪之後,八戒發號施令井井有條,四星誇獎八戒「知理明律」。八戒回答:「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學得些兒。」八戒自己知道有所長進。第一百回,八大金剛送取經團隊回到長安,擔心八戒進城以後「貪圖富貴」,誤了歸期。八戒笑著說不必過慮。當晚在洪福寺八戒「不嚷茶飯,也不弄諠頭」,和師兄弟們同樣穩重。次日就隨八大金剛去靈山報到。可見得八戒可以中規中矩。
繼續懲罰八戒其實承認了宗教,主要是佛教,轉化人性的限度。第九十八回,三藏師徒在靈山見過如來佛祖,由阿難、伽葉招待,在珍樓之下享用「與凡世不同」的「脫胎換骨之饌」。曾有評論家大為驚嘆那「脫胎換骨」所能意味的神奇食效。但為八戒食量著想而選擇賜封給他的新職,證明如來佛祖認為珍樓膳食不會改變豬身影射的超大食慾。事實正是如此。那頓飯後,八戒只有在陳家莊的首次齋筵覺得不餓,稍後在救生寺就又胃口大開。
重要的是宗教沒能消除八戒抗議自己未被封佛的膽量。八戒發言的方式是「口中嚷道」,想必意氣激動,慷慨激昂。所以佛教並未完全消除八戒強烈的自我意識。此時公然出聲極其重要。夏志清有個非常精闢的意見,說八戒在取經團隊裡修成正果的動機最弱。我們可以找到支持那看法的證據。齊天大聖原來參團的目的在擺脫五行山的壓制,後來又受頭頂緊箍兒的控管。沙僧原來在流沙河每七天便遭飛劍穿胸百餘次的刑罰,加入取經隊伍讓他逃避每週的劇痛。八戒在高家莊受丈家排斥,但是丈家根本奈何他不得,八戒大可留在高家莊繼續享受他很在乎的家室之樂。八戒起初接受觀音菩薩戒行的時候還沒有在高家莊娶妻。孫行者和八戒都瞭解那情況。所以第廿三回,孫行者說八戒「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有點強迫抓兵入伍的意思。
《西遊記》常用角色吟詩來展現個人自我意志。多年來評論家藉由本書夾詩來盛讚作者的文采,往往疏於知會作者任由角色言志、認證自我身分的開明態度。全書八戒吟詩大約九次。其中五次藉詩詞來表述「我是誰」的議題。但全書前後兩半部吟詩分布的比例非常不同。七首吟詩,包括四首言志詩,都集中在前五十回。五十回以後吟詩僅得兩次。在含有八戒吟詩的這兩回裡,八戒的自我意識都有特別突出的意義。第一次出自第六十一回與行者的對話。在那回裡八戒聽說牛魔王變作八戒模樣並因此而騙回行者手中的扇子,大怒,當面罵牛魔王:「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助戰格外威風。《西遊記》裡善變身形的人經常痛恨別人變作自己身形,因為自我身分的獨一無二性質受到侵犯。說來相當霸道。觀音菩薩、孫行者、豬八戒,沙僧,無一例外。第二次吟詩在第九十四回,我們稍後再談自我意識在那裡的特殊消長。我們現在先注意從吟詩可看出八戒伸張自我,在全書後半部不如全書前半部。所以封賞大典裡八戒終於回馬一槍,發言為自我權益爭辯,可算是種最後的復蘇。他終究沒忘了自我的重要。《西遊記》注重自我。孫行者在封賞大典裡,也在與師父的私談裡表示了對如來佛祖以及觀音菩薩使用緊箍兒的不滿。那時行者已受封成佛了,還不忘一吐心中怨氣。佛境充滿人味。
《西遊記》認證宗教的限制並不到此為止。我們繼續回顧豬八戒的處境。
三
取經團隊在路上十四年,克服了八十一個災難。如來佛祖封賞八戒的理由卻僅一條:「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再不濟事,貢獻就只挑個擔子?第廿回,八戒打死黃風怪的虎先鋒,行者大喜而誇獎:「兄弟呵,這箇功勞算你的。」第卅一回的回目有句「豬八戒義釋猴王」,有的版本作「義激」,意指孫行者第二次脫隊,多虧八戒去花果山用激將法請回。第四十一回,孫行者被紅孩兒噴煙所困,投於澗水,不料冷水一逼,火氣攻心,三魂出舍,立即有生命危險,眼看著就要「魂飛魄散喪殘生」。四海龍王急喚八戒與沙僧。兩人在急流裡救出行者身軀。八戒「將兩手搓熱,仵住他的七竅,使一個按摩禪法」,救了行者一命。第六十一回的回目有句「豬八戒助力敗魔王」。豬八戒助戰牛魔王,得行者稱許:「賢弟有功。可喜!可喜!」第六十四回,師徒一行多虧八戒開路過荊棘嶺。凡此種種都是伏筆,以便暗示作者並不同意如來佛祖的看法。
八戒的小奸小壞可真不少,如挑撥師父和師兄孫悟空之間的感情、藏私房錢、好吃懶做等等。到底是那個缺點令如來佛祖耿耿於懷,以致在賜封大典上刻意不提八戒挑擔之外的任何功勞?答案應該就在賜封訓詞的其餘部分。如來佛祖當場數說八戒「保聖僧在路,卻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如來佛祖好像煩心八戒未來仍然色情未泯,那麼所謂「脫胎換骨之饌」真是徒具虛名。更重要的是從小說創作的角度去看,作者持續八戒豬容,很可能在演示如來佛祖與豬八戒之間的一種緊張情勢,或者可稱之為故事的內在張力。一方面如來佛祖不願恢復天蓬元帥形象原狀,藉此而增加淨壇使者今後,如果他膽敢嘗試,追求異性的困難。本性難移是《西遊記》的基本人性看法,讀者熟知的證據即如來佛祖交給觀音菩薩的法寶裡有三個用來控制頑劣分子的箍兒。八戒的豬容與箍兒一樣是凶狠的懲罰。在另一方面,八戒不要求恢復天蓬元帥形象原狀,因為他知道自己當年酒醉侵犯宮女,但追求異性的興致仍在,所以沒有理由去爭取恢復原形。我們至少可說這些都是作者允許的文學聯想。
八戒不是故事裡唯一違反色戒的和尚。《西遊記》裡披上僧服的未必就是合格的和尚。第廿三回,八戒引用俗話說:「和尚是色中餓鬼。」第八十一回,金鼻白毛老鼠精在鎮海寺連續三天,變作「美貌佳人」,每天吃兩個和尚。行者變作個小和尚捉妖,隨即發現「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第九十三回,給孤布金寺那位老僧在祇園見到落難的天竺國公主,居然為了防止寺裡其他和尚「點污」,就鎖她於空房,公主也配合在眾僧面前「裝風作怪」。可見寺裡有不守清規的年輕和尚。《西遊記》肯定和尚色戒的美德,但同時確認該項操守的高難度。在那個基礎上,作者取笑但未譴責八戒懷春。
八戒入夥之後已經有所收斂。雖沒斷酒,卻未大醉鬧事,不再顯示當年醉後戲弄嫦娥宮女那種狂放。不過他嚮往成家,故事裡他是唯一持此奢望的和尚。凡間男性的成家想望不巧正是佛門忌諱,所以如來佛祖牽腸掛肚很可理解。第十九回,八戒剛剛參加取經團隊,還當著三藏和行者的面,慎重吩咐丈人好生看待妻子,如果取經不成,就回來還俗再做高家女婿。八戒的態度非常嚴肅。第廿三回,四位菩薩化身為富有的美女來測試三藏師徒,八戒自取其辱,原因即貪圖安家活口。取經途上遇到挫折,八戒常要散夥回家,與他思戀妻子高翠蘭有關。雖然高翠蘭已經見識過八戒的豬相,未必願意等八戒回來繼續婚姻,八戒卻信心滿滿,他有天罡數的變身魔法,在第十八回他說過:「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卻也不難。」第八十二回,八戒提議散夥,說自己要「去高老莊探親」,就是念念不忘高翠蘭。
第廿七回,八戒見屍魔變的美女,「見他生得俊俏,獃子就動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亂語。」結果當然是上當。第五十四回,八戒見到女人國國王而目眩神搖。用現代語言說,就是受異性吸引,算是短暫的廣義的意淫。但是八戒並未進一步闖禍。第五十五回,八戒與行者大戰蠍子精變成的女妖。兩人要確認三藏未受女妖勾引而失身。可見八戒也能「置身色外」。八戒知道自己已經是個和尚。
情慾導致的最大羞辱發生於八戒最後一次為異性動情,而且與最初被罰下界那件禍事有關。很有意思,八戒情史的頭尾就這樣串聯起來。如果陳寅恪所提、佛典裡的「驚犯宮女」事件真是豬八戒故事的前生,那麼作者始終沒忘那觸發想像的源頭。第九十四與九十五兩回,八戒助戰玉兔妖怪。月宮太陰星君協助制伏偷跑出來作怪的玉兔。孫行者引導太陰星君、眾姮娥仙子以及玉兔到天竺國宮殿上空,向地面群眾介紹神祇,要他們禮拜。這是《西遊記》重要的剎那之一。能見度良好:「一片彩霞,光明如晝」。該到的全到了:三藏、沙僧、八戒、國王、皇后、嬪妃、宮娥、綵女、朝官、滿城中各家各戶等等。作者這樣描寫八戒出醜:
豬八戒動了慾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著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獃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閑散悶耍子而已。」那太陰君令轉仙幢,與眾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
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
這不是孫行者叫八戒「獃子」或打八戒的僅例,但是從來沒有當著這麼多觀眾的面去糾正與責備。
引文裡「慾心」並非隨隨便便的,遇見陌生異性美色而自己失控。「舊相識」意指霓裳仙子可能就是當年令天蓬元帥心動、酒醉冒犯的那位嫦娥宮女。「眾嫦娥」,可見「嫦娥」並非專指一人,而是泛稱。霓裳仙子則特指某位宮女。問題是天蓬元帥外形已不復存在,霓裳仙子眼前所見的是豬八戒。她想必相當驚愕。那將會是淨壇使者今後追求異性時候的一大障礙。
前文提到第九十四回八戒最後一次吟詩,自我意志高昂。當眾出醜在次回。時段雖短, 從清醒到糊塗的神智落差卻大,足見情慾強勁而難以抑制,八戒無視客觀條件變動,忽略公眾場合的應對規則,天真誤解昔日的交情仍可延續。八戒平常缺乏孫行者火眼金睛的本領,無法辨別妖魔或神祇化身,無從認清敵我,所以作者有時也直接以「獃子」稱呼八戒。那與在霓裳仙子面前受辱略為不同。作者大概在說我們雖須肯定自我,疏導本性裡的情慾,卻得認清勢利現實,注重公眾禮儀,講求自我約束。
但作者知道多說無益。八戒總覺得自己可以吸引異性。無可救藥的情痴。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重探《西遊記》: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的重新發現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重探《西遊記》: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的重新發現
豬八戒是無可救藥的情痴?沙和尚是個超級好同事?
牛魔王的原型竟然是吳承恩的父親?徒兒仨的長相一路上嚇壞多少人?
《重探《西遊記》: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的重新發現》,作者高全之從九大方向,周密探索埋藏在《西遊記》小說中的諸多細節:
‧內丹修持和美學研究的追溯
《西遊記》小說是否刻意宣揚道教?胡適不贊同此書是部金丹妙訣,建議以「滑稽小說」和「神話小說」來定位它的價值。高全之同意《西遊記》小說作者無意遵循單一的傳統宗教信仰,但無法僅視其為取笑的娛樂文學。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更重要、更有趣的議題:《西遊記》小說的內丹修持有何美學意義?
‧影響吳承恩創作的幾部文獻
重新審視《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先府賓墓誌銘〉、《西遊記雜劇》,以及《封神演義》。高全之大膽假設,在吳承恩創作《西遊記》小說的過程中,上述這些文獻曾經直接或間接產生影響。
‧凡人的宗教經驗
《西遊記》小說反映許多平凡人半信半疑、時信時疑的宗教經驗。神人關係動盪不安的本質,是《西遊記》小說的現代意義之一。個人自我肯定與無條件虔誠敬神,兩者如何得兼?沒有其他任何中國小說更直接更生動的觸及這個議題。
‧佛教與道教相處之道
《西遊記》小說裡,道家天庭收拾不了齊天大聖,就派人求助於如來佛祖;幽冥界地藏王菩薩屬下有十殿陰君,但上司是道家天庭。吳承恩注意到玄奘時代,外來的佛教與本土的道教互相忍讓、和平相處的微妙。對比今日世間仍層出不窮的宗教戰爭,《西遊記》小說呈現的是令人嚮往的宗教融合。
‧吳承恩的宇宙觀
吳承恩筆下的西遊世界,天有多高?地有多寬?地表和海面之下又有多深?這些提問涉及道家天界、海域、幽冥界,以及計數觀念。吳承恩喜歡炫耀非常大的數字,也多次用形容詞「無窮」。但是極大或無窮,在許多例子裡仍非無限。他的宇宙是否和今日天文物理學家所建議的那樣無限伸張?
‧三藏師徒的身體美學
西遊原生故事曾是社區隊戲和舞台戲劇,演出場所無論室外室內,師徒四人的造型都需醒目而且令觀眾難忘。但目前所見的西遊漫畫、雕塑、電視、電影、電玩,很多都忽略了吳承恩在《西遊記》小說清楚界定的塊頭大小順序。他們的身體尺寸從大到小的次第是什麼?
‧取經團隊的職務分工
取經成員平時需要分擔的工作主要是挑擔與牽馬。八戒和沙僧彈性分工,有時互換挑擔和牽馬的任務。八戒和沙僧都力大,各自所持長兵器皆重達五千零四十八觔。為何八戒還要抱怨挑擔辛苦?白龍馬是五聖之一,在危機時期曾主動變回龍身挑戰妖魔,為何需要牽呢?
‧動物的尊卑貴賤
猴子是完美無缺?龍就一定尊貴?背殼爬蟲類動物的地位永遠低下?故事裡兩個老鼠妖怪的造型乃俊男美女。除了詼諧戲謔之外,他們的亮麗如何幫助我們瞭解吳承恩的老鼠思維?
‧尊重吳承恩「文學本位」的小說創作立場
小說創作與宗教或歷史相關,但它不僅是種特殊的藝術形式,而且也是不隸屬於宗教或歷史的、個別存在的人類生存紀錄。有些《西遊記》評論家宣稱吳承恩不懂佛經,或用「糾正」字眼來指出小說與史實之間的差異,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粗魯和霸道。
不論是如來佛祖的五行山、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或是八戒之好色、沙僧之影薄,《西遊記》故事已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超越國界藩籬,成為世界共通的文化風景。吳承恩架構的西遊宇宙,絢麗繽紛且充滿巧思及寓意,使這本小說絕非膚淺的娛樂而已。因此,高全之認為,《西遊記》小說與現代讀者的關係,或許像詩般美好,值得追求。
《重探《西遊記》:神佛妖魔人間事,三藏師徒取經歷險的重新發現》另有六篇兼談《水滸傳》,與西遊研究相互呼應,深入剖析小說中的殘虐故事是否反映民族性缺陷等問題。
延伸閱讀
《西遊記》,吳承恩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廖咸浩
《紅樓一夢:賈寶玉與次金釵》,歐麗娟
《潘金蓮的餃子:穿越《金瓶梅》體會人欲本色,究竟美食底蘊》,李舒著,戴敦邦繪
《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李歐梵等著
作者簡介:
高全之
1949年出生於香港,台灣成長,1975年赴美留學。電腦科學碩士。電腦工程師。退休後定居美國。大學時期開始發表文學評論,引起文壇與學界注意和推薦。作品多次收入各種文學評論選集。著有:《當代中國小說論評》(台北:幼獅,1976),改版為《從張愛玲到林懷民》(台北:三民,1998);《王禎和的小說世界》(台北:三民,1997);《張愛玲學》(台北:一方,2003);《張愛玲學(增訂版)》,《張愛玲學(增訂二版)》(台北:麥田,2008,2011);《張愛玲學續篇》(台北:麥田,2014)。
TOP
章節試閱
豬八戒──無可救藥的情痴
一
豬八戒大概是中國小說最膾炙人口、搞笑、卻令人同情的人物。那不可能是個不經意的意外的文學效應。作者如何塑造這個繁複的角色?
史學家陳寅恪在漢譯佛教經典裡追溯《西遊記》故事成型初期的文學想像,歸納「故事演變」的規律(他的措詞是「公例」)。所提諸事都是小說角色有限的屬性或活動。有關豬八戒的部分,講有位天神為救驚犯宮女、困於豬窟的比丘,化身為豬自窟走出,引誘名叫「出光」的王追殺,那位比丘就趁機逃逸。陳寅恪建議這個佛經故事指向並演化成豬八戒。
不知為何陳寅恪認為:「驚犯宮女,...
一
豬八戒大概是中國小說最膾炙人口、搞笑、卻令人同情的人物。那不可能是個不經意的意外的文學效應。作者如何塑造這個繁複的角色?
史學家陳寅恪在漢譯佛教經典裡追溯《西遊記》故事成型初期的文學想像,歸納「故事演變」的規律(他的措詞是「公例」)。所提諸事都是小說角色有限的屬性或活動。有關豬八戒的部分,講有位天神為救驚犯宮女、困於豬窟的比丘,化身為豬自窟走出,引誘名叫「出光」的王追殺,那位比丘就趁機逃逸。陳寅恪建議這個佛經故事指向並演化成豬八戒。
不知為何陳寅恪認為:「驚犯宮女,...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神佛妖魔治亂人間世
柯慶明╱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文學閱讀的性質,在上個世紀有了重大的轉變:首先它由一個人的博雅教育、文化修養、修辭應用……逐漸的轉成為一種知識、一門學問。大家不再相信,一個普通的讀者,在興高采烈的悅讀之餘,可以掌握任何文學作品的真意,於是有種種作者、版本的考證,繼之而起的則是作品內容與作者生平、時代的關聯;作品風格與文類美學特質的辨析,作品價值在文類傳統的位列評估,以及在文類發展上之承先啟後影響關係的探討。當心理分析、社會主義、存在哲學、語言符號、現象詮釋、讀者接受、...
柯慶明╱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文學閱讀的性質,在上個世紀有了重大的轉變:首先它由一個人的博雅教育、文化修養、修辭應用……逐漸的轉成為一種知識、一門學問。大家不再相信,一個普通的讀者,在興高采烈的悅讀之餘,可以掌握任何文學作品的真意,於是有種種作者、版本的考證,繼之而起的則是作品內容與作者生平、時代的關聯;作品風格與文類美學特質的辨析,作品價值在文類傳統的位列評估,以及在文類發展上之承先啟後影響關係的探討。當心理分析、社會主義、存在哲學、語言符號、現象詮釋、讀者接受、...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杖藜野客尋詩
這幾年重溫年輕時候讀過的經典小說。順便瞭解晚近的相關評論。原意是做些讀書筆記。就像本書所收有關《水滸傳》那幾篇,主要是企圖回應該書的殘虐是否反映民族性缺陷的問題。涉獵雖然有限,卻也覺得幸運,趁此機會細讀前輩鄭振鐸、孫述宇、馬幼恆。學無止境,人文與科技領域皆然。
沒想到《西遊記》激起比較全面的反省。最重要的問題,在於處理這部小說閱讀方法的反彈。胡適首先倡言不要讓道士(以及和尚、儒生)壟斷《西遊記》小說的解讀。魯迅立即響應。證道式的《西遊記》論述以及小說版本因此而式微多年,直至柳存仁發...
這幾年重溫年輕時候讀過的經典小說。順便瞭解晚近的相關評論。原意是做些讀書筆記。就像本書所收有關《水滸傳》那幾篇,主要是企圖回應該書的殘虐是否反映民族性缺陷的問題。涉獵雖然有限,卻也覺得幸運,趁此機會細讀前輩鄭振鐸、孫述宇、馬幼恆。學無止境,人文與科技領域皆然。
沒想到《西遊記》激起比較全面的反省。最重要的問題,在於處理這部小說閱讀方法的反彈。胡適首先倡言不要讓道士(以及和尚、儒生)壟斷《西遊記》小說的解讀。魯迅立即響應。證道式的《西遊記》論述以及小說版本因此而式微多年,直至柳存仁發...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神佛妖魔治亂人間世 柯慶明
自序 杖藜野客尋詩
內丹修持──神祕經驗和小說美學
精英主義和宗教平權──比較歷史玄奘和吳承恩的佛教思想
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到《西遊記》小說
從〈先府賓墓誌銘〉到《西遊記》小說
酒色和圓寂──從《西遊記雜劇》到《西遊記》小說
沙僧──超好的同事
文學驚嚇效應──從《水滸傳》到《西遊記》
猴年談猴──神我較勁與宗教薰陶
哪吒三兄弟──吳承恩宗教態度裡的嚴肅和虔誠
舊瓶新酒──孫悟空和唐三藏的分分合合
孫悟空的歲數問題──凡人宗教覺悟的侷限
混亂和秩序──《西...
自序 杖藜野客尋詩
內丹修持──神祕經驗和小說美學
精英主義和宗教平權──比較歷史玄奘和吳承恩的佛教思想
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到《西遊記》小說
從〈先府賓墓誌銘〉到《西遊記》小說
酒色和圓寂──從《西遊記雜劇》到《西遊記》小說
沙僧──超好的同事
文學驚嚇效應──從《水滸傳》到《西遊記》
猴年談猴──神我較勁與宗教薰陶
哪吒三兄弟──吳承恩宗教態度裡的嚴肅和虔誠
舊瓶新酒──孫悟空和唐三藏的分分合合
孫悟空的歲數問題──凡人宗教覺悟的侷限
混亂和秩序──《西...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全之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06 ISBN/ISSN:97895708519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24頁 開數:25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