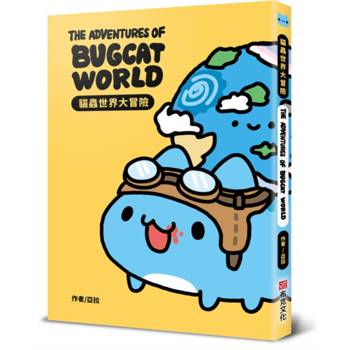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思想史8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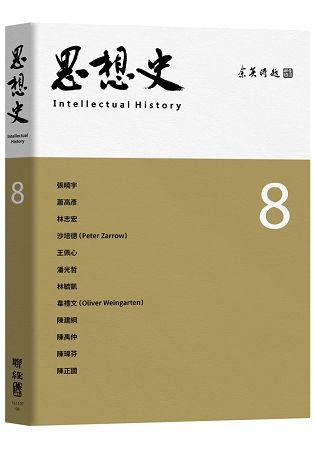 |
思想史(8) 作者:思想史編委會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2-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思想史8
內容簡介
《思想史8》收錄論文12篇,「書名及書評論文」有王佩心的〈民主的未竟之業:回顧戰前中國安那其主義研究〉;「研究紀要」有兩篇:潘光哲的〈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與「地理想像」:回顧與思考〉和林毓凱的〈「白話」作為一種性質:重探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圓桌論壇:多重文化脈下的自利觀」有四篇:Oliver Weingarten(韋禮文)的〈法家與早期兵書的賞罰思想和自利觀〉、陳建綱的〈邊沁論自利與仁厚〉、陳禹仲的〈自利與神聖正義:一個關於啟蒙運動的政治問題〉、陳瑋芬的〈近代日本「自利」概念的翻譯與傳播〉,以及論文四篇:張曉宇的〈「學派」以外:北宋士人鄒浩(1060-1111)的政治及學術思想〉、蕭高彥的〈「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林志宏的〈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1928〉、Peter Zarrow(沙培德)的〈New Culture Liberalism: Perspe ctives from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oncepts〉。
目錄
「學派」以外:北宋士人鄒浩(1060-1111)的政治及學術思想(張曉宇)
「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蕭高彥)
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1928(林志宏)
New Culture Liberal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oncepts(Peter Zarrow)
書評及書評論文
民主的未竟之業:回顧戰前中國安那其主義研究(王佩心)
研究紀要
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與「地理想像」:回顧與思考(潘光哲)
「白話」作為一種性質:重探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林毓凱)
圓桌論壇:多重文化脈下的自利觀
法家與早期兵書的賞罰思想和自利觀(Oliver Weingarten韋禮文)
邊沁論自利與仁厚(陳建綱)
自利與神聖正義:一個關於啟蒙運動的政治問題(陳禹仲)
近代日本「自利」概念的翻譯與傳播(陳瑋芬)
其他
學術悼文:紀念尼古拉斯菲利浦森(Nicholas Phillipson, 1937-2018)(陳正國)
「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蕭高彥)
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1928(林志宏)
New Culture Liberal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oncepts(Peter Zarrow)
書評及書評論文
民主的未竟之業:回顧戰前中國安那其主義研究(王佩心)
研究紀要
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與「地理想像」:回顧與思考(潘光哲)
「白話」作為一種性質:重探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林毓凱)
圓桌論壇:多重文化脈下的自利觀
法家與早期兵書的賞罰思想和自利觀(Oliver Weingarten韋禮文)
邊沁論自利與仁厚(陳建綱)
自利與神聖正義:一個關於啟蒙運動的政治問題(陳禹仲)
近代日本「自利」概念的翻譯與傳播(陳瑋芬)
其他
學術悼文:紀念尼古拉斯菲利浦森(Nicholas Phillipson, 1937-2018)(陳正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