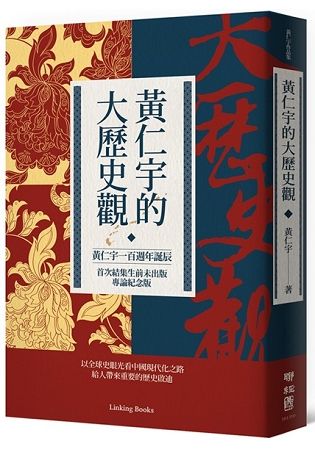黃仁宇:我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
我開始接觸(歷史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
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我才發現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緊密相連。
今日的中文閱讀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從學者、企業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領、學生等普通讀者均讚譽有加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無疑是最無爭議的人選之一。本書收錄黃仁宇未曾結集出版的單篇專文,曾散見於英國、美國、德國、香港、臺灣等地報刊雜誌,是窺視黃仁宇大歷史觀的最佳途徑。
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已經出版十餘本,但仍然有一些論文散落各處,未曾收入現已出版的著作中,對於喜愛黃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有鑑於此,在黃仁宇哲嗣黃培樂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多方途徑搜集整理黃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編成一冊,以補充現有版本的不足,同時也作為黃仁宇先生一百週年誕辰的特別紀念版。書名題為:《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也正是要再次彰顯黃仁宇先生強調長時間與慢結構的大歷史觀點。
黃仁宇先生的讀者都知道,他最擅長的就是以具體的例子說明大歷史的道理。他常提到「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這一觀念,意思是說,我們看歷史最大的通病就是以個人的道德立場講解歷史。道德不僅是一種抽象籠統的觀念,也是一種無可妥協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則涇渭分明,好人與壞人蓋棺論定,故事就此結束。然而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一個國家與社會之所以會與時代脫節,並非任何人的過失,我們要看的是,各時期的土地政策、財政管理、軍備情形、社會狀態、法律制度等。我們要考慮的是,能夠列入因果關係的,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的細微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要認為是次要的。
本書共收論文十篇,其中〈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明代的財政管理〉、〈中國社會的特質〉等四篇原為英文論文,由陳時龍先生譯為中文。透過這十篇過去沒有機會閱讀的文章,讀者當能更加體會上述的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點。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黃仁宇一百週年誕辰,首次結集生前未出版專論紀念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黃仁宇一百週年誕辰,首次結集生前未出版專論紀念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1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1936-1938),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1940),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1947),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1964)。曾任陸軍少尉排長(1941)、中尉參謀(1942)、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1943-1945)、少校參謀(1946)、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1949-1950),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著作有《緬北之戰》(1945,聯經2006、2018)、《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英文版1974,聯經中文版2001)、《萬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中國大歷史》(英文版1988,聯經中文版199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敘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聯經1991、2018)、《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近代中國的出路》(聯經1995)、《汴京殘夢》(聯經1997、2011)、《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聯經2001)、《大歷史不會萎縮》(聯經2004)、《明代的漕運,1368-1644》(聯經2006、2013)。
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1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1936-1938),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1940),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1947),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1964)。曾任陸軍少尉排長(1941)、中尉參謀(1942)、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1943-1945)、少校參謀(1946)、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1949-1950),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著作有《緬北之戰》(1945,聯經2006、2018)、《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英文版1974,聯經中文版2001)、《萬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中國大歷史》(英文版1988,聯經中文版199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敘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聯經1991、2018)、《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近代中國的出路》(聯經1995)、《汴京殘夢》(聯經1997、2011)、《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聯經2001)、《大歷史不會萎縮》(聯經2004)、《明代的漕運,1368-1644》(聯經2006、2013)。
目錄
出版說明
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
早期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農業社會的官僚政治管理
科學技術和貨幣經濟的低水平發展
社會後果
歐洲的過去和中國的未來
從唐宋帝國到明清帝國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
明代的財政管理
傳統理財思想與措施的影響
戶部及戶部尚書
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一五九○年前的財政管理
一五九○年後的財政管理
結論
什麼是資本主義?
當代論述資本主義的學派
資本主義的精神
布勞岱對中國經濟史的解釋
官僚體系的障礙
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法律與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範圍
資本主義的時空剖析
資本主義的條件
蔣介石
蔣介石的歷史地位:為陶希聖先生九十壽辰作
站在歷史的前端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臺灣的機會與困境
中國歷史的規律、節奏
黃仁宇著作目錄
中國社會的特質:一個技術層面的詮釋
早期的統一與中央集權
農業社會的官僚政治管理
科學技術和貨幣經濟的低水平發展
社會後果
歐洲的過去和中國的未來
從唐宋帝國到明清帝國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現實主義」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
明代的財政管理
傳統理財思想與措施的影響
戶部及戶部尚書
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
一五九○年前的財政管理
一五九○年後的財政管理
結論
什麼是資本主義?
當代論述資本主義的學派
資本主義的精神
布勞岱對中國經濟史的解釋
官僚體系的障礙
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法律與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範圍
資本主義的時空剖析
資本主義的條件
蔣介石
蔣介石的歷史地位:為陶希聖先生九十壽辰作
站在歷史的前端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臺灣的機會與困境
中國歷史的規律、節奏
黃仁宇著作目錄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