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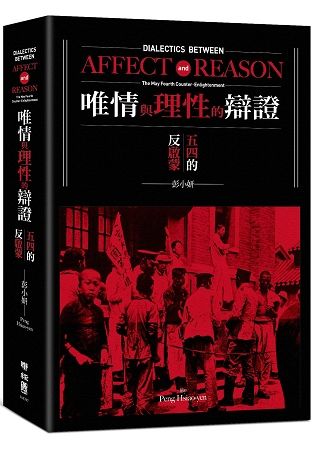 |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 作者:彭小妍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4-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作者簡介
作者:彭小妍
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方向為兩岸現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曾出版專著《超越寫實》、《海上說情欲:從張資平到劉吶鷗》、《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小說《斷掌順娘》《純真年代》,主編有《楊逵全集》。
2013年以《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聯經出版)一書榮獲第37屆金鼎獎最佳非文學圖書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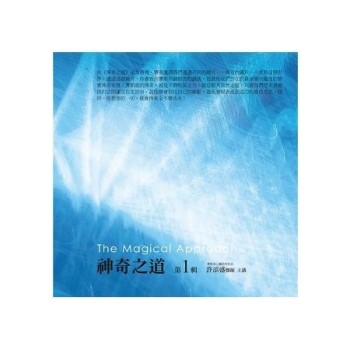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