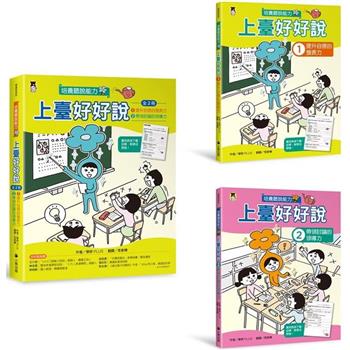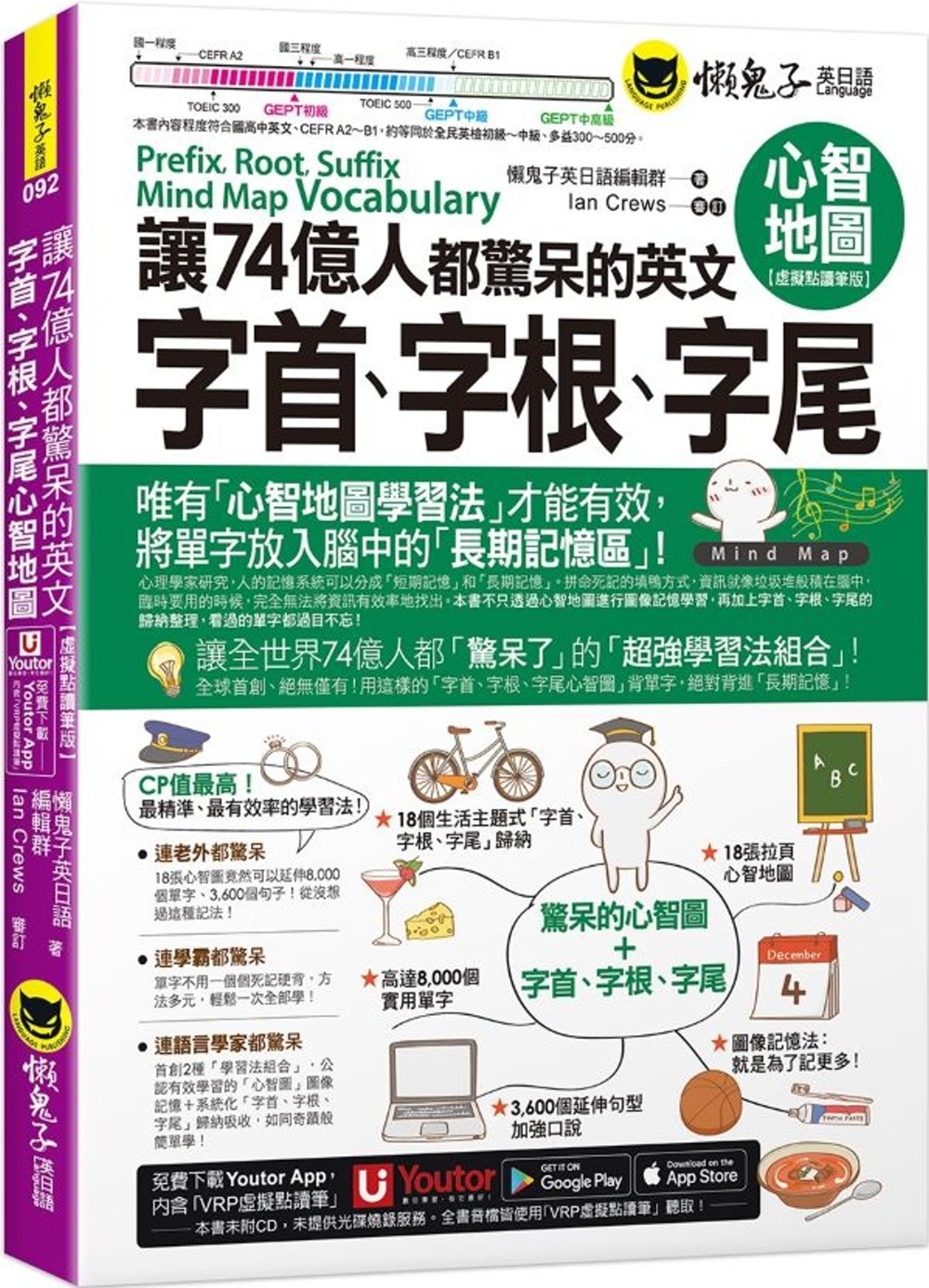圖書名稱:命子
繼《愛妻》探究兩性關係與夫妻婚姻中的愛慾本質及可能,董啟章又一人性關懷力作,從父子相處著眼,書寫父母與子女的角力與期望。
《命子》以父親的角度,進入存在或不存在的兒女之人生。第一部分〈命子:果〉以回憶錄/生活散文形式,寫父子的相處日常和兩人之間的相互「忍讓」,寫兒子果之執著,為人父母之甜蜜無奈,讀來生動幽默。第二部分〈笛卡兒的女兒〉,則是沒有女兒的作者,透過虛構笛卡兒的人物傳記,想像一個有女兒的人生。第三部分〈命子:花〉則虛構另一個不存在的兒子花的書信,試圖作為真實兒子的對照,也帶入自己孩提時的記憶,作為另一種隱性式父對子的期待。
透過寫實、虛構、再虛構的書寫策略和角度,熔散文和小說於一爐,讓父與子在最想不到的地方接通。
董啟章:關於兒子,我寫的時候極為小心,反覆思量,要怎樣措辭,怎樣挑選,怎樣剪裁,或採用怎樣的語調和角度,以呈現一個既真實但又於他無損的形象。就算我是父親,又是一個作家,我也沒有權隨意取用自己兒子的人生,作為我的寫作材料。……我給兒子親自過目……他並不介意,似乎深明寫作的本質。總體來說,他的評語是:寫得幾好笑。我認為,這是我從他身上所可能得到的最高評價。
----
作者簡介
作者:董啟章
1967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1994年以〈安卓珍尼〉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以〈少年神農〉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1995年以《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1997年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2005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誠品好讀雜誌年度之最/最佳封面設計、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2006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榮獲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2008年再以《時間繁史‧啞瓷之光》獲第二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2009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獎2007/2008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2010年《學習年代》榮獲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2011年《學習年代》榮獲「第四屆香港書獎」。2011年《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簡體版)榮獲第一屆惠生 施耐庵文學獎。2014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2017年《心》榮獲「第十屆香港書獎」。2018年《神》榮獲「第十一屆香港書獎」。2019年以《愛妻》獲2019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
著有《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紀念冊》、《小冬校園》、《家課冊》、《說書人》、《講話文章:訪問、閱讀十位香港作家》、《講話文章II:香港青年作家訪談與評介》、《同代人》、《貝貝的文字冒險》、《練習簿》、《第一千零二夜》、《體育時期》、《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對角藝術》、《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學習年代》、《致同代人》、《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博物誌》、《美德》、《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I》、《衣魚簡史: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II》、《董啟章卷》、《心》、《神》、《愛妻》、《命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