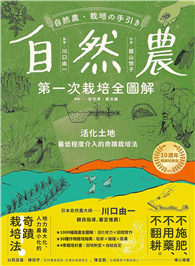這是一趟夜旅,一本思索存在與靈魂的書。
從生命的盛夏寫到秋天,
羅任玲橫越四分之一世紀第二部散文之作。
★ 楊佳嫻──專文引讀
★ 瘂弦、張曉風、陳義芝──詩心推薦
《穿越銀夜的靈魂》是羅任玲第二部散文集,亦是二十年光陰的餘音。在經歷至親走過死生的長旅,書寫成為銘記,也啟示書寫者向死而生的心。所穿越的,不只是存在與死亡,亦為練字剪裁的語言邊界,如羅任玲所說:「散文的極至是詩。」詩人穿越無人知曉的銀夜,為我們召回夢的消息。
名家推薦
瘂弦:
羅任玲深知,原來散文與詩一樣,在經緯結構上與詩同樣嚴格。好的散文文如其人,直見性情,作者的氣質人格在作品中一覽無餘;而散文的創作也跟其他文類一樣,需要自信與果斷,沒有僥倖。散文不是妥協的文類,散文也不是中間文學,要想寫出成功的散文,跟寫一首成功的詩一樣,絕對要把自己的全靈魂、全人格放進作品之中。
張曉風:
這雙冷冷的眼睛在窺伺在觀望在求索,這雙眼睛如切鱠的利刃,把往事的肌理一一呈現。……唯有愛,還在那裡,看來沒有什麼用,看來不能解決什麼,但它在那裡,你覺得心安了,因為它本來就該在那裡。
陳義芝:
羅任玲鋪寫一幅幅生動的景致,表述許多極難表述的人生況味,例如追尋、失落、抵抗、偶然與必然。唯景中有景的筆法,乃能渾融烘托出宿命般的人生感喟,而淡然得教你聽不到嘆氣聲,因此而更令人低迴悵惘。
楊佳嫻:
讀《穿越銀夜的靈魂》,一是「靈魂」,彰顯其形上的取向,二是「穿越」,讀取這世界但不拘限於這世界。身體鑲嵌於現實,容或有不自由的時候,但思維可以是自由的,想像可以是自由的。
作者簡介:
羅任玲
喜歡秋夜。老樹。星空。荒野。大海。幽深之境。
台師大文學碩士,著有詩集《密碼》、《逆光飛行》、《一整座海洋的靜寂》、《初生的白》,散文集《光之留顏》,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2020年出版散文集《穿越銀夜的靈魂》。
章節試閱
穿越銀夜的靈魂
0. 上次她和母親來到奈良是秋天,如今小雪已過。一到夜晚,遍地清冷。即使如此,也還是美的。高大的銀杏,千千萬萬個銀扇,映照重重疊疊的今日與明日。隨手撿拾一片,與多年前的那一葉並無不同。 天漸漸暗下來的東大寺,上百隻烏鴉忽然飛出來,在夜空中狂笑:「ㄚˋ—ㄚˋ—ㄚˋ」「ㄚˋ—ㄚˋ—ㄚˋ」。她抬頭望向寒冬潑墨的晚雲,那麼冷然籠罩著癡傻的人們。群鴉諷笑之後又消失在東北的深林中。那裡落單的鹿正發出詭異的鳴叫。 沿著奈良公園,她慢慢走回旅館。白天熱鬧的公園,此刻一片暗黑死寂,路上幾無人跡。左側是靜默的奈良國立博物館,館中的佛像們還在夜裡睜著不眠的眼吧。一千多年來看盡生生死死。下午她才細細與祂們對視。她特別喜愛的飛鳥時代,天真可愛的神態,童子般的微笑容貌,一再讓她想起母親。短促的此生與幾近永恆的祂們。 一個與誰都無關的旅人,在神祕的冬夜,慢慢走著。另一個東大寺博物館的佛陀影像緩緩映在夜裡,夢一般播放著:「只要你思維著我,我就和你在一起了。」此刻穿著母親送她的羽絨衣,雙手插在口袋裡,感覺著溫暖的她,也是和母親在一起的吧。原本以為會是一趟感傷之旅,她的心卻漸漸平靜下來。異地的夜漸漸覆蓋,那是母親從未離去的溫暖……
1. 第一次到日本,也是第一次出國,是升大三的暑假。當時才開放出國觀光不久,除了護照,還得申請出入境許可。到現在我仍保留著那張許可證,是當年母親幫我申請的,上面還有她的簽名。鄧是班上的日本僑生,高頭大馬膚色黝黑,戴上墨鏡時頗有大姊頭的味道,同學們都叫大姊頭「老大」。我帶著母親給的旅費,和另一個小個子的陳,由老大帶領,三個女生一路從沖繩玩到東京,最後一站到了京都。為何沒去奈良,應該是老大沒安排吧?到京都時夏正熾灼,到處都是綠蔭和無盡的蟬鳴,天氣非常非常熱,我病倒了。鄧和陳兩人出去玩,我一個人躺在旅館裡,發著高燒,意識模糊,只覺得世界變成一個銀綠色的極大的水塘,我在上面漂浮著,許久許久,終於沉入了水底,那裡蟬聲依舊不斷嘶鳴。 那一趟我們總共去了一個月,沖繩的海藍天藍,東京迪士尼樂園的神奇魔幻,京都不真實的美因為摻和了我的高燒更加夢幻迷離。那是二十歲少女沒有邊界的夏日之夢。心飛到外太空去了,在沒有手機的年代,我以找不到電話為由,整整一個月沒和家裡聯絡。卻還理直氣壯地以為,反正沒事嘛。回台灣才知道,母親著急得不得了,又完全聯絡不上我,怕我在日本出了什麼意外,差點想去報警了。
2. 二十歲就去了日本的我,卻直到母親七十多歲才第一次帶她踏上這個國度。母親還是很開心,自己收拾了行李箱。事實上,這也不過是我第二次到日本,這二十多年與日本之間的全然空白,讓我此行的心情格外複雜。我思索著,為何去了那麼多國家,卻沒想到再踏上這塊土地?彷彿才一轉眼,那個在夏日發著高燒的少女就已經老了。沒有銀綠漂浮的水塘,沒有熾烈的蟬鳴,經歷了許多人世炎涼,她再也不可能用那毫無顧忌的任性雙眼看世界了。 我一向不參加旅行團。喜歡自由自在,愛在哪裡停留多久就待多久的徒步之旅。然而當母親提議想去日本時,我卻猶豫了。首先這麼多年沒到日本,人生地不熟,如果是我一個人,那倒無所謂,我本來就偏好漫行探看,對陌生事物充滿好奇。但帶著母親就不同了。母親腳力不好,走不遠,萬一路上發生什麼事,還真是麻煩。幾經考慮,最後還是決定報名旅行團。沒想到,卻整個是一場災難。雖然我特別挑選了包含京都奈良在內的,景色優美母親可能喜歡的古都。然而整個行程卻像急行軍,不斷從此地趕到彼地,所有景點都匆匆一瞥,彷彿過眼雲煙。最可憐的是母親,她永遠趕不上隊伍。每到一處,所有人都已抵達好一陣子了,我才帶著氣喘噓噓的母親趕來。為了等她,行程也不免有所耽擱。最難過的是聽到同團的人低聲嘀咕:「走不動就不要來嘛。」 最嚴重的一次,是從東大寺出來,走到一半,一陣突如其來的暴雨,把我們和這團急行軍徹底打散了。為了怕母親滑倒以及幫她遮雨,我們走得比之前更慢,當我有空抬頭時,四周早已一片空蕩,整團人像鬼魅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只聽領隊說過待會要去用餐,卻完全不知道是哪家餐廳?拿出領隊給的有她手機號碼的紙條,我的手機卻無法撥通她的。之前行路匆匆,接過紙條時並未細看,原來上面還有一行日文:「私は迷っています。」就算不懂日文也猜得出來,這行字是「我迷路了。」她早就知道這對母女會被隊伍拋下的,而且手機撥不通就會自己去借電話。 大雨中四顧茫茫,天地空曠樹影婆娑,一幢建築物的影子都沒有。偶爾遠方閃過一兩個也在趕路躲雨的旅人,根本不可能唐突衝過去借電話。 母親很緊張,因為聽說吃完午餐就要離開奈良了,萬一他們等不到我們,就逕自出發了怎麼辦?我一面安慰母親「放心,他們一定會等我們的。」一邊帶著她繼續在大雨中艱難地往前走。沒有Google Map,只能憑判斷尋路。將近半小時,終於來到一處清幽的所在,石柱上刻著「二月堂」。寺廟在高高的半山腰,要爬許多石階才能上去,母親根本沒力氣了。我對她說「上面一定有電話,你在這裡等我,我上去借。」爬到一半,回望山腳下的母親,她正在有遮簷的地方一動不動地望著我,眼神寫滿了憂忡。 好不容易來到古樸的廟裡。因為大雨,遊人稀少更顯寧謐。時間彷彿在這裡靜止了,又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兩名僧人安靜坐在門內,我把紙條遞給其中一位。他看了一眼,忍住一絲笑意撥了電話。手機終於通了,領隊問了我們的所在,說她立刻來接我們。 掛上電話,雨勢已漸漸小了。那片刻的寧靜,我透過晶瑩的雨珠望出去,遠方是雲嵐間的黛青山色,那樣縹緲彷如幻境。我想起了多年前高燒時的銀綠水塘。沒有焦躁,沒有擔憂,沒有迷路。只有無盡的悠悠時間棲息在彼岸。 和母親一起在山腳的屋簷下又等了二十分鐘,終於看見雨中尋來的領隊,我們跟在她後頭,緩慢地走到餐廳。是定食,每人桌上都擺了一份。照例,大家都吃飽了,又坐在那裡等我們。母女默默坐下,吃著那早已冷掉的定食。母親臉上沒什麼表情,我心中卻頗自責,早知如此,就根本不該帶她參加恐怖旅行團,讓她受到這麼多的難堪和委屈。 終於結束旅程的那一天,前往關西機場的巴士上,母親望著窗外漸暗的街景,轉頭對我說:「總算到過日本了。」
3. 我一直想帶母親再去一次奈良。 安靜悠閒地, 想在哪裡待多久就待多久……
那個冬天。夢裡我終於有了兩星期的長假,我想著要去歐洲,但又想應該去日本,才能探望在呼吸照護中心的母親,但為何母親是在日本的呼吸照護中心?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著,怎能丟下母親不管?就算犧牲旅行也一定要陪伴她,不能讓她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照護中心。將醒未醒之際,濛昧寒流來襲一片漆黑清冷。我忽然意識到,哪裡有什麼呼吸照護中心,母親已經死了。 窗外銀白的月光透進來,照在空無一物的牆上。 意識模模糊糊走著。穿越了無數的銀夜…… 那是念高中的我,放學後去找母親,她在南昌路的公賣局上班。夜色將臨時我走到了警衛室,對警衛先生說:「我找黃小姐。」幾分鐘後,母親就面帶微笑從裡面走出來。總是這樣,我從沒進過母親的辦公室,也從不知道她每天上班有多累。我只知道念書時從沒為錢煩惱過。彷彿本該如此似的。 我和母親沿著南昌路,一直走到南門市場。母親會進去買一些熱騰騰的麵包給我吃,順便帶一些熟食回家,袋子裡都是沉甸甸香氣四溢的食物。她也不過四十出頭,真的還是小姐啊。 鏡頭再轉, 那是六歲的母親。提著她母親給的一塊紅燒肉,要帶去給幾條街外的公太。經過最繁華熱鬧的商店街,提著紅燒肉的六歲小女孩,好奇地一家家進去看看。有賣布的,就用手摸摸那些好看的光滑的布料;有做糖的,就盯著做糖人用長桿把熔岩般的糖神奇拉長甩向天空又接回來,雖然她口袋裡沒有錢,買不了任何一塊糖。這樣走走逛逛,每一家都新奇。直到天快黑了才把紅燒肉送到公太手上,公太很著急,以為她迷路了(啊那時我在哪裡呢)。 鏡頭轉著。 到了另一個春天的夜晚…… 回到家中,母親神祕地從她手提袋中掏出三顆石頭送給我,兩顆是我喜愛的鐵灰色,另一顆黑得發亮,像是黑曜岩。三顆都渾厚飽滿,捧在手中沉甸甸的。我想起來了,下午我在園裡拍照時,看見母親落單在遠遠的那一端,低頭不知找尋什麼。三月的園子彷如幻境,風涼颼颼的。景物都飄飛起來。後來我們離開,夜色漸漸沉落下來,母親揹著她的手提袋,什麼都沒告訴我。好沉重啊。母親竟然揹著那三顆大石頭,走了那麼遠的路。 那是她和我的最後一次出遊。 那年冬天,她獨自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4. 一生,可以很遠很遠嗎? 這個明滅的世界…… 我始終記得,那年迷路之前,在東大寺匆匆一瞥的四個字:「一即一切」。
我始終記得,送別母親的最後一刻。 閉上雙眼的她,是微笑著的……
穿越銀夜的靈魂
0. 上次她和母親來到奈良是秋天,如今小雪已過。一到夜晚,遍地清冷。即使如此,也還是美的。高大的銀杏,千千萬萬個銀扇,映照重重疊疊的今日與明日。隨手撿拾一片,與多年前的那一葉並無不同。 天漸漸暗下來的東大寺,上百隻烏鴉忽然飛出來,在夜空中狂笑:「ㄚˋ—ㄚˋ—ㄚˋ」「ㄚˋ—ㄚˋ—ㄚˋ」。她抬頭望向寒冬潑墨的晚雲,那麼冷然籠罩著癡傻的人們。群鴉諷笑之後又消失在東北的深林中。那裡落單的鹿正發出詭異的鳴叫。 沿著奈良公園,她慢慢走回旅館。白天熱鬧的公園,此刻一片暗黑死寂,路上幾無人跡。左側是...
推薦序
代序
世界是鳥籠,但靈魂可以穿越
楊佳嫻(詩人,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羅任玲的詩,安靜綿密深美,她以詩心經營散文,知道何處該繡出細節,使血肉豐勻,亦深諳空白的力量。讀她早歲散文集《光之留顏》(一九九四),許多短製篇章從雲端來,沿風而去,憑一個印象、一樁散事為起點,勾勒出生命悲愴與疑問,舉重若輕,而不傷內裡嚴肅的筋脈。莊裕安說她的散文音色絕佳,音色勝過結構,不規整,可是具有散脫的魅力;這樣的特質,也還持續保留在之後的書寫裡,具體呈現為第二部散文集,《穿越銀夜的靈魂》。 當然,二十幾年來,寫作者會滄桑,時代會變化,羅任玲的散文仍維持著清妙音色,以及不羈的形式,以之作為其散文的基礎風格。同時,那些必須積累時間才可能大量且深入體會者,也以顯著篇幅形塑出這部散文集的骨軸——無所不在的異鄉感,人間的游與思,以及死亡。 全書開篇,與書名同名的長散文,回憶與母親少有的共同旅行。以「她」來代替「我」,或許是想拉開抒情的距離,畢竟所寫是極端近身、或許難以逼視的經驗。「她」只經歷兩次日本行旅,一次是二十歲時,當年通訊不便,出國麻煩,一個月日本時光就像完全浸入陌生世界蟬鳴花水,渾然不覺家鄉;多年後才帶著七十多歲母親跟著旅遊團前往,因為老人行動較緩慢,跟不上全團步伐,而往往落得母女相依為命,迷路於異地大雨之中。自由而孤獨,彼此陪伴著迷路,都是生命中必然會有的情境。少年與中年,記得母親的方式也變得不同。追憶恍惚過渡,「母親已經死了」——死亡是跨越嗎?給予我們一個憑依,召喚遂散於銀河裡繞著這個那個結而長出來的影片,電轉拼接為迷津與長河,懷念與證悟。 與〈穿越銀夜的靈魂〉一文同樣抒寫親緣牽絆的,還有〈鱉的黃昏〉。緣於兩岸局勢,分隔了四十餘年,終於在稍微開放之後,父親與阿婆回復了聯繫。這是不是一九八.年代末兩岸開放探親以來,許多人說過寫過的故事?即使那麼多人說過寫過,即使不外乎大時代變動底下的必然,一旦發生在自己家族,那悲喜之感仍然扎實。一開始寄來照片,老家的家族照吧,其他人都擠出笑容,只有阿婆板著臉——她的神情與視線投向鏡頭之外,這是她對迢遠另一岸的兒子的心情嗎?還是一時不知道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而對於總是聽父親回憶親人的女兒來說,勾勒出來都是分離前的青壯樣貌,可是歲月之河仍在沖刷,照片裡錯失了什麼、蛀空了什麼的一張臉,是否能彌補父親的思念?後來,阿婆來了台灣,八五高齡,面對不會說家鄉話的孫女,每天等兒子下班回家。阿婆歡喜看某家餐廳門口的水族箱,水裡游著一隻鱉,醜醜的,可是會勾起久遠的畫面,那是兒子童稚時期養過的愛物..。阿婆終究得離台,短暫相處與再一次的告別裡,恍然發現,父親其實也老了。 映射敏感之人無所不在的存在困境,也同樣動人。〈雪色〉寫對於時間的思索,談時間,難免觸及死亡,談死亡,又何嘗不想起靈魂有無、靈魂歸屬的問題?然而,生時的苦楚,真能在跨越之後拋在身後?人不只可能漂泊異鄉,也可能在熟悉環境中仍舊存有異鄉之感。格格不入,有時候不是因為具體地理的乖攣,而更可能是心境、思想上的背離。所以羅任玲在文中就問了:「哪裡才是永恆的家鄉?」然而,現實中我們不得不自保,冷漠可能逐漸取代一覽無遺的熱情,「即使迷路也偽裝成無自若無懼」,掩藏靈魂,以冷淡武裝。文中提及一位女性友人,患了暴食症,與丈夫分居,居住在紐約,可是那裡只有下水道冒出的蒸氣是溫熱的。人是不是總難免要經歷下墜?或者更悲觀一些,人活著,整個就是一個下墜的過程?尋求一張溫暖的網子接住自己,是不是能得到,也許得靠一點運氣。而在〈誰也沒有真正報復過死亡〉裡,羅任玲提出,異鄉人處境活著難免,死了也未必能迴避;君不見喪禮中,反覆不見情的誦唱環繞,「長長的一生被簡化。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成為一張扁平的照片」。〈永遠的異鄉人〉更進一步揭示「世界像鳥籠」,彷彿呼應白居易〈與元微之書〉「籠鳥檻猿俱未死」一語,生命有其邊界,人間又處處設限,是誰提著我們居住的籠子? 書中另收了幾篇微型變奏,類似寓言故事,借他物映照出人類何等自擾。〈穿紫色衣服的鬥魚〉寫花瓶裡養著鬥魚,沒有同伴或敵手,鬥魚無鬥還算鬥魚嗎;文中同時寫到鬥魚主人L,卻並非尋常以鬥魚比擬人類社會鬥爭,L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鬥魚呢,只要還在人類為牠圈出的容器裡,時不時成為被觀看之物,牠恐怕不會出現和人類同樣的煩惱。〈尊者〉寫飼養烏龜,龜背上長出青苔,吃,睡,曬太陽,揹著一叢潮濕綠意,人類談論生老病死的口角,與時不時要確認牠是否仍活著的騷擾行為,甚至是那隻鬥魚的升沉,都彷彿某種紅塵漣漪,青苔尊者見而不見。鬥魚與烏龜,一勞一逸,自有其境。 最後,這部散文集也回應了作者的詩人身分。除了若干文章中談及自己某些詩作的背景,另有〈蝶影〉敘及與周夢蝶的因緣,〈詩為何物〉回憶中學國文老師、也是詩人小說家沙究,〈深秋〉則悼念楊牧。與前輩作家交遊,總涉及閱讀,從中一次次確認理解文字與文學的重量,亦可曲折看出羅任玲的創作思索之路。 羅任玲關注生活裡蘊育的精神面,加上文字的冷麗,難免給人「空靈」之感。不過,散文寫法本就不拘一線,能低低黏緊土腳,也能高高翻進月光。端視如何放置心靈與世界。怕什麼?不是距離地表遠或近,怕的是濫情,庸俗,逐流說話。讀《穿越銀夜的靈魂》,一是「靈魂」,彰顯其形上的取向,二是「穿越」,讀取這世界但不拘限於這世界,穿梭於虛與實、高與低,身體鑲嵌於現實,容或有不自由的時候,但思維可以是自由的,想像可以是自由的。
代序
世界是鳥籠,但靈魂可以穿越
楊佳嫻(詩人,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羅任玲的詩,安靜綿密深美,她以詩心經營散文,知道何處該繡出細節,使血肉豐勻,亦深諳空白的力量。讀她早歲散文集《光之留顏》(一九九四),許多短製篇章從雲端來,沿風而去,憑一個印象、一樁散事為起點,勾勒出生命悲愴與疑問,舉重若輕,而不傷內裡嚴肅的筋脈。莊裕安說她的散文音色絕佳,音色勝過結構,不規整,可是具有散脫的魅力;這樣的特質,也還持續保留在之後的書寫裡,具體呈現為第二部散文集,《穿越銀夜的靈魂》。 當然,二十幾年...
作者序
向死而生,凝視自由
0. 五歲以前,幾次夜裡睜開雙眼,明明記得漆黑一片的房間,卻有三、四個燈球在屋子上方懸著,它們緩慢飄浮,光絢但不懾人。家人都熟睡了,我獨自在黑暗裡,默默凝望那神祕的光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也不害怕,因為它們如此寧靜清亮而美麗。 光球在我進小學之後就不再出現了。 我卻從未忘記那些奇異的夜晚,也確信當年的我十分清醒。雖然並不常想起,但只要我願意,總能回到人生初始詩一般魔幻的時刻。感覺溫暖獲得力量,像一個祕密的約定。 讓我深信這世界還存在玄祕動人的事物,生命中發生的一切都有意義。雖然它們時常被裝進荒誕殘忍的盒子裡。 我忠實記下這些與那些,在還記得的時候。 所有現實的倒影,記憶給我的饋贈。
1. 這是一本思索存在與死亡的書。我斷斷續續寫著。 從生命的盛夏寫到秋天,前後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穿越」二字,我一直特別有感。 生存彷彿一場暗夜之旅,明知終點是衰老與死,除非提前殺了自己,否則還是必須往前走。這是夜旅的法則。 「穿越銀夜的靈魂」,其實早在一九九八《逆光飛行》時期就已出現在我的筆記本。真正找到相應的內容,卻是在二○一八年。並以同名長文發表於副刊。 作為全書之名,它還有多重象徵(我一向偏愛詩意且多重指涉的書名)——可以是人我異境過去未來尋常想像夢醒生死,當然更包括文類的穿越。 我也喜歡夜晚甚於白晝。 夜必然是幽暗的,「銀夜」則不全然如此。 那些幽微難辨的時刻,灰黯中透出的光亮細節,被宇宙至美又沉默包覆的我。銀夜漫遊中來了又逝去的人事物…… 穿越只能是自己安靜地穿越。 而安靜是最大的力量。我始終深信著。 這個題名陪伴了我二十年,最後成為第二本散文集的名字,或許真是因緣吧。即使「穿越什麼的什麼」,近年已被用得幾近俗濫了,我仍願意保留這書名。
2. 沒人規定散文該怎麼寫,就像沒人規定詩該寫成什麼樣子。我也從不認為散文只能敘事,它是液體不是固體;文類更不是邊界,只要作者願意,它有最大的自由可以穿透,可象徵可意識流可超現實。在時空之內及之外,一切廣闊的存在。它和所有藝術創造一樣,需要開啟全部的感官與覺知。 然而它又不必是緊張用力的,我嚮往的散文和詩並無不同——澄靜悠緩又有餘韻。 散文是靈魂的漫步與深談。散文的極至是詩。 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不也說:「永遠做一個詩人,即使在散文中。」 能去到多遠,沒有人知道。 我不免想起遙遠的,法國南方的雪維洞穴(Chauvet Cave)。約翰.伯格(John Berger)描繪的:「在洞窟深處,亦即地球深處,存在著萬事萬物,風、水、火、天涯海角、死者、雷、痛苦、小徑、牲畜、光、未來的一切……它們在岩石內等待被召喚。」 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雪維洞穴。那些被召喚而來的,都是最神祕且獨一無二的。 如今想來,那飄浮於五歲房間內的神祕光球也是召喚。彷彿預示生命將遭逢的一切,在無人知曉的銀夜,所有眼見耳聞憂傷歡愉最後都將成為創作的養分。 一切即心。 散文與詩的天涯海角,即是靈魂為萬事萬物的命名。
3. 正因散文無邊無界,看似自由且容易。我反而特別重視練字剪裁結構,以及分寸拿捏。無論三五百字的短文,或三千字以上的長文。 練字是不留廢字的基本要求,至於是否字字珠璣,端看個人才情;剪裁使文章不至蕪雜,結構使整體不至疲軟歪斜;分寸是寫或不寫的斟酌,拿捏是避免情感氾濫成災。 我希望它們有詩的眼睛,也有潑墨畫的左手,工筆畫的右手。同時腳踏背光面和向光面。 散文也需要留白,一篇上乘的散文絕不可能是鉅細靡遺的流水帳。 比起短文偏重靈光乍現,長文才是考驗作者的試金石。而無論長短,皆需沉澱。沉澱夠久,才能看清雜質所在。 我寫作的速度應該算快,但發表的速度很慢,除了少數,一篇文章或一首詩放在身邊幾個月是常有的事。我總習慣隔著時間長河回望,像陌生讀者般審視自己的文字,直到確定不需再更動了,才會放它們出去。我的筆記本裡有不少初稿,但絕少同時處理兩篇稿子。詩人導演尚.考克多(Jean Cocteau)的說法深得我心: 沒有比靈魂的旅行更緩慢的了……「迅速」會讓人陷入混亂……對作品而言,重要的是在每一部作品完成之後,等待身體擺脫殘留的氣息,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這種氣息才會離開。
至於長文,我只寫深深觸動我的,以及必須百分之百的真誠。因為這些原因,久久才完成一篇是必然的。〈鱉的黃昏〉、〈雪色〉是如此(它們曾獲第六和第十二屆梁實秋文學獎,也是我唯二參與的散文獎)。〈漆黑的夢中樹〉、〈永遠的異鄉人〉、〈日落,在北方大道〉、〈詩為何物〉,以及同書名作〈穿越銀夜的靈魂〉等,都是如此。 除了情感,散文也需要知識。我一直熱愛知識散文的深廣豐饒,手邊也有不少這類的書。我總是一再讀著它們,像踏上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旅途。我自己寫過最長的知識散文,是二○○五年出版的十七萬字《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雖被歸為論文,也毫無疑問是我用心甚深的散文集。 散文人人會寫,其中的火候工夫,和任何一門學問一樣永無止境。 4. 思索死亡,也等同於思考限制與自由。 死亡有不悲傷的嗎?我不知道。但至少,這幾年我愈來愈體悟到,死亡能奪走的東西其實很有限,除了一個舊皮囊,以及世俗的財產(如果有的話)。那些無形且真正珍貴的,是死亡無論如何也帶不走的,例如靈魂、智慧與愛。 而在有限的生之容器中,創造無限的精神世界,找到可能的自由,才是我心所嚮。
向死而生,凝視自由
0. 五歲以前,幾次夜裡睜開雙眼,明明記得漆黑一片的房間,卻有三、四個燈球在屋子上方懸著,它們緩慢飄浮,光絢但不懾人。家人都熟睡了,我獨自在黑暗裡,默默凝望那神祕的光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也不害怕,因為它們如此寧靜清亮而美麗。 光球在我進小學之後就不再出現了。 我卻從未忘記那些奇異的夜晚,也確信當年的我十分清醒。雖然並不常想起,但只要我願意,總能回到人生初始詩一般魔幻的時刻。感覺溫暖獲得力量,像一個祕密的約定。 讓我深信這世界還存在玄祕動人的事物,生命中發生的一切都有意義。雖然...
目錄
代序 世界是鳥籠,但靈魂可以穿越 楊佳嫻 自序 向死而生,凝視自由 卷一 光音之塵 穿越銀夜的靈魂 交界 廢墟 餘音 韶光樂園 光音之塵一 光音之塵二 鏡中人 憂鬱 別只是死寂 濤聲遠去 一個人的夏日花園 鯨夢 雲外書 高原的夏天 離開 冬日記憶 夏日寓言 魔術師的旅行箱 穿紫色衣服的鬥魚 尊者 綠繡眼 遺失一尾熱帶魚 卷二 召夢者 彼岸 致一九七七 月牙 雪色 煙說 是誰錯置回聲 櫻吻 蝴蝶樹 夜間訪客 遙遠的巴海貝爾 那時台北還是一片濃霧 他是有權的…… 畸形人 雪之床與夜之谷 壁癌 黃昏的絃樂 晚雲濤濤,多少逝水 淡水暮色 紀念 鱉的黃昏 卷三 漆黑的夢中樹 越界之旅 化身 大佛寺 死亡,祂輕輕靠近你 其實誰也沒有真正報復過死亡 那一方靜默的陽光 永遠的異鄉人 海潮.夜與日 是身如夢 日落,在北方大道 蝶影 詩為何物 深秋 漆黑的夢中樹 代後記
代序 世界是鳥籠,但靈魂可以穿越 楊佳嫻 自序 向死而生,凝視自由 卷一 光音之塵 穿越銀夜的靈魂 交界 廢墟 餘音 韶光樂園 光音之塵一 光音之塵二 鏡中人 憂鬱 別只是死寂 濤聲遠去 一個人的夏日花園 鯨夢 雲外書 高原的夏天 離開 冬日記憶 夏日寓言 魔術師的旅行箱 穿紫色衣服的鬥魚 尊者 綠繡眼 遺失一尾熱帶魚 卷二 召夢者 彼岸 致一九七七 月牙 雪色 煙說 是誰錯置回聲 櫻吻 蝴蝶樹 夜間訪客 遙遠的巴海貝爾 那時台北還是一片濃霧 他是有權的…… 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