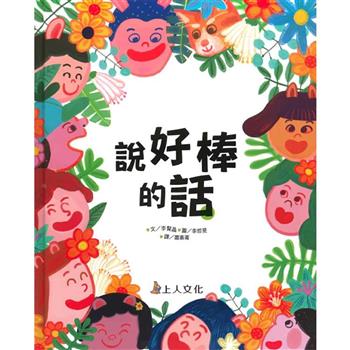「消除國界的作祟,就是精怪盛大惡作劇的真面目。」
一起機長在駕駛艙內神祕消失的事故,
一件南方澳老嫗失蹤山上的傳聞,
家鄉裡一個個戰後不見了的琉球同伴……簡直都像被魔神仔牽走?
小說家瀟湘神追蹤精怪牽人的足跡
走進臺灣與琉球歷史交織的密林
「魔神仔」是臺灣赫赫有名,在山間出沒的精怪。「牽走」這種說法,是臺灣人說明魔神仔將人帶到不可思議的地點所用的動詞。迷路的人發現自己居然不知不覺走到幾十公里之外、或爬到很高的樹上、渡過極為湍急的河流,又或是圍困於刺竹林中,當事人卻不明白是怎麼發生的,人們就會說是「被魔神仔牽走」。
記者羅雪芬為調查大學學弟、擔任機師的陳鑫垚於飛行航程中神祕消失的事件,來到舊友家鄉南方澳,聽聞鄰里談起他的奶奶陳黃慶子、外太婆玉城夏子過去失蹤的謠言。漢人繪聲繪影的「魔神仔」,對宛如受詛的家族,幾位帶有琉球血統、終戰後留在漁村的女性,心裡卻有另外的信仰。隨著深入別人家族的故事,調查將接近謎底?還是被牽走至歷史的密林?
小說家瀟湘神以精怪打造的懸疑故事、卻暗藏一則國族寓言;遍布海洋群島而變異的魔神仔,是穿越國界的存在,還是形構認同界線的深層恐懼意識?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NOFI (漫畫家)
曲辰 (大眾文學評論家)
朱宥勳(作家)
邱常婷(小說家)
張季雅(漫畫家)
盛浩偉(作家)
陳又津(小說家)
陳雪(作家)
楊双子(小說家)
溫宗翰(民俗亂彈執行編輯)
路那(推理評論家)
蝴蝶seba(作家)
作者簡介:
瀟湘神
小說家,著有小說《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金魅殺人魔術》、《都市傳說冒險團》,散文《殖民地之旅》,合著小說接龍《華麗島軼聞:鍵》、《筷:怪談競演奇物語》。關心文化資產、原住民、臺灣民俗等議題,現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參與《唯妖論》、《尋妖誌》、《臺灣妖怪學就醬》等創作計畫。
繪者簡介
潘家欣
詩人、視覺藝術工作者。曾出版《負子獸》、《失語獸》、《妖獸》等詩集;2018年主編詩選《媽媽+1:二十首絕望與希望的媽媽之歌》,2019年出版《藝術家的一日廚房》。插畫作品《暗夜的螃蟹》、《虎姑婆》、《童言放送局:日治時期臺灣童謠讀本(2)》等。
章節試閱
通過長長的縣道,就是海了。羅雪芬下了計程車,拖著行李走上斜坡,這條赤裸乾裂的水泥道路與海岸平行,漂流木被白沙覆蓋,些許奮勇的綠從潮間帶上方的石頭縫裡鑽出,整個海灘看來就像荒蕪的時間沙漏。在通往海灘的細小階梯旁,貼著意外溺死事件頻繁的告示,提醒遊客注意安全。
根據計程車上看到的景色,她覺得這個海港跟她記憶中沒太大差別,但也可能變了很多,只是她沒注意到。上次來是十幾年前的事,別說細節,連印象都很模糊,只記得瑣碎的片段,像在懸崖的岩石旁嬉鬧,或是豔陽下徒步走過巨大、白色的橋,橋旁曬了漁網跟琳瑯滿目的魚乾。
這些記憶真的太零碎了。沒辦法,當年她只是跟著社團出遊,領隊的同學帶她到哪裡,她就跟到哪。甚至在抵達目的地前,她還不知道這裡是南方澳;那時他們是來看南天宮的金媽祖,據說兩百多公斤重,價值上千萬,隨著國際金價波動,甚至可能上億,因此這尊金媽祖被當成重寶供奉著,廟裡到處是監視器。
時至今日,雪芬根本想不起那個金媽祖的大小跟樣貌,只記得當時感到「俗不可耐」——但這種想法只不過是年輕的傲慢。作為社會線記者,她已深知金媽祖不只是炫富,還關係到地方凝聚力。
記憶中,她對媽祖毫無興趣,只是兩手合十朝媽祖拜了拜,盡到禮數,就走出廟門。廟門正對著漁港,滿滿的船隻水洩不通,它們到底要怎麼出去?這麼想的時候,廟口的陳鑫垚指著右邊說:「我老家就在那。」
那是很突兀的話題,但另一個社員很感興趣,立刻追問:「這裡是你老家?那你應該很熟南方澳吧!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
雪芬也不記得鑫垚當時的回答,隱約記得他說「我老家背對著海,既是南方澳又不是南方澳,在南方澳的裡側」,因為這話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故弄玄虛,所以她還留著印象。好像也有人繼續追問,但話題很快就被拋下,畢竟南方澳不是終點,他們還急著趕路;不管鑫垚多熟悉南方澳,都不會臨時改變行程。
「是今天入住的羅小姐嗎?」
民宿老闆客氣地問,看來今天除她以外沒人入住了。雪芬說「是啊」,拿出證件,老闆檢查後領她到房間,笑著說:「這裡風景很好喔,能看到海景,天氣好的話特別漂亮。」
就像老闆說的,這間民宿位於海灣末端,雖然有點距離,但能看到最遠方的岬角;可惜房間裝潢有些俗豔,像要裝潢成大飯店,卻資金不足,只用了廉價品,結果沒了富麗堂皇,連海邊住家的情調也沒有,相當可惜。
從窗戶看到的這片海岸,有部分被房子擋住。沿著遠方岬角而來的海灣,本該蜿蜒如少女的微笑,這幾年來已是知名觀光景點,稱為情人灣;要是天氣好,想必能讓人打從心底溫暖起來吧?但今天只看到灰綠色的海,海浪匍匐席捲而來,轟轟如雷,無情又陰鬱。
「情人灣」聽來浪漫,卻沒改變海的本質;這片海繼承了臺灣東海岸的危險性格。往海的方向走,即使一開始很淺,也會在某處驟降;要是一時不察,很容易發生意外。美麗與死亡總是鄰近的——這麼說或許讓人想到激情的危險,紅與黑,愛與死,玫瑰與槍,但這片海存在的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羅雪芬向老闆道謝,關上門,放好為數不多的行李,把手機拿出來,打開錄音程式。
「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點,剛剛抵達南方澳民宿,這裡是陳鑫垚的故鄉,雖然沒什麼根據,但或許能找到他失蹤的線索。我已經試過好幾條線,全都碰了壁,要是這裡還找不到的話——」
說到這,她不知該如何繼續,按下暫停。
陳鑫垚是她大學社團認識的學弟,兩人很聊得來。雖然當時社團流動著濃郁的求偶氣氛,但他們沒發展出曖昧關係;羅雪芬對他的好感無關男女,而是他與周圍的距離感讓雪芬感到舒適。畢業一、兩年,雪芬還會找社團學弟妹出來吃飯,包括鑫垚。但隨著她越來越忙,這份關係便疏遠了。陳鑫垚不太用臉書,雪芬無從得知他的近況,本以為不會再見,但這位學弟的消息卻以預想外的形式再度傳進她耳中。
她坐在床上,緩緩躺下,放鬆成大字形。由於長期失眠,她一碰到床就想睡,但又做不到,因為她的身體與大腦總是保持毫無意義的緊繃,在墜入睡眠的瞬間驚醒。她試著整理迄今發生的事。
七天前,一班臺灣飛往日本的客機在關西國際機場降落,但旅客被禁止離開,直到兩個小時後才允許入境。這件怪事肇因於機長陳鑫垚在駕駛艙內神祕消失,副機長向塔臺報告後,為了確認陳鑫垚的行蹤,機場人員在飛機降落後立刻登機搜查,但找遍所有角落,都沒找到機長。
登機人數與離機人數不合會引發問題,這點雪芬很明白。譬如,可能有人偷渡。雖然透過客機大剌剌偷渡實在太蠢,更別說出入境有各種檢查,幾乎不可能,但既然知道少了人,還是機長,就不能裝成什麼都沒發生,因此機場高層立刻開會討論,乘客被關了兩個小時,直到機場高層跟官方有了共識,下達指令,乘客才被解放。從這件事涉及的層級看,兩小時已經算快。
既然發生了這等怪事,消息傳回國內,立刻就上了新聞,引起網民熱烈討論。不到短短一天,網路上竟出現一種陰謀論,認為陳鑫垚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機場人員登機搜查,其實是將他包庇起來,這才能解釋他怎麼在飛機上消失。
看見那些陰謀論,雪芬心裡有某種情緒安靜地燃燒。
且不論日本有沒有派間諜的必要,至少雪芬知道,陳鑫垚不可能是間諜。雖然十年沒見,但她記憶中的學弟絕對稱不上機靈,當年他總在社辦看書,明明社辦也放漫畫,他卻只看自己帶的小說。雪芬最常看到的是陳舜臣的《琉球之風》,早就被翻爛了;有時他也向雪芬推薦小說,用修長的手指指著泛黃書籍上的段落,一副文學青年的姿態。
當然,也不能說文學青年就不可能變成他國間諜,畢竟她也見過許多遭到命運惡意戲弄的人,但光是有可能,不表示她會相信。這或許能說是她對事物本質的洞見,有些本質連命運都無法侵犯;鑫垚是很纖細的,他敏感孤獨的靈魂,不可能成為間諜——但這樣的人,卻成為網路茶餘飯後的妄想材料,讓雪芬無法諒解。她明白,道聽塗說、加油添醋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無可奈何。但要是輕易向人性的輕浮妥協,身為記者的價值何在?
所以她主動向上級請纓,現在各大報紙都在報導陳鑫垚的事,但多半以日方聲明、我國政府聲明、航空公司聲明為主,關於陳鑫垚本人的調查與報告卻付之闕如;羅雪芬說,那些報導根本不想瞭解陳鑫垚,只想消費他,越是虛構,娛樂的成分就越強,這種東西稱不上報導,她能提供兼具真實與力量的東西。上級同意雪芬的請求,要她寫一篇以陳鑫垚為中心的報導,但要夠吸睛,若是陳腔濫調,可不會讓她刊登。
果然上級在乎的還是可量化的新聞點閱率吧?這點雪芬很清楚。而且她追求的也不是真實或力量那樣純粹的事物。網路上的閱聽大眾將速食情報囫圇吞下,發表的言論看似經過思考,其實不過是隨波逐流;既然如此,她的新聞即使不能擾動流向,也能吹皺一池春水。身為記者,她追求的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尊嚴——沒有人該被輕易侮辱。其實就算不是舊識,雪芬也會盡力維護,但過去這段因緣,讓她處在更接近真實的位置,這也是上級同意讓她自由發揮的資本。
但意外的是,即使雪芬自認大學時跟鑫垚關係不錯,調查起來卻處處碰壁,她甚至懷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認識鑫垚了;職場上,鑫垚的同事對他印象都很好,但要說與誰特別熟,卻也沒有。他與所有人都保持距離,從不談論私事,唯一的例外,就是曾提過有位交往多年的女友,但那位女友叫什麼、從事什麼職業,卻沒人知道,也沒人見過照片,甚至臉書上都沒有「穩定交往中」的資訊。
怎麼會這樣?即使社會評價不差,鑫垚在同事眼中竟是謎一般的人。
通過長長的縣道,就是海了。羅雪芬下了計程車,拖著行李走上斜坡,這條赤裸乾裂的水泥道路與海岸平行,漂流木被白沙覆蓋,些許奮勇的綠從潮間帶上方的石頭縫裡鑽出,整個海灘看來就像荒蕪的時間沙漏。在通往海灘的細小階梯旁,貼著意外溺死事件頻繁的告示,提醒遊客注意安全。
根據計程車上看到的景色,她覺得這個海港跟她記憶中沒太大差別,但也可能變了很多,只是她沒注意到。上次來是十幾年前的事,別說細節,連印象都很模糊,只記得瑣碎的片段,像在懸崖的岩石旁嬉鬧,或是豔陽下徒步走過巨大、白色的橋,橋旁曬了漁網跟琳瑯滿目的魚...
作者序
這篇小說雖以「魔神仔」為主題,卻很重視「巨人」意象。相對於矮矮小小的魔神仔,或許會讓讀者覺得有些突兀吧?其實這意象是有緣由的。我很喜歡石黑一雄《被埋葬的記憶》,這本小說的英文標題沒有記憶,而是「The Buried Giant」,這個「Giant」,可以被解讀成巨人。到底「Giant」是什麼呢?或許每個讀者都有不同的見解,但我則根據我的解讀,將「The Buried Giant」當成巨人,把其意象借用到這個故事中。
「南方澳真的有好多東西消失了。」
這是佑娥在故事中說過的話。在本作出版的現在,小說裡提到的那座大橋也已於二○一九年十月斷裂,又一項南方澳的事物消失了;從消失的猴猴族開始,不斷重複的喪失——這一切,都是「被牽走的巨人」。
講點題外話……不,或許也不算題外吧?畢竟與創作理想有關。總之,這篇小說是我對「後外地文學」的嘗試。
什麼是後外地文學?其實這是我瞎掰出來的創作理念——對,沒什麼了不起,只是硬要講得很酷炫而已;所謂的後外地文學,是對外地文學的回應,然而什麼是外地文學?最簡單的理解,大概就是殖民地文學吧。這是由日本時代文學研究者島田謹二提出的,他指出外地文學有三元素:
一、異國情調。
二、寫實主義。
三、鄉愁。
什麼是異國情調?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外地文學的預設作者,是那些在臺日人,他們生活在臺灣、已有臺灣生命經驗,這些人創作出來具臺灣風貌、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即是外地文學。對內地人來說,這種臺灣風景就相當於異國的幻夢吧!那是浪漫、美麗、充滿綺想的。雖然對在臺日人來說,他們可能只是書寫生命經驗,也就是寫實主義。總之,外地文學是殖民地文學,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它視作地方主義文學。
在當代的臺灣文學史研究上,外地文學飽受批判。
為什麼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異國情調」使臺灣成為被凝視的對象——相對於「內地」的「外地」,這難道不是被想像出來的嗎?舉個例子,說到原住民,許多漢人都有愛喝酒、開朗、體能很好之類的刻板印象,但這些想像也有可能不符現實。主張原住民就是那樣,當成事實在傳播,結果就是表面上在談原住民,原住民卻是缺席的……異國情調也是如此。異國必然是本國的凝視,換言之,即是他者;那以異國情調為前提書寫的臺灣,有沒有可能反而使真正的臺灣缺席呢?
這是外地文學的危險。明明在寫臺灣故事,卻讓臺灣失去主體,這在殖民體制之下更加嚴重。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有些好奇,既然外地文學如此惡名昭彰,為何後外地文學要回應它?
這是因為——「異國」確實是浪漫的。
有個審美上的弔詭。出國旅行時,宗教場所往往是重要的觀光景點,我們也著迷於那幻彩的裝飾、神祕的符號、介於神聖與恐怖間的怪異塑像;但對國內的傳統宗教場所與活動,主流意見卻傾向那是惡俗的。像是看不起廟會,覺得鞭炮聲太吵等等,但要是在國外被捲入熱鬧的大型宗教活動,再吵都能接受吧?
那畢竟是異國啊!
這種弔詭,可能肇因於我們太習慣這個環境,產生審美疲乏,以致無法將臺灣視為美的對象。對外國人來說,臺灣廟宇當然是美的——這就是異國情調;另一方面,身為都市人的我們也失去與傳統宗教的連結,高速的現代化改變了生活,傳統反而變得格格不入,我們不再抱持關心——與此同時,我們對歷史也幾乎不抱持關心了。
現在,我們或許正站在一個重要的時代交岔口。
我不想說怎麼做才是正確的。但毫無疑問,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會決定臺灣未來的樣貌;然而略過臺灣史,我們要怎麼界定臺灣呢?畢竟臺灣的族群多元而複雜,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歷史,或自己版本的歷史。如果不同族群要產生共同的臺灣想像,至少也要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但要是當代已喪失對歷史的關心,我們要如何談論臺灣?身為小說創作者,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我們怎麼引起讀者對臺灣史的興趣?
我的看法是浪漫化—─
把過去的臺灣當成異國來描寫,刻意賦予幻想怪奇,以呈現臺灣之美;如果我們能在通俗作品中燃起讀者對臺灣史的好奇,自然就有利於談論何謂臺灣,而後外地文學,就是我所提出的方法論。
參考外地文學三元素,我也提出後外地文學三元素,如下:
一、異國情調
二、實際地景
三、鄉愁
我所說的異國情調,與島田謹二的異國情調不同,是有意識地賦予幻想之美;而這份幻想之美,是奠基於時間帶來的距離感——正如外地文學的外地,是相較於中心的邊陲,如果沒有空間上的距離,異國便不存在。後外地文學則是透過時間上的距離形成異國,所謂時間上的距離,並非僅僅書寫過去某個時間點,而是意識到讀者是從當代的角度觀看該時間點。
以拙作〈潮靈夜話〉(收錄於《華麗島軼聞:鍵》,九歌出版)為例,在書寫一九三○年代的同時,特別著力於當時地景,就是企圖透過「已經不存在的風景」或「不可能的風景」來營造幻想性;現在仙洞旁邊的防波堤,已非昔貌,而社寮島上的千疊敷,也不可能有著如鏡般的海面。但這種不可思議的幻境,是奠基在讀者可能親臨基隆的仙洞與社寮島,這個當代實景與悠久時空的落差,允許幻想被覆蓋到實際地景上,真實的地理空間也成為通往歷史的門扉,那份歷史是美麗、綺想的、宛如異國的歷史。
這也是我將實際地景視為後外地文學重要元素的原因。實際地景具備身體經驗的基礎,得以成為有力的想像參照點。又如〈鱷魚之夢〉(收錄於《筷:怪談競演奇物語》,獨步出版),故事發生在被水庫淹沒的學校與村莊,但當主角抵達沉入水底的廢校時,那座學校居然完好無缺——這是不可能的場景,因為該學校已成廢墟。如果是虛構的地景,這一幕其實是「可能」的;但正是建立在實際地景上,才因不可能而夢幻。此一夢幻之所以成立,正是讀者身處的時空,成為視點的中心。
外地文學以內地為中心,後外地文學則是以當代為中心,預設中心的存在,才使異國幻想成為可能。
至於鄉愁——這是書寫後外地文學的重要動機。在現代,臺灣人對臺灣還沒有共同的想像。就算有,也很容易成為剝削式的想像。但對臺灣人來說,那個尚未出現的臺灣想像,才是理想的故鄉,不是嗎?期待這樣一個想像出現,是我書寫後外地文學的殷殷盼望。
讀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質疑,這套理論真的有必要回應外地文學嗎?說到底,此一理論的主張,不過就是根據實際地景書寫幻想,引發讀者對地方史的興趣,作為討論「何謂臺灣」的資本。即使不回應外地文學,此主張依然成立。但我是這麼想的。有意識地編造幻想——難道沒有危險嗎?畢竟歷史是無法自我主張、自我維護的。在對歷史毫無敬意的凝視下,幻想反而會扭曲歷史。選擇回應惡名昭彰的外地文學,正是一種自我提醒;在臺灣的殖民帳還沒算乾淨,甚至對臺灣想像尚未形成共識的現在,異國情調是需要格外謹慎的。
大眾小說能有助於認識「臺灣性」?
坦白說,我自己也覺得太樂觀。但要說這是徹底徒勞無功的,倒也不盡然;就算我提出的理論不堪一擊,只要我們有著共同的鄉愁,那後外地文學就像是拋磚引玉,我期待著那塊美玉能發出懾人的光輝。
在歸鄉之前,我會繼續寫作下去。
最後請容我致謝。小說中的沖繩史觀,受限於我自身知識,雖有友人宥任協助,仍有未能全面釐清之處,還請見諒;此外,由於臺語並非我的母語,本文之臺語文正字,皆由小鶴協助翻譯而成,在此感謝以上二位。也感謝我童年舊友盧博士非自願的友情客串。
這篇小說雖以「魔神仔」為主題,卻很重視「巨人」意象。相對於矮矮小小的魔神仔,或許會讓讀者覺得有些突兀吧?其實這意象是有緣由的。我很喜歡石黑一雄《被埋葬的記憶》,這本小說的英文標題沒有記憶,而是「The Buried Giant」,這個「Giant」,可以被解讀成巨人。到底「Giant」是什麼呢?或許每個讀者都有不同的見解,但我則根據我的解讀,將「The Buried Giant」當成巨人,把其意象借用到這個故事中。
「南方澳真的有好多東西消失了。」
這是佑娥在故事中說過的話。在本作出版的現在,小說裡提到的那座大橋也已於二○一九年十月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