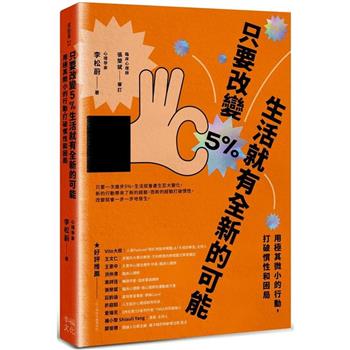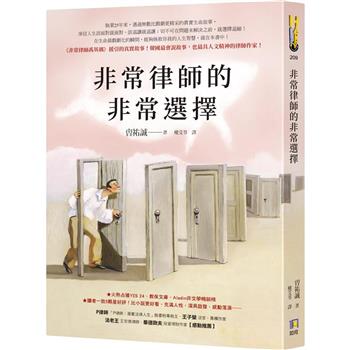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周年數位簽名紀念版)的圖書 |
 |
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周年紀念版,首度收入作者前言及後記) 作者:蕭麗紅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7-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5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450 |
小說 |
$ 458 |
現代小說 |
$ 458 |
小說 |
$ 458 |
現代散文 |
$ 458 |
文學作品 |
$ 458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58 |
Books |
$ 458 |
Books |
$ 458 |
Books |
$ 510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千江有水千江月(出版40周年數位簽名紀念版)
一封信牽起嘉義與臺北的魚雁往返
一闋詞道盡了有情故鄉的萬水千江
小說家蕭麗紅經典代表作《千江有水千江月》
出版四十周年紀念新版
故事以布袋的蕭姓大家族為中心,敘述傳統大家庭的習俗和人情瑣碎,並探討生死、親情、愛情的衝突與矛盾。生於世代養殖漁業維生的大家庭,主角貞觀巧遇表哥大信,開始了一場若有似無的愛戀。這段戀情直到貞觀上臺北工作,大信到金門當兵,兩人間的情愫也因誤解而產生令人唏噓的變化。在蕭麗紅的內容敘述中,充滿了臺灣民俗的瑰麗與趣味,而貞觀與大信古典又含蓄的戀情,為臺灣逐漸失去的純然戀歌,悠悠地低吟了一遍……
作者簡介
作者:蕭麗紅
1950年生,嘉義布袋鎮人。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獲聯合報長篇小說獎,並入選文建會中書西譯計畫。代表作有《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春夢》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