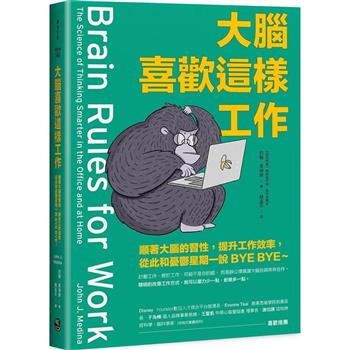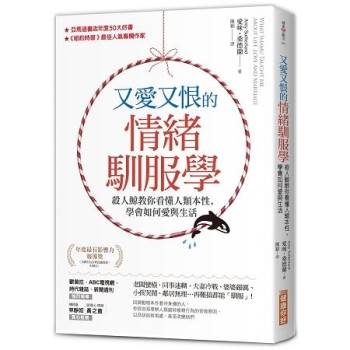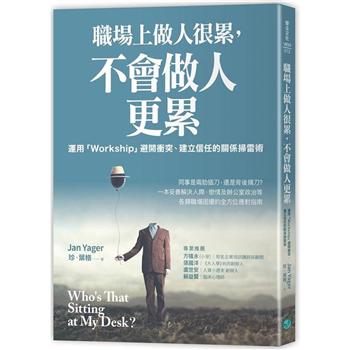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大不列顛兩千年的圖書 |
 |
大不列顛兩千年: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 作者:羅伊.史壯 / 譯者:陳建元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20 |
二手中文書 |
$ 498 |
西方歷史 |
$ 498 |
史地 |
$ 498 |
Books |
$ 536 |
旅遊 |
$ 554 |
中文書 |
電子書 |
$ 630 |
世界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大不列顛兩千年》是為新一代讀者所寫的全新英國史,豐富有趣、通俗易懂、權威且全面。本書從成為羅馬行省前,只有原住民居住的不列顛島開始講起,直到2016年的脫歐,透過七十幾個明快簡約的章節,精彩且均衡地描述英國史上各個時代,用引人入勝的敘述貫穿各時期,介紹英國兩千多年歷史中輝煌與悲鳴、起伏與轉機,並述及英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影響。
書中論及許多人熟悉的百年戰爭、都鐸王朝、莎士比亞與維多利亞女王,但全書的主題不只戰爭軍事及王權更迭,還包括經濟發展、宗教衍化、人民階級的異動、女性歷史、地景景觀及建築變化、娛樂走向、農業進程等等,讓讀者得以全面理解橫向與縱向的時空背景。
作者羅伊‧史壯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作家兼園藝家,不僅著作等身、多才多藝,更曾任英國國家肖像館和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館長,在英國文化圈中備受推崇,而長期於博物館工作的經驗,也讓他嫻熟於將看似嚴肅或複雜的議題,透過巧妙的轉化與解釋,傳達給非專業的觀眾和讀者。這項才能在本書中展露無遺,羅伊‧史壯吸收大量過往研究與各家說法,綜合出屬於個人的一家之言,讓這本書既有學術的嚴謹,又充滿著知性的趣味。
史壯在書中特別留心人民生活的面向,透過關於普羅大眾的日常,反映出英國人如何形成自我認同感,同時重視文化和思想與政治潮流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在書中多次強調,「不列顛是一座島嶼,對於要了解它的歷史而言,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都重要。」被海洋包圍的特性,創造了英國人獨特的民族性格,讓他們既追求遺世獨立、享受島嶼的庇護,又不斷想要往外冒險,探索未知的世界。對於同樣生活於群島國度的臺灣讀者,大不列顛兩千年的經驗是否也能帶來借鑑與啟發?
史壯的激情、熱情和廣博的知識,讓他成為這一趟歷史旅程的最佳導遊。了解英國歷史,對於理解世界史及全球局勢至關重要。任何好奇英國歷史,或是關心國家認同和國家前景的人,都不能錯過這本書。
博雅推薦
▍專文導讀
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國合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盧省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專業推薦
汪采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各家書評
英國歷史對於理解世界歷史至關重要,在所有關於這個主題的書籍中,羅伊.史壯的書是清晰易懂的。他將一群傑出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對每一個人物都進行了尖銳而生動的觀察。史壯把對國王和戰爭的討論穿插在對作家、作曲家、科學家和其他意識形態開拓者的論述中,他將這些不同的線索交織於宛如一大張掛毯的整體故事中。
——《基督科學箴言報》
每一位學習英國歷史的學生都會喜歡這個故事,它通俗易懂,引人入勝,深刻洞察了單獨事件所造成的深刻後果。
——《柯克斯評論》
不管是研究、組織或是呈現手法都令人印象深刻。無論是用於社區、學院、大學圖書館英國史收藏以及課堂補充閱讀材料,都將是非凡且具有持久價值的新書。
——《美國中西部書評》
典範之作。
——阿曼達.福爾曼(Amanda Foreman),《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冠軍作家
登峰造極的歷史書。
——安東尼亞.弗雷澤(Antonia Fraser),《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冠軍作家
經典的通俗史。
——安德魯.羅伯茲(Andrew Roberts),《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冠軍作家
構思巧妙、趣味盎然的一本書。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當代經典著作。
——A. N. 威爾森(A. N. Wilson),《倫敦標準晚報》
作者/譯者簡介
作者:羅伊‧史壯(Roy Strong)
歷史學家、作家和園藝家,曾任英國國家肖像館和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館長。著作約四十餘本,涉及各式各樣的主題。於1982因為對藝術的貢獻而被封為爵士,於2016年因為對英國文化發展的貢獻而被封為「榮譽勛爵」。居住於赫里福德郡,在此寫作與從事園藝。近年出版了三卷日記:《輝煌與苦難1967-1987)、《場景與幻影1988-2003》和《象徵與預兆2004-2015》。
譯者:陳建元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系博士。譯有《羅馬的崛起》、《聖殿騎士團》、《想想歷史》、《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合譯)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