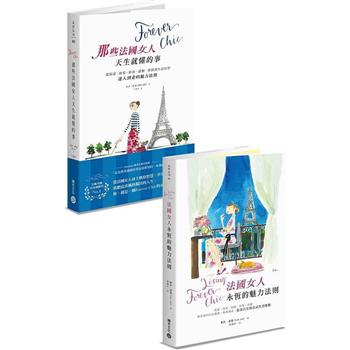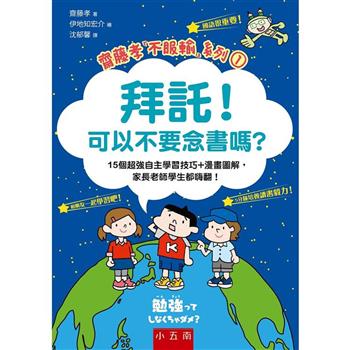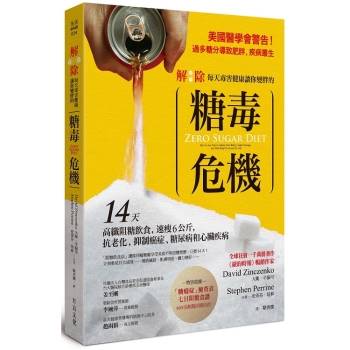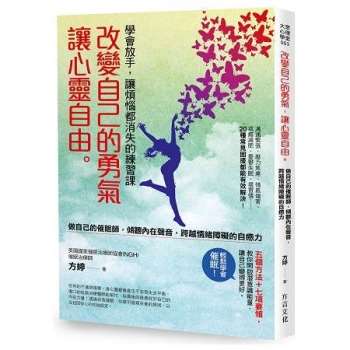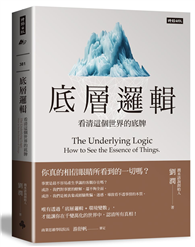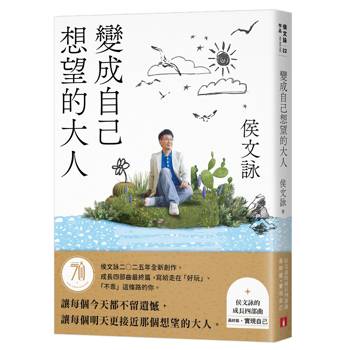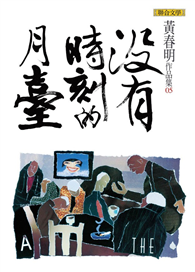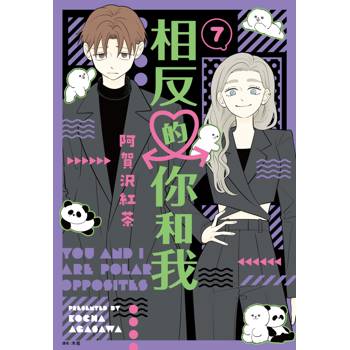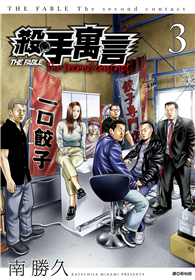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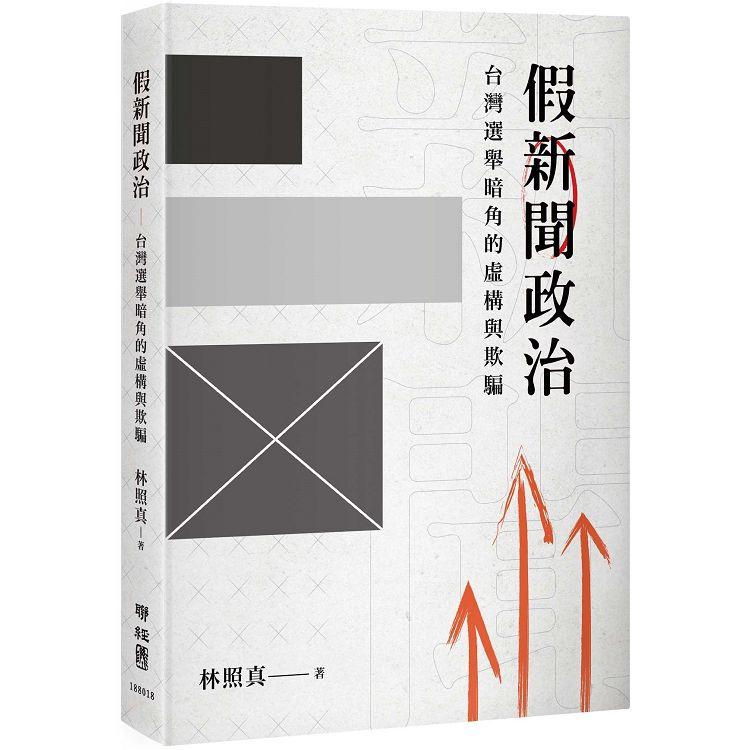 |
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林照真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2-2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58 |
新聞學 |
$ 458 |
中文書 |
$ 458 |
政治 |
$ 458 |
社會人文 |
$ 458 |
Books |
$ 458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93 |
新聞傳播 |
電子書 |
$ 580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假新聞玩弄新聞、詭辯真假,
在社群媒體上利用平台科技進行政治動員,
已使假新聞成為選舉與公投時的政治武器。
2016年先後發生英國公投、美國總統大選令人震驚意外的投票結果後,假新聞已成為全球政治傳播的重要課題。本書針對國內2018年、2020年兩次選舉進行研究,試圖探討假新聞對國內選舉的影響。
林照真認為,「假新聞政治」說明假新聞為政治化名詞,已經成為民主社會的難題。臺灣更特別的現象是,混淆的國家認同製造政治對立,提供假新聞得以擴大政治操弄的舞台。源自中國大陸的陰謀論與宣傳,更隨時企圖崩解臺灣的社會秩序與民主價值。
全書共十四章。除全面梳理假新聞相關文獻外,另分別以傳播科技、政治對抗、平台產業等不同視角,聚焦分析國內外的假新聞現象。
作者簡介
作者:林照真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取得世新大學傳播所博士學位前,曾在媒體工作二十年,為資深政治記者。主跑社會運動、西藏議題,負責進行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導。著有《覆面部隊:白團》、《喇嘛殺人》、《最後的達賴喇嘛》、《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等報導專書。進入學界的研究領域包括:收視率研究、災難研究、新媒體研究、媒體轉型研究、假新聞研究等,著有《收視率新聞學》、《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等學術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