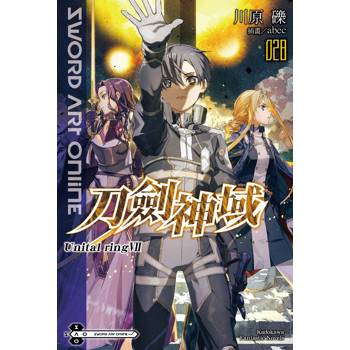後記
在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我母親會在夏天帶我和兄弟姊妹到大英博物館。那裡雖有各門各類的文化珍寶可供探索,但我們一家人一定會特地去看貝南青銅,當時是陳列在主階梯一個大平臺上。我母親之所以這麼做,是想要確保她擁有一半奈及利亞血統的混血兒女能接觸到來自父母雙方背景的藝術與文化。在那裡,在十六與十七世紀貝南的藝術傑作之前,我們感覺到與非洲的先祖血脈相連;這些飾板曾妝點歐巴皇宮,而我們與製作飾板的匠人有如同族般親密。貝南藝術的裱框照片掛在我們福利住宅的牆上,我們的非洲祖先與歐洲祖先都一樣曾創造出偉大藝術、形成有深度的文明,這是我從有記憶以來就知道的事。
我對歐洲藝術與文化的的欣賞與喜愛主要不是來自參訪博物館與畫廊,而是從另一個媒介灌注給我:電視。我個人頓悟的一刻是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那天我母親要我看BBC二臺一部紀錄片《畫家與模特兒》(Artists and Models),我在六十分鐘內飽覽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雅各─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藝術作品與精采人生,令我沉迷不已,讓我從此帶著新入教者的狂熱情懷開始去附近圖書館借書。因為《畫家與模特兒》內容與歷史和藝術都有關,兩者都使我燃起熱情,我對二次大戰那年少無知的著迷也就因此消退。
兩年後,我靠著週末與學校假日在商店打工存夠錢,踏上環遊歐洲的旅途。一路上除了在沙灘上曬太陽和拜訪朋友以外,我每到一座城市就去參觀當地大型美術館。十八歲的我來到羅浮宮,BBC節目裡出現過的畫作此時就在我眼前。一位當代作家在《畫家與模特兒》裡說雅各─路易.大衛的畫中氣氛非常冷峻,你幾乎能感覺到寒風從他的畫布裡吹來;我還記得當時站在大衛的《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前面,想要去體會那種森嚴冷氣迎面襲來的感受。對我來說,讓藝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這是何等新而令人興奮的想法;因為我母親苦心讓我接受啟發,因此我才能獲得這般美好的禮物。我先去巴黎,然後去阿姆斯特丹,去了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在那裡我頭一回看到林布蘭(Rembrandt)、維梅爾(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和其他荷蘭大師的作品。接下來我到馬德里,去看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我在那裡接觸到提香(Titian)、艾爾.葛雷科(El Greco)、畢卡索(Picasso)、迪亞哥.維拉斯貴茲(Diego Velázquez)和耶羅尼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我在普拉多博物館的紀念品販賣部買了波希《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複製畫,這是當時的我幾乎買不起的東西,也是我珍藏多年的寶物,我每換一個宿舍房間都要把它掛在牆上。
三十幾年前,一點星星之火通過我家那臺租來的四方形電視機厚螢幕觸及我,我的人生自此不同,雖然當時我並不知情。在我出生前一年,有一個電視節目立下傳統,賦予這傳統形狀與動能,而我小時所看的紀錄片節目就是這傳統的一部分。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的《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系列共有十三集,這節目在英國與美國都是電視史傳奇。它擁有數百萬觀眾,其中許多人因為這節目而改變一生,就像後來《畫家與模特兒》對我的影響一樣。在這系列開始播出的兩年前,彩色電視才剛進入英國市場,而色彩規格足以呈現這節目畫面之美的彩色電視就更少見。買得起這種電視的家庭會舉辦「《文明的軌跡》派對」,邀請原本只能用黑白兩色來欣賞歐洲藝術奇觀的親朋好友共聚同樂。連續十三週,在肯尼斯.克拉克的導覽之下,觀眾被帶往一百一十七個不同地點。節目播出的三個月內,畫廊與博物館的負責人都表示訪客數量有所增加。後來,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法國、義大利與其它地方的畫廊參觀,親眼見識肯尼斯.克拉克帶進他們客廳的那些藝術與建築經典,有報導說那一季的旅客人數因此大增。
本書是一部電視節目的姊妹作,該節目是從《文明的軌跡》獲得靈感。現在距離肯尼斯.克拉克這個系列播出時間已經將近五十年,但它依舊家喻戶曉,且理當如此。不過,《文明的軌跡》出名之處不只是因為它對觀眾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還因為它的觀點十分狹隘。它所說的故事只包括歐洲藝術與文化,其中又以義大利和法國為主,節目拍攝地點僅涵蓋十一個國家,日耳曼地區在敘事中扮演配角,英國則只有客串演出。這系列裡完全看不到西班牙藝術,此事在馬德里還引起公眾不滿。我們當然不應只憑這部電視節目就給肯尼斯.克拉克下定論,他在其他擴充著作中所展現的世界觀比節目裡要廣闊許多,比方說他終生都對日本藝術情有獨鍾。然而,就算在書裡,克拉克眼中的藝術依然是個男性主宰的天下,現代觀眾很快就能發現《文明的軌跡》系列缺乏對女性藝術家的介紹。
克拉克曾應邀參與一場BBC會議,會中用了「文明」這個詞,他就是在當時出現參與節目製作的想法。文明一詞激起克拉克的想像力、啟發他決定成為這項計劃的主持人與作者,這詞本身的作用超越其他所有動機。就在節目第一集第一景,克拉克有段著名的臺詞是以「文明」的定義做文章,他站在巴黎聖母院前面打趣的問說「什麼是文明?我不知道……不過如果我看到它,我就會認出這是文明。」
對於世界其他各種文明,或這些文明的鑄造者所具的文化想像,克拉克毫不遲疑加以批判。在與節目成套的書中,他寫了一段話,這段話並未出現在節目播出時的臺詞裡;克拉克這段話是將一面屬於布倫斯柏里(Bloomsbury)藝術家與藝評家羅傑.弗萊(Roger Fry)所有的非洲面具以及《觀景殿的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雕像頭部相比較,他寫道:
無論它身為藝術品的價值是什麼,我認為它(觀景殿的阿波羅)比起面具所蘊含的是更高的文明發展程度,此事毫無疑義。這兩樣東西都象徵著「靈」,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信使,也就是來自一個我們想像中的世界。在尼格羅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恐懼的黑暗世界,人們隨時都會因為觸犯微不足道的禁忌而遭那個世界施以嚴懲。在希臘人的想像裡,那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光明世界,裡面的神都像人一樣,只是比人更加美麗,祂們下凡來教導人們理性與和諧的法則。
我們可以說,克拉克「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用詞是一個生於愛德華時代的人會隨口說出的話,事情或許確是如此。然而,許多年前的夏天,我母親之所以帶她擁有一半非洲血統的孩子們來與貝南青銅面對面,正是因為她知道「文明」一詞是如何被用來貶抑她孩子父親的先祖。正是因為我出生長大時,「尼格羅人的想像」這種概念在英國仍被大部分人認為是原始且缺乏內涵(相較於「歐洲人的想像」),因此我們從孩提時代就被帶去參觀大英博物館、被要求接觸非洲作家的著作,讓我們穿戴上抵抗這種思想的盔甲。
我認為文化的接觸、互動與衝突是過去五百年歷史的關鍵特質;在這本小書以及成套的兩集影片裡,我試圖探索藝術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這樣做並非是要反駁肯尼斯.克拉克的觀點,這位極具重要性的文化人物是我尊崇的對象;我的目的是要提醒我自己與那些可能有興趣的人,全人類的想像都是一致的,而一切藝術都是這想像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