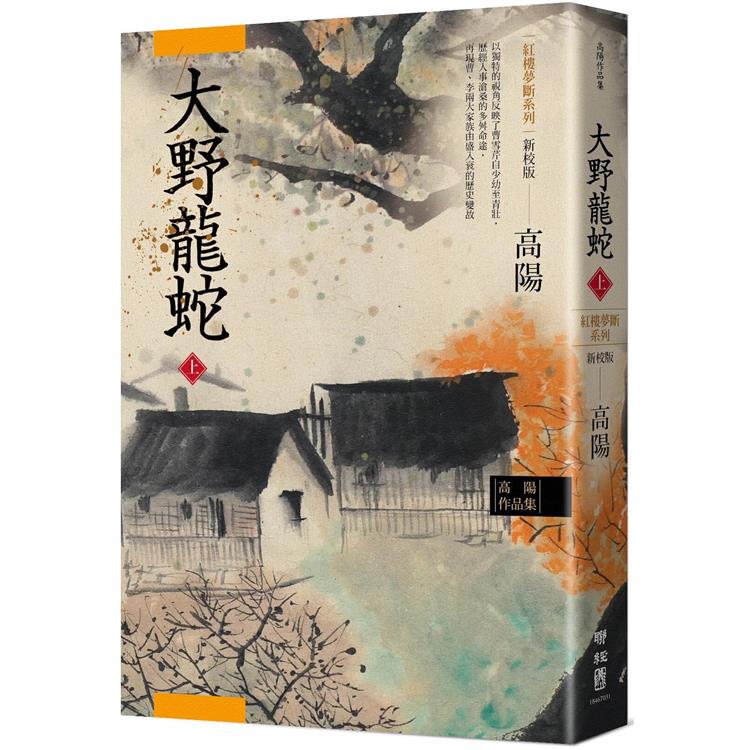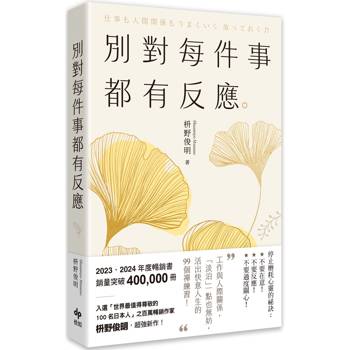華文世界歷史小說第一人高陽,又一代表作「紅樓夢斷系列」。
《紅樓夢》是曹雪芹寫賈寶玉,「紅樓夢斷系列」則是高陽寫曹雪芹的故事。
夢斷紅樓說四陵,疑真疑幻不分明,
倘能搦筆娛人意,老眼獨挑午夜燈。
作為紅學研究名家、又是極熟習清代掌故的歷史小說家,高陽的「紅樓夢斷系列」,自信其對曹雪芹的身世、時代背景及其家族可能遭遇有深度了解。在如此條件下,高陽試揣摩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所面對艱難曲折之過程。除描寫清初江寧織造曹家與蘇州織造李家的盛衰,更寫盡曹、李兩家由朱門繡戶、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沒歸京的榮辱起伏。間有宮廷祕聞、官宦醜惡,亦有世家紈絝之不知民苦、耽溺歡愛。綜觀改朝換代之物事更迭,細繪人情冷暖之無常唏噓。
《大野龍蛇》為「紅樓夢斷系列」第七部,敘述「龍」、「蛇」這兩年發生於朝廷的大事。乾隆十三年,皇后離奇死亡,曹家捲入乾隆初年的宮闈皇位之爭。繼抄家之禍後,曹家再次陷入困境,家道中落,繁華落盡,經歷由盛而衰的變遷危機,更飽嚐世態之炎涼。
對一個文藝工作者來說,曹雪芹如何創造了賈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賈寶玉這問題,更來得有興趣。「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此中艱難曲折的過程,莫非不值得寫一篇小說?這是我想寫「紅樓夢斷」的動機。
──高陽
高陽寢饋文史、浸淫至深,更有千萬字以上的小說創作經驗,有其獨到處。
讀高陽小說,層層婉轉、淋漓盡致、擘肌析理、勝義紛呈,令人目不暇給。
作者簡介:
高陽(1922-1992)
本名許晏駢,譜名儒鴻,字雁冰,浙江杭州人,出身錢塘望族,筆名「高陽」取自許氏郡望。抗日戰爭後考入杭州筧橋空軍軍官學校,並於1949年隨校遷至台灣。1959年卸軍職,投身報界,曾任《中華日報》總主筆。1962年發表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李娃》,一鳴驚人,此後著述不輟,一生創作包括九十餘部歷史小說和隨筆,逾二千五百萬字,作品對於清代歷史有獨特研究深度,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亦成一家之言。代表作有「胡雪巖系列」、《慈禧全傳》、《紅樓夢斷》等,被譽為華文世界首席歷史小說家,讀者遍及全球華人世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皇后在德州投河了!」
耳語很快地在京裡傳了開來,但妄言妄聽,大都將信將疑,只有極少數的人,包括病中的平郡王福彭,相信流言不假。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皇帝率皇后奉聖母皇太后啟鑾東巡。
這是早在上年六月初一就頒了上諭的,定於來年正月巡幸東魯,親奠孔林;復奉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宜崇報饗,一切典禮由大學士會同禮部,稽考舊章,詳議具奏。
皇帝祭孔的禮節,有康熙二十三年的成規,可資遵循;太后上泰山去燒香,無例可援,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禮部尚書王安國去請教保和殿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他很隨便地說:「我們現在的這位太后,越老越健旺,不過想逛逛泰山而已。拈香的儀節,無可考察,亦不必考察,一句話:踵事增華,成就皇上的孝思。」
張廷玉的話涉譏諷,但也是實話;六、七年來,年年由皇帝陪侍出遊,遠至蒙古、盛京、山西,近則東陵、西陵,至於熱河不在話下,常是六、七月間啟鑾,過了八月十三皇帝的生日方始回京。這一次也是太后想到泰山去燒香,皇帝才有了以祭孔為名的打算。
不想到了十月裡,太后聖躬違和,皇帝宿在慈寧宮每日三次視藥;皇后更是衣不解帶地侍奉,一個多月的仔細調養,太后是復元了,不道皇后遭遇了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皇七子永琮夭折了。
皇后的第一個兒子,皇二子永璉夭逝於乾隆三年;八年之後,也就是乾隆十一年的四月,皇后才生了她的第二個兒子,肥頭大耳,茁壯可愛,皇帝命名為永琮;鄭康成注《周禮》說:「琮之言宗也;八方所宗。」皇帝已暗示著將來會傳位給他的這個嫡出之子。
不想在世只得二十個月,便因出痘而不治,皇后哭得死去活來;她的傷心之處不止一端,自顧年已三十有六,難望再能生育,此其一;出痘是小兒必經的一關,最要緊的是看護周到,但皇后因侍奉太后湯藥之故,不免疏於照料,可說永琮是為太后而犧牲了;再有一樁,便更使皇后鬱結難宣了。不知甚麼時候,皇帝與一直在陪伴太后的「舅嫂」──傅太太勾搭上手,而且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福康安,這年六歲,一直養在太后宮中。
這些悲痛在心頭烙出深刻的痕跡,不是短短的日子中能夠彌補的,儘管東巡啟鑾的日子,由正月延到二月,但皇后意興闌珊,任憑如何鼓舞,始終打不起精神,對太后的晨昏定省,更視為莫大的苦事,因為看到福康安就會想到永璉與永琮,尤其是太后、皇帝、福康安三代人在一起的那幅「天倫樂」的畫面,更讓她心如刀絞,簡直要發狂,但是為了維持皇后的尊嚴,還有更重要的「母儀天下」的典範,她不能不咬緊牙關克制著自己。
儘管如此,皇帝還是不諒解,因為她從永琮夭折以後,就從沒有笑臉。
一路上不斷在齟齬。從曲阜到泰安,太后登上五嶽之首泰山,心情舒暢地遍歷道觀佛閣,皇帝也憑弔了孔子「小天下處」、秦始皇避雨的「五大夫松」、宋真宗封禪的遺址,然後下山駐蹕濟南,皇帝的興致極好,奉太后遊賞趵突泉,還閱了兵,又單獨祭了舜廟,並巡閱濟南府城,六月十一日到了與直隸接壤之處的德州。
德州是水陸要衝的一個大碼頭,來時捨舟登陸;歸時下輿乘舟,寬敞華麗的「龍船」,是名副其實的行宮。這天晚上二更時分,變起不測,說皇后失足落水了。兩岸「營盤」上護蹕的禁軍,都點起了燈籠,照耀得亮如白晝,但河水的浮光之下,一片深黑,會水的侍衛與太監,紛紛跳入河中,撈救了好半天,才把皇后找到,自然早就沒氣了。
第二天發布上諭「皇后同朕奉皇太后東巡,諸禮已畢,忽在濟南微感寒疾,將息數天,已覺漸癒,誠恐久駐勞眾,重厪聖母之念,勸朕回鑾。朕亦以膚疴已痊,途次亦可將息,因命車駕回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變故,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來,誠敬皇考,孝奉聖母,事朕盡禮,待下極仁,此亦宮中府中所盡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內佐,痛何忍言?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況皇后隨朕事聖母膝下,仙逝於此,亦所愉快。一應典禮,至京舉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這一來,天下之人無不驚疑,照皇后在濟南感寒致疾看來,「忽遭變故」應該是病歿,但既稱「膚疴」,何以忽成絕症?且扈從的御醫極多,曾否召來請脈;那怕是中風之類的暴症,亦斷無不作急救之理。然則皇后的死因成謎了。
謎底很快地便能揭曉,那天晚上,皇帝在皇后的船上,大吵了一架;皇帝揮拳揍了皇后,氣沖沖回到自己的船上,皇后一個想不開,拉開窗子投水自盡。
當夜,在內務府造辦處當差的曹震,奉禮部尚書兼內務府大臣海望之命,與同事三人,星夜急馳到京,預備迎靈;其間抽空去見了平郡王,細陳這番變故的由來。
「那麼,皇上呢?是不是已經回鑾了?」平郡王問。
「皇帝還在德州;大概會由陸路回京。」
「太后亦走陸路?」
「不!皇上派莊親王跟和親王,護送太后,仍舊由運河到通州,再轉陸路回京。」
「喔!」平郡王想了一下問:「皇上是怎麼個態度?」
「有、有點抬不起頭來的樣子。」
「當然囉,鬧這麼一個笑話,真正騰笑天下。不過──。」平郡王忽然嚥住了,落入沉思之中。
曹震不敢打攪,息了好一會,正想動問,倘無別話,便待告退時,平郡王忽又開口了。
「傅春和呢?」
「春和」是皇后的胞兄,戶部尚書傅恆的號;曹震答說:「王爺知道的,傅大人是出了名的忠厚,除了大哭一場以外,我看也不敢說甚麼。」
「嗯!」平郡王說:「他雖不敢說甚麼,皇上一定會有表示。」
「是。」
「你見著方問亭了沒有?」
曹震當然見到了方觀承,他從乾隆七年外放直隸清河道後,官符如火,第二年就升了臬司;乾隆九年命他隨大學士訥親勘察浙江海塘及山東、江南河道回來,調升為藩司;前年山東巡撫出缺,特為隔省調他去署理,直到去年方始回任。這一回是以直隸藩司的身分,出境迎駕,早就到了德州;扈從的曹震屬於先遣人員,因而得與方觀承敘舊,曾一再提起平郡王,問他的身子如何?
聽得這些話,平郡王又安慰,又憂傷;只要有人談到他的病痛,他就會記起蘇州名醫葉天士去年進京時,為他所開的脈案:「左手之部,絃大而堅,知為腎臟養傷,壯火食氣之候。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脈訣他不懂,「顛仆不仁」即是中風,卻很明白。又聽說剛成名的葉天士,有能斷人生死之譽。因此一想起便揪心。
「通聲!」平郡王說道:「你倒替我訪一訪一塵子,看他在那裡?」
「在濟南。」
「你怎麼知道?」
「這一回扈駕經過濟南,看他在歷下亭設硯。」曹震答說:「本想去請他算算流年,到底抽不出空。」
「你還得想法子抽個空,拿我的八字再去問一問他看,這兩年的運氣如何?」
「是。」曹震答說:「等皇上回京,辦了皇后的喪事,一到能請假的時候,我馬上就去。」
皇帝是三月十七日,親自護送大行皇后的梓宮到京的。梓宮奉安在西六宮的長春宮,上諭派履親王允祹總理喪事。首先是議禮。皇后之崩,除京師以外,各省皆不治喪;這是因為康熙十三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難產,皇子胤礽的小命雖保住了,皇后卻崩逝了。其時正逢三藩之亂,平西王吳三桂於上年十二月起兵造反;接著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孫延齡、靖南王耿精忠,在廣西、福建舉兵響應。康熙為了決心削藩,將吳三桂的兒子、尚太宗幼女恪純長公主的吳應熊,以及長公主所生的兒子吳世霖,明正典刑,以示絕不妥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外省舉哀成服,容易誤會為皇帝駕崩;民心士氣一動搖,危亡立見,所以哀詔不頒外省,自然亦就不必治喪。
但「皇叔」履親王承皇帝意旨,主張恢復順治年間的舊典,王公大臣自然毫無異言,上諭中不提當年何以不為皇后治喪的原因,只引《周禮》說「為王后服衰」,內外臣無異;《明會典》亦規定,皇后喪儀,「外省官吏軍民,服制與京師同」,如今「大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應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服制上規定,文武官員百日之內,不准薙髮。
「大家會不會聽呢?」皇帝這樣發問。
「上諭孰敢不遵?」刑部尚書阿克敦回奏。
「不遵又如何?」
「不遵即是抗旨,有《大清律》在。」
「好!」皇帝點點頭,當著群臣不欲多問;退朝後命養心殿的太監,傳旨「叫起」。
原來皇帝自無心中闖下這場大禍,自覺在眾目睽睽之下,逼得皇后不能不投河以求解脫,實在是莫大之辱;因而又自顧身世,彷彿生下來就是一個讓人看笑話、抬不起頭來的人,即使做了皇帝,依然如此。
父死子繼,他的皇位其實來得很正,可是大家總覺得他之得位,都由巧取豪奪,沒有大家幫襯,他永遠做不了皇帝。
由近及遠,一個個想過去,第一個是胞弟和親王弘晝,言語之間,直來直去,毫無人臣之禮。
第二個是十年前薨逝的「十七叔」果親王允禮,經常跟他抬槓,最後只好請他節勞,不必進宮辦事。
第三個是理親王弘晳,想到乾隆四年那重公案,一直遺恨不釋。
第四個是他的表叔訥親,自恃功高,時常嚕囌,漸漸有跋扈不臣之意,只有常常派他出差;如今是在浙江查案,覆命以後,還得派他一個甚麼差使,讓他走得遠遠地圖個耳根清淨。
第五個是張廷玉。想起他來,皇帝心事重重,他們父子間的祕密,完全在他肚子裡,這是個必須置於耳目所及,以便監視的人,但是他卻要告老還鄉了!一回到桐城,且不說與野老閒話,會在不經意之間洩漏若干不足為外人道的宮廷實況,更怕他會將當年如何承旨撰寫《大義覺迷錄》等等上諭的經過記下來,而且「過則歸君」,以求自解於後世。
如果他只是有這樣意向,而未明言,可以不理;那知就在他東巡啟駕之前,居然面奏陳情,甚至泫然欲涕;幸而皇帝早就想過這件事,當下很從容地答覆他說:「你受兩朝厚恩,而且先帝遺命,將來要配享太廟;豈有生死都要追隨先帝左右的重臣,歸田終老之理?」
「宋明配享之臣,亦有請退而獲准的,像宋朝的韓世忠、明朝的劉基就是。」
「韓世忠、劉基都是去世以後,優詔准予配享;不像你,生前就受先帝的特恩。」
「不過臣年已七十有九。」張廷玉說:「七十懸車,古之通義。」
「不然。」皇帝提出反駁:「如果七十懸車不出,何以又有八十杖朝?」
皇帝反覆開導,勸慰百端,最後並准他解除兼管吏部事務;張廷玉始終怏怏,遲早還有第二次的陳情,那時又如何應付。
皇帝越想越煩,終於突破平日意念的樊籬,深悔一開頭像民間的童養媳似地,總覺得自己該受委屈,根本就錯了。
「我為甚麼要受委屈?」他喃喃地自語:「我是皇上,我是皇上。聖祖是漢文帝,阿瑪是漢景帝,我,我應該是漢武帝!」他突然頓一頓足,昂起頭來,大聲說道:「乾綱獨振!」
「阿克敦,你是刑部尚書,我倒問你,行法以何者為重?」
阿克敦毫不遲疑地答說:「持平。」
「既不失出,亦不失入,謂之持平。是不是?」
「是。」
「我一直屈己從人。」皇帝問道:「這不是持平吧?」
「皇上屈己,蒼生之福。」
「你錯!我屈己從人,是蒼生之禍,非蒼生之福。像張廣泗征金川,老師糜餉!我要查辦,總有人替他說好話,好吧,我就再看一看。這樣下去,調兵運糧,到處拉伕,苦的是百姓。」
「是。」阿克敦解釋他自己的話,「臣愚意是,皇上屈己,就是納諫;非事事屈己。」
「這話還差不多。不過,以前一直都是屈己從人,現在我說,以後令出必行,人家未必會聽,聽了亦未見得認真。阿克敦,你說該怎麼辦?」
阿克敦知道該怎麼辦,卻不肯說;因為這句話的關係太重了。因此,只是碰頭。
「立威如何?」
「立威」二字,正是阿克敦想說而不肯說的;此刻皇上自己說出來了,阿克敦只好勸他不要用殺大臣之類過於激烈的手段。
「皇上明鑒,立威之道甚多,總以能令人懍於天威不測,知道權操自上,兢兢自守為主;太平之世,不必重典。」
皇帝想了一會說:「我知道你的用心,你一向主張犯十分罪,只能處五、六分刑。現在我要問你,我要借你來立我的不測之威,你肯不肯委屈?」
「雷霆雨露,莫非皇恩。臣豈有自道委屈之理?」
「你能這麼想,必有後福。」
皇帝覺得阿克敦所說,「立威之道甚多」這句話,很值得細味,手段不妨由輕而重;步驟不妨由近而遠,倘能見效,自然不必用嚴刑峻法。細想了一下,決定拿「大阿哥」來作個訓誡的榜樣。
大阿哥名叫永璜,是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出,今年十九歲,已經娶了福晉,只以秉性庸弱,一向不為皇帝所喜。皇后之喪,迎靈時神情呆滯,近乎麻木不仁;皇帝已當面訓斥過一次;這一回特頒硃諭:「阿哥之師傅,諳達,所以誘掖訓誨,教阿哥以孝道禮儀者;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此等事,謂必閱歷而後能行,可乎?此皆師傅,諳達平時並未盡心教導之所致也。伊等深負朕倚用之恩,阿哥經朕訓飭外,和親王、來保、鄂容安著各罰食俸三年,其餘師傅、諳達,著各罰俸一年。張廷玉、梁詩正俱非專師,著免其罰俸。」
皇子在上書房念書,教漢文的稱為師傅;教清文及騎射,仍用滿洲話的稱呼,叫做諳達。內務府大臣來保是諳達;鄂爾泰之子兵部侍郎鄂容安是師傅;和親王弘晝則負有稽察上書房的全責,所以獲咎較重。
和親王口沒遮攔,第二天上朝看到上諭,向同在王公朝房辦理皇后喪儀的傅恆笑道:「皇上是惱羞成怒了。」
「五爺,五爺!」和親王弘晝與皇帝同歲,行五,所以椒房貴戚的傅恆,一直用這種家人之間的稱呼叫他,「你千萬別這麼說。」
傅恆忠厚懦弱,但帷薄不修,且胞妹因此自盡,鬧出偌大風波,居然仍舊是這樣膽小怕事,在和親王看來,真窩囊得不像個人了。可是轉念間為傅恆設身處地想一想,妻子的情夫是皇帝,他又能如何?
傅恆還想規勸和親王,語言以檢點為宜,像他的身分,縱不致多言賈禍,但怎麼樣也不會有好處。
「傅大人,」軍機處的蘇拉來通知:「叫起了。」
召見謂之「叫起」。每天第一起必是軍機;軍機大臣原有七人,但四個出差,張廷玉又請假,所以只有傅恆跟汪由敦兩人在養心殿進見。
當時的頭一件大事,是皇后的喪儀,傅恆將預備的情形,一一面奏,接著便請示大行皇后的諡號。
「孝賢。」皇帝脫口答說:「昨天我做皇后的輓詩,其中有一聯:『聖慈深憶孝,宮坤盡稱賢。』從來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知妻亦莫如夫,大行皇后一生的淑德,只有『孝賢』二字,可以包括。」說著,皇帝的眼睛眨了幾下,彷彿忍淚的模樣。
第一章
「皇后在德州投河了!」
耳語很快地在京裡傳了開來,但妄言妄聽,大都將信將疑,只有極少數的人,包括病中的平郡王福彭,相信流言不假。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皇帝率皇后奉聖母皇太后啟鑾東巡。
這是早在上年六月初一就頒了上諭的,定於來年正月巡幸東魯,親奠孔林;復奉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嶽,宜崇報饗,一切典禮由大學士會同禮部,稽考舊章,詳議具奏。
皇帝祭孔的禮節,有康熙二十三年的成規,可資遵循;太后上泰山去燒香,無例可援,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禮部尚書王安國去請教保和殿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他很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