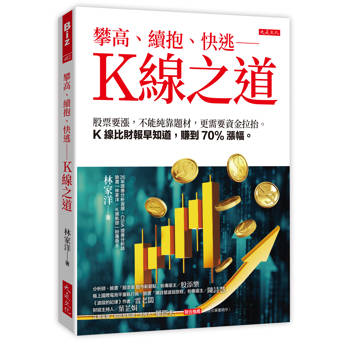人類痛苦史是歷史研究中不朽課題。痛苦與死,相知相惜。德國思想史學家羅森(Jörn Rüsen)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最後引用十九世紀瑞士歷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話結束他的回憶:「這是一切事物的永恒中心──人類的痛苦及奮鬥。就像他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所做的那樣。」人的永恒史是所有人經歷的痛苦。
我所敘述的不是一個清末民初學者的痛苦;痛苦是每一個人的體驗。每一個人在他不同的時刻,例如痛苦的生計、持續的病痛等,他們如何去做選擇?英國思想家路易斯寫道:「苦難(tribulation)隨時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順應頗良之人及審慎之人,恰如其隨時降至其他任何人。」因此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情感。
我這本專書探究王國維的痛苦生存狀態(ipseity)及其生命最後發明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 之間的關係。二重證據法如何是一種厚概念(thick notion)?歷史如何透過對證據的省思重新被塑造與轉化?
思考一個人的自殺抉擇,應嚴肅以待。如何探索一個學者崩潰的個案(a burnt-out case)?我想起了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將自己痛苦的故事寫進學術專書。人往往生活在自己所不相信的生活裡。而「所有會成為人們關注的倫理議題,都必然出自於現實生活中道德—情緒—政治上的混亂。」我審慎的考慮王國維形成其獨特性格和學術事業所面臨的情緒問題。
不知死的不可知,人如何活下去?「但若從來不思考這個問題,則是對於思考的放棄。」我這本書是對人類永恆史的迴向思考。
夏目漱石的《我是貓》,我讀過最少幾種不同的中文譯本。貓說:「只敘述大事而忽視小事,自古以來便是歷史家常犯的弊病。」死亡不是小事。雖然我討論王國維的新傳記,也涉及到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三二年的大事件,但一九二七年這個自殺的落腳點有何意義?「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明治時代的大作家夏目漱石的預言:「死是萬物注定的命運,生而無大用,早死也許是聰明之舉。依諸位先生之說,人類的命運終將走向自殺一途。」
人的痛苦感如何推動人的歷史?史都華‧克拉克(Stuart Clark)在討論法國年鑑學派時,提到人類歷史中大人物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人類歷史中,有些力量也控制了這些大人物的行為:「在這一世界中,大人物會有規則地出現來組織事物,就如同指揮家組織合唱家一樣。但他們未能認知另外的力量。這些力量與他們相分離,但卻決定了他們的所為。」痛苦就是人類一種未能認知的力量。
王國維具有敏感的自我。如萊恩(R. D. Laing)所提問,每一個人究竟在多少
程度會忠於自己。而這種「我」具備一種明確尋死的方向性。芸芸眾生以死亡為息肩之所。人之痛苦尚不止此,死亡與學者形成中的學問的關係又為何?王國維自殺是本書問題性的最終形式(為什麼在那個時間呢?在哪兒?用什麼方式?王氏的自殺為何有意義?)
「死亡是『說』的不能,因為死去的總是他人,一旦死去,則使言說(解釋、死亡的經驗談)永恆缺席。」歷史書寫的啟動,使得王國維的自殺及相關事件的缺席宛如在場。
什麼是人的痛苦?外科醫生班德(Paul Brand)認為「受苦是一種精神狀態,影響整個人。」不是身體的痛苦,受苦是整整一個人的痛苦。個人的受苦,如同李歐梵《看電影》中的提問:「涕淚交零在歷史文化框架中的意義又是什麼?」痛苦無法與他人分擔:「痛苦沒有外在的實質存在。兩個人可以同看一棵樹,卻不能分擔對方的胃痛。這就是為何處理痛十分困難。沒有人,不論是醫生、父母或朋友,可以真正進入另一人的痛經驗。痛是最私人、最孤獨的感覺。」我這本書第一次探索王國維死的孤獨。
王國維生長於清末。牟宗三形容「清代三百年是中國民族最沒出息的時代」。王國維在這個沒有出息的時代,如何對待自己的生存?楊聯陞〈朝代間的比賽〉這篇大論文以長歷史的眼光比較中國各個朝代的長處與缺點,他認為明清相較之前的朝代的確比較保守。牟宗三又說:「人又能放棄自己的生命,最顯然的例,就是人能自殺。自殺雖不好,但確能表示人能提起來,駕臨於他的自然生命以上,而由己以操縱之。」
一九二七年,王國維結束自我生命。這件自殺事件長期以來已引起各式各樣的討論。剛剛過世的英國詩人艾瓦里茲(A. Alvares)的《自殺的研究》花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西方世界對自殺者死後懲罰的歷史:「歐洲各地的處置方法,雖各有異,但對自殺者的鄙視則同。在法國,依各地的習慣,縛住屍體的腳,用囚車拖在街上走。然後火化,棄於垃圾堆。」現代社會對自殺者寬容多了,但「許多都是基於他們對人類的漠不關心」。
王氏處於兩個時代之中。周中孚曾提問:「凡一人屆兩代之間,作史者宜應傳在何處?」周氏設一比喻,如果一位女性跟過不只一位男人,「或以臣道比妻道,當如婦人屢嫁,以最後所適為定,似太拘泥。」意思是一人屆兩代之間,也可以前代為定。
王國維為何不死於一九一一年?一個人死亡的時間,與其預備自殺的時間之間的差異「與因果連續不互相依賴的」。決定自殺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思考自殺與最後死亡之間,因果並無依賴的關係。大部份自殺「總是被當成一種外在事件,以一種艱困處境呈現(失敗、意外、疾病、災難)。然而,這種必要難道不也會來自靈魂?」靈魂究竟與自殺有何關係?王氏延遲的自殺至一九二七年實現。
一九二七年是王國維自殺的一年。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無法忘卻的一年。一九三○年曾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回憶這一年對他的改變:「李大釗先生和別的一批革命者,被張作霖絞死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消息傳來,我的腦子曾有一兩分鐘失去感覺,有兩三天像鬼迷似地心裡沒有一點主意。這個刺激,是他對我的最後的影響,我覺得對我是有確定我一生做人的作用的。」馮雪峰在作家張天翼的介紹之下,在這一年加入北京大學的共產黨。同樣對時代黑暗敏感的王國維,為什麼一九二七年一定會死?在那個知識分子一個又一個死亡的年代。
同一年,魯迅以極特別的形式,提及王國維及其一生的朋友羅振玉對待其研究古文物的關係:「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為什麼?借用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話,羅振玉是民國時期一位「有權勢的知識分子」。
魯迅指出,羅、王二人將新出土的許多文物及古物「偷完」。如何偷?羅振玉「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羅、王兩人具有買賣古物廣告意味的題跋?桑兵提到的學問知識「本來就是二三荒江野老的志業」。
王國維的志業更接近這種境界。羅氏變賣國寶是其一生生意,深溺於生計大慾不可自拔,而此事王國維「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魯迅點出了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的危險關係。王氏代表作《觀堂集林》(一九二一),大量以「題跋」體發表的作品,是否有著買賣古文物的意味?
魯迅在一九二七年紀念王國維的短文,為什麼不提到王氏的自殺?魯迅的小說《孤獨者》中的主人翁魏連殳,以肉體及精神的雙重自殺,這篇作品表達了知識份子對當時的中國進行報復。魏連殳是一位同情兒童的孤獨知識人。故事的主人翁也為生計所綑。魏連殳在故事中自問:「然而就活下去麼?」魯迅不會不了解王國維的自殺是一種對中華民國的報復。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的圖書 |
 |
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 作者:李建民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8-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中國當代人物 |
$ 300 |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
$ 300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23 |
社會人文 |
$ 334 |
中文書 |
$ 342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380 |
人物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
「人是藉著痛苦認識智慧,而不是透過享樂。」
──法國思想家西蒙・韋伊(Simone Weil)
是什麼樣的時代,讓有思想的人不願活著?
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投湖自盡,留下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身為民國初年最具聲望的學者,王國維突如其來的死亡,為當代中國知識界帶來極大震撼,對他的自殺動機,歷來更是爭論不絕、眾說紛紜。有人宣稱他是以遺老身份殉清、或為中國文化衰微而死,卻也有人認為他是經濟現實的因素而走上絕路。
但人的死亡,能夠如此輕易歸結嗎?一位知識份子選擇告別人世,原因又真會如此單純?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王國維之死?又該如何在歷史之中,理解人的痛苦?
在《民國的痛苦》一書中,作者李建民重新探訪這個謎團,試圖理解王國維的生平、性格與他所處的時代,以詩意與富有情感的文筆,描繪王國維生前內心的幽憤、苦悶與哀傷,他所面臨的生活磨難、他與恩師羅振玉之間的矛盾糾結,還有對政治與外在環境日益增加的疏離與危亡之感。作者也指出,王氏死於一九二七年並非偶然,這是令許多人徬徨而無奈的時刻,在動盪不安、悲觀煩悶的氣氛中,知識份子一個又一個離去。絕望的一九二七,是集體自殺的年代,王國維不過是最具代表性之一人。
痛苦的故事是人的故事,也是歷史研究的不朽課題。透過王國維的死亡抉擇,本書呈現人性的複雜與歷史的暴虐,也反覆對「我們到底為何而活」這樣的根本問題,發出最深層的哲學叩問。
作者簡介:
李建民
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喜歡的書是《史記》等。喜歡看老電影,因為可以想念與爸爸的時光。最喜歡的導演為Chris Marker(1921-2012)。不用電腦。沒有手機。不會開車。最好的朋友:中南街上的流浪貓。曾發表文學、神學作品。
章節試閱
人類痛苦史是歷史研究中不朽課題。痛苦與死,相知相惜。德國思想史學家羅森(Jörn Rüsen)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最後引用十九世紀瑞士歷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話結束他的回憶:「這是一切事物的永恒中心──人類的痛苦及奮鬥。就像他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所做的那樣。」人的永恒史是所有人經歷的痛苦。
我所敘述的不是一個清末民初學者的痛苦;痛苦是每一個人的體驗。每一個人在他不同的時刻,例如痛苦的生計、持續的病痛等,他們如何去做選擇?英國思想家路易斯寫道:「苦難(tribulation)隨時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順應頗...
我所敘述的不是一個清末民初學者的痛苦;痛苦是每一個人的體驗。每一個人在他不同的時刻,例如痛苦的生計、持續的病痛等,他們如何去做選擇?英國思想家路易斯寫道:「苦難(tribulation)隨時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順應頗...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王國維,我們的同時代人?
第一章 「沒有任何事物比死亡更長久」
第二章 時間斷裂及「驚嚇感」
一、王國維的明治青春
二、京都的死與美
第三章 王國維知道什麼?──二重證據法是懷疑的方法
一、共死之道,同死之時
二、二重證據並不存在必真的東西
三、四一二事件與王國維之死
四、被壓抑的痛苦史
第四章 再思,人的痛苦史
後記
註釋
第一章 「沒有任何事物比死亡更長久」
第二章 時間斷裂及「驚嚇感」
一、王國維的明治青春
二、京都的死與美
第三章 王國維知道什麼?──二重證據法是懷疑的方法
一、共死之道,同死之時
二、二重證據並不存在必真的東西
三、四一二事件與王國維之死
四、被壓抑的痛苦史
第四章 再思,人的痛苦史
後記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