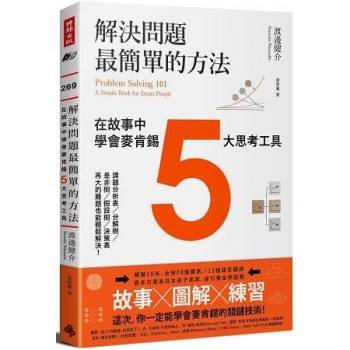我舅舅上個世紀(二十世紀)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歲,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確的說法是不該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筆記、相片,除此之外,我還記得他的樣子。他是個膚色黝黑的大個子,年輕時頭髮很多,老了就禿了。他們那個時候的事情,我們知道的只是:當時燒煤,燒得整個天空烏煙瘴氣,而且大多數人騎車上班。自行車這種體育器械,在當年是一種代步工具,樣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兩個輪子之間有一個三角形的鋼管架子,還有一根管子豎在此架子之上。流傳到現在的車裡有一小部分該管子上面有個車座,另一部分上面什麼都沒有;此種情形使考古學家大惑不解,有人說後一些車子的座子遺失了,還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釋──當時的人裡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較好的生活,有座的車就屬於他們。另一部分的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須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權利,故而這種不帶座子的自行車就是他對肛門、會陰部實施自殘自虐的工具。根據我的童年印象,這後一種說法頗為牽強。我還記得人們是怎麼騎自行車的。但是我不想和權威爭辯──上級現在還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討沒趣。
我舅舅是個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沒發表過,這是他不受信任的鐵證。因為這個緣故,他的作品現在得以出版,並且堆積在書店裡無人問津。眾所周知,現在和那時大不一樣了,我們的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麼說吧,作為外甥,我該為此大為歡喜,但是書商恐怕會有另一種結論。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該由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來評判,我知道的只是:現在紙張書籍根本不受歡迎,受歡迎的是電子書籍,還該有多媒體插圖。所以書商真的要讓我舅舅重見天日的話,就該多投點資,把我舅舅的書編得像點樣子。現在他們又找到我,讓我給他老人家寫一本傳記,其中必須包括他騎那種沒有座的自行車,並且要考據出他得了痔瘡,甚至前列腺癌。但是根據我掌握的資料,我舅舅患有各種疾病,包括關節炎、心臟病,但上述器官沒有一種長在肛門附近,是那種殘酷的車輛導致的。他死於一次電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壓扁了,這是個讓人羨慕的死法,明顯地好於死於前列腺癌。這就使我很為難了。我本人是學歷史的,歷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導向原則──這就是說,一切形成文字的東西,都應當導向一個對我們有利的結論。我舅舅已經死了,讓他死於痔瘡、前列腺癌,對我們有利,就讓他這樣死,本無不可。但是這樣一來,我就不知死在電梯裡的那個老頭子是誰了。他死時我已經二十歲,記得事。當時他坐電梯要到十四樓,卻到了地下室,而且變得肢體殘缺。有人說,那電梯是廢品,每天都壞,還說管房子的收了包工頭的回扣。這樣說不夠「導向」──這樣他就是死於某個人的貪心、而不是死於制度的弊病了。必須另給他個死法。這個問題我能解決,因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幾年的寫作課,專門研究如何臭編的問題。
有關歷史的導向原則,還有必要補充幾句,它是由兩個自相矛盾的要求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學的研究、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好的結論;其二是:一切上述討論,都要導出現在比過去壞。第一個原則適用於文化、制度、物質生活,第二個適用於人。這麼說還是不明白。無數的史學同仁就因為弄不明白栽了跟頭。我有個最簡明的說法,那就是說到生活,就是今天比過去好;說到老百姓,那就是現在比過去壞。這樣導出的結論總是對我們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們」是誰。
我舅舅的事情是這樣的:他生於一九五二年,長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農村去插隊,在那裡得了心臟病。從「導向」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太過久遠,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後來懷才不遇,作品發表不了。那時候他有四十幾歲,獨自住在北京城裡。我記得他有一點錢,是跑東歐作買賣掙的,所以他就不出來工作。春天裡,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園,這時候,他穿了一件黃色燈芯絨的上衣,白色燈芯絨的褲子,頭上留著長長的頭髮。我不知道他常去哪個公園,根據他日記的記載,彷彿是西山八大處,或者是香山一類的地方,因為他說,那是個長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蔥蘢的地方。我舅舅的褲子膝蓋上老是鼓著大包,這是因為他不提褲子。而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過心臟病,假如束緊褲帶就會喘不過氣來。因為這個緣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別人知道他是個大作家,也就不會大驚小怪,問題就在於別人並不知道。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未來世界(二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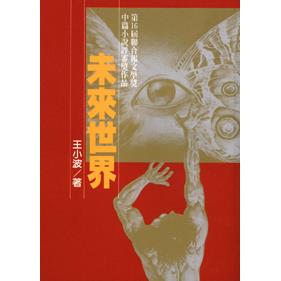 |
未來世界【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3-02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現代小說 |
$ 198 |
小說 |
$ 198 |
聯經出版 |
$ 220 |
中文書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未來世界(二版)
第16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評審獎作品
《未來世界》榮獲第16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評審獎作品。以一個虛擬的時空,反映大陸目前的社會狀況,如官僚問題、地方和中央利益衝突的問題,可說是大陸上人性鬥爭的故事;並點出未來各種形式緊緊壓迫的控制,好讓我們感受到未來世界的特質。
作者簡介:
王小波(1952-1997)
原籍四川渠縣,1952年生於北京。1959年入學,1966年因文革停課。1969年5月到雲南隴川插隊,後來,又轉到山東牟平插隊。1974年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廠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84年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遊歷了歐洲和美國各地。1992年後志於自由撰稿。1997年4月11日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北京。其作品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壇最美的收穫」。
章節試閱
我舅舅上個世紀(二十世紀)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歲,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確的說法是不該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筆記、相片,除此之外,我還記得他的樣子。他是個膚色黝黑的大個子,年輕時頭髮很多,老了就禿了。他們那個時候的事情,我們知道的只是:當時燒煤,燒得整個天空烏煙瘴氣,而且大多數人騎車上班。自行車這種體育器械,在當年是一種代步工具,樣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兩個輪子之間有一個三角形的鋼管架子,還...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有些讀者會把「未來世界」當作一部科幻小說,我對此有一些不同意見。寫未來的小說裡,當然有很多屬於科幻一類,比如說威爾斯(Wells, H. G.)的很多長篇小說,但若把喬治・奧威爾(Orwell, G.)的「一九八四」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一九八四」中並不是主題。我們把寫過去的小說都叫作歷史小說,但卡爾維諾(Calvino. I)的小說「我們的祖先」裡,也毫無真實歷史的影子。有一些小說家喜歡讓故事發生在過去或者未來,但這些故事既非對未來的展望,也非對歷史的回顧,比之展望和回顧,他們更加關注故事本身。有...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小評「未來世界」/平路
得獎感言
上篇:我的舅舅
下篇:我自己
小評「未來世界」/平路
得獎感言
上篇:我的舅舅
下篇: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