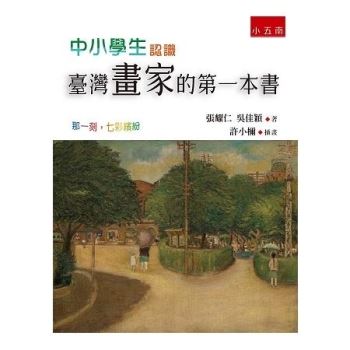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的圖書 |
 |
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 / 譯者:林俊宏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6-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74 |
二手中文書 |
$ 410 |
中文書 |
$ 411 |
國際關係 |
$ 411 |
政治 |
$ 411 |
聯經出版 |
$ 468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520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個以謊言與虛構組成的新政治型態,正盤旋在當代世界上空。若跟隨著獨裁者的指引,我們終將走向不自由之路。
繼《暴政》、《黑土》、《重病的美國》之後,著名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又一警世巨作!
當上個世紀冷戰結束之際,人們一度歡欣鼓舞迎接「歷史的終結」,相信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相信未來必然會往光明的方向前進。如此天真樂觀的態度,將各種事實編織成一張幸福之網,創造出史奈德所謂的「線性必然政治」:市場會帶來民主,民主會帶來幸福,進步的法則都在掌握之中。
然而,線性政治令人懈怠,它腐蝕公民責任,培養出沒有歷史的千禧世代,讓人遺忘自由與民主曾是如此得來不易。而今二十世紀腳步已遠,但人們並沒有從殘酷歷史中學到教訓。
■ 大謊言時代的降臨
歷史從未終結,線性政治尚未走到那美好的未來,便開始瓦解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迴圈永恆政治」:國家落入被害者的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重複過去的威脅。在線性政治裡,人人都知道一切終將進步,所以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在迴圈政治裡,人人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也沒有人能負起責任。
迴圈政治中的政治人物,操弄情緒、製造危機,用謊言混淆事實,讓公民交替體驗著暴怒與狂喜,以現在淹沒未來。2012年的俄羅斯選舉舞弊,普丁贏得大選,卻摧毀了法治。2014年俄國入侵烏克蘭,普丁卻宣稱這是西方意圖分裂偉大的俄羅斯文明。「讓事實畫下終點,就是永恆的開始。」而現在,普丁要將這套迴圈政治出口到全世界。
■ 我們唯一能掌握的,唯有歷史與真相
當權力扭曲事實,歷史只為政治利益服務,我們將喪失的不僅僅是過去。在迴圈政治裡,人們會逐漸喪失思考的能力,一步步走向「不自由之路」。在這個充斥各種幻象、機器人與網軍的年代裡,史奈德透過回望歷史,剖析當代全球民主最深刻的危機。
他說,唯有追求真相,才能讓我們遠離不自由的道路;唯有喚醒歷史,才能在線性與迴圈中打開一道縫隙。「如果我們能誠實面對歷史,就能看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知道自己可以改變什麼、怎樣可以做得更好。於是,也就不再無意識地從線性必然走向永恆迴圈,不再走著通往不自由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責任政治才得以開展,而我們也將看見自己仍能有所作為,世界仍能被改變。
聯合推薦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房慧真/作家
晏山農/文化工作者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陳健民/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序)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極具洞見又令人不安的分析之作,一個所有人都應該瞭解的,吞噬全球的政治危機。
——哈拉瑞,《人類大歷史》作者
我們正急速走向法西斯主義,提摩希.史奈德這位美國作者為我們指出了這項事實。
——斯維拉娜.亞莉塞維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提摩希.史奈德描述了此時此地、過去與現在,我們正面臨的人類活動陰暗面……但就如他在《暴政》傳達的,即使災難伺機而動,他也拒絕臣服。
——喬納森.克希,暢銷宗教書作家
《到不自由之路》提供了一個簡短有力、考據詳實的歷史紀錄──關於普丁對俄羅斯統治、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及俄羅斯如何介入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
——《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
我們生處在一個危機時代,提摩希.史奈德言詞有力地指出,如要瞭解普丁,必須從他的想法著手……《到不自由之路》是一本極好的敲門磚。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提摩希深諳此議題……如今面對愈來愈多的政治謊言、掩蓋真相等邁向法西斯的徵兆,很難不為此感到戰慄。
——丹尼爾.德雷納,《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扼要卻令人不寒而慄、無法忽視的閱讀體驗。
——《衛報》(The Guardian)
在所有試圖解釋西方民主制度的著作中,沒有一本比提摩希.史奈德《到不自由之路》更流暢、也更令人驚怖。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作者/譯者簡介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巴黎、維也納和哈佛大學擔任過研究員。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文章評論散見全美各大媒體、報章雜誌專欄。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血色大地》、《黑土》、《暴政》、《重病的美國》等。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
Author Photo-Timothy Snyder, Credit Ine Gundersveen
譯者:林俊宏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喜好電影、音樂、閱讀、閒晃,覺得把話講清楚比什麼都重要。譯有《人類大歷史》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