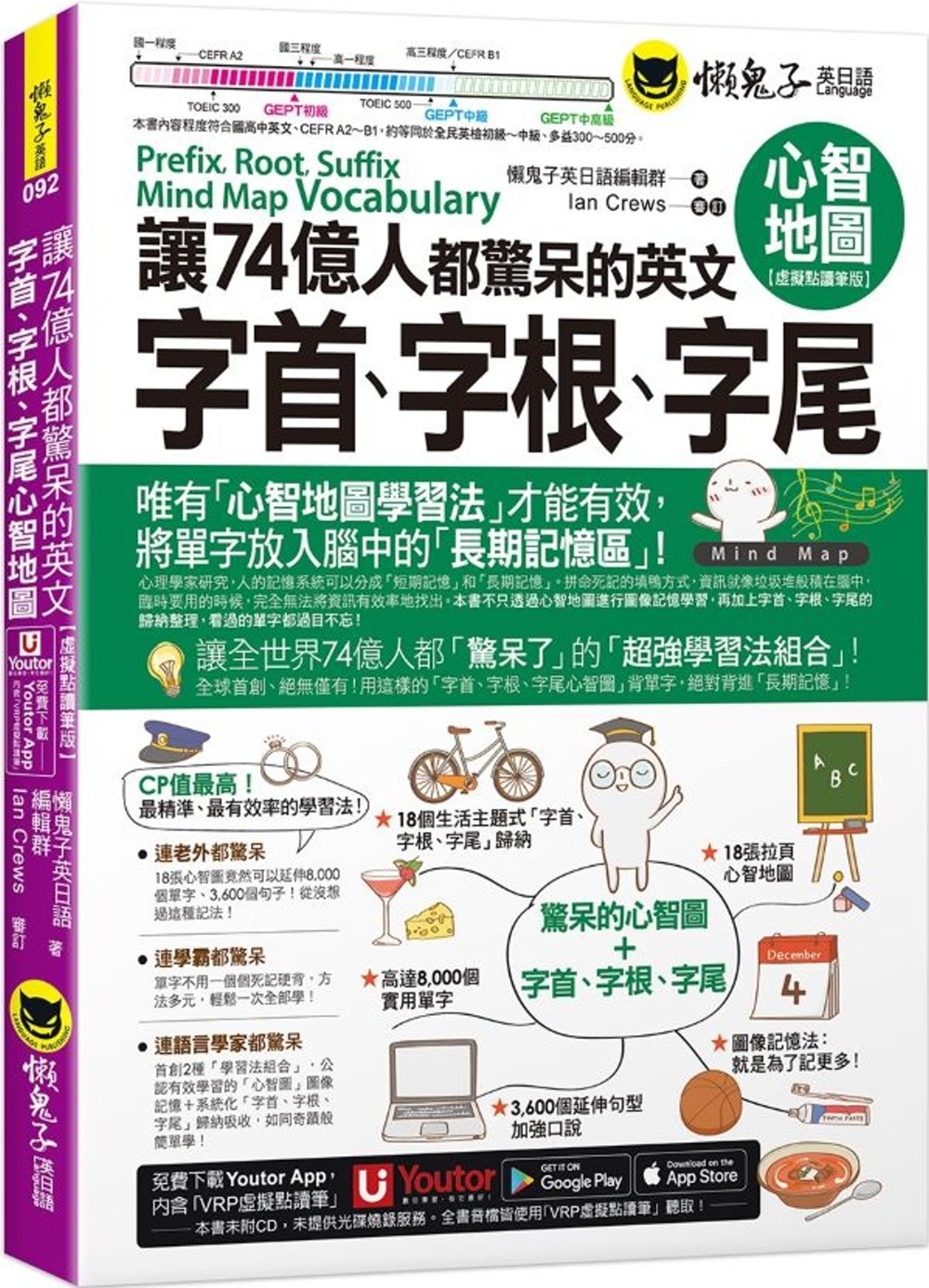為何我們依舊需要閱讀歷史?歴史的範圍不斷擴大,愈來愈包括沒有個人意志,或個人意志不直接表現在史事上的歴史。傳統史學中的宏大鑑誡觀,或「歴史作為人生導師」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與歴史的直接關係上的「史用學」,現在是否已失效?
王汎森主張,各種型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啟示,但他除了期待歴史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更應强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的圖書 |
 |
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10-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一九五八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書。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一九五八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近年來將研究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書。
目錄
序
導 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
「未來」的不透明性
軟、硬律則
培養長程與全景式的眼光
把握歷史發展中的「風勢」
歷史點染人生的作用
「歷史」的鑑誡作用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意識」
「沒有歷史的人」
「可能性知識」的價值
「重訪」歷史以開拓各種認識的可能性
「在心上的」與「在手上的」
第三章 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模式
「性格與歷史」
歷史中的典範人物
第四章 如何讀史?: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觀點
「觀其得失而悟其會通」
「讀者對話論」
讀史與關鍵時刻
讀史要能「大出入」
「關聯」與「呼應」
第五章 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
讀史與「心量」的擴充
試著從歷史中獲得智慧與勇氣
導 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
「未來」的不透明性
軟、硬律則
培養長程與全景式的眼光
把握歷史發展中的「風勢」
歷史點染人生的作用
「歷史」的鑑誡作用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意識」
「沒有歷史的人」
「可能性知識」的價值
「重訪」歷史以開拓各種認識的可能性
「在心上的」與「在手上的」
第三章 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模式
「性格與歷史」
歷史中的典範人物
第四章 如何讀史?: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觀點
「觀其得失而悟其會通」
「讀者對話論」
讀史與關鍵時刻
讀史要能「大出入」
「關聯」與「呼應」
第五章 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
讀史與「心量」的擴充
試著從歷史中獲得智慧與勇氣
序
序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於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有過相當精彩的討論。一九○二年,當梁啟超掀起新史學革命時,反覆強調的是「自動者」才是歷史,「他動者」不是歷史。另外,在〈新史學〉中,他區分「歷史學」與「天然學」,認為歷史是敘述進化之現象的,說:「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天然學」研究的是「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天然學」是「非歷史」的。在西方二十世紀的英國史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主張,凡有思想的行動是歷史的,沒有思想的便是非歷史的,所以柯林伍德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
但是現代史學界對上述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自然界」是不是就一定是如梁啟超所說的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而沒有歷史;歷史是不是一定是「思想的歷史」?人們對這些問題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在Dipesh Chakrabarty(1948-)的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一文中,他批評了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柯林伍德(他不知道梁啟超的說法)以降,區分「歷史的」與「自然的」觀點。他說,因以人類為主的意識過度誇大,如地貌的急遽改變、生態環境的快速變遷,使得自然界不再是「昨日如此,明日如此」,故自然也有了歷史,太過膨脹的「人定勝天」、「戡天役物」,造成自然界的變化。
近幾十年來,流行各種新史學,如「環境史」,我們可以發現過去梁啟超等人可能認為是「自然的」而「非歷史」的範疇,如今變成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變化非常廣泛,使得歷史的範圍一步一步加寬,當我們在討論歷史與現實的關係時,也不能不正視這個變化。過去史學的一些拿手好戲,包括人物的、政治的、制度的、事件的、興衰的、國族的歷史,很不幸的,都不再是專業史家關心的重點。現代史學雖然對人物的歷史失去興趣,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史學界對無名者的歷史、過去沒有面目者的歷史、被壓抑者的歷史、過去不被注意的歷史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興趣,這是新史學的重要面目。
歷史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且愈來愈包括沒有個人意志,或個人意志不直接表現在史事上的歷史。那麼傳統史學中那種宏大的鑑誡觀,或「歷史作為人生導師」那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與歷史的直接關係上的「史用學」,現在是不是失效了。本書秉持「從史中求史識」(陳寅恪)的態度,傾向於認為各種型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啟示,但我想強調:相對於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我更強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這本小書便是試著針對這個課題所進行的一點嘗試。
這是一本「引論」性質的書,討論如何將歷史知識引到與人生發生關聯的路上。本書的內容曾先後在諸多講座中講過:如東海大學的「吳德耀講座」、北京大學高研院的講座、成功大學的「成功人文講座」等等,在這裡要特別謝謝這些單位。原本我有將講座內容整輯成書的義務,但我都未能交差,也都得到主辦單位的諒解。本書的簡體版,緣起自二○一六年羅志田兄提議編寫一套叢書,如果沒有羅志田兄的提議,這本小書是決不可能寫成的。如今這本小書的完成,正是我向它們繳交成果的時候。由於本書原先是演講稿,所以未能處處詳注,希望讀者諒察。在整理成書稿的過程中,王健文教授、譚徐鋒博士、蔡錫能先生、陳昀秀女士都曾惠予協助,謹此致謝。
最後我要強調:「歷史與人生」是一道非常複雜的習題,本書中的觀點,只是其中幾個側面而已,這是不能不特別在此鄭重聲明的。
導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歷史比小說動人,有哪位小說家能編出凱撒的故事呢?
歷史這門學問有很長遠的根源。在世界眾多民族之中,中國是特別重視歷史的民族,印度則是特別不重視歷史的民族。所以印度佛經裡面,即使講歷史,也僅是大象從水裡浮出來,背著典冊,歷史從此就開始了。但中國文化特別重視歷史,自古以來史書就非常多,連小說都要寫成像歷史的樣子,譬如《牡丹亭》,一開始就要先說宋代南安太守如何如何。
西方不像中國那麼重視,但也不像印度那樣輕視歷史,不過希臘、羅馬以來的史學,與中國正史的寫作風格不太一樣。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曾提到過,西方史學的書寫方式受史詩的影響,故其歷史敘述,從開始便好似有一條線索將眾史實綰合在一起,形成像一條高度同質的史實大河(homogeneous stream)。中國正史的書寫方式區分為本紀、世家、書、表、列傳,就好像一個一個不同的格子,貯存著不同的歷史,形成種種的「格套」。普實克在這篇文章中是想為中國歷史辯護,認為它們比希臘、羅馬的史學高明。事實上是否如此,則是見仁見智。
早期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預言」與「歷史」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且這兩個工作經常是同一批人在掌握。美索不達米亞的卜辭是預言未來的「參考資料庫」,愈詳細愈好,好像法官判案時,所根據的判例愈完整、愈詳細愈好。但這是一種以「徵象」的重複性來決定未來可能怎樣,譬如,如果雞的內臟是這樣,那國王已經攻下城池了;如果是那樣,則國王正在攻城。3我個人以為,殷墟卜辭儲存成倉庫,且似有人看守,卜辭的文句又與《春秋》甚為相近,恐怕也反映了「預言」與「歷史」的一體性。如果讀史可以擴充心量,那麼一如美索不達米亞卜辭庫的豐富規模,或如大數據的樣本數,則掌握「或然率」的比例較高,也就比較容易把握「未來」。
本書討論的不是「史學研究」,而是「歷史與人生」這個嚴肅的主題。當我投入歷史這個行業時,歷史與現實、歷史與人生的關係,似乎還比較容易回答,但後來史學與現實俱變,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難回答。
我想先檢視三種很有影響力的觀點。第一、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曾經用異常凶悍的筆調寫過一本小冊子《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他用了許多尖刻的話來形容「歷史的疾病」,意思是人們如果讀了太多歷史,會被過度的「歷史重負」壓得直不起身子來,變成早熟灰暗的青年,這種病的解藥是「破歷史」與「超歷史」。尼采認為只有服務於人生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文明的包袱越少越好,他抗議學習太多的歷史只是加重人身上的負擔。第二、因為許多史家刻意迎合當代的需求(如國族認同)或當代的渴望,寫出來的歷史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翻版。就像在一個情報局中,情報員所收集的材料太想迎合局長的偏好,以致所搜集的情報變得毫無用處,歷史成了「活人在死人身上玩弄詭計」。第三、人類始終有一種古老的期望,希望能夠藉由閱讀歷史獲得像占星家般預測未來的能力。近代史學的發展雖然早已擺脫這種思維,但是一般的歷史閱聽者卻仍然渴切地想找到這方面的指引。事實上,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最大的不同而又同樣精采之處,即在於其無限可能性及不可定律性。當人們模糊地感覺到他們已經走到一個盡頭,變不出什麼新花樣時,下一代人卻馬上翻新出奇、另進一境。人的無限性、複雜性及創造性即展現在這些地方,所以歷史中不可能有像地心引力那般精確的規律。
英國史家亨利.巴克爾(Henry Buckle, 1821-1862)的《英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曾經試著導出一些規律,即當氣候、物質條件變化時,人的出生率、自殺率、離婚率會呈現何種變化;巴克爾曾經風靡一時,可是後來漸漸被拋棄,可見要在歷史中建立某種定律是近乎不可能的。話說回來,雖然牛頓從蘋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的規律,卻不能預測蘋果將於何時掉落。
此外,在現代的史學研究中,歷史不但沒有規律也不會重演,人們認為過去歷史有現實用處時,常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假設即歷史會重演。例如一九三六年,陳登原寫過一本小書《歷史之重演》,用許多古往今來的事例,說明歷史會重演。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玩味書中所舉的大大小小事例,會發現有許多在今天看來是荒謬無稽,或勉強之至的事,書中從古今事例中歸納出種種的「例」,大多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當人類生活的改變一日千里,硬性意義下的「重演」也就更不可能,使得要從過去事件中推出可用的教訓,變得愈來愈難,所以「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稀薄。
所以有不少人直接宣揚「歷史無用」論。一九六九年,約翰‧普朗博(J.H. Plumb, 1911-2001)的一本小書The Death of Past,便宣稱歷史的死亡,主要是說學院化的歷史不再有任何現實的用處。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說:「找史學家來幫忙總是一件不幸的事」、「那些愚蠢可笑的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 1912-1989)便以她引用歷史研究西班牙內戰的發展的著作為例,說明歷史幾乎沒有辦法直接地預測未來。7
回顧過去,近一個世紀的史學發展,人們經常感到:專業史學的進步與歷史對日常人生的導引往往形成反比。何以歷史變得沒有明顯的用處,我認為有兩部分的原因:一、傳統史學以及近百年來史學的典範逐漸失去籠罩力;二、當代史學發展中的若干層面,把歷史與人生拉得愈來愈遠。相較於傳統派史學或左派史學因為明火執杖地鼓吹某些價值或指出未來的方向,現代專業史家恐怕需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一些被丟掉將近一個世紀的老課題—歷史對人格的培養、對價值及方向的引導、對治亂興衰的鑑誡作用等。
但是,歷史就歸於無用了嗎?事實上,傳統史學強調「以史為鑑」,歷史的功能以及歷史與人生、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客觀考證史學興起之後,它變成了一道難以解決的課題。然而,人注定是歷史的動物,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雖不能取消前一刻,卻能超越前一刻,否則孔子、孟子等人的出現便不能完全解釋了,甚至於家族中六百年來沒有人中過任何科名的曾國藩,也沒有辦法完全解釋了。人即使能超越前一刻,也還是活在整個古往今來的歷史之中,所以在超越前一刻之前,仍然得好好了解前一刻,就像看電影不能只看最後那一幕,也不能滿眼只是現在。所以,了解「歷史」與「人生」、「歷史」與「現實」是一道不可能推卻的習題。
為了對應上述的悲觀論調,我想提出「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的觀點。為什麼說讀史可以擴充「心量」?譬如說看到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成就,因而希望向他看齊,不以眼前的自己為滿足,希望達到一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譬如說藉著讀史不斷地積貯內心中的資糧,使得思考、應事時有更多憑藉,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也就是說把人的內在世界想像成是一個空間,平日就不斷地開拓它、充實它,使它日漸廣大,不至於心量淺陋,甚至收縮成一道扁平的細縫。
如果把歷史作為擴充(既擴又充)「心量」的資糧,自然而然便有「用」在其中。我們要積貯各種知識、經驗來擴充「心量」,積貯的內容可以是各式各樣,而歷史知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心量廣闊充實的人,立身、應事,志量視野都比較寬大,而且因為資源豐富,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用處。如果心量過狹或心中沒有積貯,即使是天資非常高的人,其深度、廣度都很有限,只能靠著一些天生的小聰明(street smart)來應事。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於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有過相當精彩的討論。一九○二年,當梁啟超掀起新史學革命時,反覆強調的是「自動者」才是歷史,「他動者」不是歷史。另外,在〈新史學〉中,他區分「歷史學」與「天然學」,認為歷史是敘述進化之現象的,說:「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天然學」研究的是「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天然學」是「非歷史」的。在西方二十世紀的英國史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主張,凡有思想的行動是歷史的,沒有思想的便是非歷史的,所以柯林伍德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
但是現代史學界對上述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自然界」是不是就一定是如梁啟超所說的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而沒有歷史;歷史是不是一定是「思想的歷史」?人們對這些問題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在Dipesh Chakrabarty(1948-)的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一文中,他批評了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柯林伍德(他不知道梁啟超的說法)以降,區分「歷史的」與「自然的」觀點。他說,因以人類為主的意識過度誇大,如地貌的急遽改變、生態環境的快速變遷,使得自然界不再是「昨日如此,明日如此」,故自然也有了歷史,太過膨脹的「人定勝天」、「戡天役物」,造成自然界的變化。
近幾十年來,流行各種新史學,如「環境史」,我們可以發現過去梁啟超等人可能認為是「自然的」而「非歷史」的範疇,如今變成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變化非常廣泛,使得歷史的範圍一步一步加寬,當我們在討論歷史與現實的關係時,也不能不正視這個變化。過去史學的一些拿手好戲,包括人物的、政治的、制度的、事件的、興衰的、國族的歷史,很不幸的,都不再是專業史家關心的重點。現代史學雖然對人物的歷史失去興趣,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史學界對無名者的歷史、過去沒有面目者的歷史、被壓抑者的歷史、過去不被注意的歷史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興趣,這是新史學的重要面目。
歷史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且愈來愈包括沒有個人意志,或個人意志不直接表現在史事上的歷史。那麼傳統史學中那種宏大的鑑誡觀,或「歷史作為人生導師」那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與歷史的直接關係上的「史用學」,現在是不是失效了。本書秉持「從史中求史識」(陳寅恪)的態度,傾向於認為各種型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啟示,但我想強調:相對於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我更強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這本小書便是試著針對這個課題所進行的一點嘗試。
這是一本「引論」性質的書,討論如何將歷史知識引到與人生發生關聯的路上。本書的內容曾先後在諸多講座中講過:如東海大學的「吳德耀講座」、北京大學高研院的講座、成功大學的「成功人文講座」等等,在這裡要特別謝謝這些單位。原本我有將講座內容整輯成書的義務,但我都未能交差,也都得到主辦單位的諒解。本書的簡體版,緣起自二○一六年羅志田兄提議編寫一套叢書,如果沒有羅志田兄的提議,這本小書是決不可能寫成的。如今這本小書的完成,正是我向它們繳交成果的時候。由於本書原先是演講稿,所以未能處處詳注,希望讀者諒察。在整理成書稿的過程中,王健文教授、譚徐鋒博士、蔡錫能先生、陳昀秀女士都曾惠予協助,謹此致謝。
最後我要強調:「歷史與人生」是一道非常複雜的習題,本書中的觀點,只是其中幾個側面而已,這是不能不特別在此鄭重聲明的。
導言
我們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歷史比小說動人,有哪位小說家能編出凱撒的故事呢?
歷史這門學問有很長遠的根源。在世界眾多民族之中,中國是特別重視歷史的民族,印度則是特別不重視歷史的民族。所以印度佛經裡面,即使講歷史,也僅是大象從水裡浮出來,背著典冊,歷史從此就開始了。但中國文化特別重視歷史,自古以來史書就非常多,連小說都要寫成像歷史的樣子,譬如《牡丹亭》,一開始就要先說宋代南安太守如何如何。
西方不像中國那麼重視,但也不像印度那樣輕視歷史,不過希臘、羅馬以來的史學,與中國正史的寫作風格不太一樣。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曾提到過,西方史學的書寫方式受史詩的影響,故其歷史敘述,從開始便好似有一條線索將眾史實綰合在一起,形成像一條高度同質的史實大河(homogeneous stream)。中國正史的書寫方式區分為本紀、世家、書、表、列傳,就好像一個一個不同的格子,貯存著不同的歷史,形成種種的「格套」。普實克在這篇文章中是想為中國歷史辯護,認為它們比希臘、羅馬的史學高明。事實上是否如此,則是見仁見智。
早期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中「預言」與「歷史」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且這兩個工作經常是同一批人在掌握。美索不達米亞的卜辭是預言未來的「參考資料庫」,愈詳細愈好,好像法官判案時,所根據的判例愈完整、愈詳細愈好。但這是一種以「徵象」的重複性來決定未來可能怎樣,譬如,如果雞的內臟是這樣,那國王已經攻下城池了;如果是那樣,則國王正在攻城。3我個人以為,殷墟卜辭儲存成倉庫,且似有人看守,卜辭的文句又與《春秋》甚為相近,恐怕也反映了「預言」與「歷史」的一體性。如果讀史可以擴充心量,那麼一如美索不達米亞卜辭庫的豐富規模,或如大數據的樣本數,則掌握「或然率」的比例較高,也就比較容易把握「未來」。
本書討論的不是「史學研究」,而是「歷史與人生」這個嚴肅的主題。當我投入歷史這個行業時,歷史與現實、歷史與人生的關係,似乎還比較容易回答,但後來史學與現實俱變,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難回答。
我想先檢視三種很有影響力的觀點。第一、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曾經用異常凶悍的筆調寫過一本小冊子《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他用了許多尖刻的話來形容「歷史的疾病」,意思是人們如果讀了太多歷史,會被過度的「歷史重負」壓得直不起身子來,變成早熟灰暗的青年,這種病的解藥是「破歷史」與「超歷史」。尼采認為只有服務於人生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文明的包袱越少越好,他抗議學習太多的歷史只是加重人身上的負擔。第二、因為許多史家刻意迎合當代的需求(如國族認同)或當代的渴望,寫出來的歷史變成了現代社會的翻版。就像在一個情報局中,情報員所收集的材料太想迎合局長的偏好,以致所搜集的情報變得毫無用處,歷史成了「活人在死人身上玩弄詭計」。第三、人類始終有一種古老的期望,希望能夠藉由閱讀歷史獲得像占星家般預測未來的能力。近代史學的發展雖然早已擺脫這種思維,但是一般的歷史閱聽者卻仍然渴切地想找到這方面的指引。事實上,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最大的不同而又同樣精采之處,即在於其無限可能性及不可定律性。當人們模糊地感覺到他們已經走到一個盡頭,變不出什麼新花樣時,下一代人卻馬上翻新出奇、另進一境。人的無限性、複雜性及創造性即展現在這些地方,所以歷史中不可能有像地心引力那般精確的規律。
英國史家亨利.巴克爾(Henry Buckle, 1821-1862)的《英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曾經試著導出一些規律,即當氣候、物質條件變化時,人的出生率、自殺率、離婚率會呈現何種變化;巴克爾曾經風靡一時,可是後來漸漸被拋棄,可見要在歷史中建立某種定律是近乎不可能的。話說回來,雖然牛頓從蘋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的規律,卻不能預測蘋果將於何時掉落。
此外,在現代的史學研究中,歷史不但沒有規律也不會重演,人們認為過去歷史有現實用處時,常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假設即歷史會重演。例如一九三六年,陳登原寫過一本小書《歷史之重演》,用許多古往今來的事例,說明歷史會重演。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玩味書中所舉的大大小小事例,會發現有許多在今天看來是荒謬無稽,或勉強之至的事,書中從古今事例中歸納出種種的「例」,大多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當人類生活的改變一日千里,硬性意義下的「重演」也就更不可能,使得要從過去事件中推出可用的教訓,變得愈來愈難,所以「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稀薄。
所以有不少人直接宣揚「歷史無用」論。一九六九年,約翰‧普朗博(J.H. Plumb, 1911-2001)的一本小書The Death of Past,便宣稱歷史的死亡,主要是說學院化的歷史不再有任何現實的用處。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說:「找史學家來幫忙總是一件不幸的事」、「那些愚蠢可笑的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 1912-1989)便以她引用歷史研究西班牙內戰的發展的著作為例,說明歷史幾乎沒有辦法直接地預測未來。7
回顧過去,近一個世紀的史學發展,人們經常感到:專業史學的進步與歷史對日常人生的導引往往形成反比。何以歷史變得沒有明顯的用處,我認為有兩部分的原因:一、傳統史學以及近百年來史學的典範逐漸失去籠罩力;二、當代史學發展中的若干層面,把歷史與人生拉得愈來愈遠。相較於傳統派史學或左派史學因為明火執杖地鼓吹某些價值或指出未來的方向,現代專業史家恐怕需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一些被丟掉將近一個世紀的老課題—歷史對人格的培養、對價值及方向的引導、對治亂興衰的鑑誡作用等。
但是,歷史就歸於無用了嗎?事實上,傳統史學強調「以史為鑑」,歷史的功能以及歷史與人生、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客觀考證史學興起之後,它變成了一道難以解決的課題。然而,人注定是歷史的動物,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雖不能取消前一刻,卻能超越前一刻,否則孔子、孟子等人的出現便不能完全解釋了,甚至於家族中六百年來沒有人中過任何科名的曾國藩,也沒有辦法完全解釋了。人即使能超越前一刻,也還是活在整個古往今來的歷史之中,所以在超越前一刻之前,仍然得好好了解前一刻,就像看電影不能只看最後那一幕,也不能滿眼只是現在。所以,了解「歷史」與「人生」、「歷史」與「現實」是一道不可能推卻的習題。
為了對應上述的悲觀論調,我想提出「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的觀點。為什麼說讀史可以擴充「心量」?譬如說看到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成就,因而希望向他看齊,不以眼前的自己為滿足,希望達到一個更遠大的人生目標,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譬如說藉著讀史不斷地積貯內心中的資糧,使得思考、應事時有更多憑藉,即是以史來擴充「心量」。也就是說把人的內在世界想像成是一個空間,平日就不斷地開拓它、充實它,使它日漸廣大,不至於心量淺陋,甚至收縮成一道扁平的細縫。
如果把歷史作為擴充(既擴又充)「心量」的資糧,自然而然便有「用」在其中。我們要積貯各種知識、經驗來擴充「心量」,積貯的內容可以是各式各樣,而歷史知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心量廣闊充實的人,立身、應事,志量視野都比較寬大,而且因為資源豐富,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用處。如果心量過狹或心中沒有積貯,即使是天資非常高的人,其深度、廣度都很有限,只能靠著一些天生的小聰明(street smart)來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