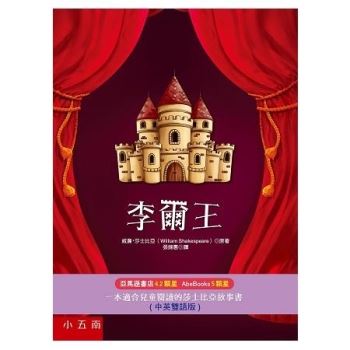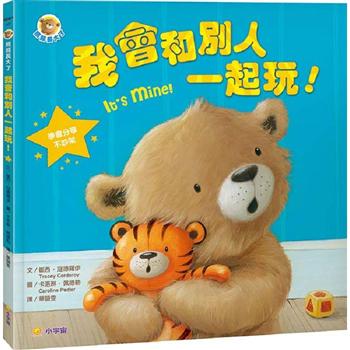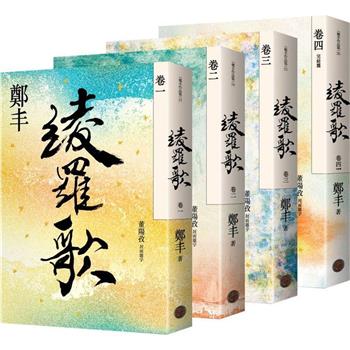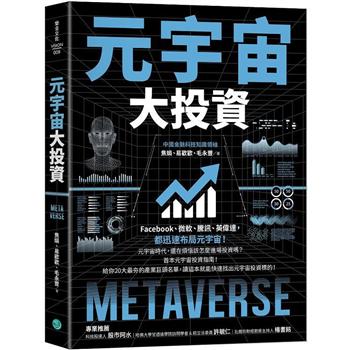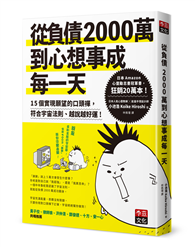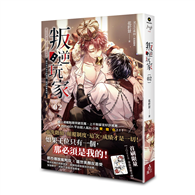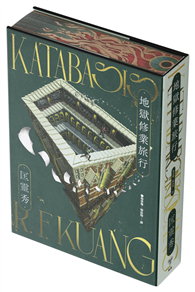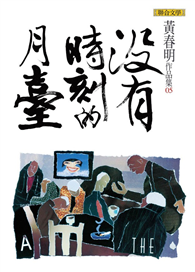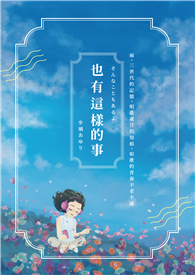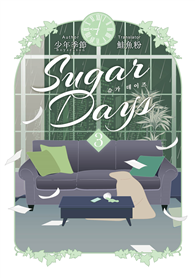★亞洲史研究巔峰.集英社創社95週年紀念鉅獻★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壓迫與變革交錯的時代、民族意識覺醒、
每個選擇都形塑了亞洲的未來
《亞洲人物史》第十卷聚焦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這是一個抗爭、獨立與變革的時代,亞洲各地在帝國主義壓迫與近代變革浪潮下掙扎求存,殖民統治與近代化的矛盾激發民族意識覺醒,各地人民在不同處境下,探索通往解放、獨立與自由的道路。
從革命志士到女性運動先驅,從民族獨立領袖到文學思想家,各地人民不僅對抗外來殖民統治,也在階級、性別、宗教與知識體系上展開抗爭。在朝鮮,有人積極投身獨立運動,也有人選擇調和折衷;在中國,文學與思想界交鋒激盪;在蒙古與阿富汗,政治與軍事變革塑造新國家;在阿拉伯與印度,憲政運動與女性解放並行推進。本書描繪了亞洲如何在壓迫中尋找生機,如何在西方主導的知識體系中重建自身的歷史話語。
本書不僅探討獨立運動與民族抗爭,也關注那些選擇不同道路的人們。透過這些人物的故事,重構亞洲歷史,呈現「民族解放之夢」的多重樣貌,並深思壓迫與自主、傳統與變革之間的複雜關係。
【本卷主要人物】
尹致昊/金瑪利亞/李載裕/魯迅/張愛玲/林獻堂/卡蒂妮/卡瑪拉德維・查托帕迪亞/奧爾佳・列別傑娃/阿卜杜勒希德・易卜拉欣/多斯特・穆罕默德/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薩德・扎格盧勒/瑪拉克・希夫尼・納西夫/後藤新平/夏目漱石/柳田國男/與謝野晶子
叢書特色
• 跨越地域,從東亞到西亞,涵蓋整個亞洲的歷史長河。
• 突出「交流」視角,深挖和平與衝突中的文化碰撞。
• 匯聚現代亞洲史研究權威,打造精緻的評傳與分析。
歷史不僅僅是故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關照。
開啟您對亞洲文明的全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