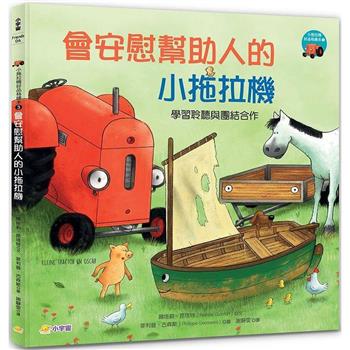1.
梅貝莉.蘿思(Maybelle Rose)驚聲尖叫。
星期二,剛過上午八點,在森林小丘(Forest Hills)慣常安靜的街道上,距離法拉盛草原公園(Flushing Meadows Park)和席亞球場(Shea Stadium)幾哩之遙的地方,年約五十歲且身材肥胖的黑人婦女梅貝莉,站在一間兩層樓高的白色房屋前。
住在隔壁的亞倫.葛希干(Aaron Gohegan)正在刮鬍子,他的電動刮鬍刀近乎無聲。他聽見了尖叫聲,於是拿著刮鬍刀,走過他的妻子珍(Jean),來到臥室的窗戶旁。戴著眼罩和紫色耳塞的珍,正發出微弱的鼾聲。
梅貝莉.蘿思發狂似地看著四周,一邊尖叫一邊哭泣。
此時還穿著內衣和睡褲並打赤腳的亞倫,總是在早上八點十五分出發到曼哈頓(Manhattan)上班。十二年來如一日。這個守時可靠的好名聲,讓他在五十二歲時便成為雷文生投資公司(Ravenson Investments)最年輕的副總裁。
今天,當他和梅貝莉的眼神交會時,他知道好名聲將會受損。亞倫穿上昨晚便已掛在衣櫃門上的畢挺白襯衫,再穿上鞋襪,然後走出房門並下樓。
在他身後,妻子正喃喃地說著他無法理解的夢話。
現在,梅貝莉聲嘶俱裂地吼叫著,發狂地向四處求助;此刻亞倫正走出家門口。
亞倫跑過草坪,朝梅貝莉而去,而住在對街的七十一歲寡婦,瑪亞.安德森(Maya Anderson),也正急忙趕到尖叫女人那裡。
兩位鄰居此時已來到梅貝莉身旁,並看到了她臉上斗大的汗珠。
體重約有二百五十磅的梅貝莉,倒在瑪亞.安德森的懷中,而後者的體重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多磅。令人驚異地,在亞倫過來幫忙前,老婦人竟然有辦法扶住這個哭泣女人。
梅貝莉的粗壯雙腿不停地顫抖,在深呼吸一口之後,她一臉哀戚地望著亞倫。
「出了什麼事?」瑪亞輕聲問道。
梅貝莉轉頭看著這位老婦,並試圖開口說話。可是,卻只發出乾澀的粗嘎聲,以及模糊難辨的單字。
亞倫和瑪亞輕輕地讓梅貝莉坐在草坪上。她的呼吸急促,並試圖換口氣。然後她說:「死了。」
「死了?」亞倫重覆道,「誰死了?」
「所有人,」梅貝莉轉頭看著身後的房子說。
房子的大門開著。曾在第一次波灣戰爭(Gulf War)期間當過軍醫的亞倫,站起身並回頭面向那間屋子。現在,梅貝莉越來越喘不過氣了。她將手放在胸膛上,喃喃地說:「喔,我親愛的上帝。」
「我想她的心臟病發作了,」亞倫說,一邊伸手取出口袋裡的手機。
「惡魔造訪了那間屋子,」梅貝莉低聲地說。
「別說話,」瑪亞說,一旁的亞倫正打電話報警。
但是,梅貝莉還沒把話說完。
「親愛的上帝,鮮血。羔羊的鮮血洗滌了他們的全身。他們漂浮在羔羊的鮮血中。惡魔……。」
亞倫決定,在警方到達之前,不踏進那間屋子。
六個小時前,丹尼.麥瑟(Danny Messer)坐上了地鐵。除了丹尼之外,車上並沒有其他乘客。他放下背包,攤手攤腳地坐在椅子上,拿下眼鏡並揉一揉鼻樑。
他剛連續看了十六個鐘頭的蛆,期間只短暫休息了兩次。那些蛆絕大部分是在泰瑞莎.貝克斯(Teresa Backles)的撕裂胃部中被發現。十歲的泰瑞莎被埋在哈林區(Harlem)一個補助公寓社區後方的垃圾車內。有時候,一個星期或甚至更久都沒人來清運垃圾。這次正是其中一次。高溫加速了蛆的生長以及女孩屍體的腐爛。
丹尼重新戴上眼鏡,閉上了雙眼,卻還是看到不停蠕動的白蛆。雖然他們是犯罪現場調查員的朋友,會透露死者的秘密,但是丹尼依然忍不住想有朝一日他……。
他判定女孩死於五天前。他幾乎可以指出正確時間。有時候,蛆比驗屍官更精準,特別是當你知道要找什麼的時候。丹尼知道。
丹尼戴上面罩,爬進垃圾車內,搜尋每一項物品,其中包括腐爛及滿是螞蟻的外帶食物,跟一隻張口露齒的皮包骨死老鼠。
最後一次見到泰瑞莎是什麼時候?女孩母親的男朋友撒了謊。蛆已經告訴丹尼,而且絕對不會錯。那個男朋友,柯爾.賽恩(Cole Thane),今年二十二歲,當面對包含在垃圾車外找到的一枚指紋等證據時,終於吐出了實情。他原本打算強姦這個女孩,然後殺了她,但當時機到來時,他卻突然下不了手——一個有良心的兒童姦殺犯。所以,他只有殺了她,並且毀屍滅跡。
柯爾.賽恩在丹尼的眼中尋求憐憫。
一顆藥丸和幾小時的睡眠便能讓丹尼回到工作崗位上。犯罪現場永不停止。他們會不斷地堆積。屍體:新鮮的、腐爛的、驚駭的,或是安詳的。一天比一天多。
緝兇的動機是什麼?正義、復仇、病態的好奇心、抑或是工作上的成就感?
蛆。柯爾.賽恩尋求憐憫。丹尼的手臂開始隱隱作痛,那隻在大聯盟選秀賽時不幸受傷的手臂。沒什麼新鮮事。
地鐵車廂內的冷氣很弱。起皺的白襯衫黏附在丹尼身上。他可以感覺到汗珠滴滴落在胸膛和胃上。
沖個澡。吃顆藥。睡一會兒。
在丹尼的右手邊,兩節車廂間的門打開了。他緩緩地坐直身子,疲倦地將右手放在背包上。
兩個西班牙人走了進來,兩人都不出二十歲,一個瘦削,一個肌肉發達。他們穿著一樣的黑色圓領衫,在心口處印有白色的字母「T」。
他們或許就這麼走過去,不過,丹尼.麥瑟可是黑白兩道都混過的人,他比誰都清楚。現在,他們離他只有幾呎遠了。
丹尼感覺到了一些東西——不是恐懼,而是某種多年來不曾再感受到的東西。這種感覺摻雜了在他腦海中閃過的影像:蠕動的蛆、垃圾車內那個被乾涸血液和蛆包覆的黑人小女孩,以及堅信自己值得同情的柯爾.賽恩。
這兩個年輕人停在丹尼面前。瘦削的年輕人從口袋中的刀鞘中拔出刀子。結實的那一個則拿著一根短鉛管。
丹尼的背包裡塞滿了厚重的書本。他站起身,同時拿起背包揮向那個結實的小子。他用力地揮舞,並發出動物般的低吼聲。
清晨六點,麥克.泰勒(Mac Taylor)獨自坐在哥倫布圓環(Columbus Circle)的史蒂芬速食店(Stephan’s Deli)。桌上攤了一份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陽光尚不成氣候的拂曉黎明,他已經到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完成了例行的三英哩晨跑。
氣溫預計在正午攀升至濕熱的華氏一百度。麥克吃了半熟蛋及全麥吐司,還喝了小杯的柳橙汁。此刻,他正一邊喝著第二杯咖啡,一邊看報紙。
店裡並不擠;大約有十二個人分別坐在吧檯和六張餐桌旁。在史蒂芬速食店內,不會有人來煩他。女服務生們尊重他的恍惚眼神。他們知道,他是個警察,他常常看見人們祈禱自己一輩子都別見到的東西。
年近六十歲的康妮(Connie),帶著慣常的虛弱笑容,過來幫麥克斟滿咖啡。他點點頭表示感謝。
「還蠻燙口的,」康妮說。
麥克點點頭,同時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今天會很忙嗎?」她問道。
麥克迎向她那雙寂寞雙眼並露出微笑。
「還不知道,」他說。
手機響了。麥克取出口袋裡的手機,然後說:「我是泰勒。」
他聽著電話,而站在旁邊的康妮正希望能跟這個熱血警察繼續聊天,而他說:「我馬上到。」
他闔上手機蓋,從皮夾中取出一張十元和二張一元的紙鈔,並把它們放在康妮留在桌上的帳單旁邊。他站起身。
「是壞事嗎?」她問道。
「是壞事,」麥克證實。
丹尼.麥瑟將眼鏡推回鼻樑上,一邊聽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一邊開車。塞車。曼哈頓老是塞車,但是他知道如何避開擁塞的路段。這是他的城市。
丹尼昏昏沉沉地睡了四個鐘頭。他沒有夢到死去的小女孩,也沒有夢到在地鐵上對那兩個年輕人所做的事。
但是,他卻夢到了一個月多前的姦殺案。年僅十五歲的受害者,被殘忍地凌虐強暴,而眼睛還被挖了出來。然後,兇手將屍體丟棄在黑巷中,任憑老鼠處置。
兇手留下了精液,因此利用例行程序便能知道他的身分。兇手叫做藍尼.路克(Lenny Zooker),從五年前便開始連續犯下強暴罪行。當丹尼和唐.弗拉克(Don Flack)去抓他時,他正在九十八街(98nd Street)的破爛套房中,看著重播的安迪.葛瑞菲斯秀(The Andy Griffith Show)。他的身形枯瘦,面容憔悴,而稀疏的頭髮往後梳理。他有亂齒及濕潤的棕色眸子。
路克笑著開門讓他們進屋。房間正中央有一具十歲小女孩的屍體,以及幾近黑色且蒼蠅滿佈的一灘濃稠血跡。
路克看著血灘。地板和破舊傢俱上到處都有飛濺的血滴。
「還沒時間清理乾淨,」路克帶著歉意說。「應該有時間才對。正等你們來。」
丹尼發出痛苦的嘶吼聲,一拳揮向那個面帶笑容的兇手。路克往後摔,滑倒在死去女孩的血泊中。
此刻,在前往皇后區(Queens)的途中,他看著自己的右手。那隻手正不停地打顫。從他今天早上起床時就開始了。從他夢到藍尼.路克和那兩名死去的小女孩後就開始了。
在夢中,他竭盡全力要救活她們,要讓她們從血泊中站起來。黛比(Debbie),十五歲;愛麗絲(Alice),十歲。丹尼竭盡全力要救活她們,而就在他確定黛比的右手出現抽搐時,丹尼驚醒了,汗水淋漓,下巴疼痛,右手抽搐。當時是凌晨六點四十分。丹尼起床。他不想睡了。他不想做夢了。
四十分鐘後,丹尼將車子停進麥克車子後面的停車位上。這裡是森林小丘的某一個社區,擁有經悉心照料的舊時大宅,以及相得益彰的完美草坪。跟丹尼長大的地方比起來,無論是地段、面積和安全性,均大不相同。他下了車,先到後車廂拿蒐證工具,然後穿過好奇圍觀的人牆,朝同樣提著工具箱站在門口的麥克走去。
「出了什麼事?」一個染紅髮的女人問道。她用雙手將睡袍緊緊地裹住自己。
丹尼沒有回答。
一位巡警站在前門。麥克和丹尼分別拿出自己的犯罪現場調查員識別證,並把它掛在脖子上。丹尼握緊拳頭,試圖隱藏顫抖,不過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了。
「什麼狀況?」麥克詢問那名巡警。他的名牌上寫著魏奇克(Wychecka)。
魏奇克絕不出二十五歲。
「多名死者,」魏奇克說。「在樓上。迪凡索(Defenzo)和席維斯(Sylvester)警探在裡面。」
「沒有其他人進去過,」麥克說。「沒有。連你也沒有。」
魏奇克點點頭。
麥克也點點頭,然後帶著丹尼走過巡警身旁。這兩個人同時將手伸進口袋內並取出乳膠手套。丹尼好不容易才把手套戴上。
「你還好嗎?」麥克問道。
「很好;開始工作吧。」
麥克看著丹尼,後者從工具箱中取出了照相機,然後準備上樓,邊走邊拍。
當他們朝這棟屋子的二樓移動時,他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聞到了鮮血的味道。
這間屋子擁有明亮的光線,以及賞心悅目、略嫌華麗且昂貴的古董臻品。屋內的冷氣已開到最強。
他們走在光潔明亮的木質地板上,朝傳出聲音的臥室移動。房門開著,床上有兩具血淋淋的女屍,雙手交疊於胸前,頭部躺在枕頭上,雙眼緊閉。年紀較大的女性穿著鮮豔的中國式睡袍。另一名較為年輕的死者只穿了一件 XXXL 尺碼的T恤,印在上面的黑人小伙子張著嘴巴,彷彿正為死者吟唱無聲之歌;而照片上還印有「Usher」的字樣。在地上,有一具男性屍體;他的身子向右頹倒,雙腿呈現怪異的角度,雙眼圓睜,而身上的浴袍已被鮮血浸濕了。
現場兩位警探用搖頭向這兩位犯罪現場調查表示問候。
「迪凡索,」年紀較長的警探,身形矮小,肌肉結實,一頭灰髮向後梳理。
另一位警探年輕一點。他是個黑人,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有著不亞於電視明星的俊帥面孔。他叫做特倫特.席維斯(Trent Sylvester)。
麥克遞給兩位警探一人一雙乳膠手套。他們將手套戴上;事實上,早在他們進屋時就該完成這個動作。
丹尼替這三具屍體及這間臥室拍了許多照片,接著將工具放在地板上,這時迪凡索說:「床上的兩名死者分別是依芙.沃赫斯(Eve Vorhees)和十七歲的貝琪.沃赫斯(Becky Vorhees),兩人是母女關係。地上的男性死者則是丈夫和父親,霍華.沃赫斯(Howard Vorhees)。」
當丹尼拍照時,麥克謹慎地用棉花棒收集血液檢體,接著小心地將它們放進密封塑膠袋,再將袋子放進工具箱內。
麥克環顧四周。這是少女的房間,房內到處都是化妝品和少男少女在鏡頭前擺首弄姿的小幅照片。金髮碧眼的貝琪.沃赫斯是個美人兒,每張照片都有她,其中伸出舌頭時的模樣最為常見。麥克傾身靠近這位死去的女孩,然後用手腕觸碰她的手臂。
摸起來溫暖且僵硬,顯示她已死亡三至八小時。如果摸起來溫暖但不僵硬,麥克會估計她死亡不到三小時。反之,如果冰冷且僵硬,就表示她已死亡超過八至三十六個小時。如果冰冷但不僵硬,便可能已死亡超過三十六個小時或以上。這是一種鑑識經驗法則;不算很精準,但還算有用。
較為正確的死亡時間還是要等到法醫(Medical Examiner)薛爾登.霍克(Sheldon Hawkes)驗完屍後才會知道。當三名沃赫斯的家族成員一死,他們腸道內的有機體便隨即活躍起來,並開始攻擊腸道和血液。腸氣的形成可能會導致腸道破裂,而有機體一經釋放後,便會攻擊其他器官。缺氧的肌肉細胞會製造高濃度乳酸。這將會導致連鎖反應,構成肌肉的蛋白質,亦即肌動蛋白和肌凝蛋白,會結合成一種膠化體,讓屍體僵硬,直到腐爛為止。在醫學上稱為死後僵硬的屍體僵直情形,便是肇因於這個化學反應。
透過驗屍,端視屍體腐爛的程度,霍克可以判定更為精確的死亡時間跟其他事情。
但是,解剖屍體可以透露更多訊息。這意味著麥克和丹尼的動作必須要迅速且確實,並盡快將這三具屍體送到實驗室。
麥克低頭看著霍華.沃赫斯的屍體,他縮著身子,不是要止住迅速流失的血液,就是要保護自己免於另一次攻擊。
「打掃的女傭,梅貝莉.蘿思,在幾個小時前進屋時發現屍體,」席維斯說。「她在隔壁鄰居家。我們曾試著要問她話,但她只是不停地哭。」
「我們待會再找她談談,」麥克說。
「兇器呢?」丹尼問道。
「正在找,」迪凡索說。「但我們不光是只有找兇器而已。這家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兒子,雅各(Jacob)。我們找不到他。」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CSI犯罪現場:紐約 赤血烈日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0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7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CSI犯罪現場:紐約 赤血烈日
【媒體推薦】 最受歡迎的犯罪影集CSI,最暢銷的改編小說! 【內容簡介】 皇后區近郊的某高級住宅區內,任誰都料想不到,這裡竟然發生了恐怖殺人事件:一對夫妻連同女兒在自家慘遭殺害,然而,現場卻未見小兒子的蹤影。麥克. 泰勒和丹尼.麥瑟隨即發現,小孩子可能已經遭到綁架。時間緊迫,他們能及時找到他嗎? 布魯克林區裡,一個宗教色彩濃重的正統猶太教社區,一名虔誠的男性陳屍在猶太教會堂的地板,宛如進行一場儀式。從一開始,史黛拉.波納席拉和艾婷.波恩便認為:曾與被害者會眾發生衝突的基本教義派團
章節試閱
1.梅貝莉.蘿思(Maybelle Rose)驚聲尖叫。星期二,剛過上午八點,在森林小丘(Forest Hills)慣常安靜的街道上,距離法拉盛草原公園(Flushing Meadows Park)和席亞球場(Shea Stadium)幾哩之遙的地方,年約五十歲且身材肥胖的黑人婦女梅貝莉,站在一間兩層樓高的白色房屋前。住在隔壁的亞倫.葛希干(Aaron Gohegan)正在刮鬍子,他的電動刮鬍刀近乎無聲。他聽見了尖叫聲,於是拿著刮鬍刀,走過他的妻子珍(Jean),來到臥室的窗戶旁。戴著眼罩和紫色耳塞的珍,正發出微弱的鼾聲。梅貝莉.蘿思發狂似地看著四周,一邊尖叫一邊哭泣。此...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史都華‧凱民斯基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7-03-21 ISBN/ISSN:97895710352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