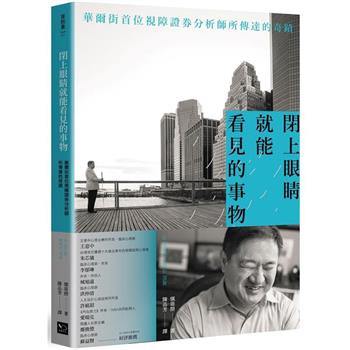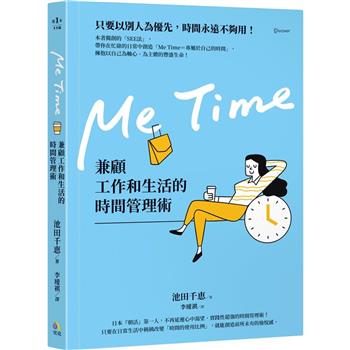美國亞馬遜五顆星推薦!
超越湯姆.克蘭西與丹.布朗,新一代驚悚冒險小說霸主--詹姆士.羅林斯!
達爾文與納粹僅一線之隔,進化與屠殺為一念之間!
哥本哈根一家書店被邪惡的大火吞噬,啓動一場跨越四個國家的獵捕行動。蓄意縱火和謀殺,只為了盜取一本曾經屬於進化論之父達爾文的《聖經》。葛雷‧皮爾斯指揮官尋線追蹤,進入了當年納粹深深埋起的祕密……一個可怕的實驗計畫。
另一塊大陸上,尼泊爾一座偏遠寺廟發生僧侶瘋狂砍殺事件。意外被捲入砍殺事件的年輕美國醫生麗莎‧卡明斯,突然變成殘暴殺手的目標,一支祕密軍隊打算不擇手段地殺人滅口,而隱藏身分的旅人潘特‧克羅是麗莎唯一的伙伴。
救出潘特與麗莎、阻止世界大亂的重責大任就落在葛雷和西格瑪身上。他們傾盡全力破解一個破壞世界、改變人類命運的百年陰謀。
詹姆士‧羅林斯的《黑色密令》是一本大師級的冒險小說,結合了歷史謎題以及動作小說的刺激與驚悚。帶領讀者進行一場鬥智鬥力的精采旅程……並開展視野,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我們的生命和環境。
章節試閱
一九四五
五月四日
清晨 06:22
波蘭 布雷斯勞要塞城
那具屍體漂在潮濕的下水道汚水裡。是一具男孩的屍體。浮腫的身體被老鼠咬得爛爛的,上衣、褲子和鞋子都被人脫下拿走。在這個被敵軍包圍的城市裡,就連破爛的衣物都很寶貴,沒有東西會被浪費。
武裝親衞隊二級上將賈柯•史波倫伯快速經過那具男孩的屍體,噁心的屍體讓他胃部一陣翻騰。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屍體泡在血液跟膽汁裡,內臟外流、腸子裡的糞便四散,即使用濕圍巾摀住嘴鼻,也阻擋不了嗆鼻的屍臭。這就是這場偉大戰爭的結果,並且害他落到如此下場,必須從下水道逃生,這根本不是生性高傲的他會做的事,不過,他身負重責大任。
蘇聯的巨型大砲轟隆隆地重擊著頭頂上的城市。每一次劇烈的爆炸,都幾乎震碎他的內臟。蘇聯紅軍已經炸開城門、炸毀機場,坦克車隆隆駛過圓石街道的同時,運輸機降落在凱撒大街。那條大街已經變成一條降落跑道,大街兩邊平行地排列著正在燃燒的油桶。翻騰的黑煙,讓濃煙密布的清晨更加窒息、讓清晨的河灣仍像黎明一樣昏暗。槍聲、爆炸聲充斥各個角落、每一棟房子──從閣樓到地下室,到處都是戰場。
每棟房子都是一座碉堡。
那是地方官漢基對民眾下的最後一道命令。他們必須盡可能地守住這座城市,越久越好。第三帝國的未來,就看他們能撐多久。
帝國的未來,也在賈柯•史波倫伯身上。
「Mach schnell(德語:快)!」他催促著後面的士兵。
賈柯帶著負責撤空重要設備的帝國保安部隊,走在這條水深及膝的骯髒水道裡。十四個穿著黑色衣服的士兵,全副武裝,都背著沉重的背包。走在隊伍中間的是四個個子最高大的士兵。原本是北海漁場碼頭工人的他們,肩上扛著橫桿,橫桿上吊著一個大木箱。
紅軍大舉進攻這座位在德國及波蘭邊界,蘇台德深山裡的城市──布雷斯勞──是有原因的。這座孤城守衞著通往後面高山的隘口。過去兩年來,德軍從格羅斯羅森集中營調來的犯人,挖通了這座城市附近的一座山峰。犯人在嚴格控管下炸出,並挖出數條總長近一百公里的隧道。這些深山隧道是為了祕密進行一項研究計畫,使敵對的同盟國無法接近刺探。
Die Riese(德語)……那真是工程浩大。
但是祕密還是洩露出去了。可能是文斯勞斯坑道附近村民談論某種怪病時──坑道附近村莊的村民都突然紛紛病倒,連身體健壯的人也不例外──讓間諜聽到傳了出去。
如果他們有更多時間完成那項研究的話……
不過,賈柯遲疑了。他並不完全瞭解那項祕密研究計畫,只知道它的暗號是:「時間」。可是,他知道的夠多了。他聽過被當做實驗品的人的慘叫聲,也看過那些實驗過後的屍體。
憎恨。
這個詞出現在賈柯腦海裡,讓他全身一陣冰涼。
他不眨眼地處決了那些科學家。六十二位男女科學家被拉到戶外,頭部都中了兩槍而亡。不能讓文斯勞斯坑道深處的研究計畫外洩……尤其是那個發現。只有一位科學家必須活著。
多拉•希爾斯費爾德博士。
賈柯聽到她踩著水跟在後面。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後,被一個士兵半拉著往前走。就女人來講,她算長得很高,大約二十八、九歲,小胸脯,腰雖然粗,雙腿線條卻很優美。她的頭髮又黑又滑,皮膚因為在地底待了好幾個月而像牛奶一樣慘白。她原本會和其他科學家一起被處死,可是她的父親──雨果•希爾斯費爾德,高級研究局長、研究計畫的負責人──背叛了他們,他終於露出猶太血統的卑劣。雨果想毀了自己的研究檔案,可是沒有成功。在他炸毀辦公室前,一位士兵射殺了他。幸好他的女兒完全瞭解die Glocke(德語:那座鐘),可以代替父親繼續研究。和父親一樣是天才的她,比其他科學家更瞭解那項研究。
不過,他們必須先安撫她。
每當賈柯望向她時,她眼裡都燃燒著怒火。他感受得到她像火爐一樣熾烈的恨意。不過,她會合作的……就像她的父親一樣。賈柯知道如何應付這些混血的雜種猶太人。他們是最糟糕的人種。第三帝國軍隊裡有上萬個這一類「半個猶太人」。雖然納粹法律特赦這些混血猶太軍人,讓他們繼續活著為帝國服務,不過,他們必須付出代價。這些雜種通常為了證明對帝國的忠心,而更英勇奮戰。
然而,賈柯從來都不相信他們。多拉的父親就證明了他的疑慮是正確的。賈柯一點都不訝異那位博士會背叛帝國。根本不能相信猶太人,那個種族應該被根除。
可是,雨果•希爾斯費爾德的特赦令是領導親自簽署的。領導不只特赦了他和他的女兒,還包括雨果住在德國中部的年老雙親。所以,雖然賈柯不相信這些雜種,但他相信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領導的信函寫著清楚的指示:撤離必要的設備和檔案以便未來繼續研究,其餘的全部摧毀。
這表示他必須留下雨果的女兒。
還有那個嬰兒。
那個出生不到一個月的猶太男嬰被包在背包裡,他們為他注射了微量鎮靜劑,以確保男嬰在逃亡期間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這個男嬰體內跳動著一顆邪惡的心,他是賈柯如此憤怒不平的主要原因。第三帝國的全部希望全在他身上──一個猶太嬰兒。一想到這裡,他又燃起一股怒火,想要一刀刺死男嬰,卻又不能違背上級的命令。他也注意到多拉看著男嬰的眼神混雜著愛憐和哀傷。多拉除了協助父親進行研究外,還扮演嬰兒的養母,哄他睡覺、餵他喝奶。那個嬰兒是多拉願意和他們合作的原因。他們以嬰兒的性命要脅,多拉只好默然遵從賈柯的命令。
一顆迫擊砲在下水道上方爆炸,震得他們全都跪了下去,響亮的爆炸聲也震聾了他們。石灰和塵土紛紛掉入汚穢的髒水裡。
賈柯爬起來,低聲咒駡著。
副指揮官奧斯卡•亨利克,走到他旁邊指著前面一條下水道分支。
「我們走這條分支,上將。它是一條乾涸的舊防洪道。根據這張手繪地圖,這條分支最後注入那條河,出口離大教堂島不遠。」
賈柯點點頭。由另一隊突擊隊駕駛的兩艘武裝快艇,正藏在大教堂島附近等著接應。賈柯他們就快到了。
他加快脚步帶領士兵走上那條分支。頭頂上的爆炸更加密集了,蘇聯全力攻擊入侵這座城市,投降是遲早的事。
賈柯來到分支,他爬出汚水上到防洪道的水泥台上,靴子隨著脚步嘎吱作響。那股內臟腐臭味越來越濃,下水道的惡臭似乎找到方法緊隨著他不放。
其他士兵也爬上水泥台。
賈柯打開手電筒照著前方。臭味是不是變淡了?他的心情和步伐都稍稍輕快了起來,就快成功逃出這座城市了,他的任務就要完成了。蘇聯紅軍抵達地道密布的文斯勞斯坑道時,他和士兵已經進入西利西亞地區。為了好好迎接紅軍,賈柯在坑道內的所有地道都安排了炸彈。蘇聯紅軍和同盟國聯軍會發現,在那座高山坑道裡什麼也沒有,只有炸彈。
賈柯一邊得意地想著,一邊快步走向出口,走向新鮮空氣。防水道緩緩往下傾斜,他們快步跑下。頭頂上的爆炸突然安靜下來,他們更加快步伐,因為紅軍已經攻占了布雷斯勞市。
應該快到了。紅軍會馬上封鎖河道。
好像察覺到緊張的氣氛,嬰兒輕輕哭了一聲──一聲充滿威脅的哭聲,鎮靜劑的藥效過了。賈柯要求軍醫儘量減輕藥量,他們不能冒險,因為這個嬰兒很重要。也許,「減輕藥量」是個錯誤的決定……
孩子的哭聲越來越響。
北方有顆迫擊砲爆炸。
嬰兒嚎啕大哭起來。他的哭聲在石頭隧道裡迴響著遠去。
「讓他閉嘴。」賈柯命令抱著男嬰的士兵。
那位像蘆葦一樣瘦細,臉色灰白的士兵,邊走邊從肩膀上卸下背著孩子的背包。士兵頭上的黑色帽子掉了下來,手腳笨拙的他努力從背包裡抱出孩子。嬰兒的哭聲更大了。
「讓──讓我來,」多拉央求道。她掙扎著,想從抓著她的士兵手中掙脫。「他需要我。」
背著男嬰的士兵看著賈柯。下水道上方一片安靜,而男嬰繼續尖聲哭泣。
受不了的賈柯,勉強點頭。
綁住多拉手腕的繩子被割斷。她搓揉著手腕,走向背著男嬰的士兵。那位士兵高興地交出重擔。她彎著手臂撐住嬰兒的頭,用雙手做了一個搖籃,輕柔地搖著他。她低下頭傾向男嬰,將他更往懷裡抱,輕哼的歌聲充滿安慰,穿透了男嬰的哭聲。她的温柔籠罩著嬰兒。
男嬰尖聲的哭泣慢慢安靜下來。
賈柯滿意地對看守她的士兵點頭。那位士兵拿起盧格手槍,頂著多拉的背。嬰兒安靜下來後,他們繼續在布雷斯勞繁密的下水道網絡中前進。
一會兒後,一股濃厚的煙味掩蓋住了下水道的臭味。他的手電筒照著前方的煙幕,那意謂著那裡就是防洪道出口。下水道上方不再響起爆炸聲,紅軍停止了大砲的發射,但是機關槍的嗒嗒聲仍然不斷--槍聲大多集中在東邊。已經非常接近了,已經可以清楚聽到奔瀉的水聲了。
賈柯以手勢示意身後的士兵停下脚步,並招手要通訊兵到出口處。「通知那些船。」
通訊兵俐落地點了個頭,往前走去,消失在灰暗的煙霧裡。一會兒後,幾道閃光將暗語傳到附近那座小島。那兩艘船,一分鐘後就會通過海峽抵達他們的所在地。
賈柯轉向多拉,她仍抱著嬰兒。而男嬰安靜下來後,便閉上眼睛沉睡著。
多拉迎上賈柯的注視,眼睛眨也不眨。「你知道我父親是對的,」她堅定並且冷靜地說。多拉看向那個封死的木箱,然後又看著賈柯。「你的表情告訴我,你也認為我們的所作所為……太過分了。」
「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賈柯回答。
「那誰可以決定?」
賈柯搖頭轉身。這道撤空坑道的命令,是海因里希•希姆萊親自交代給他的。以自己的階級身分,他沒有資格質問上級命令的正當性。可是雖然如此,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個女人無畏的注視。
「我們在扮演上帝主宰萬物。」她輕聲說。
回報的通訊兵救了他。「船過來了。」通訊兵從轟隆的下水道出口走回來宣布。
賈柯命令士兵們就定位,並領著它們走向下水道終點陡峭的奧得河河岸。走向光亮的他們,逐漸失去黑暗的屏障。雖然東方朝陽閃耀,河面上黑色的煙霧及奔騰的水氣,位他們提供了有效的掩護。
不過,能保護他們多久呢?
機關槍聲繼續輕快地響著,像慶祝布雷斯勞毀滅的鞭炮聲。
離開惡臭的下水道後,賈柯拉開濕圍巾,深深吸了一口乾淨的空氣。他在鉛一般灰色的河面上搜尋著。兩艘只有二十英尺高的船,發出低沉單調的引擎聲,劃開河水朝他們駛來。每艘船上,未綁死的綠色防水布下都藏著一對槍口已經升起的MG四二機關槍。
船後的小島只是一團勉強看得見的黑影。大教堂島並不是一座真正的小島。它形成於十九世紀,由淤泥堆積而成。一座同世紀建成的翠綠色鐵橋橫跨過河,連結小島和這邊的河岸。鐵橋下,那兩艘船繞過石橋墩,朝他們接近。
一道耀眼的陽光射向那座大教堂兩座高塔的尖端,吸引了賈柯的注意力,他抬頭看著尖塔。這個上世紀形成的小島,就是根據那間教堂命名的。小島上擠著六間教堂,這是其中一間。
多拉的話,仍在賈柯腦海裡迴盪。
我們在扮演上帝主宰萬物。
清晨的寒冷鑽進濕衣服裡,他感到刺痛又冰冷。遠離這裡後,他就能忘掉過去幾天在這裡發生的事,那會讓他很開心。
第一艘船抵達岸邊。雖然剛剛對未來的想像讓賈柯分心,但他很開心,甚至比船的到達更讓他快樂。他催促著屬下上船。
多拉抱著嬰兒站到旁邊,由同一位士兵看守著。她也看到那兩座在濃煙瀰漫天空中閃耀的尖塔。槍聲繼續響著,並且越來越接近他們,已經可以清楚聽到慢速前進的坦克車碾過大街的聲音,其中點綴著哭喊和尖叫聲。
她不敢違抗的上帝在哪裡?
絕對不在這裡。
屬下都上船後,賈柯走向多拉說:「上船。」他原本打算嚴厲地命令她,但她臉上的某個表情軟化了他。
她順從地上船,但仍看著那間教堂,思緒飛向遙遠的上天。
就在這個時刻,賈柯發現她原來可以這麼美……即使她是個混血雜種。她突然絆了一下,往前撲去又回復重心,然後低頭檢查嬰兒的狀況。她抬頭望著灰色的河水和黑霧,臉上的表情堅硬了起來──和石頭一樣堅硬,就連尋找座位時的眼神也一樣剛硬。
她坐在右舷邊的長椅上。看守她的士兵一步一趨地跟著她。
賈柯在她對面坐下,對船長揮手開船。「我們一定要準時到達。」他看著河水。他們正朝著西方前進,遠離東邊的出海口,遠離正在升起的朝陽。
他看著手錶。一架德國Junker Ju 52 運輸機應該正在十公里外,一個廢棄的機場等著他們。這架運輸機漆上了德國紅十字的字樣,偽裝成醫療救難用機,以躲過敵軍的攻擊。
船轉了一圈,航向河的上游,引擎聲大聲揚起。紅軍阻止不了他們了。結束了。
某個動作將他的思緒拉回,他看向對面。
多拉低頭彎向嬰兒,輕輕吻上嬰兒有著細軟頭髮的頭部。她抬起頭,迎向賈柯的注視。他在她臉上看不到反抗和怒氣,只看到決心。
賈柯明白了即將發生的事:「不要──」
太遲了。
多拉站起來往後靠向低矮的欄杆,雙脚一踢,抱著嬰兒後翻掉入冰冷的河水中。
看守她的士兵被她突然的舉動嚇到了,他轉身朝河水狂亂掃射。
賈柯衝到士兵旁邊,揚手將士兵手中的槍揮開:「你會射死那個嬰兒。」
賈柯彎身在河水裡搜尋,其他士兵也站了起來,船身搖晃著。賈柯在鉛一般的河水上只看到自己的倒影。他比了個手勢要船長繞一圈。
什麼也沒有。
他搜尋從水裡冒上來的氣泡,但滿載著人而吃水很深的船身激起了翻騰的尾波,攪得河水混亂無法辯識。他一拳擊向欄杆。
有其父……必有其女……
只有雜種會採取如此極端的手段。他以前也親眼見識過:猶太母親悶死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得以解脫。他以為多拉比那些母親更堅強,但最後……也許她沒有別的選擇。
他又讓船繞了一段時間,以尋找她的下落。他的屬下分散在船的四周搜尋著。她不見了。
頭頂上,咻的一聲劃過一顆炮彈,他們不能再逗留了。
賈柯揮手要士兵們回到位子上坐好。他指向西方,指向那架正等著他們的飛機。他們至少還有那些木箱和資料,沒有多拉和那個孩子會很麻煩,但還有別的辦法。他們能成功製造出那個嬰兒,就能再造一個。
「走。」他命令著。
兩艘船再一次出發前進,引擎聲漸漸高漲,油門全開快速駛去。
一會兒後,兩艘船都消失在煙霧中。布雷斯勞被熊熊烈火包圍著。
多拉聽著兩艘船駛向遠方。
她在支撐那座古老鐵橋的一根石柱後方踩著水,一隻手緊緊蓋住嬰兒的嘴巴,以免他出聲大哭,並祈禱他能從鼻子得到足夠的氧氣,但是嬰兒現在的呼吸很微弱。
她也是。
一顆子彈劃傷了她脖子的側邊,鮮血大量流出,染紅了河水。她的視線模糊,但是仍然用盡全力將嬰兒高舉在水面上。
翻下船前,她原本決心淹死自己和嬰兒。可是,冰冷的河水凍醒了她,再加上脖子傷口的灼痛,她自殺的決心被扯裂了。她想起教堂尖塔的光亮。她並不信仰基督宗教,教堂也不屬於她成長背景的一部分,但那提醒她,眼前的黑暗會過去,光明會再重現。那時,人類不再攻擊自己的手足,母親不再需要溺死自己的孩子。
她踢水游進深水域,任由水流將她帶向那座橋。她在水面下緊捏著嬰兒的鼻子,並將空氣吐入他嘴裡,以維持孩子的生命。雖然她原本打算自殺,但是活著的慾望一旦被燃起,就越來越熾旺,胸口燃著一團求生烈火。
這個男孩還沒有名字。
人不能沒有名字就死去。
她在水流中載沉載浮,急促地呼吸著,並將空氣送入孩子口中。河面下,一片漆黑。是不可思議的運氣,將她帶到那根石柱,讓她有個地方立足藏身。
現在兩艘船都駛遠,她不能再在這裡逗留。
血,從脖子大量湧出。她知道自己還活著是因為寒冷,但是同樣的寒冷正在凍結嬰兒脆弱的生命。
她笨拙地踢水游向河岸。她的身體逐漸衰弱麻木,每一個動作都讓她經歷類似被鞭打的痛楚。她沉下去,嬰兒也沉下去。
不。
她掙扎著浮出水面,但河水突然變得很厚重,根本踢不動。
她拒絕投降。
她的靴子撞上滑溜的石頭,脚趾傳來劇痛。她大叫,忘記自己是在水裡,所以吃了一大口水。她又往下沉,最後奮力一踢,踢離那些看起來很模糊的石頭。她的頭往後倒去,水流將她的下半身帶向前,帶向河岸。
脚下突然碰到升起的河岸。
她手脚並用,使出全力離開河水。她將嬰兒舉在自己脖子前,走上河岸,面朝下地倒在石頭岸邊。她動不了了,全身無力。脖子傷口流出的血染紅了嬰兒。她擠出最後一絲力量,確認男孩的情況。
他没有任何動靜,胸口沒有呼吸的起伏。
她閉上眼睛禱告,被永無止盡的黑暗呑入。
哭,可惡,哭啊……
瓦里克神父是第一位聽到低泣聲的人。
他和教友們躲在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的地下酒窖裡。昨晚蘇聯紅軍開始轟炸布雷斯勞時,他們逃入了這裡。他們跪著祈禱小島能躲過劫難。這座建於十五世紀的教堂,百年來躲過了數個改變布雷斯勞這個邊界城市的重大事件。他們祈禱著,希望上帝能再保護他們一次。
就是在這樣虔誠的靜穆時刻,悲哀的哭泣聲傳到這些修士的耳中。
年邁的瓦里克神父慢慢地蹣跚站起來。
「你要去哪裡?」法蘭茲問。
「貓咪在叫我。」神父回答。
二十多年來,他一直餵河邊野貓剩菜剩飯,所以教堂常聽到野貓乞食的叫聲。
「現在出去太危險了。」另一位修士警告他,聲音充滿恐懼。
瓦里克神父活了大半輩子,已經不怕死亡,反而充滿了年輕人的熱情。他穿過地窖彎身進入那道短走廊,走廊盡頭就是位在河邊的門。以前,都是經由這條走廊,將煤炭從船上運到現在儲存精緻綠酒瓶的地窖。綠酒瓶棲息在灰塵和橡木桶之間。
他走向那扇古老的門,抬起門閂,用肩膀將門頂開。
嗆鼻的黑煙迎面撲來──然後那個哭聲吸引他的視線下移。「我的天……」
支撐這間河邊教堂的扶壁上有扇門,門旁邊趴著一個女人。她靜臥不動。神父快步走到她身邊,跪下來祈禱著。
他觸摸她的頸動脈以確認生命跡象,但已經沒有任何跳動,只剩下血液和傷口。她全身濕透,和石頭一樣冰冷。
死了。
然後,又傳來那個哭聲……從她的另一邊傳來的。
他移向女人的另一邊,找到一個嬰兒。孩子的半身被女人壓著,也被血染得通紅。
嬰兒雖然全身濕透,已經冷到臉色發青,但仍然活著。神父將孩子抱起──好重,因為他的襁褓濕淋淋的。
一個男孩。
他迅速檢查孩子的小小身體,發現那些血不是孩子的,孩子沒有任何傷口。
血,是媽媽的。
神父哀傷地看著女人。這麼多的死亡。他遙望河的另一邊。燃燒中的布雷斯勞,清晨的天空瀰漫著上升的黑煙。槍聲不斷。她是從那邊游過來的嗎?只為了救孩子?
「安息吧,」他低語著:「妳救活了妳的孩子。」
神父抱著孩子走回那扇通往地窖的門。他將孩子臉上的血和水擦掉。孩子的頭髮又軟又細,不過髮色仍然像雪一樣白。他絕對不超過一個月大。
嬰兒在神父的撫摸下,皺著臉越哭越厲害,但他仍然虛弱,冰冷的手脚軟綿綿地垂著。
「哭吧,小東西。」
嬰兒像是回應他的話似的,張開腫脹的小眼睛。看著神父的一雙藍色眼睛,明亮又清澈。雖然大部分剛出生的小嬰兒,眼睛都是藍色的,神父仍然感到這雙眼睛能讓天空湛藍起來。
他把男孩抱得更緊,讓他温暖起來。一個有顏色的東西吸引了神父的目光。那是什麼?他把男孩的脚轉過來。有人在男孩的後脚跟上畫了一個符號。
不,不是畫的。神父摩擦那個符號以確定。
是用深紅色墨水刺上去的。
神父研究著那個符號。它看起來像個烏鴉的爪子。
神父年輕時曾在芬蘭待過很長一段時間。他認得那個符號:那是古北歐民族使用的文字之一,但他不知道是哪個民族,也不知道它的意思。他搖搖頭。誰會對一個剛出生的孩子做出這樣的傻事?
他皺眉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女人。
不重要了,父祖輩的罪惡,都不應該由他們的子孫來承擔。
他將男嬰頭頂上的血擦掉,拉開暖和的長袍包住嬰兒。
「可憐的男孩……一出生就遇到這種事。」
一九四五五月四日清晨 06:22波蘭 布雷斯勞要塞城那具屍體漂在潮濕的下水道汚水裡。是一具男孩的屍體。浮腫的身體被老鼠咬得爛爛的,上衣、褲子和鞋子都被人脫下拿走。在這個被敵軍包圍的城市裡,就連破爛的衣物都很寶貴,沒有東西會被浪費。武裝親衞隊二級上將賈柯•史波倫伯快速經過那具男孩的屍體,噁心的屍體讓他胃部一陣翻騰。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屍體泡在血液跟膽汁裡,內臟外流、腸子裡的糞便四散,即使用濕圍巾摀住嘴鼻,也阻擋不了嗆鼻的屍臭。這就是這場偉大戰爭的結果,並且害他落到如此下場,必須從下水道逃生,這根...


 2009/05/12
2009/05/12 2009/05/11
2009/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