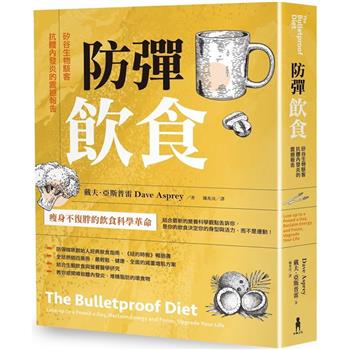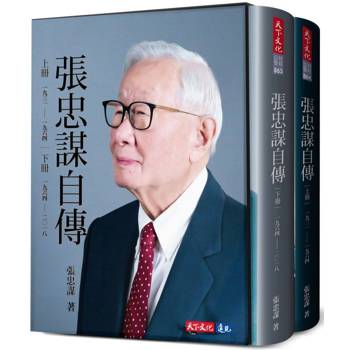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貧窮皇族參上
對蕭逐而言,若因為去國離家三千里而產生惆悵感慨這種情感的話,也僅僅只持續到出了大越國境而已。在他們踏上雲林江之後,他就被葉蘭心興致勃勃的八卦包圍了。
「我祖父皇在這裡養過二奶哦!嘿嘿,結果被我祖母抓X在X!」
「啊,還有這裡這裡,我曾祖父皇在這裡跟我曾祖母跪地求婚,被我曾祖母一腳踹了個山路十八彎耶!」
「前面更是絕對不能錯過!我曾曾祖父皇在這裡被我曾曾祖母一劍架在脖子上,邪魅一笑,說:『公子,你就從了奴家吧!包你跟著我吃香喝辣,奴家絕不納小!』」
諸如此類的八卦伴隨蕭逐整整一路,讓他的愁思半點都不存。偏偏一樣是野史,從她嘴裡說出來就繪聲繪色,彷彿她親眼見過一樣,直聽得蕭逐暗想,她沒去當說書的真是東陸藝術的損失啊……
另外,塑月葉家的剽悍也果然其來有自。
就在抵達瑞城之前,他親身體驗了塑月葉家另外一個角度的剽悍。
事情的起源是這樣的,蕭逐在離開順京的時候,被自家姪兒皇帝拎著耳朵調教,說:「你雖然嫁過去了,但是我給你包了大把嫁妝,你在國內的封地也轉成你的湯沐邑了,你敢讓自己被欺負,墮了我大越名聲,我跟你沒完沒了!告訴你,該揍就揍,該生氣就生氣,你性格太老實了!」
看著自己姪子在面前張牙舞爪口沫橫飛,蕭逐一句「那邊是我丈母娘不是我婆婆」被堵在嗓子裡,沒說出來,還乖乖點點頭。
然後就和葉蘭心一起蹲一邊,看著大越德熙帝熱鬧鬧從珍寶庫裡朝外拉出嫁妝,忽然覺得,說不定這個比自己大了三歲的姪子一直把自己當女兒看待……
一時之間,蕭逐蕭瑟無比,只差捂著胸口對著梅花懨懨地吐上小半口血來表達一下自己的惆悵……
對於他嫁妝的豐厚問題,真都帝的態度是一看禮部送過來的嫁妝單子,立刻豪氣拍桌,說:「姑爺既然都這麼大方了,那我塑月也就——不準備啥了。你說這啥都有,我們再嘰嘰歪歪的,顯得矯情是不是?反正婚後住在蘭心的少凰宮,把牆抹一抹,地縫補一補……」
她話愈說愈小聲,最後在眾臣鄙視的眼神裡,她豁出去一咬牙,說:「咱也不能墮了塑月氣派,給儲君之夫封二千戶的湯沐邑,就從儲君封地裡扣。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他們小夫妻嘛……」
眾臣內心吐槽:好個錢鬼!
這封書信遞到葉蘭心手裡的時候,船隊正在榮陽的江域裡航行,葉蘭心在心裡嘀咕一句:「娘妳真小氣巴拉的!」齜著牙一步一步到了蕭逐房門前,怯怯地敲了敲門。蕭逐開門見她難得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先讓她進來,心裡覺得詫異:「這到底怎麼了?當初她向他求婚這種大事都毫不遲疑的,怎麼今天這樣?」他也不說話,等著她先開口。
葉蘭心在心裡把自己的娘顛來倒去地問候一番:「妳要我怎麼跟人家說,我們家彩禮不如聘禮多?這怎麼說出口啊!」
葉蘭心想了想,終於抓住一個切入點,說:「阿逐,你可知道,東陸之上最窮的皇室是哪家?」
這個問題把蕭逐問倒了,他仔細想了想,輕輕搖頭。葉蘭心繼續說下去:「就是塑月。」
「……?」蕭逐用眼神問了一個為什麼。葉蘭心抓抓頭,繼續說下去:「我朝立國的時候,就皇族問題,太祖皇帝和天下百姓約法三章:第一,永不增加皇莊田地;第二,永不增添宮室行館;第三,永不加宮內使役。第三也就罷了,第二嘛,塑月本來就沒有妾制,也沒那麼多皇子皇女,大家擠一擠就好了。問題出在第一條上……」
說到這裡,她偷眼看了一下蕭逐,看他面無慍色,才繼續說下去:「結果就是……那個……塑月皇室……比較窮……」
「然後?」蕭逐耐心看她。
葉蘭心的眼神飄了飄,低低說:「對不起……跟你帶來的東西比……可能……我這邊的……呃,東西……會比較少……」說完這句,她又想了想,就義一般抬頭看向蕭逐,豁出去似地說:「好吧!其實不是比較少,而是非常少。大概只有封邑二千戶……」
聽了這番話,蕭逐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面前眼神依舊飄啊飄的女子,忽然伸出手,把她一雙手握在手裡,一雙漆黑美麗的眼眸定定看她,輕聲道:「妳認為我會因為這個而生氣?」
葉蘭心看著他,搖頭,然後自動自發坐上他大腿,手在他頸後一攏,撒嬌似地把自己埋了過去。
已經訂下婚約,兩人日後就是夫妻,所以葉蘭心私下的親暱,蕭逐也不再推拒。看著懷裡女子像隻幼貓一樣把頭埋了過來,蕭逐撫摸她柔亮黑髮,輕聲道:「那為什麼要道歉呢?」
「因為……你值得更好的。這樣寒酸,覺得對不起你。」她埋頭在他肩膀上,說話聲音彆彆扭扭。說完之後,頭又埋得更深一些,蕭逐卻一震,然後慢慢溫柔笑開。
他輕輕拍了拍葉蘭心的肩背,柔聲道:「妳知道嗎?在我們大越,女子出嫁的時候,收到的聘禮和彩禮都是屬於那女子的私房了。按照我們大越的規矩,我帶來的這些和妳的那些,都是妳的,我只怕薄待了妳,妳擔心什麼?」
葉蘭心一聽,心裡想著:「幸好剛才自己管住嘴,沒順口溜出『嫁妝』二字。」聽蕭逐這樣說,她也鬆了口氣,拍拍胸口,說:「那我就放心了,我的封邑保住了。」
「?」這關她封邑什麼事?蕭逐不解地看她,她從袖子裡把真都帝的信拿了出來。「因為母皇說,給你的封邑從我的封邑裡扣啊……」
「……」一瞬間,蕭逐蕭瑟了。
這是怎樣貧窮而剽悍的皇室啊?
把信遞出去,葉蘭心放下心裡一塊大石,蹦著就出去了,喚來蕭逐的屬官,吩咐把蕭逐的嫁妝看牢些。屬官滿頭霧水地看她,她滿臉嚴肅,說了一句:「最近晏初回宮,他的用度不算在舅舅帳上了,我怕我母皇窮瘋,連自己女婿嫁妝的主意都打。」
先不論會讓自己女兒有這種想法的娘,單論能想到這點的女兒,就不得不讓人拜服在塑月皇族的剽悍之下。
這件事之後,從蕭逐到大越使節,都開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塑月皇族了……
然後,當船隊順著雲林江而下,即將到達塑月邊境的時候,蕭逐才真正有了一種從骨子裡生出的寂寥。
他有生之年,從未想過自己也會有今天這樣的際遇:和親而來,到達異國他鄉,成為一個未來女帝的丈夫,與她一起統治一個偌大帝國。
這裡就是他將為之奉獻,並且終老的國家。
然後,更難以釐清的是,他自己的心情和定位。
他並不是第一次成婚,他和元妃柳氏成婚之時,少年夫妻恩愛綢繆,那時誠惶誠恐,心下既害羞又歡喜。現在明明是第二次,沒有了惶恐,心底下的不安卻愈來愈濃。
大概是,第一次婚姻,他是主導者;而這次,他最多只是一個協力者。
話說,還真快就體會到了遠嫁和親的公主們的感覺呢!
奇怪的感覺漸漸在胸裡蔓生,他看向身旁與他共看面前波光的女子。彷彿察覺到他的視線一般,葉蘭心轉頭看他,定定看了他片刻,微笑,卻什麼都沒說,只是伸出手,握住他的手。黑色和紅色的廣袖垂拂而下,遮掩住那兩隻交握的手。
被她的手握住的一刻,他低頭看去,絲綢交疊之間,露出一痕她纖細的指尖,忽然就有一種無比奇妙的感覺——身旁這個人即將成為自己的妻子了。
握了片刻,葉蘭心抓著他的手提到兩人面前,笑得見牙不見眼。「你的手好冷。」
低頭看了看她,蕭逐反握住她的手,說:「……我會努力的,努力讓我們兩個人都好好的。」
葉蘭心沒說話,只是仰著臉看他,淡灰色的眼睛映著蒼天白雲,無限清澈深遠了起來。
被他這樣看著,蕭逐心裡的不安慢慢散去,唇角帶出一線笑意。她跟著笑了,握住他的手搖了搖,笑道:「那是自然,你是我選中的人,我信你。」
蕭逐笑了開來。就在他們培養感情的時候,有禮官來報,說已經快進入塑月國境,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從前天開始,船上似乎就在叮叮咚咚地不知道搞什麼,蕭逐也不明白,看了一眼葉蘭心。葉蘭心點點頭,拉著蕭逐去更衣。
侍女為兩人換上祭禮用的袍服,再出船艙的時候,蕭逐才發現整個船隊上下全換了祭祀的用品,下了錨,停在江中。
不遠處就是分隔沉國和塑月的內江,他們一會兒就要從這條內江進入塑月國境,現在為何停在這裡?
蕭逐正思忖,葉蘭心拍拍他,指向內江江口,道:「前面就是我朝純皇帝的皇陵,每到這裡,我塑月上下都要祭祀的。」
「皇陵?」蕭逐瞪大眼睛,看著一平如鏡,很明確什麼建築都沒有的江面,腦子裡快速掃過關於塑月純皇帝的資料。
塑月純皇帝是開國太祖的嫡親姊姊,少時戰亂離家,出而為黃冠,後來輾轉和太祖皇帝相認,也不還俗,就以道姑的身分輔佐養育太祖,終於使太祖得以開國立朝,她本人卻在太祖登基之前就去世了。太祖登基之後,感懷姊姊,便追封為純皇帝。
歷史上對這位皇帝提得很少,蕭逐也沒怎麼留意,今日看到面前一片蒼茫水域說是純皇帝的皇陵,不禁感到奇怪。
葉蘭心卻笑起來,淡淡地說:「純皇帝確實就葬在這裡。她過世前留下遺囑,死後將她焚為飛灰,撒入這內江之中。」
東陸之人極為重視全屍,這樣要求匪夷所思。蕭逐看著葉蘭心,葉蘭心看了他一眼,輕輕嘆氣,道:「你知道沉國的楚靖王吧?」
蕭逐點頭,數百年前,恰逢沉、大越、塑月三國先後立國,湧出了無數豪傑,塑月之純皇帝,沉國之楚靖王,都是一時之選。
這時船已開動,前驅的船上飄來祭皇陵用的《肅咸樂》。葉蘭心原本靠在船頭,音樂一起,也端正起來,目視前方,輕聲說道:「當時天下紛亂,楚靖王和純皇帝少年時代曾一起共游天下。楚靖王曾發下誓言,有生之年,絕不踏過純皇帝埋骨之處,必將殘生守護,不離左右。後來純皇帝回國輔佐太祖,楚靖王則跟隨兄長創下沉國。十多年後,內江一戰,我國不敵,岌岌可危,純皇帝自刎於江邊,焚骨成灰,撒於內江之中,一江遂成埋骨之地。楚靖王遵循諾言,不再進兵一步,就在內江旁築屋而居。」
聽到這裡,蕭逐向江面遙望而去,片刻之後,默默閉上眼睛,感覺帶著水冷的江風從他鬢邊拂過,絲絲的寒意。
數百年前,就在這裡,兩國大軍以命相搏,一個女子自刎而死,血濺五步,阻止大軍步伐;然後在江的對面,一代英雄枯守墳塚,漫漫拋擲年華,只為昔年千金一諾。
怎樣的少年意氣風發把臂同遊,才能有這樣誓言?只要略略一想,明明他未曾見過的場景,幾乎如他親見所見般躍入他的腦海裡。
想當年,必然有少年少女抱著膝蓋從這條大江上順流而下,那少年握了少女的手,悄悄說,若妳死了,我就在妳身邊陪妳一輩子。
然後,十數年後,大軍相持,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那個女子血濺江水,焚屍拋骨,擁抱不得。
思緒輕輕飄著,耳畔塑月儲君的聲音依然在訴說著:「當時沉國太祖已歿,嗣皇帝尚且年幼,一切朝政軍務都靠楚靖王守護,他遵守誓言,止步內江,沉國也就沒了再侵之力。直到楚靖王死後,兩國再度交鋒,塑月那時雖然沒了純皇帝,卻已得到皇夫葉氏的六州之地,三十萬兵馬,沉國自然沒有比較佔優勢。最後,以內江為界,兩國劃定疆域。所以我們經過內江的時候,都要來祭奠純皇帝。沒有她,不會有今日塑月。」
正說話的時候,船隊已漸次在一個碼頭前停下,岸上早停滿了來迎接的人,禮樂喧天,香煙繚繞,正在祭奠。
葉蘭心朝碼頭一指,「那裡就是純皇帝骨灰初入水的地方,也是我們要登岸之處。」說罷,她手指劃了個半圓,指向對面。「那邊就是沉國。」
說到這裡,看蕭逐沒有表情,葉蘭心忽然笑了笑,拍拍他的手。「我的意思是,論起仇怨,大越和塑月那種追人沒追到的事不算什麼,我們共同的仇家是沉國。」
聽她說到這裡,蕭逐猛地一警!
在向蕭羌告辭之前,他曾被招入宮中,蕭羌詳詳細細地跟他說明了自己未來計畫,明確告訴他,三年之內,必然要對沉國再次用兵。
沉國兩年前和大越交兵,慘敗而回,被割去了土地,現在大越已做好了再戰的準備,沉國卻還沒緩過氣來,自然要趁機一絕後患,讓病虎痊癒是絕對要不得的。
葉蘭心這番話,就等於在告訴他,如果大越對沉國用兵,那麼塑月會有所支援。
他思考的時候,船已靠港,正準備下船,音樂也一改,奏的是《迎神曲》。葉蘭心往搭上的舢板走了幾步,回頭看看他,又走回來,扯了扯他袖子。蕭逐跟她一起下船,悄聲問了一句:「這話什麼意思?」
葉蘭心現在滿臉堆著一點都不像她的優雅從容笑容,一邊朝周圍城市村落蜂擁而來觀禮的百姓揮手,一邊輕聲笑道:「就是說,如果大越要對沉國用兵的話,大家盟國之屬,自會支持。」
蕭逐聽得心裡一跳,面子上卻雲淡風輕的一笑,「妳說笑了。」
「呀,我如果是德熙帝的話,肯定趁這個機會拿下沉國,難道還要等沉國養精蓄銳,再一較高下嗎?」葉蘭心笑著說完,人已到了岸上,立刻被官員們包圍而上,略寒暄幾句,就向祭祀的臺上而去,行主祭之禮。
原來之前江上那一大段故事全為剛才這輕飄飄的一句鋪墊。
看著遠去的那個玄衣女子,蕭逐不由得想起陽泉的那句話。陽家的年輕族長說她是天生帝王,現在看來,確實不錯。
蕭逐現在還不算塑月皇族的一員,這祭典不關他事,就在一邊看著。
所幸塑月不若大越一般繁文縟節,燒了香,唸了悼詞,一行人就按照身分各自登車,向瑞城而去。
前方瑞城同時扼守榮陽、大越、沉國三國邊境,乃是塑月第一重鎮,駐守這裡的親王,就是葉蘭心的舅舅──安王葉詢。行程早已定下,這裡祭祀完畢,就要去拜見葉詢了。
蕭逐和葉蘭心在一輛馬車上。上了馬車,葉蘭心很嚴肅地對蕭逐伸出兩根指頭。
「現在你有兩個選擇:一,當我的抱枕;二,我當你的抱枕。」
「……」大越平王殿下看了她片刻,平靜地給出第三個答案:「我要看風景。」然後,他又瞄了一眼作勢打算撲過來的儲君殿下,說:「妳要是撲過來的話,我不介意點了妳的穴道看風景。」
所謂拳頭才是硬道理啊……葉蘭心咬著手絹鬱悶地縮在馬車角落。
蕭逐拒絕她之後其實挺想和她再說說話的,但根據過往的經驗以及葉蘭心死皮賴臉的個性……他決定安心看風景,順便想一想,待會兒見面,葉詢能問自己什麼,而自己又該怎麼答。
他可沒有忘記,葉詢是晏初的養父,榮陽一行一路波折,最後傷了葉蘭心一隻右手,都和晏初脫不了關係,就算葉詢沒有指使晏初,至少也是默許,這些事情,他全都記著。
葉蘭心說不關晏初事,晏初不會背叛她。她不追究,沒關係,他替她記著。
這麼想的時候,他那雙清澈眼眸裡有了一線銳利之色,向旁邊雙手托著下巴看著他發呆的女子看了一眼,掉轉視線,繼續看向窗外。
塑月九月正是風景好的時候,層巒疊嶂,層林盡染,讓人望之立刻心生開闊之感——看到美景是很好,但是,誰能告訴他,為什麼看著看著,這馬車就開始朝深山裡拐了?
如果說最開始出城他還能理解,說不定安王不喜歡城裡嘈雜,喜歡住在郊外也說不定,但是眼看道路兩旁漸漸地連田地都沒了,開始拿荒山當背景,蕭逐倒吸一口涼氣,第一反應是:塑月皇族再窮也不至於穴居吧……
葉蘭心一直看著他,一眼就看出他的疑惑,喂了一聲,驀然伸出手去抓住他耳朵,把蕭逐整個人向他面前一拖。蕭逐吃疼,嚴厲地瞪了她一眼,說:「我告訴妳,我要是被拉成兔子耳朵,妳要負責。」
看他耳朵被自己拉紅,葉蘭心俯過去吹了吹。聽到這一句,無賴地笑起來,乾乾脆脆往他肩頭上一趴。「呿,怕什麼,到時候大不了讓你把我耳朵也拉成兔子樣就成了,兩個人都長耳朵,還可以打結咧!」
「……」他錯了,他居然有那麼一瞬間指望這女人腦子裡有正常想法……他錯了。
趴在他肩膀上,葉蘭心朝外抬了抬下巴。「你知道的,我舅舅早年在沙場上和人奮戰,弄得一身傷病。這附近有個冰火洞,從那時候開始,他就一直在這裡療養。舅舅傷得極重,甚至不能踏出洞外一步,所以才讓母皇繼位。」
「……」沒想到還真是穴居呢!蕭逐沉默了。葉蘭心看著他,卻扯出一個懶懶笑容,不知從哪裡拉出一柄泥金摺扇,敲了敲蕭逐的肩膀,道:「我說,杜笑兒也在那裡哦!」
「——!」聽到杜笑兒三個字的一瞬間,蕭逐一雙眼睛猛地瞪大,他一把握住葉蘭心雙臂,把她稍微推開,直直瞪著她,剛要開口,卻發現自己什麼都說不出來。
該說什麼?
他即將成親的妻子笑吟吟對他說出他至今難忘的深愛女子的名字,他該說什麼?
蕭逐從來不像他風流多情的姪子皇帝,他向來老實正直,被人笑說,這樣木訥,枉費辜負了那張絕好皮相。
看他愣住,葉蘭心的心情不由得大好起來。二話不說把扇子一丟,又抓住他耳朵,把他朝面前拽了拽。
他們兩人挨得本來就極近,這一下,蕭逐的鼻子幾乎觸到她的臉龐,她越發笑得見牙不見眼。「阿逐,你想見她嗎?」
聽了這句,蕭逐心裡一驚,看著葉蘭心,心裡一片茫茫然。
想不想見她?見杜笑兒,自己愛了那麼久的女子?
可是見了又能怎樣?
她不愛他,他即將成親,有需要他去愛的女子。
不由得想起,杜笑兒離開大越宮廷前夕,在御池旁邊,他幾乎丟盡所有尊嚴,那樣卑微地僅問她一句:「妳可曾喜歡過我?」
那個女子對他恭敬躬身,告訴他,她從沒有一天愛過他。
那麼,現在見了又能怎樣?
低頭看著懷裡的女子,葉蘭心一雙淡灰色的眼睛定定看他,依舊是笑盈盈的,沒有一點動搖,他本來隱隱作痛的心情在看到那柔和眼神的瞬間,奇妙地慢慢平復。他很認真,很努力的想了想,搖搖頭,說:「不,我不去看她了。」
事已至此,再去看杜笑兒又有何意義?他現在要做的是好好保護葉蘭心,好好愛她,和她踏踏實實過完下半生。
其他的,都是前塵浮雲。
聽到他這麼說,語氣堅定,葉蘭心卻笑起來。「啊,你不去是吧?我倒是要去見她呢!」
「妳要去見她?」莫名的,蕭逐心裡抽動一下。
葉蘭心繼續微笑,「是啊,我要去見她,德熙帝可是托我去看看杜昭儀過得好不好。」說完,她想了想,看他,聲音柔和,道:「再說,你也想知道她到底好不好,對吧?」
蕭逐愣了一下,隨即苦笑。
她真的能看穿自己的想法。他在她面前,無所遁形。
他確實是這麼想的,但是……
大越的平王殿下平靜地伸手到自己後方,把塑月儲君神不知鬼不覺伸到他衣服裡的一隻爪子拎出來。「蘭心,我覺得我們還是說話歸說話,不要亂動手動腳的好。」
第二十二章 葉詢
走了大半日,過午時分總算到了冰火洞外。
冰火洞在一個山谷之中,四周峰壁插天,只有一條羊腸小徑通向深處。按照道理,這裡好歹是葉家現任族長安王葉詢住的地方,目光所及,卻一個人都沒有。
所有隨行官員全部駐紮在谷外,進去的只有熒惑和蕭逐、葉蘭心。
入谷之前,葉蘭心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跟牢熒惑,不然很容易迷路。蕭逐不解,葉蘭心解釋了一番,他才知道,不單晏初是葉詢的養子,就連熒惑,都是葉詢一手調教而出。
東陸之上列強紛立,其中以龍樓最為神祕。不僅遠在內陸群山之中,自古閉關鎖國,從不與他國來往,又以巫蠱之術立國,更平添了一層神祕。
伏師桔氏一族是在塑月立國之初從龍樓而來,即以幻術而揚名天下,但是傳承至今,真正高深的祕術多半失傳,只剩下一些皮毛。至於葉詢,他的母親是龍樓皇族之女,也是千年以來,唯一一個嫁入其他國家的龍樓皇族。當年剛嫁入塑月之時,上一代的伏師就慕名而去請教,一番話談下來,讚不絕口,說這位皇后祕術之精,說不定猶在初代伏師之上。
但這位皇后甚是短命,在葉詢七八歲左右便去世,但即便只是這七八年時間,葉詢已得了母親真傳。後來熒惑出世,被譽為百年來桔家第一天才,便送到葉詢這裡來學藝。
聽了葉蘭心這番解釋,蕭逐猛地想起之前兩人被困在幻術中,葉蘭心曾說過,能做到這樣程度的人,她認識兩個,其中一個是熒惑,那另外一個應該就是安王葉詢了。
到了這裡,熒惑看起來也頗有幾分心事,一路不語,僅慢慢走著。蕭逐對他沒什麼好感,他不說話,自然他也不搭話。
看身邊兩個人都一臉陰沉地悶著,葉蘭心很識相地也閉上嘴。
所幸沒有沉悶多久,片刻之後,在山谷裡繞了好半天,眼前霍然開朗,看到一個洞口,洞口收拾得分外雅致,下面是綠茵一樣的草,上面一架紫藤,九月深秋了,居然還盛開著,垂下女人鬢邊流蘇般的花朵。
來這地方之前,葉蘭心就跟蕭逐說過,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按她的說法,玩巫幻之術的主兒住的地方,你覺得能啥樣?
於是蕭逐連那架不合時節盛開的藤花都沒多看第二眼,就進了洞。
哪知洞裡和外界完全不一樣,站在洞口的時候,還感覺洞外溫度適宜,涼風習習,哪知一踏進洞裡,就這一步之差,一股寒風襲來,蕭逐身負武功,都覺得渾身一陣激靈,惡寒透體而入!
熒惑走在前面,全不在意似地伸手到一個暗格裡摸了摸,拿出三個項圈,也不看身後,凌空一拋,其中兩個分毫不差地落在了蕭逐和葉蘭心手裡。
項圈是黃金打造,上面綴了一塊冰白裡帶著絲絲焰紅的石頭。蕭逐學著熒惑的樣子戴上,項圈剛一觸體,立刻一股溫暖席捲上四肢百骸,那股陡然寒氣便消失似地再也感覺不到了。
這地方不愧是傳說中的休養聖地,果然處處透著奇詭。蕭逐心下讚嘆,回頭看了一眼葉蘭心,發現儲君殿下躲在他後面沒進洞,一絲風都沒吹到,脖子上項圈已經掛好,明顯熟門熟路的樣子。
蕭逐倒鬆了口氣。葉蘭心畢竟是個沒有武功的女子,被這風一吹怕要受風涼。
戴好項圈,葉蘭心向前一步,和蕭逐並肩向裡走去。她顯然對這裡熟極了,看都不看路,顧著向蕭逐指點洞裡別致景色。蕭逐一一看去,也不禁感嘆造化神奇。
這洞裡四壁皆是他頸子上掛的那種冰白帶焰紅的石頭,偶爾碰到,入手是冰涼的,但是稍微久一些,又慢慢泛起一股熱力。蕭逐覺得好奇,摸了摸頸上的石頭,入手溫涼,卻不像石壁一般,又冷又熱,溫度恆定,毫無變化。
洞內深幽,觸目所及,只有幾個地方能看到燃著蠟燭,但是安放位置巧妙,借著如鏡面般光滑的石壁反光,洞內絲毫不顯得陰暗,教人不易看出蠟燭的確切方位。
這洞內極是曲折,走了大概三四丈遠,便看到有幾條岔路。蕭逐目力不弱,一眼就看到岔路修整平坦,顯然也有人在使用。
就這麼七拐八繞到了深處,蕭逐暗暗把路全都記下來。片刻之後,邁過一道門,就在看清面前景物的一瞬間,蕭逐整個人愣在那裡。這個千軍萬馬中從容而過的青年,完全被眼前看到的奇景所震懾。
他面前是一個山谷般廣闊深遠的山洞,朝前幾丈,有一個足有百丈之寬的漆黑深洞,從他方向看去,此洞深不可測,彷彿一直蔓延到地心中一般。就是這樣廣大深洞之中,一股地心澎湃烈火洶湧狂囂席捲而上,彷彿要燎天而去——然後,就在這般洶湧地火燒到中途之時,由洞穴頂端一股雪盈冰晶靜謐而下,狂囂地火甫到半空,即被晶瑩雪柱無聲凍結,澎湃地火竟然被凍結在冰雪瑩潤之中!
冰火相接之處,如同外面的洞壁,冰雪之中絲絲如焰火紅,漸往下去,天冰漸消漸融,便能看到冰柱裡火焰緩慢躍動的奇景。
地火天冰便在這空間裡形成無比瑰麗的景象,洞穴上半部分如冰洞雪窖,下半部分地火脫離天冰凍結,地面便如溶岩地獄,這大概就是此冰火洞之名的由來。
這樣天地搏擊的奇景,蕭逐不要說看過,就連想都沒有想過,他足足愣了好一會,才感覺到身後有人捅了捅自己。他回過頭去,看到葉蘭心笑瞇瞇看著他,很滿足似地瞇起眼睛,說:「很漂亮吧?」
蕭逐本想答一句「是」,但看到她一臉「你誇這漂亮等於誇我漂亮」一樣搖尾巴等待誇獎的樣子,蕭逐就立刻不想答是了,反而眼波淡淡掃過去,輕聲道:「就算這漂亮,也跟妳無關。」
這句話一出口,他就覺得自己怎麼說得這麼賭氣,剛要開口挽回,卻看葉蘭心大大方方挽了他的手,笑吟吟邁步向裡走去,笑道:「這裡好歹是塑月的地盤,你誇一句我的祖國漂亮,我心裡就歡喜。」
聽了這一句,蕭逐心裡一動,低頭看去,只見在四壁冰白火紅繚繞之中,她一張面容素白如玉,神情平和,睫毛微微垂著,籠著一雙灰色眸子如煙如水,便有了一種微妙的風情。看得蕭逐心裡一怔,愣了一下,才急急收回視線,覺得自己看到了什麼不該看到的東西。
被她牽著的手,也沒來由地燙熱了起來。
熒惑已經轉過那地洞去了,葉蘭心也不著急,慢慢牽著蕭逐的手向前走去。
她對這裡很熟,哪裡轉彎哪裡突起,哪裡高了哪裡低了,都低低說來,柔軟吐息全灑在他頸邊肩上。蕭逐忽然有些恍惚,覺得路變得遙遠起來,總不到盡頭。
四周地火天冰,雪白囂紅,這樣長的一條路,只有他和她攜手走來,慢慢而行。
心底無限柔軟起來。蕭逐輕輕喚了聲「蘭心」。葉蘭心抬頭看他,唇角柔軟,應了聲:「嗯?」蕭逐也笑了,沒說話,緊了緊她的手,向前而去。
非常奇妙,她那一聲「嗯」裡,蕭逐覺得,自己後半生情動情生,都能和她慢慢走來了……
冰火奇景的後面很多岔路,他們走進了其中一條。走了片刻,眼前霍然有陽光明亮,卻是一個極大的山洞,洞頂有半面透光,燦爛陽光射了進來,正射在洞中一個小湖上,照得四周碧草茵茵,上面點綴各色花朵,如一匹錦緞。
湖面上幾間精舍,高處有個小亭,亭子裡坐了兩個人正在對弈,旁邊垂手侍立的人修長清瘦,正是熒惑。
亭中對弈的兩個男人,都是一色玄衣,其中面對他們而坐的那個,看上去四十上下,氣質雍容,眼睛一抬,看到他們來了,拈著玉白棋子的手輕輕招了招。看到他,葉蘭心也「咦」的一聲脫口而出,失聲喚了一句:「父君,你怎麼來了?」
蕭逐心下一凜,那個中年人居然是葉蘭心和晏初的父親,真都帝的夫君,永茂帝君。
聽了這一聲,那個背對他們正待落子的男人徐徐轉過頭來,卻是一名二十七八,容貌秀雅的青年,看到兩人,輕輕一笑,道:「怎麼,你父君來不得?」
這樣一句,聲音柔和,只有寵溺,全不見一點兒責備。葉蘭心也不在意,笑嘻嘻牽了蕭逐過去,先帶著蕭逐到永茂帝君面前磕頭,然後轉向朝青年男子行了單膝禮,喚了一聲:「王舅。」
然後,今天不知第幾次,蕭逐又被驚了。
他反射似地立刻抬頭。他面前玄衣廣袖的,正是塑月葉氏一族的族長、年名會的最高年官、當今真都帝的兄長、葉蘭心和晏初姊弟的舅舅──葉詢。
那卻是一個和他想像中截然不同的男子。
葉詢年長真都帝十幾歲,按照年紀推斷,現在應該是已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可是站在他面前的卻是修長清雅的一名青年,看上去最多不過二十七八年紀,容貌秀雅,氣質溫煦,站在葉蘭心身邊,有如她的兄長,哪裡像是她的舅舅。
來之前,葉蘭心就跟他說過,這冰火洞裡,鮮花不敗,草木不腐,進來之後,時間流逝地極慢,杜笑兒就是因為身中無藥可解的慢性毒藥,離發作只剩幾個月,才被送到這裡,希望借冰火洞的這個特性來壓抑她所中的劇毒。
之前他還半信半疑,現在有葉詢這活生生的例子在面前,他也不得不信了。
葉詢想必很習慣第一次看到他的人慣有的驚詫,對蕭逐微微一笑,輕輕招手,示意他靠近自己一些。
蕭逐不明其意,但是長輩有喚,他不得不從,就跪近了一些。
然後他看到葉詢俯首向他,他只覺得脖子一涼,領口被拉開了寸許。蕭逐還以為自己衣服上有髒汙,正緊張的時候,便看到葉詢若無其事地轉頭,悠悠地對帝君說了一句話。
他說:「沒事兒,沒印子,小葉子應該還沒吃到平王。」
「——!」有那麼一瞬,蕭逐只想昏倒。
所謂塑月皇族。
蕭逐聽了這句,立刻當場石化。葉蘭心則巴著永茂帝君,跳腳不服,「嘖!我才不要偷吃呢,要吃也要正大光明的吃!」
蕭逐已經完全說不出話來了,葉詢卻只是溫雅一笑,然後毫不留情地朝死穴戳過去。「那是因為妳撲過去會被一拳揍掉牙吧?」
葉蘭心立刻哇呀呀地撲到葉詢身上撒嬌。然後剛才被女兒當抱枕一樣手腳並用撲纏上來,也依然保持優雅笑容的帝君伸手把石化狀態的蕭逐攙了起來,語氣榮辱不驚,雲淡風輕地說:「家風如此,請見諒。」
蕭逐忽然有了預感,自己未來幾十年生命裡,大概也要和面前這個男人一樣,對所有被塑月皇族的剽悍驚悚到的人們說,家風如此,請見諒。
這是多麼令人掩面悲泣的人生啊……
在這一刻,還處在二十六年華一朵花水嫩嫩的平王殿下,就早衰地覺得,他的人生真是到了塑月之後就沒啥好指望的了啊……
又寒暄了一陣,帝君微笑微笑再微笑,那微笑下散發出的警告好歹讓葉家的另外兩位直系收斂了些。喝過一杯茶,帝君起身,笑看向蕭逐,道:「平王和我一起走走,如何?」
蕭逐連忙起身微躬道:「全聽帝君吩咐。」
葉蘭心也站起來,對葉詢擺擺手,說了一句:「那我也去玩了。」就跟著蕭逐和帝君一起朝另外一邊的出口而去。
知道她要去見杜笑兒,蕭逐只略看了她一眼,收到葉蘭心拋回來活似眼睛抽筋的一枚媚眼,渾身惡寒地趕緊走開了。
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安王葉詢輕笑著看向自己剛才拉過蕭逐領子的指頭,臉上慢慢地,露出一個微妙的笑容。
「……啊……蕭逐啊……」他輕輕地這麼唸著。
永茂帝君一直都笑瞇瞇的,蕭逐又從來不是個多話的人,便默默跟在帝君身後漫步。走了半天,面前還是迂迂曲曲的路,蕭逐也不得不驚嘆於這個冰火洞佔地之廣大。
老是不說話也不是辦法。蕭逐憋了一會兒,開口說了一句:「冰火洞真是曲折迷離,很容易就迷路呢!帝君能把路線記得這樣牢,實在了不起。」
前面走得異常堅定毫不遲疑的永茂帝君聽了,也沒回頭,只是點點頭,說:「嗯,確實是,我也是第一次來,沒想到真的這麼大。我一個轉彎都沒記住。」
聽了這話,蕭逐腳下不知怎地一滑,差點摔在地上。看著前面還施施然走得氣定神閒的背影,沉默了一會兒小心問道:「……那……要是迷路了怎麼辦?」
帝君一點兒都不急,笑吟吟滿不在乎地答道:「沒事兒,安王要是發現我們一兩天都沒走回去,應該會來找我們的。」
「……」這就是所謂的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嗎?啊不,是他太膚淺了,剛才居然還覺得也許永茂帝君是不一樣的,現在看來,分明是蛇鼠一窩……不,不對,這樣豈不把他自己也罵進去了?對了,他是出淤泥而不染!嗯!沒錯!
堅定自己是正常人的信念後,蕭逐無奈跟上永茂帝君迷路而悠閒果斷的腳步……
怕啥,不就一兩天嘛,他習武之人沒在怕的!
兩人一路迷路前行,走著走著,前面沒路了,只有一扇門。按照一般理解,應該轉頭向後走,但是很明顯,永茂帝君是不走回頭路的典範,勇往直前地一掌推開門,那義無反顧毫不猶豫的模樣,看得蕭逐心裡陡然湧起一個感想:這面前要是一堵牆,帝君大人也會照樣一掌拍開,接著往前走吧?
門吱呀一聲洞開,內裡極為寬敞,觸目所及,牆壁上和靠牆的地上擺滿了兵器架子,有各種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兵器,中間一大塊空地,看起來是個小型的室內武場。
帝君看到屋裡東西,愣了一下,隨即輕輕一笑,信步走了過去,到了一個武架面前,足尖一點,只看武架一震,最上方兩柄長劍震出,剛好落在帝君掌心。
這一下乾淨俐落,蕭逐也另眼相看。想起剛才和帝君行走對談之時,雖然姿態沉穩,他卻沒看出帝君身懷武功。現在看來,原來永茂帝君已到了返樸歸真的程度,不可小覷。
帝君掂了掂手裡長劍,隨手丟了一把給蕭逐,只聽匡噹一聲,帝君長劍出鞘,雪亮鋒刃指著對面蕭逐,輕輕一笑。「好歹在和陛下成婚之前也當過將軍,看到這些東西不免技癢,平王要不要陪我活動一下筋骨?」
這……這問題有點難辦……
永茂帝君武功雖高,但跟蕭逐相比猶有差距,你說這要是贏了他,好歹是自己公公……呸呸,是自己老丈人,面子上不好過;要是輸了,他好歹是現在東陸第一高手,明顯太造假了,說不過去。只好應付上幾百個回合,讓自己贏得艱難一點好了。
蕭逐接過劍,擺了一個晚輩見長輩的起手式,道了一聲承讓。帝君輕笑,「不用這麼嚴肅嘛!喏,平王要是贏了,我就給平王一份彩頭如何?」
我可以說,你們葉家的彩頭我一點都不想要嗎?雖然心裡這麼想著,蕭逐臉上還是一笑,輕輕頷首,手腕一抖,挽出三朵劍花,正是向長輩請求指點的劍招。
帝君看到這一手劍法,眼裡精光微動,臉上卻依舊悠閒含笑,長鋒輕劃一個半弧,一聲金鐵交鳴,兩人手中長劍同時震動,卻沒有真氣激蕩。原來兩人這一劍上,都沒有貫注內力。
狡猾的小子。帝君看著一劍刺來的蕭逐,心裡暗笑。
剛才若自己劍上帶了內力,震飛他的長劍,蕭逐就可以借坡下驢,顧全雙方面子了。
啊,自己女兒找到這樣一個男人嫁,似乎也是很不錯的事情。
帝君一心二用,手下劍招卻絲毫不見鬆懈,逼得蕭逐也只能認真應對,兩人走了快一百個回合時,帝君忽然回手撤身,隨手一拋,長劍落入武架。他輕笑出聲,拍拍手,道:「好了好了,給老人家留一點面子,別真讓我輸得太慘。」
蕭逐聽得心中一凜,立刻躬身,剛要說話,卻被永茂帝君揮揮手,制止了。
帝君負手而立,環視這間武室,過了片刻,輕輕一笑,換了個話題:「平王,你覺得這冰火洞裡的牆壁,像不像琉璃?」
這冰火洞裡牆壁宛如天冰蘊火,像極了琉璃,蕭逐點點頭。帝君看了他一會,忽然非常溫柔地笑了起來。
「在我這個做父親的看來,我的女兒也很像這琉璃呢……」
「……」好吧,琉璃清澈,如果說對自己的欲望非常坦白也算的話,那麼葉蘭心確實滿像琉璃的。
——此時的蕭逐並不知道,永茂帝君所說的琉璃,並不是清澈通透,心無塵埃,而是離於愛憎,不生憂怖。
說到自己的女兒,帝君臉上泛起淡淡笑意,但是隨即,眼裡流過一線奇妙的感傷。他向前幾步,走到蕭逐身前,看著向自己禮貌頷首的青年,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慢慢笑道:「我那個女兒呢,是比較……呃,出格了一點兒。我呢,從她出生開始,就沒盡過父親的義務,雖然對你不公平,但是為人父者,還是希望你能讓蘭心幸福。因為這麼多年……」說到這裡,帝君頓了頓,眼神裡奇妙的感傷慢慢溢出來。片晌,才開口說道:「你對那孩子而言,是唯一特殊的人……所以,請無論如何,別讓她不幸。」
那是,一個父親對即將娶走自己女兒的男子的託付。
他在拜託,希望自己能照顧好他唯一的女兒,讓她幸福。
他的父親去世得早,他從未曾好好孝順過生育自己的人,現在,聽到這個塑月帝國最尊貴的男人這樣拜託他,心裡油然而生一股微微酸楚的暖意。他低頭,答了一聲:「是的,我會盡量讓儲君一生安樂無憂。」
「還有你自己也不要忘記。」帝君溫和的聲音從他頭頂上方落下,男人覆在他肩膀上的力道溫和地加重,有一種讓人安穩的力量。「你也要幸福啊!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情,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幸福,只有你們兩個人一起幸福,我的女兒才會幸福。嗯?」
那是……如同父親的感覺。
如果自己的父親還活著的話,大概也是這樣吧?
蕭逐沒有說話,他抬頭看了一眼面前笑容溫雅的中年男子,深深地用力點頭。
「好孩子。」帝君笑道,然後一擊掌。「對了,說到給你的彩頭,就是這個。」他從懷裡取出一個小錦囊,遞給蕭逐,示意他打開看。蕭逐看去,裡面是一個印璽和一疊地契,他不明白地抬頭看了一眼帝君,帝君微笑。「陛下劃給你的湯沐邑是蘭心的封地對吧?你肯定不會用的。這是我一半的湯沐邑,你好歹也是塑月帝國儲君的丈夫,總要有自己的一份財產,若真到了你需要賞賜下官的時候,拿的是鑄著大越徽號的銀錠,豈不讓我塑月很沒面子?」
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再拒絕下去也矯情,蕭逐鄭重收好錦囊,向帝君行禮。帝君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若無其事地邁著果斷的步子向門外走去。「來來來,讓我們繼續走走看,看到底能通到哪裡吧!」
剛才打了一場,體力說不定不夠撐上一兩天……雖然轉著這樣的念頭,但依然只能跟隨的蕭逐,認命跟在帝君身後,邁出了步伐……
然後幸好,他們在晚飯之前摸了回去。
幸好幸好,肚子沒咕嚕咕嚕地叫啊……
第二十三章 盡是前緣
杜笑兒是個怎麼樣的女人呢?
在慢悠悠晃晃蕩蕩朝杜笑兒所在的地方走去的時候,葉蘭心一直在思考這個嚴肅的問題。
就蕭逐這一路上的弱女保護態度看來,那應該是一個小白花一般纖弱的女子吧!
不過,也說不定是個出乎意料性格彪悍,宛如武則天再世的女人——畢竟蕭逐那種從外表到內在都很極品的男人說甩就甩說揍就揍,又能把德熙帝那隻陰險狡詐的皇帝迷得七葷八素,實在是不簡單啊!
在心裡轉著有的沒的,葉蘭心信步來到杜笑兒所居住的區域之前。
杜笑兒是德熙帝最寵愛的妃子,雖然現在不在宮內,但是為了避嫌起見,她住的地方是在冰火洞裡的最深處,平常往來,都是靠她帶來的一個侍女。她一路走來,私下打聽了冰火洞裡幾個伺候葉詢的下人,對這位異國來的昭儀娘娘都一問三不知。
結果就是,當她站在杜笑兒房門前的時候,她很難得用了一會兒工夫思考自己該說什麼。
塑月儲君葉蘭心推演能力當世無雙,但是,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等她終於把各種可能都推演完畢之後,手剛貼上門打算推開的一瞬間,她只覺得掌心一震,眼前那扇木門眼睜睜地朝她砸了下來——
啊咧,現在這是哪齣?
葉蘭心立刻向旁邊一撲,門板剛好擦著她腳邊砸下去,一股黑煙從裡面咕嘟嘟冒了出來。葉蘭心還沒反應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門裡衝出一個人,一把抓了她就朝外跑,直跑到煙再也熏不過來的地方,兩個人都扶著牆彎腰大口喘氣。過了一會兒,她旁邊那人氣先喘勻了,也不說話,先伸出手在她身上從上到下拍了一遍。
說實話,長這麼大,從來都是葉蘭心猥瑣伸出爪子去拍人,現在陡然遭受祿山之爪襲擊,她渾身僵了一下。對方幽幽吐出一口氣,說:「還好……沒少啥……」
說完這句,對方抬頭,只見黑漆漆一張糊滿煙灰的臉上森森然一咧,露出一口整整齊齊切金斷玉的雪白牙齒,說:「啊,忘記自我介紹了,我是杜笑兒。」
轟隆隆天雷降臨,塑月儲君腦海裡「小白花」和「武則天」六個字一起喀嚓碎成了渣。嬌軀一震的同時,葉蘭心不由得對大越皇族對女人的審美品味有了一個嶄新而深刻的認識。
調整好心態,葉蘭心回爪一巴掌拍在杜笑兒的肩膀上,笑得見牙不見臉。「我是葉蘭心,很高興見到你。」
蕭逐的舊愛——葉蘭心的視角。
平王的新歡——杜笑兒的視角。
兩雙眼睛裡都心懷鬼胎的精光一閃,然後兩個女人「哈哈哈哈」地互搭爪子。
而此時,正陪著永茂帝君迷路的蕭逐,只覺得自己渾身沒道理的惡寒了一下……
葉蘭心預定在安王葉詢這裡停留五天,自從見了杜笑兒的第二天起,她天一亮就朝杜笑兒那裡跑,搞得出於避嫌出於被甩,怎麼也不好意思去看杜笑兒的蕭逐非常鬱悶。
這算啥啊,我到底算什麼啊!
——不知為何有點嫉妒但很鬱悶地不知該嫉妒誰的平王殿下進入內心呐喊模式……
而基本上出乎所有人意外之外,杜笑兒和葉蘭心處得相當好。
如果說最開始葉蘭心確實是衝著看情敵的態度去的,但從那扇被炸飛的門板開始,她對杜笑兒的興趣就從「情敵」轉到了「杜笑兒」身上。
第一天去,門板炸飛,兩人攜手奔命。
第二天去,杜笑兒慷慨贈送了據說叫花水和精油的東西,葉蘭心抹了兩把在臉上,很嫩。
第三天去,杜笑兒正在一套奇怪的爐具面前鼓搗什麼,一桶桶的酒倒進去,最後弄出一小碗透明的水,聞起來味道有些刺鼻,拿火在上面一撩,就很活潑地燒起來一簇火,還怎麼都不滅。
然後第三天去過後,葉蘭心啪啦啪啦去找蕭逐。蕭逐心裡想著,您終於想起我了……
結果葉蘭心蹲到他對面椅子上,兩根手指互點一會兒,才很哀怨地抬頭看他,說,「阿逐。」
「嗯?」
「我雖然不是笨蛋,但腦子通常一滑就滑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
「……嗯?」難得,妳有自知之明。
說到這裡,葉蘭心忽然不說話了。她雙手攏在膝蓋上,頭微微側下,枕在自己的臂彎上。她認真看著蕭逐,在那個男人放下手裡的一切,用溫柔的眼神回看她的時候,她幾乎是孩子氣的伸手。
也不說話,只是小動物一樣伸出手去。蕭逐無奈輕笑,到她面前,輕輕把她抱在懷裡。
反手抱住他的腰,葉蘭心聲音悶悶地說:「我告訴你哦,我沒有杜笑兒聰明,沒她知道得多,也沒她會做那麼多奇怪的東西,也不會弄那種『嘶啦』一聲自己就能燒起來的水,但是……你是我的!」
說罷又惡狠狠抱緊一點。蕭逐哭笑不得。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他摸著葉蘭心的髮頂,輕笑道:「妳到底在說什麼啊?笑……啊,杜昭儀從小我看著長大的,最懶散又不愛讀書,小時候又經過火災,妳們到底說了什麼啊?」
聽到這裡,他懷裡的葉蘭心靜默了一下,隨即朝他懷裡又拱了拱,然後不再說話。
感覺到懷裡屬於妙齡女性的柔軟身軀緊緊貼在他身上,蕭逐腦子裡男女授受不親這樣的古板念頭還沒浮上來,另外一個奇妙的感覺浮了上來。猶豫一下,他拍拍葉蘭心的肩膀,低聲道:「……妳……在不安?」
「——!」葉蘭心猛地在他懷裡睜大了眼睛。
他說什麼?
她在不安?
不……安嗎?
在兩個身體之間小小地移動著手指,她按上自己心臟的位置。
指尖上傳來的觸感微弱地跳動。
不安嗎?現在心裡這種奇妙的感覺,即便現在進行的事情和推算出來的結果完全一樣,即便自己推算了無數次,結果都是一樣,但總覺得有什麼東西自己忘記了,有什麼要素自己忽略了,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重複推算。
原來,這就是不安。
那麼,自己在不安什麼?
把整個對話從頭到尾完全順了一遍,葉蘭心發現,她的不安,源自杜笑兒。
那麼,杜笑兒身上有什麼好讓她不安的呢?
是因為她所知道的和蕭逐所提供給她的截然不同?
不,不是這個,這個不是不安定因素。
那麼,到底是什麼?
沉默無言地依偎在蕭逐懷裡,她不斷推算回想,卻茫然得不出任何結論。
問出問題之後,卻得不到葉蘭心回答,蕭逐在過了片刻之後,用了一點力,把她抱得緊一些,聽到她悶悶地問:「你怎麼知道我在不安?」
「……這個,我就是知道。」
聽了這句話,非常奇妙地,她心裡的不安忽然一下全都消散了。葉蘭心在他懷裡眨眨眼,按著自己心口,只覺得不可思議。
毫無來由的不安,毫無來由地消散,就在他一句話之間。
她從未感覺過這樣的感受。
但是……感覺不壞。
她又朝蕭逐懷裡蹭了點兒。
第四天,也就是他們在冰火洞裡住的最後一天,按照慣例,葉蘭心躂躂躂地跑去找杜笑兒,到她的房間卻撲了個空,被杜笑兒那個美麗程度遠超過主人數倍的侍女禮貌告知:「杜昭儀去旁邊的小湖了。」她二話不說,就殺了過去。
冰火洞裡以葉詢築屋居住的那個湖為源頭,洞內各有幾個小湖,杜笑兒所在的附近,就有一個,是除了葉詢的湖之外,洞裡唯一的一個半開洞頂,有陽光可以透下來的小湖。
她到的時候,杜笑兒正在弄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那是一個大概有兩個西瓜大小的皮囊,底朝上,開口的部分小而上面的容量大,開口四邊上面綴著幾根線,吊著一個托盞一樣的東西,裡面盛了昨天杜笑兒給她看的,味道刺鼻會燃燒的「水」。
她到的時候,杜笑兒已經點著了「水」,小心捏著那個樣子古怪的皮囊上方,過了片刻,就看皮囊上方漸漸鼓了起來,然後搖搖晃晃地開始朝上飛去。杜笑兒小心提起皮囊,過了一會,她鬆手,就看到底下燒著「水」的皮囊,竟然慢慢飛了起來!
雖然離地不高,飛得也晃晃悠悠的,但是確實飛了起來!
不像鳥類依靠翅膀,也不像風箏依靠風速,這個湖邊一絲風都沒有,那個皮囊就這麼吊著一團火飛了起來!
這是葉蘭心從未見到過的景象——
杜笑兒很開心地追著那個皮囊慢慢跑,絲毫沒有注意到洞門口站著葉蘭心這麼大的人,葉蘭心則死死盯著她的背影,頃刻後,唇角慢慢一彎。
確實,是不需要容貌就可以讓男人動心的女子。
才能,也是魅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項。
不過……她所知道的關於杜笑兒的資料以及蕭逐提供的杜笑兒的資料,似乎……對不太上。
她記得非常清楚,蕭逐說過,杜笑兒怕火,而且討厭讀書。
大越中書令花竹意的來信上則提到過,杜笑兒才智過人,學識淵博。
她面前的杜笑兒,能製造出匪夷所思的奇怪東西,並且,不怕火。
她在腦海裡整理關於面前這個女子的所有資料,陡然想起其中一句。
對的,她記得,杜笑兒入宮之前,曾經因為溺水而險些死亡。
唔……她記得很清楚,當時對於杜笑兒溺水的說法是,奇跡般的死而復生。
而所有關於杜笑兒的資料分歧,全部以進宮作為一個分岔——
啊啊,似乎是很有趣的事。
想到這裡,葉蘭心臉上掛起懶洋洋的笑容,輕輕拍拍手,喚了一聲:「笑兒!」
那個追著皮囊跑的女子猛地回頭,看到是她,笑了開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女皇陛下的笑話婚姻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0 |
小說 |
$ 221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女皇陛下的笑話婚姻2
《宅女在古代後宮的幸福生活》續篇加演! 被災難星纏上的小豬,還會遇到哪些令人汗顏的倒楣事? 謎之音:宅腐女眼中的「女王攻王爺」也有被攻的一天…… 號外號外!天大的好消息啊! 咱們女帝真是有眼光、有手段,拐到這麼漂亮的美人當丈夫! 就算女帝長得再貌不出眾,下一代也應該會是大美人吧? 可是這位美人不像王夫,倒更像皇后耶! 來來來!下注賭這麼漂亮的美人何時爬牆! ──就在塑月儲君葉蘭心歷經辛苦帶回大越親王蕭逐時,以民風自由出名的塑月百姓,忍不住對未來的王夫品頭論足一番,下了一個結論:一強二
章節試閱
第二十一章 貧窮皇族參上對蕭逐而言,若因為去國離家三千里而產生惆悵感慨這種情感的話,也僅僅只持續到出了大越國境而已。在他們踏上雲林江之後,他就被葉蘭心興致勃勃的八卦包圍了。「我祖父皇在這裡養過二奶哦!嘿嘿,結果被我祖母抓X在X!」「啊,還有這裡這裡,我曾祖父皇在這裡跟我曾祖母跪地求婚,被我曾祖母一腳踹了個山路十八彎耶!」「前面更是絕對不能錯過!我曾曾祖父皇在這裡被我曾曾祖母一劍架在脖子上,邪魅一笑,說:『公子,你就從了奴家吧!包你跟著我吃香喝辣,奴家絕不納小!』」諸如此類的八卦伴隨蕭逐整整一路,...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云狐不喜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9-09-18 ISBN/ISSN:978957104123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