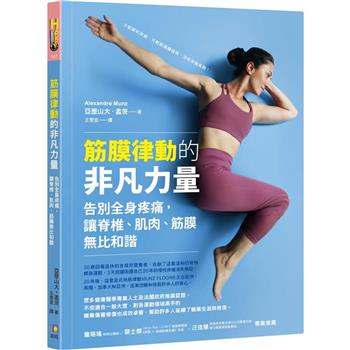我的歷史
當個騙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要開始說謊的人,你得一直追蹤自己都說過些什麼。記得你每句話是怎麼說的,又是對誰說的。因此,第一個謊言,總是會引來第二個。
謊言永遠不會只有一個。
因此,最好的辦法是保持簡潔──這讓你比較有機會能好好追蹤所有的絲絲縷縷,將它們緊纏密織在一起,同時希望別再衍生出更多謊言來。
要把所有那些謊言妥善保持好,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想像一下你要把上千支好好綁在一起的火把,重新擺放個位置試試看。或讓全世界最複雜的機器,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的機器跑跑看。
最算是最厲害的騙子,甚至那些擁有最佳記憶力,能縱覽全局又看到最細微末節的人,就算是他們,也有被逮到的一天。他們也許不是所有的謊言都遭到揭穿,但總會有一兩個,或再多幾個被識破。事情總是這樣子的。
我痛恨遭到揭穿的時候。我痛恨當他們發現你說的不是真話,你精心編織的整件事被粉碎的時候。
謊言停止旋轉織纏,齒輪跟齒輪咬死了,沒得潤滑。那就是在我大笑著說:「丫頭,真有妳的。」之後,莎菈瞪著我的那一刻。
那一刻可以持續一週、一個月、一年。
我羞恥、憤怒、痛恨自己被逮到,同時腦中也快轉著更多解釋這一切的謊言。
但被逮到也讓人大鬆一口氣。永遠都令人大鬆一口氣。
因為再也不用去保持了;現在,至少我可以說真話了。從此刻開始,每件事都會是真的。一個真實的人生,不是建造在腐敗的根基上。信任、瞭解。每件事都是嶄新的,閃閃發亮。
只除了我沒辦法,永遠保持這樣。
因為,我的真話,是如此令人難以置信。
第一部 說真話
保證
我出生的時候,全身長滿了細毛。
三天之後,這些毛全部脫落,不過傷害已經造成。我媽不再信任我爸,因為這是家族遺傳,他卻沒告訴她。這是許多的疏漏和欺騙之一。
我爸是個騙子,我也是。
但我一定要停止說謊。我必須停止。
我會告訴你我的故事,我會坦白直接。沒有謊言,沒有疏漏。
這是我的保證。
這次我是真心誠意的保證。
。。。。。。
之後
星期二早上,當我發現柴克沒來上學時,我開始擔心。他說星期一晚上會打電話給我,可是沒有。我上次見到他是在上星期五晚上。這很不尋常。
柴克.魯賓是我男朋友。他不是全世界最棒的男朋友,但是他通常說到做到。
如果他要蹺課,他一定會拉著我一起蹺。我們可以到布魯克林橋下溜達,或整天在地鐵裡打混,對瘋狂無聊的事嘻嘻哈哈,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做。
有一次,我們從史泰登島渡船口,一路走到英伍德那棟大醫院跟通往布朗克斯的橋旁。那花了我們整整一天的時間。我們繞了路,去搞清楚狀況啦,東逛西看啊什麼的。享受四處遊走的新奇,不是拔足狂奔。我們朝北走,選擇由百老匯大街穿過這島。柴克說,這本來是一條印地安人走的小徑,這使得這條街成了曼哈頓島上最古老的一條路。這是為什麼它繞來繞去,有時候像條對角線,有時候又像筆直的大道。
我和柴克爭論過,橋下通往布朗克斯的那條河,該叫什麼。是哈得遜河,還是東河?或者,這兩條河是正好在橋底下交會?不管它叫什麼,呈灰棕色的河水看起來都很髒。所以,這髒水可能來自其中一條河。
那是我們在一起最美好的一天。
我希望柴克不是又去做那麼酷的事,卻沒帶我一起去。果真如此,我一定會宰了他。
我獨自一人吃午餐。一個冷的牛肉三明治,麵包吸了肉汁,濕答答又灰撲撲的。我把牛肉吃了,剩下的全扔掉。
上課的時候,我瞪著窗戶,看著班上同學的影子跟窗外的鐵欄杆一起疊映在斑駁的窗玻璃上。我想著柴克對我露出笑容時的模樣。
。。。。。。
之後
第二天,柴克還是沒來學校,我戴上了面具。我這樣維持了三天,偽造一張我爸寫的請假條,說我出了可怕的疹子,醫生指示我得保護著直到好了為止。我把這假條拿到我上的每堂課,他們都相信了。
面具是我爸從威尼斯買回來的。皮製黑色的,上面繪著銀色的圖案,每個角落都有,像羊齒蕨。那銀是真的銀。
面具底下,我的皮膚好癢。
星期四第三節課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柴克死了。
校長保羅.瓊斯來到我們的課堂上。他臉上沒有笑容。大家面面相覷,竊竊私語。我聽到柴克的名字。我轉開頭。
「我有個壞消息。」校長多此一舉地說。我可以嗅到他全身散發著壞消息的味道。
現在,我們大家全盯著他。每個人都很安靜。他的眼睛有點紅。我很好奇,他是走過全校每一班,還是只來我們高年級班。我們肯定是最先獲得通知的。柴克是高年級生。
我可以聽見白色鐘面上分針走過的聲音。不是滴答,是喀嚓。喀嚓、喀嚓、喀嚓、喀嚓,不是滴答、滴答。
教室裡有一隻蒼蠅。風扇的葉片在空氣中旋轉。有道陰鬱的陽光橫射過教室前方,就在校長站的地方。光線讓空氣中的塵埃粒粒可見,還有,校長眼睛旁、前額上、嘴角的皺紋,都歷歷可數。
莎菈.華盛頓在椅子上動來動去,兩隻腳痛苦地磨著木頭地板,很大聲。我轉頭瞪著她。大家也都轉頭瞪著她。她轉頭避開眾人的視線。
「柴奇瑞.魯賓已經不再是失蹤人口。他的屍體被找到了。」校長保羅的嘴臉扭曲成介於痛苦鬼臉和齜牙咧嘴之間的某種怪樣。
教室裡泛起一陣聲響。好一會兒,我才明白,有一半的女生在哭。還有幾個男生也是。莎菈.華盛頓則前後搖晃著身子,眼睛瞪得大大的。
雙眼乾澀不堪,我拿下了面具。
。。。。。。
之前
我當新鮮人那年的頭兩天,我是個男孩。
事情是從我高中第一天的第一堂課,英語課,開始的。英迪菈.佳波塔老師譴責我沒有注意聽。她叫我威爾金斯先生。在我們學校裡,沒有人會稱呼任何其他的人某某先生或女士。佳波塔很火大。我停止瞪著窗外,轉過頭來看她,懷疑教室裡是不是還有另一個人姓威爾金斯。
「對,就是你。麥可.威爾金斯先生。當我說話的時候,我期望你全神貫注地聽我講,而不是注意著外面來來往往的情況。」
沒有人笑,或說:「她是女生啦。」
我以前曾經被錯認做男生過。不常有,但次數也夠多,所以我也不太驚訝。我遺傳了鬈毛基因,所以我把頭髮剪得很短,伏貼在頭皮上。這樣,我就不用費事去梳鬆、梳直或梳開來。我的胸部很平,我的屁股窄又小。我既不化妝,又不戴首飾。他們,所有的老師和學生,過去從未見過我。
「聽懂了嗎?」佳波塔說,依舊憤憤地瞪著我。
我點頭,盡我所能壓低聲音說:「是,女士。」那就是我在新學校裡說的第一句話。這回我要保持低調,不惹人注目,不做那個在走過大堂走廊時,眾人所指所傳的:「看到那個人嗎?那是麥可。她很愛說謊。不,認真來講,她說的每件事都是騙人的。」我才沒有每件事都說謊。只有說到我父母(索馬利海盜、職業賭徒、毒販、間諜),我從哪裡來(列支敦士登、阿魯巴、澳洲、津巴布韋),我做過什麼(詐騙、得過英勇勳章、被綁架過),這類的事時,我才騙人。
我從不對我的過去說謊。
當個男生有什麼不好?一個安靜陰沉的男生一點也不怪。一個愛跑步,不逛街購物,對電視上的衣服鞋子不感興趣的男生。這樣的男生很普通。還有什麼比當個普通男生更不引人注意?
當個男生,一定會比我做女生來得出色。
午餐的時候,我跟三個在課堂上見過的男生同桌:泰山.威廉斯、威爾.丹尼爾斯,以及柴奇瑞.魯賓。我很想說,一看見柴克我就知道我們會有牽扯,但這麼說會變成說謊,而我不打算再騙人了。記得吧?他不過就是另一個男生,是個有橄欖色皮膚的白人男生,跟泰山比起來,顯得蒼白又瘦弱,泰山的膚色比我爸還黑。
他們點點頭。我點點頭。他們已經認識彼此。他們的談話裡混雜著早已熟知的人名、地點、隊伍。
我吃著我的肉丸跟蕃茄醬,決定放學後要一口氣跑到中央公園。我會繼續穿著身上那件鬆鬆垮垮的長袖運動衫。
「你打球嗎?」泰山問我。
我點頭,因為這樣比問打哪種球來得安全。男生總是曉得這種事。
「放學後我們要繼續練。」他說。
我盡量像男生那樣哼了哼。沒想到聲音比我預期的還低沉,彷彿有一隻狼進到了我的喉嚨裡。
「你要來嗎?」柴克問,輕搥了下我的肩膀。
「好啊。」我說:「在哪?」
「那邊。」他用拇指比了下學校旁邊公園的方向。那裡有個鋪碎石的籃球場,露天看臺,有個小形的菱形棒球場,還有個旋轉木馬臺,每隻木馬靠很近,有比賽進行時,根本不可能每隻都坐人玩。我跑步時從它旁經過十幾次。每次都看到有比賽在進行。
上課鈴響了。泰山站起來,一巴掌拍在我背上,說:「待會見。」
我笑了,想這真是太容易了。
當個男生,馬上變成我最喜歡的一個謊言。
。。。。。。
學校的歷史
所有的白人小孩全坐在一起。我的意思是,所有有錢的白人小孩。
我們這所高中很小,很先進,也很花錢。雖然沒上城的那些學校貴,但也不是免費。只有那些拿獎學金的孩子才讀免錢,而他們絕大部分不是白人。他們免學雜費,只要付課本的錢。他們大多數都不會參加郊遊旅行。
絕大部分的白人小孩都不信上帝;絕大部分的黑人小孩相信。
我則還沒決定,卡在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就像我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樣,卡在中間:一半黑,一半白;一半女,一半男;拿一半獎學金。
我無論啥事都是一半。
。。。。。。
之後
我們全被送去做心理輔導。有個人的部分也有群體的部分,群體的部分先。那真是場惡夢。吉兒.王(對,她真叫這名字)要我們把桌子都挪開,然後把椅子圍成一個大圓圈。我之前曾被迫來見這位王老師。她真誠到令人抓狂。她相信你告訴她的每件事。包括我的謊言在內。
我們全坐在椅子上,沒有書桌可躲。我真希望自己是在圖書館裡讀書。
布蘭登.唐肯瞪著我的胸前,問題是我幾乎沒有胸部。
莎菈.華盛頓也轉過頭來看我,她的視線也停在我眼睛下方,不過沒到布蘭登那麼低的地方。「妳這段期間為什麼說謊?」她輕聲問。
「妳又為什麼說謊?」我說,雖然我從來不知道她會說謊。我跟她一樣很小聲說話,但是盡我可能凶猛地瞪回去,強迫我的目光穿透她皮膚上的毛孔。我想像自己能感覺到她血管中血液的流動,她肺裡呼吸的聲音,她腦袋裡神經鍵的活動。她真是聰明,反應又快:「人人都說謊。」
「我們在這裡,是要來談所發生的事,還有我們的感觸。」輔導員說:「你們想分享什麼都可以,只要是有關──」
「別說他的名字!」莎菈大吼。
現在,所有的人都瞪著她了。她的心跳得飛快,迫使血液在她的血管中急速流動。
「我不說。」吉兒.王說:「你們不要我說,我就不說。」
輔導員總是講這類的話。我見過的輔導員可多著啦。心理學家,心理醫生,治療師。全都一個樣兒。他們應該要使我說謊的事停下來,但是他們相信我告訴他們的每件事。
「我們不要妳說。」莎菈咕噥著。
「你們大部分人我都沒見過,跟我自我介紹一下吧。讓我們繞著圓圈來。告訴我你想要描述自己時,所想到的頭一個字。」吉兒.王對我點了點頭。
「凶猛。」我說。
莎菈顫抖了一下。
「酷。」布蘭登說。好幾個人笑起來。
「熱。」泰山說。他是學校裡最受歡迎的傢伙,所以也有笑聲。但我很肯定,他不是那個意思。不是性感受歡迎的意思。比較像是熱得扎人。比如他得鬆開領口的釦子。我的領口也弄得我很癢。氣溫太高。蒸汽管子發出吭噹悶吼,叫喊著它們自己的言語。
每個學生說一個形容字。沒一個是對的。
門就在我背後,距離不到六呎。我想像著跳出這圓圈,躍過坐在椅子上怒視著自己膝蓋的莎菈,我可以跑走。
我會跑走。
「灰色。」莎菈說,結束了這一圈的介紹。一滴眼淚隨著她的話淌過臉頰,在她下巴上停了不到一秒,然後跌落到她的毛料長褲上,消失。
「有沒有誰想要談談……」吉兒停了停,嚥下柴克的名字。「我聽說他很受歡迎。」
「妳該問麥可。」布蘭登說:「她是他女朋友。」
又一陣笑。現在他們全盯著我看,所有的人,除了莎菈。她的頭垂得更低了,她試圖停止哭泣,呼吸變得淺而急。她快要失控了。我希望她失控。
「非常好笑。」泰山瞪著布蘭登說。我看得出來,他不相信這話。泰山是柴克最好的朋友。他們倆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是好朋友了。
我想宰了布蘭登。我知道他為什麼告訴大家這件事:想製造麻煩。布蘭登就幹這種事。可是,他是怎麼曉得的?
大家還是瞪著我。我抬高下巴,瞪回去。當人們看著我的時候,我會起雞皮疙瘩。但我從來不讓他們發現。
「妳想說說話嗎?」吉兒.王說。
「不想。」我說。
「她才不是他女朋友。」莎菈說:「我才是。」
泰山和錢陀以及其他人都同意她說的。
「妳是他在學校裡的女朋友。」布蘭登告訴莎菈:「麥可是放學以後的。」他露出牙齒笑著。
莎菈又開始哭。泰山看起來像要宰了布蘭登一樣。我樂於幫忙。
吉兒.王從布蘭登看到莎菈,再看到我。我看得出來,她在衡量著要說什麼。
「我有個問題。」亞歷山卓說。
她點頭要他繼續往下說。
「大家都在談悲傷哀悼一類的屁話──對不起──的事。隨便啦。但是就是沒人說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一直聽到謠傳,還有警察之類的。但是沒有人說到底怎麼回事。沒人真的講明白。所以,謠傳是真的嗎?他是被謀殺了?」
輔導員張開雙手,張得大大的,眼睛一一看過我們每個人,跟我們保證,現在她要講的是真的。「我知道的跟你們一樣多。警察正在調查,要確定這究竟是不是一件犯罪案件。」
亞歷山卓沒再吭聲。但是他看起來仍不滿意。我們也沒人滿意。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說‧謊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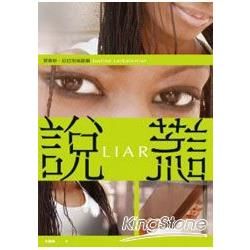 |
說‧謊 作者:賈斯婷.拉巴里絲提爾 / 譯者:安麗姬 出版社: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1-01-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9 |
二手中文書 |
$ 187 |
小說/文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說‧謊
我們挑戰你相信她!
麥可毫無顧慮地承認她是個強迫性說謊者,但這可能是她告訴過你最誠實的一件事。
多年來,她一直欺騙她的同學、老師,甚至她父母,她總是有辦法先一步讓謊言不被拆穿,直到她的男朋友慘死,她的欺騙才開始反噬。
當一個人說謊欺騙自然到像呼吸一樣的地步,這人還有可能會說真話嗎?讀者將深入這位少女的心靈,她會說任何話來說服你們――還有她自己,她最後是清白的。《說‧謊》是一本讓人戰慄入骨的書,會讓讀者從頭到尾都看見謊言與真相之間的每一點。保證童叟無欺。
作者簡介:
賈斯婷‧拉巴里絲提爾(Justine Larbalestier)是How to Ditch Your Fairy以及The acclaimed Magic or Madness三部曲的作者。她在澳洲雪梨出生與成長,現今居住在雪梨和紐約市。喜歡賈斯婷作品的朋友請上:http://www.justinelarbalestier.com
譯者簡介:
安麗姬
專職譯者,從事翻譯工作十餘年。英國Newcastle大學應用語言學碩士。譯作見聯經、臉譜、奇幻基地、商周等出版社。
章節試閱
我的歷史
當個騙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要開始說謊的人,你得一直追蹤自己都說過些什麼。記得你每句話是怎麼說的,又是對誰說的。因此,第一個謊言,總是會引來第二個。
謊言永遠不會只有一個。
因此,最好的辦法是保持簡潔──這讓你比較有機會能好好追蹤所有的絲絲縷縷,將它們緊纏密織在一起,同時希望別再衍生出更多謊言來。
要把所有那些謊言妥善保持好,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想像一下你要把上千支好好綁在一起的火把,重新擺放個位置試試看。或讓全世界最複雜的機器,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的機器跑跑看。
最算是最...
當個騙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要開始說謊的人,你得一直追蹤自己都說過些什麼。記得你每句話是怎麼說的,又是對誰說的。因此,第一個謊言,總是會引來第二個。
謊言永遠不會只有一個。
因此,最好的辦法是保持簡潔──這讓你比較有機會能好好追蹤所有的絲絲縷縷,將它們緊纏密織在一起,同時希望別再衍生出更多謊言來。
要把所有那些謊言妥善保持好,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想像一下你要把上千支好好綁在一起的火把,重新擺放個位置試試看。或讓全世界最複雜的機器,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連著輪子連著齒輪的機器跑跑看。
最算是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賈斯婷.拉巴里絲提爾 譯者: 安麗姬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1-01-11 ISBN/ISSN:97895710437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