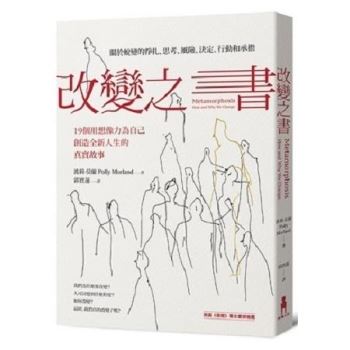十六歲試閱
鬧哄哄的黃金週結束了,坐落在東京盡頭的月島又變回往常的冷清城鎮。連假期間,西仲通上的所有文字燒店(終於突破一百家了!)門前都大排長龍,整個城鎮就像尖峰時刻的月台一樣嘈雜。當然,身為在地人的我們就只能靜靜地在後巷裡等待這場風暴過去。
五月是一年最棒的季節,電視上的氣象預報是這麼說的。不冷不熱,雨不多雲也不多。加上颱風和低氣壓都不會來襲,不會颳起強風,溼度也高低適中,不至於讓人感到不快。這樣的好天氣一年之中似乎只有幾天的樣子。以英文來說就是Beautiful day。如此美好的幾天最有可能在微風吹拂的五月來臨。
話雖如此,不管是多麼美好的Beautiful day,對高中一年級生來說也不是那麼地重要。畢竟藍天啦、陽光啦,還有氣溫與溼度這些東西,和每天堆積如山的煩悶一點關係也沒有。就算天氣再怎麼好,也不可能把十六歲的心像洗過的衣物一樣輕易地晾乾。
這個時期被我們當成基地的是一家叫「向日葵」的文字燒店。
口號是「既然大家都很閒,那要不要去向日葵?」。
喜歡講冷笑話的阿大最先說出口後,我們幾乎每天都把這口號掛在嘴上。不過可不要誤會了。那家店和雜誌上的月島特集時常介紹的許多漂亮乾淨的店面截然不同。
首先,那家店根本就讓人摸不清楚正確的位置。就連土生土長的我們,第一次找到看板時也嚇了一跳。從文字燒通走進狹窄的巷弄裡,接著再九十度拐進一整排普通民房之間後,就能看到空啤酒箱上貼著一張畫得很差勁的向日葵水彩畫,以及「文字燒 向日葵」的手寫文字。那不是看板那種煞有其事的東西,只是一張裝在塑膠袋裡的圖畫紙。
咖啦咖啦地打開毛玻璃的拉門後,可以看到兩張桌子擺放在跟土間
一樣潮濕的水泥地上。裡頭有一個三疊榻榻米大小的包廂,這邊也擺了兩張矮桌。小小的文字燒店裡總共只有四面感覺有點生鏽的老舊鐵板。
落伍的並不是只有店面的外觀而已。整間店只有一個有點重聽的老婆婆在照料,但沒有人知道這位老婆婆的正確年齡。我記得公園的角落邊長著一棵大樹,而老婆婆的肌膚就跟那乾燥龜裂的樹皮一模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反問我們點了什麼的佐知婆婆,不知道為什麼總是穿著華麗的夏季印花洋裝。而且還誇張地抹上又藍又紅的眼影,嘴唇上也仔細地塗了口紅。她是那種如果走夜路時碰上了,就會讓人不禁自動讓出一條路來的類型。月島的主婦們也時常傳些有關佐知婆婆的流言蜚語。
不過既然會被我們當成秘密基地,這間店當然也有它的優點。就算在黃金週期間,向日葵也鮮少會有客人造訪。由於店裡總是空空蕩蕩的,因此包廂裡的桌子自然就成了我們的預約席。而且最重要的是餐點實在是太便宜了。沒有加任何配料的傳統醬汁口味文字燒只要一百五十元。沒什麼錢的時候,我們總是如文字燒的名字一般,用這素文字燒在鐵板上寫下喜歡的偶像(綾瀨遙或Suzanne)或自己的名字,然後烤焦吃掉。這樣就夠好吃了。
在一年最Beautiful的這一天裡,我們幾個熟面孔圍坐在鐵板邊。因為手頭稍微寬裕了些,我們點了素文字燒加蛋及高麗菜。矮桌上並排著碳酸汽水的淡綠色瓶子。淳對大打呵欠的阿大說:
「我說你啊,最近碰面時總是一副愛睏的臉呢。」
呵欠似乎會喚來呵欠的樣子。阿大第二次張大了嘴,眼眶也濕潤起來。
「沒辦法啊。我一大早就要出門工作,中午回家小睡一下後,晚上又要上夜校。我真是個了不起的勤勞學生啊。」
阿大、淳、直人,還有我,以堅固的羈絆和輕鬆的玩笑話凝聚起來,宛如銅牆鐵壁般的四個人,從月島中學畢業後分別進了不同的高中。雖然國三時被考試折磨得很慘,不過我討厭沉悶的話題,所以還是別提了吧。我想那些大家也同樣經歷過了,但考試這種話題根本沒有拿出來討論的價值。
「阿大的確很了不起呢。因為他從來沒有跟學校請過假。」
阿大從一大清早到中午都在築地場外市場的某間海產製品批發商工作。手抵在油漬滲透的矮桌上撐著臉頰,看起來稍微有點大人樣的阿大說:
「哦──,不愧是唸同一所高中的哲郎,你還真了解我啊。」
我騎著自行車橫越佃大橋,到位於鄰鎮新富町的都立高中上學。雖然那以前是很有名的升學學校,但如今只是一所悠悠哉哉的高中。對我而言剛剛好。淳嘴對著瓶口喝起了碳酸汽水。
「是是是。這麼說起來,哲郎的確和阿大同校呢,雖然有日間部和夜間部的差別就是了。要是我也去唸普通的都立高中就好了。既不用穿制服,校規也不嚴,而且還是男女同校。」
阿大用宛如法蘭客福大熱狗的指尖戳了戳淳的肩膀。
「嘿嘿嘿嘿,你羨慕的只有最後的女孩子那點吧。」
「對啊。因為淳唸的開城學院不是東京第一的升學學校嗎?今年又有幾個人進東大啦?」
淳露出一派無聊的表情。
「一百七十個人左右吧。」
這是個有點嚇人的數字。既然如此,那乾脆把開城學院設為東大附設高中算了。阿大一臉不可思議地說:
「那麼用功是要幹麻啊?」
「天曉得,大概是要當政府官員吧。我班上幾乎都是以後想進財務省的傢伙。」
「嗯──,感覺好像外星人哦。我覺得市場裡那些整天繞著柏青哥、賽馬和酒打轉的老頭還比較正常。」
我插進兩人的對話中。
「重點是淳的成績怎麼樣?」
「大概在前段後半吧。」
「那麼這樣一來……。」
月島國中第一名的秀才一臉無趣地說:
「是啊。只要不挑科系的話,大概上得了東大吧。」
阿大笑著將烤焦的文字燒塞進嘴裡。
「我們兩人是不是該趁現在跟你要簽名啊?」
「別這樣,真噁心。話說回來,直人那傢伙還真慢啊。」
我看了手機裡的時間。已經快四點半了。直人唸的是有樂町線上一所直升的私立少爺學校。由於直人患有名為早衰症的特殊疾病,直人媽媽為了不讓他為大學考試操心才選擇了這所學校。
這時,玻璃門發出咖啦咖啦的開門聲。阿大說:
「直人,你在幹麻……。」
然而從敞開的門口裡出現的卻是一位戴著太陽眼鏡的女人。白色T恤像絲襪一樣薄,使得胸部的形狀顯而易見,是個大波霸。由於T恤的長度很短,牛仔褲又是低腰的款式,因此曬黑的肚臍與閃閃發光的肚臍環看得一清二楚。這家店還是第一次有女客人獨自前來。
她拖著行李箱走進文字燒店後,便摘掉太陽眼鏡環顧著店內。雖然她的打扮很年輕,但從眼尾的皺紋卻能看出她年約三十歲左右。淳突然坐立不安地蠢動起來。自從與人妻玲美的短暫戀情結束以來,淳的喜好徹底地轉向了年長的女性。
「這家店一點都沒變呢。」
在小櫃檯裡的老婆婆似乎完全沒注意到的樣子。就連我們點的東西也被擱置了二十分鐘之久。
「讓你們久等了。」
玻璃拉門再度打開,這回則是直人氣勢洶洶地衝了進來。他似乎又長高了一點。如少年般細瘦的身軀上方,頂著一頭變成半白的頭髮。直人避開在狹窄的店裡佇立不動的女人來到包廂裡後,便輕聲對我們說:
「那個人是誰?」
我們全都搖了搖頭。除了那絕妙的身材有如牆上一張老舊海報裡的泳裝女孩以外,那女人的一切都是個謎。直人拔高聲音好讓老婆婆能夠聽見。
「請給我一瓶碳酸汽水。」
這時,女人毫不猶豫地從玻璃的冷藏櫃裡拿出碳酸汽水,並且拔掉瓶栓,然後走向我們的桌子。女人每走一步,胸部也跟著上下搖晃。就算同樣都是脂肪,女人的胸部還是跟阿大的有著天壤之別。直人滿臉通紅,死都不看女人的胸部。
「來,請用。」
女人回頭對著櫃檯裡大叫:
「媽,有客人。用杯子裝冰塊過來。」
我們四個人嚇了一跳,並且緊盯著繃緊了T恤的背部。屁股稍微往上一點的地方是藏青色的機械刺青。那是一小片延展開來的天使翅膀。老婆婆拿著杯子過來。
「妳是怎麼搞的。既然回來了就說一聲啊。」
這麼美麗的女神維納斯居然是從這株朽木裡誕生的。人體還真是驚奇啊。淳硬是裝出紳士般的聲音說:
「佐知婆婆,這位是?」
將杯子砰一聲地放在矮桌上後,穿著夏季印花洋裝的老婆婆說:
「是離婚跑回來的女兒。」
穿著T恤的女人莞爾一笑。
「我叫森安美沙緒,是這家店的獨生女。你們是店裡的常客吧,請多指教哦。」
身材好得像玩伴女郎的她雙手叉腰,並且對我們點頭示意。我們四個人就這樣坐在原地用力地點了點頭。阿大戳了戳身旁的直人。
「我們說不定要開始走運囉。今年春天真是幸運啊。」
淳立刻說:
「那好運也不是像你這種有女朋友的傢伙招來的。」
阿大正和在新宿的俱樂部裡認識的女高中生夕菜交往。對方有個小男嬰,不過不是阿大的小孩就是了。佐知婆婆突然生起氣來。
「什麼請多指教啊。離開時只丟下一句話就突然從家裡消失,要回來時也只打了通電話就突然跑回來。又不是狗啊貓的,就算是母女也該好好打招呼吧。」
美沙緒也不甘示弱地說:
「妳在說什麼啊?明明自己還隨便拿我的衣服去穿。我也是因為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才回來的啊。就是因為妳老是這個樣子,老爸才會跑掉吧。」
「那妳自己又怎樣?妳的男人不也一樣跑掉了嗎?」
在傍晚昏暗的文字燒店裡,兩個女人狠狠地瞪著彼此。她們似乎完全忘記我們這些客人的存在了。一旦暴露了本性,女人就會變得相當可怕。特別是像月島這種工商業都市的女性,個性全都既剛強又可怕。阿大打圓場似地說:
「算了算了,吵架就到此為止,好好工作吧。欸,直人,點些費工又豪華的文字燒嘛。」
直人看著貼在牆壁上的手寫菜單短籤。
「那我要明太子麻薯起士加王子麵。」
佐知婆婆喝道:
「好好。」
美沙緒一把抓住行李箱。
「開什麼玩笑。誰要在這種店裡幫忙啊?」
她拖著行李箱從玻璃門走出去。淳輕聲哀嘆:
「咦──,不會吧。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說,這樣就結束了哦?」
我對東大候補的友人說:
「你已經迷上她啦?淳。」
「嗯嗯,高中同學那種小鬼又不能當成對象。看到那個肚臍環跟腰上的刺青了沒?」
阿大也撐開了鼻孔。
「看到了看到了。還有那個奶子。」
「就算失敗了也沒差,我要試著攻陷美沙緒小姐。」
我對淳的勇氣刮目相看了。這傢伙並非只是個會唸書的秀才而已。雖然平常對成績方面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但在這種時候,淳總是讓我的內心湧現出些許的劣等感。如果沒有這種程度的幹勁,或許就沒辦法順利地和女孩子交往也說不定。
「好期待今年夏天的到來啊。」
這麼說完後,淳仰頭露出纖細的喉頭,一口氣喝光了淡綠色瓶子裡的碳酸汽水。
到了該離開店裡的時間了。向日葵只是大家在晚餐前隨便吃些點心的店。畢竟我們的食慾大到連自己都覺得誇張的地步。特別是阿大,他一天居然可以若無其事地解決七餐。
每個人付完四百元後,佐知婆婆開口說:
「欸,你們今天接下來還有空嗎?」
阿大看了看手錶。
「我不行。六點要開始上課。」
「那你們呢?」
佐知婆婆斜眼看著剩下的三個人。說得客氣一點,佐知婆婆那道斜視的目光感覺就跟恐怖電影一樣。
「要是不回家吃晚餐的話,我媽會很囉唆的,所以我大概不行吧。」
在佃島的超高大廈三十四樓,直人那優雅的媽媽做了計算過維他命與礦物質(真的給人這種感覺)的晚餐等著他。這時,淳輕輕地頂一下我的腰側。
「只要事先打過一通電話,這傢伙跟我就算晚點回去也沒關係。你說是吧?哲郎!」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嗎?我想起了準備高中考試時記住的諺語。這諺語真是形容得恰到好處。人們或許病態地喜歡以滑稽的方式形容一件事情也說不定。仔細一想,我們四個人的對話也有將近百分之九十是玩笑話。
「是嗎?那麼你們過來後面一下。」
阿大和直人消失在暗下來的巷子裡後,我們便繞到了店的後方。佐知婆婆迅速地將藍色防水塑膠布從沿著牆壁堆起來的小山上拉開。
「哇,好厲害。」
我忍不住驚呼出聲。微波爐、映像管電視、烤麵包機、錄放影機、附音箱的立體音響組。各種電器製品像拼圖般毫無空隙地堆疊在那裡。淳開口說:
「這些全是佐知婆婆收集來的嗎?」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6TEEN 十六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6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日本文學 |
$ 234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6TEEN 十六歲
16歲。
我相信我能接受她的一切。
石田衣良直木賞得獎作品《4TEEN 十四歲》裡的那四個人變成高中生回來了!
笨拙的戀情,第一次的背叛,還有稍微增加了點真實感的未來……
在抬頭可見超高大廈的月島巷弄裡,我們思考著這世界的構成方式。
阿大、淳、直人、哲郎──永遠的青春小說。
【延伸閱讀】
4TEEN十四歲
月島,一個「今天」與「明天」共存的市鎮。劃開天際的摩天大樓、馬路上隨處可見的長屋和文字燒店鋪。
現在與未來,交互穿插,融合,最後消失。
我們在月島戀愛、受傷、踏上旅程,甚至和死亡擦身而過,然後,慢慢長大……
詳實描寫14歲四人組一年間所遭遇的八個故事,刻畫「當下」的青春物語。
作者簡介:
石田衣良
1997年以《池袋西口公園》登上日本文壇,並獲得了該年的「ALL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接下來不停地發表多部短篇、長篇作品,2003年再以《4TEEN》一書贏得了第129屆直木獎,其成就有目共睹,為當前日本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十六歲試閱
鬧哄哄的黃金週結束了,坐落在東京盡頭的月島又變回往常的冷清城鎮。連假期間,西仲通上的所有文字燒店(終於突破一百家了!)門前都大排長龍,整個城鎮就像尖峰時刻的月台一樣嘈雜。當然,身為在地人的我們就只能靜靜地在後巷裡等待這場風暴過去。
五月是一年最棒的季節,電視上的氣象預報是這麼說的。不冷不熱,雨不多雲也不多。加上颱風和低氣壓都不會來襲,不會颳起強風,溼度也高低適中,不至於讓人感到不快。這樣的好天氣一年之中似乎只有幾天的樣子。以英文來說就是Beautiful day。如此美好的幾天最有可能在微風吹拂的...
鬧哄哄的黃金週結束了,坐落在東京盡頭的月島又變回往常的冷清城鎮。連假期間,西仲通上的所有文字燒店(終於突破一百家了!)門前都大排長龍,整個城鎮就像尖峰時刻的月台一樣嘈雜。當然,身為在地人的我們就只能靜靜地在後巷裡等待這場風暴過去。
五月是一年最棒的季節,電視上的氣象預報是這麼說的。不冷不熱,雨不多雲也不多。加上颱風和低氣壓都不會來襲,不會颳起強風,溼度也高低適中,不至於讓人感到不快。這樣的好天氣一年之中似乎只有幾天的樣子。以英文來說就是Beautiful day。如此美好的幾天最有可能在微風吹拂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石田衣良 譯者: 黃健育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11-04-07 ISBN/ISSN:978957104482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